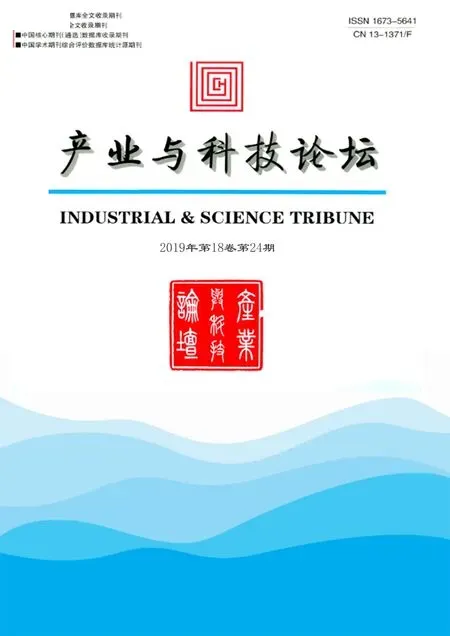乡村振兴须走出城乡关系认识误区
□宋 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强调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为乡村振兴中处理好城乡关系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仍未完成,城乡二元的制度印记仍较显著,长期形成的关于城乡关系的一些认识误区仍广泛存在,并对各级政府的决策、对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带来了明显的不良影响。不澄清这些片面的认识,就会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甚至强化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不利于乡村振兴工作的顺利推进,甚至会造成资金资源的巨大浪费。
一、认识误区之一:把城乡融合发展片面理解为增加农业农村投入,将乡村振兴等同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对立起来
乡村振兴战略对新时代“三农”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进一步明确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指导思想。毋容置疑,国家现代化,农业农村必须现代化,必须通过加快农业农村发展补足乡村发展短板。但需要全面认识的是,城市与非农产业占GDP比重上升、农业农村占GDP比重下降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普遍趋势。2016、2017、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6%、7.9%、7.2%,下降的趋势也非常明显。依靠第一产业已经低于10%且仍持续下降的经济比重支撑总人口占比超过40%的农村人口实现现代化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乡村难以承担超过其承载能力的责任和功能。所以,虽然各界一直强调农业农村优先投入、优先发展,但却不能因此忽视乡村创造财富能力有限、人口承载力有限、无法承载比例如此之高的农村人口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事实,不能忽视农业人口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的收入增长效果,更不能用乡村振兴对抗城镇化。人地矛盾仍然是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与农业农村发展对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同等重要,乡村振兴不能仅在农业农村一个维度推进,不仅不能弱化、相反应进一步强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研究和制度安排,以“城乡融合”破除“城乡分割”,在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同时,同等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在城镇化大框架内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同时推动乡村冗余要素向城市转移、城市优质要素向乡村转移,通过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逐步实现城乡产出、人口、要素总量和结构均衡。
二、认识误区之二:城镇化占用大量土地而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不足,故城镇化率不能太高,把耕地保护与城镇化对立起来
全球和中国城镇化实践清楚显示,与农村农业相比城市是更集约节约使用土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城市单位面积土地创造的产值与容纳的人口远高于农村。从人均占地看,按照城市规划与实际发展状况,城市人口密度一般为每平方公里一万人,即人均100平方米可以满足一个城市人口就业、居住、消费等所有日常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全部空间。我国大城市人口密度多高于每平方公里一万人,中西部一些县级城市人口密度相对较小为每平方公里8,000人左右,人均占地达到125平方米。而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均用地要多得多,截至2015年底我国农村常住人口60,346万、农村居民点占地1,812万公顷,人均占地为300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用地是城市人均用地的3倍。显然,从人多地少、城镇化会占用大量土地得出我国城镇化率不能太高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将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对立起来是经不起推敲的。相反,恰恰是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均占地越少,越是人多地少越需要推进城镇化。造成这种片面认识的原因是只看到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耕地不断减少的表象,忽略了城市集约节约土地的实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耕地不断减少的根本原因不是城镇化,而是城镇化不彻底形成了以3亿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两栖人口,造成城镇化高速推进、城市常住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占地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村居民点没有随着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而减少、反而也在增加。所以,需要通过更全面地推进城镇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来解决城市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全球经济爆发式增长的过程,就是人口从人均劳动生产率低、收入低、就业不充分的农村流向人均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就业相对充分的城市的过程,直至实现城乡产业、就业、人口的相对均衡。所以不能因噎废食,人口密度大、人口总量多的巨型国家特征恰恰为中国城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可以比人口密度小、人口总量小的国家建设更多高水平的大都市与城市群,获得更多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更好提升产业层级、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更广泛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认识误区之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是农民的最后立足地,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与农民进城不利于农民利益保护,把保护农民利益与城镇化对立起来
这种说法背后的逻辑是:土地和农村是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如果农民工在城市失业了,回家有地种,而且农村生活成本低,仍然可以生活下去。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推敲。以河南省为例,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全省人均一亩耕地,实际经营状况是不考虑劳动力投入、仅扣除一年两季种植小麦、玉米的种子、化肥、农药、耕种操作等需要支付资金的各种投入后每亩净收益为800~1,000元/年,意味着靠1亩承包地这个“命根子”,一位农民年收入最多1,000元(远远低于2018年年人均3,500多元的贫困标准、低于各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每个月只有83.3元、平均每天只有2.8元,即使农村物价低,这样的收入水平也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甚至吃饱饭都是问题,所以靠人均1亩土地和农村的低生活成本为农民提供最后的保障、把农村作为农民的最后立足地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样的底线不具任何实际意义。如果真的出现大量农民工失业回到农村仅靠种地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对中国来说无疑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是全国人民不可承受之重、是中国现代化不可承受之重。如果要把人均1亩承包地作为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那就等于认为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将长期处于极低甚至不具实际意义的状态,显然这与经济社会全面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目标背道而驰。在现代化快速推进、外出务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工市民化需求越来越强烈的新时代,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会造成农民流离失所,相反,应彻底破除“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是农民最后立足地”这一观念对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障碍,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及其他各类资源资产的产权归属与权利界限,疏通农村土地及其他各类资源资产的流转和市场交易渠道,实现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关系,激发提高农村土地及其他各类资源要素的活力、效率、效益,拓宽与提高农户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与能力,提高农业农村对资金、技术、人才、优质劳动力的吸引力,使城乡融合发展、要素双向流动落到实处。
四、认识误区之四:城镇化会破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将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乡愁”等与城镇化对立起来
近年来,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规划千城一面、建设贪大求洋、过度开发等导致传统文脉、自然景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现象较为普遍,并出现了污染、脏乱、拥堵、嘈杂等城市病,但这些现象并不仅出现在城市,农村情况也不容乐观。与过去相比,农村民居与村落的特色也在弱化、千村一面问题同样突出,垃圾、污水等导致的脏乱差问题同样突出,滥用化肥农药致使土壤质量下降、农产品质量品质下降等问题同样突出。这些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飞速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既出现在城市也出现在农村,不能片面地归结为城镇化造成的。
城乡人居环境出现相关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太快,而政府、民众的思想观念、认知水平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没有跟上造成的。在工业消费品匮乏、传统农业及手工业产品为消费主体的年代,人们生活简单朴素,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数量少且各种不能自然降解的有毒有害残留物质含量极低,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可以就近就地排放通过自然生态循环自净,不会产生明显的环境问题。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20年来工业化快速推进使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消费品日趋丰富,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数量均呈几何级数增加,其中塑料垃圾袋与各种包装材料形成的生活垃圾已不能就近就地通过自然生态循环自净,食品衣物洗涤、居民洗浴等形成的生活污水中的化学物质比例和种类大大提高也已经不能通过自然生态循环自净,垃圾污水等有害物质的数量及处理难度均大大增加。生活方式的工业化既给城乡居民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也对改变传统的自然生态循环为主的垃圾污水处理方式,投入资金设备、构建管理体系对其进行集中收集、集中处理产生了客观要求,这是生活方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即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就要承担现代化的后果,就必须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对垃圾污水等进行处理整治,否则就要承担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的代价。与乡村相比,城市人口密度大需处理的垃圾污水数量更多、难度更大,如果不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垃圾污水等进行处理整治,在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方面会受到更大的惩罚。但是,由于思想观念、认知水平落后,尤其是发展初期公众与政府均缺乏垃圾污水集中收集、集中处理的理念,再加上各级地方政府财力确实不足,农村没有对生活方式的工业化带来的垃圾污水采取相应的措施,城市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导致农村与城市均出现了污染、脏乱差等现象。所以,城乡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出现的问题是对进入工业社会后居民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垃圾污水处理等环境问题预判不足、应对不足、投入不足造成的。不过城市相关问题出现的相对较早,经过增加投入、强化管理情况已经逐渐好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已经从口号落实到行动,并产生了一批批实质性成果;乡村相关问题比城市出现的稍晚,近年来通过增加投入、大力整治也出现了明显好转,但由于居住分散、人口密度低、治理成本高、治理难度大,进展稍慢于城市。所以,城乡同时出现的环境问题既不能作为反对现代化的理由,也不能作为反对城镇化的理由,而是要通过转变观念、增加投入、完善治理来解决。
至于城市“千城一面”、农村“千村一面”也是由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推进速度超乎寻常,对历经数千年传统农业、乡村文明形成的传统村落结构和民居形态如何适应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在人口高密度集聚、业态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中如何演化等问题,既缺乏经验,又没有也来不及认真研究思考,于是被动接受、照搬照抄甚至主动模仿发达国家现成模式造成的。村落民居等传统文化需要继承,但不能为了继承传统文化而拒绝现代化,相反应该研究和思考村落民居等传统文化如何以现代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既能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满足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各种需求。在城乡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应对传统民居形态如何以现代形式体现在当代乡村聚落和民居形态中、如何以现代形式体现在城市空间和建筑形态中进行反思与研究,探索出切实可行的表现形式,同样不能将之作为反对现代化、反对城镇化的理由。
所谓乡愁,其实质是人们对美丽田园风光、良好人居环境、简单人际关系、简朴生活方式的向往,对简单、轻松、欢快、美丽田园生活的向往,而不是对“缺乏活力”、“无法使用”乡村遗迹的向往,更不是对贫穷、落后、困顿、不便的回味。目前部分地区城市发展中确实出现公共机构及产业功能区人口密度低、环境秀丽,而居民居住区高度集聚、建筑越来越高、密度越来越大的趋势,对于居住在密集“高层塔楼森林”的老百姓来说“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确实成为一种奢望。但是,目前不但城市看不见乡愁,不少农村也同样承载不了真正的乡愁。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演进,乡村青壮年人口外出、经济活力下降、人居环境恶化,呈现衰败乃至凋零迹象,在乡村感受到的是贫穷、落后、困顿、不便,而不是简单、轻松、欢快、美丽的乡愁。所以,留住“乡愁”需要的是新的城乡建设方式,立足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秉承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新思路新理念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才能真正留住“乡愁”;换一种城市规划建设思路,通过科学的、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同样可以产生能够承载“乡愁”的美丽城市。“乡愁”与现代化、城镇化也不是对立的,相反,科学合理的城镇化与科学合理的美丽乡村建设一样,均可以承载乡愁,“乡愁”也不应成为反对现代化、反对城镇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