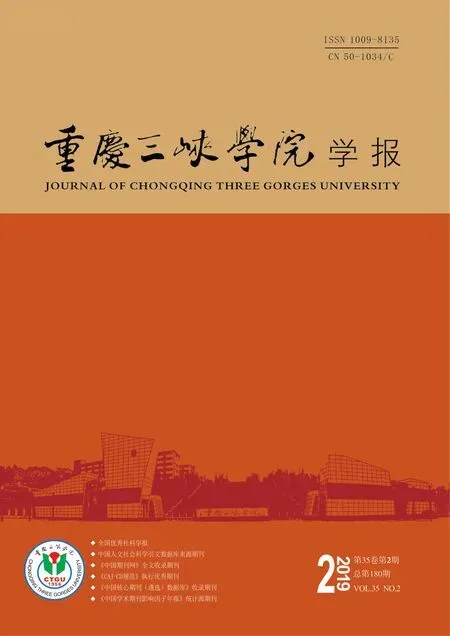现代性解码:阿来《机村史诗》“树”意象研究
罗兴萍 何梦洁
现代性解码:阿来《机村史诗》“树”意象研究
罗兴萍 何梦洁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机村史诗》是阿来一部反映藏族村庄生活的当代编年史。从小说中“树”的意象切入,系统阐释阿来小说中“树”的象征意义。围绕着“树”和森林的消失与重建的过程,阿来揭示出机村在现代化转型中被迫付出的生态代价和族群伤痛,诉说了现代思想入侵给机村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分析了传统藏族文化遭遇到信仰崩塌与强行断裂所带来的焦虑,但随着“树”(森林)的修复也传递出阿来对文化发展所持有的希冀。这部作品不仅在反思乡村历史变迁的多元性和阐释文化冲突的普遍性角度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为民族写作提供新的可能性。
阿来;机村史诗;“树”意象;现代性
2018年1月,沉寂一段时间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带着他再版的新作《机村史诗》(原名《空山》)进入大家视野。从《空山》到《机村史诗》的更名,体现了阿来对以机村为代表的藏族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艰难蜕变意义的认同,以及对乡村未来发展境遇的自信和希望,所以他说:“那时的现实还让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构的蓝图……今天打算重版此书时,我更是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1]《机村史诗》包含《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和《空山》六部曲。几年前,这一系列小说一经发表,便在文坛引起不小波澜。小说独特的花瓣式叙述结构、富有特色的传奇人物、反映的深刻社会现实问题,都注定让这部作品不会被淹没于浩瀚书海。郜元宝、张学昕等学者对其展开了细致剖析,他们努力捕捉阿来在文本中呈现的记忆碎片和历史痕迹,从叙事策略、文化立场、人性分析等多方面解读这部关于藏族村庄的史诗传奇。
最初以诗人身份进入文坛的阿来,在转向小说创作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诗性气质和美学意象成为其小说的独特标志,也成为我们走进阿来文学世界的一把重要钥匙。学者王泉通过对“白色、梦、尘埃”[2]等意象解读,阐释了阿来对人性和生存问题的思考;刘琴攀着“灵魂、预兆、梦”等意象凝结成的绳索,探入到阿来以藏传佛教为主的神秘精神世界[3]。除此之外,蘑菇、虫草、鱼、槐花等自然元素也成为解读阿来笔下藏族乡村破碎与修复的重要密码。但是学界关于阿来小说意象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前后期中短篇小说上,像《机村史诗》这样具有价值的作品,在意象解读方面也仅有南帆的《美学意象与历史的幻象》一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读者可以发现“树”这个意象不仅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是解码“机村”现代化嬗变的重要线索。在爬梳“树”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基础上,论文尝试揭示“机村”在现代文明里的风云变幻,探究《机村史诗》呈现出的文学张力和情感深度。
一、意象解读:“树”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在文学上,“树”不仅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自然事物,也是一种蕴含丰富内涵的文化载体。早在《论语·子罕》中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之说,已把“树”与人联系起来。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也积淀下许多与“树”相关的文学作品,例如归有光在项脊轩庭外亲手种植枇杷树以怀亡妻,鲁迅用冷峻的笔调刻画傲然挺立于秋夜的两棵枣树。阿来从小在藏族乡村长大,广袤的森林和辽阔的草原是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已经消失的森林》《河上柏影》等多部作品中我们都能找到大量关于“树”的描写,而且围绕着“树”阿来还创作了最新再版的小说《机村史诗》。阿来笔下的“树”蕴含丰富的内涵,不仅是个体生命状态的象征,也成为人们物质世界和精神信仰的荷载物。
树是个体生命状态的象征。在《机村史诗》里,作为个体的“树”常被看作是像人一样的自然生命,具有人格化特征。在传统藏族观念中,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无论是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还是花草鱼虫。作为生命象征的“树”,联系着大地和苍穹,它的枯荣成为人类生老病死的暗示,标志着生命的韧度而被讴歌与赞美。在《机村史诗》系列小说中,随处可见阿来以树喻人,以人喻树的例子,譬如《天火》里的索波因很多年都在努力成为先进人物,于是他被阿来称作一棵“躯干像珊瑚,枝叶像祥云的树”[4]175;在《达瑟与达戈》里,当达瑟指着书页上的一棵巨大孤立的大树问“我”是否认识时,“我”说“就像一个见过很多面,又没有说过话的人”[5]85。个体的“树”在阿来笔下常常与机村的某个个体相比拟,写“树”的状态往往也是在诉说人的某种状态,这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有声有色的鲜明物象来暗示微妙的心灵世界的诗学原则”[6]。
为什么“树”能成为个体生命的象征呢?这与“树”自身的特性息息相关,也就是格式塔心理学上所说的“意象具有自我表现性”。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意象的表现性不是由人类的情感附加上去的,而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特征,是指该事物在客观上与人类情感相通,亦即‘异质同构’”[7]。作为自然物种的树木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极易唤起人类的情感共鸣,能够给予人最深切也最完整的生命感。人的生死、成败、得失似乎也都可以纳入“树”的缩写之中,因此“树”这种事物也就与人建立起了情感上的联系,最终达到“异质同构”。阿来新作《机村史诗》中的松、杉、柏、桦等也因为自身的特性与人的情感相通,成为意念的集合,富有多重意义。这种相通性使树与个体生命状态沟通,成为个体生命的象征。
如果说个体的“树”对应的是个体的人的生命状态,那森林则具有群体性特征。它不仅暗示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还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象征。森林作为“树”在数量上的比较级,它提供给人们物质生活上的依凭感也更充足。在原始狩猎和采集时代,森林成为人类生存与活动的必需场所,虽然《机村史诗》并非讲述的是原始时期的故事,但是阿来笔下的机村是一个半牧半耕的藏族乡村,因此森林对机村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生存依凭。从这个角度而言,森林成为大自然的缩影,也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的象征。而且在对《机村史诗》中的“机村”进行释义后,我们也能感受到“树”呈现出的群体化特征,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机”在嘉绒藏族方言中的意思是“种子或者根”,可以看出阿来在对乡村的命名上已经将“机村”与“树”建立起某种联系,村子之于人们就如同森林之于树。藏族崇尚万物有灵的思想,星月山河在人们眼中都被赋予灵魂,“树”在机村人心中也具有某种特殊的信仰意义,仿佛具有强大的治愈能力,成为在世之人身体和灵魂的栖息地。因此,由众多“树”组成的森林也就成为他们的精神原乡。在小说中阿来不止一次提到当人迷惘困顿、疲惫不堪时会依着一棵树休息,让哗啦哗啦的林涛声进入思绪里,进入梦里。“树”安慰了被冤枉的格拉,也给予达瑟精神上的庇护,还成为逝去祖辈的寄魂之所。在《轻雷》里,阿来详细描写老人崔巴噶瓦编结并在森林深处寻找大树挂五彩经幡的情节,老人说:“挂上了这些五彩的经幡,对于逝去的人来说,那就是寄魂之所,对于活着的人来说,那是命息所在的地方。所以,那样的大树就叫做寄命树或者寄魂树。”[8]182这种“神树崇拜”思想的存在是藏族历史文化、地缘优势等各种因素自然选择的结果,“其间渗透着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积淀,反映了各族人民对生命的完整过程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愿望,同时,凝聚着民族文化与群众智慧的结晶”[9]。
“树”最早只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是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生活背景,但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树”逐渐被赋予象征特质,最终成为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文化,开始拥有被各种阐释的可能性。在《机村史诗》里,“树”被看作是一种自然生命,映射着人的状态,具有人格化特征。而且“树”也被崇拜,被神化,成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信仰的象征,给予人身体和灵魂上的抚慰。此外,在阿来所写下的关于机村的故事中,还有许多涉及到森林消失的内容。那么,“树”或者说“森林”除了以上我们所分析的象征意义外,它与机村的变迁之间又有何联系呢?森林的消失揭示了什么现代性因素?
二、历史管窥:“树”所隐喻的历史变迁
与《尘埃落定》相似,《机村史诗》也隐含着阿来对再现历史的兴趣,讲述的是一个藏族村落的当代史。小说以位于川西高原群山褶皱里的机村为主角,通过拼贴的方式,展现出机村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变迁。学者颜炼军说:“一个在大历史旋涡边缘的小村庄,必将有许多强制性的、偶然的力量和逻辑,不断地搅动和改变它的历史进程。”[10]机村也是如此,在新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潮流涌入后,这个藏族乡村的前现代时期与现代社会之间出现断裂,而“树”则成为连接机村不同阶段的重要锁链。简而言之,“树”在《机村史诗》中贯穿起深浅、明暗两条线索,因此对小说中的“树”进行详细解析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捕捉到机村在自然环境方面的改变,还能感受到乡村的现代化蜕变对个体及整个民族所带来的伤痛。
从“树”所展现的表层意义,森林的消失、自然的毁败体现的是机村在被现代化裹挟的大形势下,被迫转型所付出的生态代价。阿来用大量的篇幅描写机村环境的破碎与牺牲。《随风飘散》里展示了现代社会敲开机村大门的第一个信号:汽车把树木运出深山。“斧子的声音打破了那漂亮树林的平静。一株株修长挺直的白桦树,吱吱嘎嘎旋转着树冠,有些不情愿地轰然倒下。”[11]白桦树被砍伐只是机村森林毁灭的开始,随后阿来在《天火》里写了一场森林大火。当森林燃起来的时候,人们忙着斗争、开会,对熊熊燃烧的大火视而不见。“火焰的巨浪崩溃了!落在河岸边大片依山而上的树林上。那些树不是一棵一棵依次燃起来了,而是好几百棵树巨大的树冠同时燃成耀眼的火球。”[4]83-84这场触目惊心的大火不仅烧掉机村周围大部分森林,而且为了灭火,机村的神湖——色嫫措也被炸毁。森林被烧,神湖被毁,百兽众禽失去家园,位于群山之间的机村也失去了依凭。大火之后,国营伐木工人迁走了,但是伐木工作依然在继续,因为随着城市消费需求的影响,机村百姓开始对着“树”举起了刀斧。从《随风飘散》中的白桦树开始,到杉树、楸树、柏树,再到《轻雷》中的落叶松,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地区的森林都难逃消失的命运。伴随着森林的毁坏,机村一步步从古老走向现代,跨越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时代,在转型中承受着人与自然关系破裂和生态环境毁灭的剧痛。
从“树”所代表的深层含义看,《机村史诗》中森林的毁败不仅显示出生态的恶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契约破裂,还为揭示机村在时代变迁中的阶段性特征,感受机村经历的希望与困惑提供了重要线索。在《随风飘散》里,国营伐木工人进驻机村,打开了处于前现代时期机村的大门,原本属于大自然的森林被叫作“国家”的主人接管,机村需要献出山坡上最美的桦树修建万岁宫,人们对新时代的生活充满期盼;在《天火》里,阿来表面呈现的是被大火烧光森林的机村,实际上通过森林的烧毁影射的是一个被激进政治氛围笼罩的时代。所以阿来在森林里烈焰升腾时说:“那毁灭的力量里包含的宏大美感很容易跟这个动乱时代人们狂躁的内心取得共振。”[4]83在《达瑟与达戈》与《荒芜》两部小说中,森林遭受的毁坏程度加深,原本外来的伐木力量已经变成以村民为主的内部力量。伴随着“树”的毁灭,商品经济与现代化的幽灵交织着入侵乡村经济。《轻雷》是《机村史诗》的第五部,也是一个因为木材贩卖而兴起的小镇的名字。“改革开放了,木材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买卖,那些残剩的森林,对当地政府和机村的老百姓来说,如果只是论钱,还有上亿上十亿的价值。”[8]4经济时代的浪潮涌入机村,人们开始因为木材买卖而疯狂。在《机村史诗》的尾章《空山》中,出现了一个曾毁坏树木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于是森林开始被修复。阿来说:“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5]277这个人物的出现拯救了森林,实际上也为机村未来的发展点亮了希望之光。森林消失又被重建的过程无形之中串联起机村的变迁,于是森林的“逐渐死亡,死而复生”隐喻着机村在政治运动和经济潮流的激荡中,破碎又不断重建,断裂又再修复的过程。
“树”的消失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蕴含着个体到族群最本质的悲剧性。阿来利用“树”建构起机村社会的消费链条,串起整个环节过程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体。一棵生长千百年的树在森林中因为刀斧而倒下,意味着无数生命的丧失,而整个森林的消失则意味着自然界的毁坏。机村自然环境的毁坏的确让阿来倍感心痛,可是他更关注围绕着森林的消失世道人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个体生命和整个藏族又遭遇了些什么?就像学者张学昕所说:“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植物,一个乡村,或一种生灵,缘何存在、缘何消失、缘何发展,这是阿来也是许多人被困扰的、又不得不反复思考的命题。”[12]在《机村史诗》中,围绕着“砍树——运树——买卖树——种树”的链条,机村以被动或主动的姿态走向现代化,但新时代除了给这个藏族乡村带来破碎的自然,还造成个体生命的痛苦和整个族群的哀伤。沐浴着新时代气息成长起来的索波、央金在斗争、仇恨等意识形态的裹挟下逐渐失去自我,丧失正确的价值判断。像格桑旺堆村长、驼子书记这样对森林、土地有着浓厚眷恋感的老一辈领导者,却因为跟不上形势也逐渐被时代的红尘淹没。对改革开放后的新青年拉加泽里而言,他缺乏阿甘本所谓的“让潜能处于持有状态”[13]的能力,所以对前途没有正确的认知和谋划,也就没有去建构一种不行动的能力,最终只能任由欲望驱使,在伐木犯法的路上越走越远。看似阿来在小说中展现的是个体生命在历史中的挣扎和痛苦,实际上揭示的是以机村为代表的整个族群在现代化过程中破碎再修复的哀伤。
机村所经历的环境、时局和人心的改变也许是每一个从古老进入现代的村庄必然经历的挣扎与蜕变,其中隐含着“现代”嬗变所携带的希望与痛苦。但是阿来借助森林的消逝除了关注机村的变迁,还诉说个体、族群在宏大历史中的苦痛。在《机村史诗》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阿来对为时代进步承受痛苦和付出代价的个体、群体深怀同情,因为在阿来眼中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而是情感的深度和体验的深度,文学所肩负的最大责任是同情,所以他说:“一个刚刚由矇昧走向开化的族群中的那些普通人的命运理应从这个世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同情。”[14]158在历史的巨轮越滚越快时,阿来看到机村被现代化裹挟的事实,也体悟到人们在与时俱进中的纠结疑虑和苦痛挣扎。这种浸润在文字中的“同情”也有效地扩展了作品的情感空间和意义空间。
三、文化解码:“树”所呈现的冲突
阿来在《草木的理想国》访谈里说:“一个城市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比人的生命更为长久的呢?那就是本土的植物,是树。它们或者在院中,在巷口,一株老树给了几代人共同的荫庇与具体的记忆。”[15]在阿来看来,“树”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其他建筑一起构成城市的风貌,其实乡村的记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它与世世代代在这儿生长的“树”联系在一起,“树”浸透着村庄的个性、情感和精神。《机村史诗》是一部围绕着“树”的消亡和重构而展开的藏族乡村当代史,也是一部讲述旧传统瓦解和新秩序艰难建立的文化史。“树”的命运隐喻了时代变迁中乡村的命运,也展现出新意识形态与现代思想交织涌入给机村带来的文化冲突。
“树”建立起机村与外界的联系,新意识形态的涌入导致传统信仰崩塌以及传统藏文化的强行断裂。所谓新意识形态,是指与藏族传统的意识形态相区别的,蕴含政府主流价值内涵的意识形态。机村是一个被不断进步的文明世界区隔很久的相对封闭的空间,所以当公路像血管一样插进深山,汽车输送“血液”(树)去往外面世界的时候,以汉族文化为主的新意识形态冲击着机村传统的信仰观念。在前现代时期,机村人受传统影响信奉神灵,几乎“村里每家人火塘上首,都有一个神龛,里面通常供有一尊佛像,一两本写着日常祈祷词的经书,有时还会摆着些需要神力加持的草药”[4]43。但是自从“树”揭开机村的现代化之路后,所有与宗教相关的事情都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明令禁止。一开始这些“封建迷信”都只是从形式上被消除,但随着森林之火燃起,新的意识形态也火急火燎地将机村的神树、神灵崇拜从人们心里赶了出去。斗争和革命成为机村年轻人新的崇拜,而老一辈人因为个人能力和觉悟不够只能被形势抛弃,所以在老一辈身上,我们能更明显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在此时强行断裂的痕迹。《荒芜》中机村因为贡献森林而被泥石流冲毁了土地,再也种不出果腹的粮食。在那个所有神祇都被要求从记忆中剔除的年代,“运动”“错误”等庞大空洞的字眼再也撑不起青年们的崇拜。阿来曾说:“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至少是太操之过急了。结果是消灭了旧的,而未能建立新的。”[16]当旧信仰消失,新时代带着乌托邦构想和许多无从理解的宏大观念出现,也导致藏文化的断裂。
“树”增强了机村与城市的连接,城市文化的冲击加速了传统藏族文化的消逝。在《机村史诗》的前四部曲中,阿来展现的是现代化强行进入造成的森林毁坏和文化断裂,而在《轻雷》中阿来着重探讨的是机村人疯狂砍伐和贩卖木材的行为到底意味着什么?改革开放让市场拥有自由贸易的权利,城市对木材的需求增加,过去反感伐木场大面积采伐森林的村民如今也都成为技术娴熟的伐木者。消费主义的热潮激发了人们对金钱的渴望,高中生拉加泽里也弃学赚钱从机村来到双江口镇(别名“轻雷”)。有一次他需要收购一卡车最好的木头,这样的木头纹理清晰,木质紧密就像是少年男子一样俊美。
在传统藏族文化里,世间万物的生命都值得敬惜,树木也和人一样,所以在歌谣中有许多吟唱“树”的歌,例如:“红脸膛的卷发汉子,挺拔的身躯像笔直的铁杉,在断开的截口上,看见你的心湖,仿佛年轮一圈一圈均匀又圆满!”[8]59这首歌前两句将拥有挺拔身姿的藏族汉子比作树干匀直的铁杉,然后吟唱树被截开之后的年轮,字里行间中蕴含着怜惜与敬意。但是像拉加泽里这样的年轻人已经不会再怀着敬意吟唱树木了,也并不关心“树”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他们只将其视作利益的源泉。在现代社会里,敬爱生命的藏族传统与功利实用主义相比丧失了竞争力。阿来在《轻雷》中还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崔巴噶瓦。他是机村唯一还留着辫子,编织着红丝绦的人,也是商品经济时代还捍卫藏族古老乡规民约的人。机村也只有崔巴噶瓦这样顽固守旧的老人还坚持着“轮伐薪林”的传统和对神树的崇敬,会“在深山里寻找古老的树,把折满了祈求灵魂有所皈依的经幡挂在树上”[8]182-183。在这个所有人都因金钱而狂热的时代,诸如经幡、祈祷这类的东西早已被放逐于视线以外,等崔巴噶瓦这样的老人去世,人们就会完全忘记布条上印着的字母和图案,也很难与“祖先寄魂,活人命息”的传统建立起某种联系。在新世纪,经幡的文化意义也被经济利益所取代,成为发展旅游的一种噱头。最后,城市消费主义浪潮激发了机村的欲望,传统藏族文化在与金钱至上的现代观念的交锋中败下阵来。
在“树”所勾连起的机村与现代化之间的线性发展轨迹中,藏族传统文化因汉族文化、消费文化的渗入遭遇了冲击和挫折,但阿来对其发展还持有一定希望。这种期盼在《轻雷》的尾声和《空山》中,能够明显感受到。首先,从主要人物的性格转变可以看出阿来对文化发展的祈愿。拉加泽里因滥伐林木入狱,在出狱后他首先关心的是崔巴噶瓦坚守的林子;而且他还在狱中修了森林环保的学位,成为修复山林的专业人员。树木和树人在道理上大抵是相通的,拉加泽里的救赎行为实际象征着民族精神的重构,以及对多元文化冲突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其次,人物冲突的和解预示阿来对文化冲突的新期盼。索波曾是机村的民兵队长,代表着较为激进的文化理念;而驼子是流落机村的红军,对土地具有深重的眷恋,他代表的是传统农耕文化。他们在《荒芜》中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存在冲突,最后在《空山》中实现和解。当机村人都为了多拿政府赔偿而扩建房屋时,索波与驼子的儿子林军展开了一场对话。索波愤怒地敲着桌子对林军说:“想想,你父亲是什么人!他活着是不会让你这么干的!”林军犹豫了也有些害怕了,“也许,他老人家真要不高兴了!”[17]161虽然此时驼子已经去世了,但是借助儿子的话语驼子和索波实现了一次超现实的会晤,两个人在新形势下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体现出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主动适应性,正如学者贺绍俊所言:“文化的冲突不仅仅造成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害和吞并,也带来文化的新的生长点。”[18]文化的冲突既能带来交融也具有大浪淘沙般的功效,被时间筛选下来的就是传统文化里最具生命活力的部分,也就是文化新的生长点。最后,阿来为即将消失的机村寻觅了一所最佳去处:博物馆。这较为直接地传递出阿来对传统文化发展前路的希冀。在森林消失后,机村也即将因为修建水电站被淹没。后来由于考古学家在干涸的色嫫措河底发现了一个古代村落,机村由此获得新生。它不用被淹没只是迁址并在“新机村增设一个古代村落博物馆”[17]214。古代村落的发现是为了证实机村悠久的历史和绵延至今的文化,虽然新事物的涌入导致许多旧事物的消失,但是有些东西并没有彻底消失,比如能够串联起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向度的机村博物馆,或者说文化线。此时,面对机村的现代性转型之路,阿来流露出更多的希冀,他坚信在现代化蜕变过程中,机村物质层面的东西也许彻底消失了,但精神层面的东西却得以用另一种形式流传下来。
在小说中,阿来以一种哀伤的笔调写森林的消失和文化的消逝,但在传统藏族文化经历信仰崩塌,强行断裂甚至部分消逝后,阿来对文化的发展还是持有温暖的向往。他说“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给予了更高的希望,希望其更人道,更文明。”[16]看似阿来始终在诉说机村所遭受的文化冲突,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机村史诗》是一部封闭式的地域性展示作品。阿来写机村也是写藏区、写中国,或者说其实他是站在更高的层面,进行世界性的文化冲突和交流的言说,如他自己所说:“作家表达一种文化,不是为了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不是急于向世界呈现某种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图像更臻完整。”[14]168正是阿来这种较为宏大的文化观让我们看到他为民族写作提供的新的可能性。
四、结 语
在阿来的小说中,“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但蕴含丰富的象征和隐喻,而且出现在《机村史诗》系列小说的各个阶段。“树”对于机村而言,似乎是温尼科特所谓的“过渡性客体”,起到沟通整合历史和文化的作用。“树”的消失与重建过程呈现出环境的毁败,串联起机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也揭示出个体和群体在历史前行道路上所遭受的挣扎与痛苦。这些都是机村藏族在汇入现代化大形势下,被迫转型所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树”建立起机村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也正式掀开机村文化冲突的序幕。在与汉文化、消费文化的激烈交锋中,传统藏族文化遭受严重的冲击和破碎,但阿来对于其发展前景还是持有温暖的向往。因为文化是动态变化的,多种文化在不断融合和排斥的过程中必然催生出新的元素,阿来也相信传统藏区文化会在多元的交互中,不断容纳、净化和发展。有学者认为阿来的《机村史诗》是迄今为止“中国作家书写藏族生活、表现生命韧性和存在奥义的最为典范之作”[19]。其实这部作品在反思乡村历史变迁的多元性和阐释文化冲突的普遍性角度也具有重要价值。
[1] 阿来.机村史诗•荒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230.
[2] 王泉.论阿来小说中的几个主要意象[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105-106.
[3] 刘琴,毕耕.阿来小说中的意象分析[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6):112-113.
[4] 阿来.机村史诗•天火[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5] 阿来.机村史诗•达瑟与达戈[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6]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8.
[7] 吴晓.诗歌意象的符号质、系统质、功能质[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116-124.
[8] 阿来.机村史诗•轻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9] 陈西平.中国民俗中的树文化内涵[J].前沿,2003(8):139-142.
[10]颜炼军.“空”难交响曲——阿来《空山》三部曲阅读札记[J].当代文坛,2011(1):85-88.
[11] 阿来.机村史诗•随风飘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143.
[12]张学昕.孤独“机村”的存在维度——阿来《空山》论[J].当代文坛,2010(2):28-31+40.
[13] 阿甘本.潜能[M].黄立秋,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295.
[14] 阿来.阿来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15] 梅柏青.阿来:可以生根的爱[N].成都日报,2011-11-03(10).
[16] 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J].扬子江评论,2009(2):1-5.
[17] 阿来.机村史诗•空山[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18]贺绍俊.一座凝聚着“盼望”、连接着时间的“博物馆”——读阿来的《空山》[J].扬子江评论,2009(2):6-11.
[19] 于国华.生态文学的典范:阿来的“山珍三部”[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59-63.
Decoding Modernity: An Analysis on the Image of “Tree” in A Lai’s
LUO Xingping HE Mengjie
is a contemporary chronicle that reflects the life of Tibetan villages. Taking the image of “tree” in the novel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ree” in A Lai’s novels. Around the process of the disappear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ee” and forest, A Lai reveals the ecological cost and ethnic pain that the village was forced to pay in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t tells the cultural conflict brought by the modern thought invasion to the village; it tells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 to encounter the collapse of the faith and the anxiety caused by the forced break. But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ree” (forest),it also conveys the hope that A Lai holds for 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work not only has important value in rethinking the diversity of rural historical changes and interpreting the universality of cultural conflicts, but also provides new possibilities for national writing.
A Lai;; “Tree” image; modernity
罗兴萍(1964—),女,四川宜宾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何梦洁(1993—),女,四川自贡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7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阿来小说中的生态元素及其当代意义”(KYCX17_1491)。
I206.7
A
1009-8135(2019)02-0049-08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