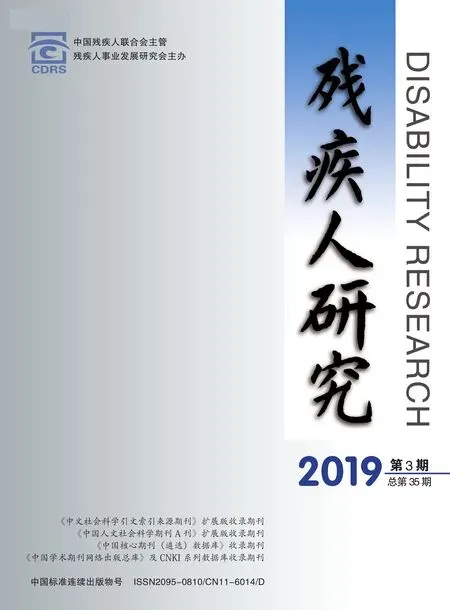《残疾人权利公约》:诞生、解读及中国贡献
李 敬 亓彩云
前言
两次世界大战,除了给全人类带来无法抚平之创伤外,也分别在战后推动了各国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服务制度体系的建立。这些体系肇始于战后退伍(伤残)军人的安置和家园重建,并随着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扩展到其他有需要的人群,其中,残障社群逐渐成为各国福利支持的受益人群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伴随着联合国的成立,残疾人事务逐渐从某个国家的国内事务,上升为国家间交流、对话、互助乃至相互指责的内容之一(俗称“人权外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层面就有针对智力残疾人、(全体)残疾人、精神残疾人等不同人群的若干国际文件,如1971年《智力迟钝者权利宣言》、1975年《残废者权利宣言》、1991年《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原则》等。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二战后残疾人运动的兴起和迈克.奥利弗(Mike Oliver)等一批卓越残疾人学者与社会活动家的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其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探索,涉及残障研究的各类成果不断涌现。联合国的相关机制,对残疾人问题也日渐重视起来(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动组织出台的各类涉及残障的文件、政策等)。
联合国将1981年定为“国际残疾人年”,随后于1982年,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设立“残疾人十年”(1983—1992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国际大背景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登上了世界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舞台。一个例证为,中国残联联合亚太其他国家的残疾人组织,在联合国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成功推动了亚太地区建立“亚太残疾人十年”,到如今这一运动已持续了三个“十年”的光阴(1993—2002、2003—2012、2013—2022)。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层面上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关于起草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动议。1993年,联合国仅以《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准则》这一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件,向世界各国宣告保障残疾人权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毋庸置疑,残障人权利保障的议题已经缓慢而坚定地进入联合国及世界各国的社会政策核心议程[1]。
1.《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诞生历程及相关问题说明
1.1 第一次和第二次特设委员会全体大会
2001年,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次全体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开放的特设委员会,考虑在残障领域制定一个全面、综合的新公约[2]。前述联合国网站及一些残障人权学者[3]和残障社会活动家[4]的文章显示,2002年7月29日至8月9日,特设委员会第一次总结报告(文件编号A/57/357)时,各国代表们尚不清楚这一特设委员会具体需要做什么,同时,对于残障领域是否需要一个全新的公约,与会各国代表们的意见也不一致[5]。
2003年6月16—27日,特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经一系列讨论(主要围绕三个专题讨论:对国际人权公约和相应机制类型的讨论、对非歧视原则在各国立法实践的讨论和对新残障观及各类残障概念比较分析的讨论),代表们在报告(文件编号A/58/118 & Corr.1)中表示:遵循前述联合国56/168决议精神,结合已有的人权保障机制模式(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许多国家的残障反歧视立法经验,在残障领域起草一部新法,以便让联合国传统人权保护领域里“不可见的”残障社群变得清晰可见。
《公约》的实际起草行动,始于2003年底。为筹备将于2004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特设委员会全体大会,第二次特设委员会大会决定,成立《公约》草案起草工作组,为特设委员会的下一次讨论准备材料。该工作组由27个国家、12个民间组织和1个国家人权机构的代表构成,中国政府有1名代表参与。
1.2 第三次至第六次特设委员会全体大会阶段
2004年1月5—16日,工作组结合各国各界提交的资料形成“工作组文本”(Working Group Text),成为特设委员会后续磋商的基础文本。
有了2004年1月的工作组文本后,5月24日至6月4日,特设委员会进行了预定的第三次集中讨论,这一次的报告(文件编号A/AC.265/2004/5 and Corr.1)显示,全体大会对工作组文本的第1—24条条款进行了详细、快速的审读和讨论,并就增加监督/监测机制一项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2004年8月23日至9月3日,特设委员会进行了第四次集中讨论(文件编号A/59/360)。会议期间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新西兰常驻联合国大使唐.麦凯(Don Mackay)成为大会的非正式协调人。他独具个人魅力,积极协调各方,使人们对磋商中意见相左的若干条款达成共识,为随后全体大会达成最终的共识奠定了基础。
2005年1月24日至2月4日,特设委员会进行第五次集中讨论,麦凯大使继续充当协调人角色。全体大会结束前夕,他被选为第二任特设委员会主席。2005年8月1—12日,第六次特设委员会召开。这两次全体大会对工作组的整个文本及各国各方提交的各类建议作了较充分的讨论(第五次会议报告文件编号A/AC.265/2005/2、第六次会议报告文件编号A/60/266)。
1.3 第七次和第八次特设委员会全体大会阶段
2005年10月7日,为筹备即将在2006年初召开的第七次会议,特设委员会新主席、新西兰常驻联合国大使唐.麦凯特意写信给全体代表,将前六次全体大会集体讨论所产生的文本进行编辑整理,形成了他的主席版本(Chair's Text),并通报各国各界代表周知,请参会者针对主席版本进行评价和回应(A/AC.265/2006/1)。
2006年1月16日至2月3日,麦凯主持下的第七次特设委员会全体大会开幕,会议对主席版本的第1—34条进行了紧张激烈的讨论。代表们经过三周的唇枪舌战,于2月3日达成口头一致,形成了第七次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文件编号A/AC.265/ 2006/2),它的附件是共有33个条文的《公约》工作文本(Working Text)。
有意思的是,2006年8月14日—25日及2006年12月5日召开的第八次特设委员会全体大会的会议内容,至今尚无任何公开的速记资料可查。8月,特设委员会临时报告(文件编号A/AC.265/2006/4)中的《公约》草案,和最终通过的《公约》版本几无差异了(但第12条存在一个脚注,这说明与会代表对某些概念如“Legal capacity”的理解存在异议)。9—10月,特设委员会下属撰写小组(Drafting Group)工作期间,前后形成了四稿《公约》草案(关于第12条的那个脚注一直被保留)。
1.4 《公约》和《任择议定书》诞生
针对各国代表就《公约》草案里的第12条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存在脚注这一问题,2006年11月29日,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凯致信全体代表,希望大家就《公约》草案第12条的脚注问题达成谅解,并可在《公约》正式通过时去掉此脚注。 12月5日,在第八次特设委员会全体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伊拉克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和芬兰代表的欧盟通过公开信形式,就草案第12条中的“Legal capacity”的理解问题达成谅解,即阿拉伯世界坚持认为“Legal capacity”在其语言和文化中的含义是“法律权利能力”,而欧洲诸国认可《公约》各语言版本里的对等概念,含义一致。伊拉克和芬兰等信件资料都公开于前述网站。
12月6日,特设委员会将草案上报联合国大会(文件编号A/61/611)。12月13日,《公约》获联大全体大会顺利通过。至此,在21世纪伊始,由联合国领导、各国集体努力下的新人权成果——《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文件编号A/RES/61/106)终于完成,只待完成相关法定程序后正式生效。
1.5 《公约》和《任择议定书》的关系及其各语言文本效力说明
《公约》和《任择议定书》是两个完全独立但有一定相互关系的法律文书[6]。《任择议定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公约》起草过程中,一些国家主张加强未来建立的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准司法”能力(即委员会可在接受缔约国个人或团体投诉后,对被投诉国家或事项进行调查)。但这一主张一经提出,就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因此,特设委员会协商的结果是,《公约》与《任择议定书》分开撰写,前者是基本法律文书,有意愿加入的诸国需要签署和批准(部分国家的国内法规定,不经签署就可直接批准国际法)。后者只是附带性文书,缔约国可签可不签,不影响《公约》对缔约国的效力。因此,特设委员会会议期间未对《任择议定书》进行任何公开磋商,仅委托专业人士撰写。《任择议定书》不能单独签署。
还要指出的是,联合国作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家园,二战后确立了六种官方工作语言,分别是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早在1969年联合国《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里,就有对同一文书、不同语言版本的效力的明确规定。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所产生的同一文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这也是《公约》第50条和其他联合国通过的法律文书一样庄严声明“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语、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同等作准。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的原因。《任择议定书》第18条对语言文本效力也作了同样的声明。
换句话说,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所形成的法定文书,其法律效力是一样的。不存在某个语种的文本效力高于其他语种文本的情况,也不能以对某一语种文本里的个别词汇的解释,去曲解、误导乃至压制其他语种文本中的对等概念。在这方面,国内出现了一些反面例证[7],这类情况的出现,说明涉及《公约》领域研究的学术规范有待加强。
更为重要的是,每个缔约国都有依据自身国内法认可的独特官方语言。在理解和落实本国业已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条约时,必然是以本国官方语言的作准文本为落实、学习乃至研究的对象。在中国,中文是中国人的官方和日常语言。中文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在我国以《公约》作准中文版作为研究、学习和倡导使用的资料,合乎法理人情。
出于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之目的,研究者或其他使用人自然可参照其他语言文本,以便更深入、从更多角度,抑或更为周全地理解某些概念,甚至进行一些针对语言差异/法律(文化)体系差异的学术讨论。但本国语言作准文本里的法定概念是不容质疑和诋毁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格外严肃的法律专业和学术伦理问题。
1.6 国际法的国内适用
国际法如何在国内适用,过去曾是中国学界研究的一个问题点,但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至少在宪法和国际法学界早有共识[8-10]。可惜,目前不少《公约》人权保障角度的论文,无视或忽视了这一重要的国际法的国内转化前提[11-12]。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适用问题并无明确规定。目前已批准加入的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主要体现为立法部门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国内现实需要,主动参照批准的相关国际法规定,有针对地对国内法律法规及政策做出更改修订,学界一般称之为对国际标准的吸收和转化。
这一转化和吸收的前提,是相关国际法的内容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而非来自国外压力(或挟所谓国际潮流的国内游说组织的鼓吹)。站在中国残疾人政策和中国残障社群发展需要的立足点上,客观、准确、透彻、审慎地研究各类中外情况,利用对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最有利的资源,也是中国多年来积极发展国际交流,推动《公约》诞生,不断以《公约》中的积极内容促进国内残疾人政策和服务体系发展的出发点和持久动力。
1.7 目前世界各国批准情况评价
据联合国网站统计,截止到2017年9月,世界范围内,已有161个国家(地区)签署了《公约》,177个国家(地区)批准。其中一些国家(如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法国等)对《公约》某些条款的内容(如第12条)做了保留,即表示该缔约国在批准《公约》时保留本国对那一条的解读权和在缔约国内适用的限制,换言之,就是那一条在该国不适用。另签署和批准《任择议定书》的国家(地区)有92个。
有趣的是,美国仅签署但尚未批准《公约》,也就是说,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并未正式加入《残疾人公约》,不须履行任何《公约》义务。
2.如何客观、准确解读《公约》,造福国内残障社群
《公约》诞生后,国内对如何准确理解《公约》,真正造福本国残障社群,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据笔者观察,目前,绝大多数研究、使用和讨论《公约》的人,对本文前述的一些基础而关键性问题,如《公约》各语言版本间的关系、国人讨论《公约》首选哪种语言版本、《公约》对国内法的效力等,尚无准确认识,对《公约》缔约谈判中某些条款的具体磋商过程也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事实上,对如何解释国际条约,联合国早在1969年通过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3]中就有规定,我国于1997年批准加入该条约。
2.1 遵从联合国已有的国际公约之解释规范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作为规范国际条约的国际法,它的第31、32和33条专门规定了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国际条约,其中第31条的内容是关键:
“第三十一条 解释之通则
一、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
二、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指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并应包括:
(a)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
(b)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
三、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
(a)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
(b)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
(c)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四、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
目前国内《公约》研究多追随西方某些文献或派别的研究,尚未见有人使用上述解释规则对《公约》具体条款进行研究,提出基于历史事实或有中国特色的成果。
2.2 深刻了解磋商过程中立法者的本意
除遵循通用规则外,在具体理解《公约》某些条款或具体问题上,笔者建议:为尽可能客观、准确地理解条款本意,一个非常基础但又很根本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回归当时的讨论现场,通过已公开的各类资料,了解当初参与立法的人员是怎么讨论某个问题的,以及就哪些问题达成了一致,哪些没有达成一致及其可能的原因。
回到立法起点,仔细研究磋商过程及其主要争鸣的各类问题,可以为客观、准确地了解某个条款的来龙去脉提供历史依据,奠定扎实的证据基础。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某些具体条款的研究中,由于缺乏历史角度,未能广泛阅读文献,存在偏读偏解的现象。[7]
2.3 参考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颁布的文件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Disability Rights Committee)针对各国履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出台的《一般性意见》和在审查各国履约情况时给出的《结论性意见》也是一种理解(解读)公约内容的手段。
按照《公约》第34、36、37和39条,委员会有审阅、评价和指导说明的权责。但委员会公布的任何文件都无法律效力,仅是一种软约束机制,缔约国无履行义务。缔约国仅是从道义角度考虑,对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发布的各类文件和说法表示尊重和视情况择机遵循。
例如,委员会2014年颁布的第一个《一般性意见》就被一些学者指责片面解读了第12条[14]。笔者认为,残疾人委员会无视《公约》本身是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混合,实现《公约》里所载的任何一项权利,都需缔约国从多方面着手。它执意在第一个《一般性意见》中把“Legal capacity”归属为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范畴,要求缔约国立即实施,这一解释,是不妥的,也扭曲了特设委员会全体大会讨论期间各国达成的共识,这里不再赘述。
2.4 立足中国国情,问计咨政于民
《公约》对缔约国而言,是一种政治道义和国际承诺。如何理解并具体落实要依据各国特定的民意国情,才是最根本的。因此,相关部门、组织及学界在研究、领会和理解《公约》基本原则和具体条款所规定的内容时,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基层需求,从基层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才有可能对《公约》本意做出符合当下本国残障社群民意的最好理解。换句话说,如果,《公约》本意是要造福全球残障社群的话,那么,本国的理解和落实就是为了造福本国残障人群。
2.5 从学术研究/讨论角度的解读
除上述几个角度外,相关学术研究思想的贡献作用也不容小觑。这一部分从这些年不断发表的学术文章和博士硕士论文数量上就能看出端倪。
总体而言,基于文献回顾,笔者发现,当下的国内研究大多尚停留在对《公约》文本的规范性解读上(且经常不以作准中文版本为基础)。研究往往简单地以《公约》为视角/讨论起点,对部分国内相关社会问题进行“问题—对策”类的宏大叙述,却忘记在使用《公约》前,把国际法的国内转化等一系列基础问题进行前提性讨论或设定。还有不少研究把《公约》置于“神坛”,不敢进行任何质疑或讨论,忽略其是政治和法律性文件,本质上是协商妥协的成果,因而,本身就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为此,笔者希望本文能帮助国内研究澄清一些《公约》的规范性和法理性前提基础。
3.《公约》形成中的中国贡献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新千年伊始后的2001年2月,联合国秘书处下辖的社会政策与发展处,就曾支持社会发展理事会和残障特别报告员就残障人权保障举行过非正式咨商会议。中国残联当时作为非政府组织代表,应邀就2000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残疾人非政府组织国际峰会”中形成的共识做通报,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残障人权保障的关注和倡议。
在《公约》磋商前后,中国作为国家总人口、残疾人口两个世界第一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推动公约的制定(如中国残联牵头或积极参与在中国香港和北京、泰国等地组织的相关讨论,中国残联创始人邓朴方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周游各地倡导演说)。客观地讲,中国政府和中国残联在促成《公约》诞生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上述内容在联合国网站和中国残联网站都有记录。
2006年12月,联合国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这正是过去几十年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残障社群共同奋斗的成果。2007年3月30日,《公约》开放签署,中国政府代表作为第一批国家于当日签署完毕。2008年5月3日,《公约》正式生效,中国人大常委会于同年6月无保留地正式批准了《公约》。 2010年8月和2018年8月,中国政府分别如期提交了《首期履约报告》(文件编号CRPD/C/CHN/1)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实施情况缔约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合并定期报告.中国》(文件编号CRPD/C/CHN/2-3)等文书。可以说,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组织在履约及报告等方面,体现了守信用的大国典范。
总之,《残疾人权利公约》作为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认真参与和道义缔结所形成的国际人权法文书,需要中国的相关部门、组织、学界、广大残障社群及有兴趣的社会大众,在客观、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积极应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乃至积累未来修订《公约》之素材。造福中国乃至全球残障社群,打造基于尊重多元文化、接纳差异、保护具有脆弱特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积极倡导和认真务实履行《公约》过程中不变的宗旨和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