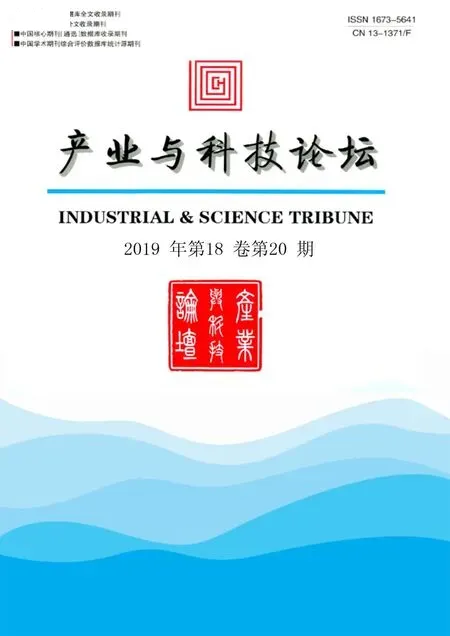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专门制度保护衔接研究
□周 允
一、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现状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到要对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保护与进一步挖掘,同时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完善中医医疗技术目录及技术操作规范。加强对中医药百年老字号的保护。《2018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中也再次提到要做好建设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名录、保护制度的工作,对古代经典名方类中药制剂知识产权保护。201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医药法》第43条规定国家要在数据库、名录和制度建设上做好工作。这是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将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确立下来,但事实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2004~2005年左右开展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专题研究,就已经指出了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概念以及内涵、保护宗旨、保护内容和保护方法。而且自2013年就已设立中医药行业专项项目“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技术研究”,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数据库即已经构建,其中名录数据库首先推出的是方剂库,隋唐以前32种方剂类古籍内容共计38,000多首方剂已收录,同时也已实现主题、全文、复合检索,并有对应图像。后续将唐代到清朝的大约5万多首方剂也放入名录数据库中。同时,积极对收集、纳入符合入选标准的中医药传统知识项目进行登记和立档,进行编码,方便以后检索。这项工作涉及全国31个省市参加,先是进行摸底调查,只要持有人手中掌握有祖传且正在使用的特色中药炮制技术、方剂等中医药传统项目,流传超过50年以上或家族三代以上,均可参加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医疗机构、家族、师承群体、学派、老字号企业及特定地区(民族聚集地、村落等)中传承应用的活态性的中医药传统制剂方法、炮制、经验方和诊疗技术等。在摸底调查和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筛选及确认,登记并建档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中医药传统知识项目。对于活态性中医药传统知识项目现已收集五千多项。
可见,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已经是逐步落实和推进。但问题依然是存在的,比如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形式是采取以知识产权方式为主,或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专门保护制度,又或是要进行综合保护。若采取综合保护又该如何衔接二者。专门制度这一权利行使的主体界定、客体的内涵、权利义务的要求等都需要得到解答。
二、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局限性
目前国内涉及的中医药传统知识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规定在《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中,因此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一)专利权制度保护的局限性。以专利对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提炼出来的中药制剂进行保护,是较为通行的一种方式。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专利主体、客体不确定、实质审查标准过高和侵权认定困难。第一,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主体在《中医药法》第43条第2款中定义为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关于持有人,可能是个人、群体、集体或者国家,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持有”并非一般“私权”上的“占有”,可能会涉及“公权”的“占有”,因此需要有确定主体的专利权显然不适合保护主体不确定性的中医药传统知识;第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中,将中医药传统知识定义为: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世代相传并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或潜在价值的医药卫生知识;同时,包括了由该领域中智力活动所产生的革新和创造。包括中医药理论知识、技术知识、遗传资源和特有标记符号。具有主体多样性、地域性、传承性、根植于传统文化、人身依附性、整体观念等基本特征。主要有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医传统制剂、中药炮制、针灸、中医方剂、中医正骨、医疗器具、中医文献、道地药材、医药文物等。《专利法》第2条将专利的客体定位在发明创造,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对比两者,不难发现专利制度保护的是从中医药传统知识中通过创新衍生出来的产物,比如已制成药品的有效提取化合物、有效提取部位、原料组成和制造方法,但并不是该传统知识本身;第三,关于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专利实质审查的“三性”是焦点问题之一,核心标准为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这些起源于西方的标准对中医药传统知识来说反而是一种桎梏。新颖性采取的“绝对新颖性”标准,事实上大量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包括中药配方组成、工艺制法和中医临床经验、有效配方等是古籍中记载流传至今,可以说早已处于公知领域;创造性要求实质性特点和进步,中药源自自然药材,成分构成复杂,分界本身就不如西药明晰,再加上中药的药效并不是单一的,可能是多种活性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许仅进行简单的药物加减就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但是要进行物理化学系统地论证又较为艰难;实用性要求能够进行工业上的制造和使用,即使是对于中药来说也会由于制作方法和使用材料的特殊而难以实现;第四,中医药专利侵权认定困难,与中医药成分的不确定以及现有检测技术的限制有关。
(二)商标权制度保护的局限性。中医药传统知识中符合商标法规定的情形,比如道地药材,是可以通过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进行保护的,《中医药法》第23条也对此进行了确认,国家鼓励采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措施保护道地中药材,这是一种重要的导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之中依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从《商标法》第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商标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区别商品的来源和服务的提供者,也即是商标是和商品和服务捆绑在一起,需要在经济活动中使用,否则超过一定期限,就有被撤销的可能。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作为商标的一种,也应遵循此种规定;第二,《商标法》规定,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的使用需注册进行,企业、政府或行业协会都可以成为注册人,因此地理标志权应该首先是一种“私权”,但是道地药材作为典型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它的主体属性具有特殊性,可能是个人、群体、集体或者国家,体现“私权”的同时也需要“公权”的介入。也就意味着道地药材既体现种植、加工者个人利益,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因为是同一地域所有种植、加工者共享。
(三)著作权制度保护的局限性。中医药传统知识的著作权保护虽然并直接涉及配方、工艺等具体内容,保护的力度和方式不如专利权、商标权和商业秘密权等制度,但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它的局限性依然是不能忽视的:第一,《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强调的是作品的表达方式的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并不是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或者理念,而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内核正是通过时间淬炼形成的一整套理论、知识和技能,并不仅只是表达方式本身,同时也就意味着不能阻止别人利用其作品中表达出来的思想进行重新创作;第二,著作人身权在保护时间上虽然不受限制,但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而言,主体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权利的行使,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时间是作者生前和死后50年,有大量的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时间已经很难考证,早就超出期限进入了公知领域。例如经方,主要指汉代以前经典医药著作中记载的方剂,这是人们在中医学实践中形成的,不仅主体难以确定,同时独创性也不清晰,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都难以实现。
三、中医药传统知识知识产权和专门制度衔接保护的必要性
(一)知识产权和专门制度保护的联系。在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上,知识产权和专门制度的保护虽然分别有其独特的法律制度构成,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也成为需要将二者共同探讨提供基础:第一,虽然学界目前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专门制度保护达成一定共识,也将其体现在《中医药法》中,但争论之处依然存在,而知识产权理论可以为专门制度的构建提供基础和经验借鉴,强调对“知识”的保护是知识产权和专门制度的共同特点,其中的利益平衡原则可以在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的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中发挥作用;第二,中医药传统知识知识产权和专门制度保护的主体有其共通之处。知识产权的主要权利主体包括著作权人、专利权人和商标权人,他们也可能会参与到专门制度保护的法律关系中,比如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持有人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继而申请知识产权成为权利人;第三,在保护内容上,专门制度保护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也含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第四,中医药传统知识作为知识产权的源头,知识产权是在对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专门制度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
(二)知识产权和专门制度保护的综合保护。如前文所述,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的问题中有些是可以通过修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达到保护目的的,但有些是不能的。比如确定中医药传统知识权利主体和客体,既体现中医药传统知识在专利权制度、商标权制度和著作权制度的保护,同时也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即使再扩大保护范围、再扩大解释也无法完全涵盖的,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即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必须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和专门制度同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