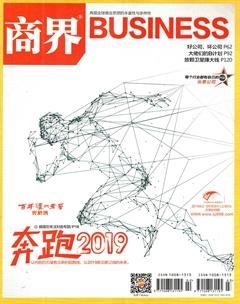放颗卫星赚大钱
王思宇

去年冬天,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去了一趟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这里的气温只有零下20摄氏度,他的双脚被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当天下午4点左右。冯仑亲眼见证了自己的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被长征二号丁火箭送上了太空。仅过了2分钟,这颗花费100万美元的卫星就消失在他的视野中。
从2015年我国首颗商业化卫星“吉林一号”成功上天,3年里,中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商业卫星公司。天仪研究院、珠海欧比特等企业已经成功将自己的数枚卫星送上太空,而九天微星更是凭借“瓢虫系列”火箭,一次放飞了7枚卫星,刷新了国内民营单次发射数量纪录。
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没有优质的研发环境,但这些民营企业凭借对成本的严格控制,愣是将卫星放上了天。
SpaceX的中国学徒
杨蜂是“被迫”进入航天领域的。
2007年,出身北航电子工程系的杨峰离开央企创业。但他的物联网技术公司一直赚不了钱,很快濒临倒闭,连合伙人都跑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做的事情太超前,反倒做成了行业的先烈”。
在公司快关门的时候,杨峰听说同学那里有一份航天五院总体部软件开发的外部协作项目,顾不上合适与否,他快速接下了这份能拯救公司的业务。靠着这份“外快”,杨峰的公司很快便起死回生。尝到甜头后,他们干脆转型做起了航天领域的软件供应商。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卫星的制造成本和发射成本都比以往大大降低。虽然单颗星完全比不上大卫星的能力,但是他们拼的就是“一箭多星”。
2015年3月1日,一个叫做马斯克的美国人,在大洋彼岸用自己公司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将一枚通讯卫星送入太空轨道。当天,杨峰和公司同事们都看到了这则震惊世界的新闻。
看完新闻之后,杨峰和同事们沉默许久,看着彼此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做中国的SpaceX?”事实上,靠着给航天配套做一些边缘工作,虽然收入不错,但始终只是小打小闹,发展非常受限,因此杨峰动了效仿马斯克发射卫星的大胆念头
趋势远比杨峰和同事们的预想更快,同一年,政府便开始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到卫星研制与商业发射领域。“政府给我们开了一扇门,我们就立刻跳了进去,成立了天仪研究院。”
热血归热血,杨峰清楚的知道照搬SpaceX模式在中国难以实现。中美两国政策差异较大。国家刚放开民营航天的“口子”,未来趋势还不甚明朗。资金方面也是一个大问题,SpaceX的资金可以依靠马斯克另一家知名电动车企特斯拉支持,但天仪和杨峰却什么都没有。
依靠着前期航天领域的软件供应商角色,杨峰大致摸清了商业航天领域的门道。天仪要做的绝不是与“国家队”竞争,他因此向公司提出“三不”原则:不直接承接国家任务,不和体制内传统科研院所竞争国家卫星任务;不销售单颗卫星;不做国家已布局的卫星应用,不直接涉足遥感、通信、导航三大传统卫星领域。
那什么才是天仪的核心?答案是“快”和“低”。
杨峰对于天仪的思考,来源于SpaceX。毫无疑问,SpaceX是目前最成功的商业航天公司。也是發射失败最多的公司。它主动寻求低价。把成本越做越低,把速度和基础迭代越做越快。
“上去的东西多了,应用就多了,市场就大了。计算机不是这么演变的吗?通信行业不是这么演变吗?汽车行业不是这么演变的吗?航空工业不是这么演变的吗?为什么航天就一直有居高不下的成本呢?”
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卫星的制造成本和发射成本都比以往大大降低。虽然单颗星完全比不上大卫星的能力,但是他们拼的就是“一箭多星”。这样就能够在提供更好服务的同时,也大大降低行业门槛。
上天的生意
2016年11月份,在经历近1年的研发后,天仪自主研制的卫星——也是中国首颗民营卫星正准备接受发射的考验。
按照当初的发射计划,是1枚火箭搭载5颗卫星上天,天仪研究所的卫星刚好排在队列第5,而杨峰恰好也是发射指挥大厅中唯一的商业公司代表。
指挥厅大屏上,卫星分离成功后屏幕上的标点就会由红转绿。到最后,整个屏幕都是绿色的,只有天仪的那一角是红色。杨峰焦急地盯着屏幕,从第4颗卫星分离,到天仪的卫星分离,一共用了19秒。这19秒,是他度过的最为煎熬、最为漫长的19秒。
火箭发射成功后,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随后,进入卫星与火箭的分离阶段,每当有一颗卫星成功分离,会场就会响起一片掌声。
“我们天仪是最后一颗星。而我是最后一个还没有庆祝的人。”伴随着最后一个红点变成绿色,杨峰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为了这个19秒,天仪团队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
“办公室在2楼,员工宿舍在5楼,实验室在1楼,很多同事累到没有力气上下楼。直接往实验室的地上一躺就睡了。”
这颗被命名为“潇湘一号”的卫星入轨后将进行多项航天技术试验,包括空间软件无线电试验、导航信号增强试验、新型星载计算机搭载试验、高精度光学稳像试验等。这些科研实验是由天仪和航天一院十四所、中科院光电院等航天传统优势单位联合研制的。
客户对于卫星的需求多种多样,比如冯仑希望自己的卫星能通过手机进行太空直播;通讯公司希望卫星能够代替地面基站,覆盖更多地区;科研单位希望卫星能够携带实验样本上天,并在太空中完成实验。
为太空科研搭个桥,是杨峰和另一位合伙人任维佳为天仪思考的商业模式。对于太空科研市场来说,缺的不是钱,而是“上天”的机会。
任维佳毕业于清华,曾在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任主任工程师。先后参与了从神舟三号到神舟八号六艘飞船,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等研发任务。工作过程中,任维佳注意到大量需要被带上天的科研项目,都因为排期的问题而被无限期搁置。
“如果是一个籍籍无名的青年科学家呢?或许10年,甚至一辈子,他可能都很难等到一个机会对太空验证。而现在,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缺位的需求。”
科研单位有明确的需求和充裕的付费能力,这个市场规模小,“国家队”看不上,其他民营企业也没有涉足,天仪要抓住的就是这些机会。因此,面向全世界的科研院所与科学家,提供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验证的服务,成为天仪对自己的业务定位。
上天的生意看似容易,实际上并不容易。它意味着,天仪团队不但需要了解航天工程的指标要求,还需要了解科学家的科研需求。
天仪的很多客户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技术牛人或是大企业,但他们自身并不懂航天方面的专业知识,只能说清楚自己的科研需求。而天仪团队中,既有航天工程师,又能听懂他们专业领域的专业需求描述,大家可以无障碍沟通。
经过2年多的摸索,天仪依靠这种模式成功发射了10余颗卫星,获得超6000万元的卫星业务收入,成功闯进“2018中国商业航天企业30强”。

稳定压倒一切
商业航天好消息很多,坏消息也不少。
冯仑冒着严寒放出的那颗“风马牛一号”,没能达到他要求的太空直播目标。这枚上天的卫星最终因为无法回传图像数据。而被搁置在寒冷的外太空。
2018年11月,中国首枚民营运载火箭“朱雀一号”在发射过程中,同样因三级火箭姿态出现异常湮灭在大气层里。
可以确定的是,坏消息并没有影响后继者继续仰望星空的热情。时至今日,火箭运载、空間科研、导航通讯等越来越多的商业航天项目不断涌现。后进玩家们不断寻找着“上天生意”里的每一个可能性。
资本的表现更加疯狂,据哈工创投对将近50家商业航天企业的统计,2018年,中国共有19家企业获得23亿元以上的投资,卫星星座运营领域8家企业融资总额超4亿元。其中,天仪的B轮融资。就贡献了1.5亿元。
相对于投资者和从业者的热情,潜在客户更关心的是民营航天的安全和稳定性。毕竟,谁都不想因为一次失败的发射,而将自己的产品连同火箭一同付之一炬。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国务院在2015年10月印发了《关于印发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的通知》。这似乎表明,国家开始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卫星研制及系统建设。
所以,趋势可能是,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各个商业航天创业者还有足够的时间试错和迭代。抛开投机者制造的泡沫,商业航天的全部价值都必须建立在航天服务的稳定提供之上。稳定压倒一切,不压倒稳定.注定会被稳定所压倒。
要知道,在这个自带“烧钱”属性的行业,稳定考验的是创业者的综合实力。研发、制造、发射、运营和维护。每个环节的背后都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与精力。
总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行业。马斯克将它视为宏伟的梦想,而中国玩家考量更多的是生意本身。在无数凝视太空的眼神中,有冯仑,也有杨峰和任维佳。以及前仆后继的太空创业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