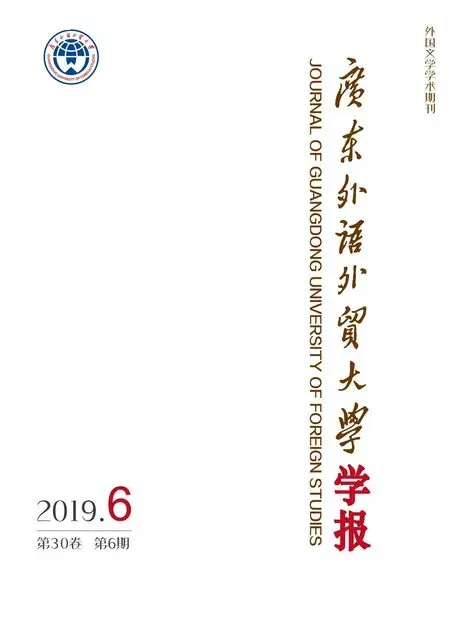彼得·比克瑟叙事作品中的宗教元素分析
姜 丽
一、引言
在《读者·叙述》这部作品中,瑞士作家彼得·比克瑟(Peter Bichsel)(1935-)写道:一个为某部作品而兴奋不已的读者可以很寂寞,可能与之对话的就是文学评论者(Bichsel,1997: 29)。然而相比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作品而言,某一语言的文学评论者,尤其是针对某一位作家的评论者,还是非常之少的。在中国,比克瑟的评论者也会很寂寞,因为他虽然获得大量德国与瑞士文学奖项,却没有引起中国日耳曼学者的公开关注。或许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在以思想深刻见长的德语作家中,比克瑟的作品的确过于简单,简单得令他的一位瑞士读者都不禁觉得自己没有理解他的作品,因为他不相信一位作家会写这么简单的东西,固执地认为必有深意,便反复追问比克瑟。比克瑟坦白地告诉他,自己的作品的确就写了这些内容,但转而又说“正如歌德所言,如果不曾有所感觉,你们也不会追寻。”(Bichsel,1997:50)那个表示不懂的读者或许就是感知到了什么,却无法言明。经过大量阅读和思考,笔者发现:比克瑟用笔描写的平常生活和平常人形象,为自己和读者竖起一面镜子,于无声中打开一扇思考的大门,引导读者通过叙述,让自己的人生拥有意义。
二、比克瑟的创作成就及其对叙事功能的理解
彼得·比克瑟出生在瑞士卢采恩,主要作品都是短小的故事和专栏文章。1964年,比克瑟以一部短篇故事集《布鲁姆夫人其实想认识送奶工》(以下简称《布鲁姆夫人》)(EigentlichmöchteFrauBlumdenMilchmannkennenlernen)赢得四七社成员的一致称赞,1965年获四七社文学奖。这些故事“逻辑紧密,表达精确”(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语言有着“奇妙的乐性”(汉斯·迈耶尔 Hans Mayer),“其结构使得日常生活所具有的多前线阵地很好地得以展示”(瓦尔特·霍勒赫 Walter Höllerer)。此后,比克瑟便被人与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 和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相比,打上“短篇大师”的标签。发表于1969年的第三部叙事作品《儿童故事》(Kindergeschichten)更以其“形式简单却意味深长”的特点而令人难忘。不过,他的其余作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甚至遭遇了批评与否定。他的第二部作品《四季》(DieJahreszeiten,1967)没有继续第一部作品的风格,而是让人不得其解的百余页的长篇,惹起评论界尖利的批评,被称为“文学作坊里的事故”(Reich-Ranicki,1984:36)。第五部故事集《去巴黎》(ZurStadtParis, 1993)更是短的靠近了沉默的边界。第四部作品《秃鹰》(DerBusant, 1985)和后面的《采若宾·哈默和采若宾·哈默》(CherubinHammerundCherubinHammer, 1999)也都没有超越《布鲁姆夫人》和《儿童故事》的成就。1982年,比克瑟在《法兰克福诗学讲座》(FrankfurterPoetik-Vorlesungen)中向世人讲解了自己对叙事的理解。查理特·杜荣凡(Chalit Durongphan)在自己的专著《彼得·比克瑟的叙事诗学与实践》(PoetikundPraxisdesErzählensbeiPeterBichsel,2005)中,通过梳理比克瑟的叙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在其创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一个对叙事的功能有着“乌托邦式(Durongphan, 2005: 110)”见解的比克瑟。1982年1月12日至2月9日,比克瑟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做了五次关于文学的讲座,其间比克瑟向听者阐述了自己对叙事的思考。此外,其专栏作品中也有涉及叙事的内容。因本文侧重于比克瑟叙事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所以主要从与读者相关的视角来看比克瑟对叙事功能的理解,具体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一)叙述能够让人感受时间,抗拒死亡
在《读者·叙事》中,比克瑟讲道:人愿意听故事,也愿意讲故事,故事的内容各种各样,具有教育意义。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会有故事以及人为什么要讲故事。讲故事时,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时间”这个概念,知道我们以及我们的朋友总有生命终结的一天。由此而产生的悲哀无论你是拒绝,还是接受,都是无法战胜的。讲故事就是接受这一悲哀。这悲哀让人成为讲故事的人。没有时间概念或许就不会有故事,没有悲哀倾向的人,也不会读文学。文学的世界是多愁善感的(Bichsel, 1997: 11-12)。在专栏作品集《关于上帝与世界》中,比克瑟写道:“母亲在床边讲的睡前故事是一种对抗绝望的方法,是最后的保护,是人走入黑夜的陪伴。”(Bichsel, 2009: 174)在《对抗死亡的叙述》一文中,比克瑟提到了《一千零一夜》里绝望讲述的桑鲁卓。“只要她的故事在继续,她就可以活着。”(Bichsel, 2009: 81)
(二)叙述能够赋予生命意义,让世界变得清晰
比克瑟认为,“得到塑造,获得形式的,我们都觉得是有意义的”(Bichsel, 1990: 220)。比克瑟相信叙述因为具有赋予意义的潜力,所以是有实用意义的,可以为人提供生命故事的讲述模式。比克瑟言道:“严格来说,没有生活所写的故事。一定要先有故事,然后我们才能认识到这可以是生活写的故事。”(Bichsel, 1990: 219)比克瑟的朋友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有着相似的想法:“我们贪求故事,可是我们是否想过这些故事都是从何而来?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是想象的游戏,图像,真的只是图像,是映像。每个人,即便不是作家,都会创造自己的故事。否则我们无法看到我们的经历模式,我们的经验。”(Frisch, 1965: 9)而人之所以会渴求叙述模式,是因为生活这个庞大的复合体是无法描述的。作家要面对的就是这个不可能的描述任务(Bichsel, 1997: 22-23)。“不能讲述”对比克瑟就来说是“生命质量的损失”,“不是生活不再值得讲述,而是我们缺少讲述的时间和技巧。”(Bichsel, 1997: 91)比克瑟认为,文学“要为平庸之事找到叙述模式。”(Bichsel, 1990: 222)“要把越来越多的事件纳入文学,让他们发现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件都是故事”(Bichsel, 1997: 95),让读者在自己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可以称之为故事的事件。比克瑟说“我觉得文学的意义不在于传递内容,而是坚持叙述”。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模仿的不是现实,而是叙述的情境。“文学的目的不是内容,而是叙述。”(Bichsel, 1997: 8)所谓叙述的形式指的不是文本的特征,而是叙述行为本身。在比克瑟看来:“之所以存在叙述,就是要把讲述展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造出自己的故事。我们便可以默默地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生存。”(Bichsel, 1997: 88)这就是说,作家的讲述是为了教人讲故事,不要忘记叙述。
(三)文学是作者与读者的一种交际
比克瑟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Durongphan, 2005: 84),对他来说:写下的东西总是为一个读者而考虑的。……写东西总是在表达自己,要向外展示什么(Hoven, 1991: 22)。由此看来,写作是一种交际手段,是作者与读者的一种交流。这一说法比较接近接受美学的观点:文本只有在阅读过程中通过与读者的互动才能完成,只有通过这一具体化最终完整出现。一个作者总是要面对不同的选择,即他想或者能写给读者什么,可以理解的程度,是否要留给读者发现的快乐(Bichsel, 1997: 56)。因此,一个理想的读者就是可以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人,可以为之兴奋的人,一个大度宽容的人,而不是用现实生活的真实去衡量判断其价值与意义。在比克瑟看来,文学是人的一种交际形式,对人的生活起着某种作用,因为艺术与生活是相互影响的。在法兰克福诗学讲座中,比克瑟多次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生活模仿艺术的情况要远远多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Bichsel, 1997: 77)
三、比克瑟的文学创作所展示的宗教情怀
杜荣凡认为比克瑟赋予叙事的种种功能都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因而比克瑟心目中的文学是一种理想的文学,一个乌托邦。但在笔者看来,比克瑟之所以会如此看待叙事,强调读者,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虽然比克瑟在专栏文章中表现得很有政治意识,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对宗教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的宗教情怀也有着明显流露,这里我们就以他饱受赞誉的短篇故事为例从三个方面对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元素进行深入分析。
(一)叙事动机:重归神性情境
从前文提到的比克瑟对叙述乃至文学的功能理解来看, 叙述对人有着非凡的意义。杜荣凡称之为的乌托邦的文学功能,在笔者看来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对文学的宗教性认知。比克瑟认为讲述或者故事的一切都是源于叙述的传统(Bichsel, 1997: 94)。“讲故事不同于说话——讲故事是一种沉默的形式,讲故事是通往寂静的路。”(Bichsel, 2009: 98)叙述是在重复一种情境,叙事的情境。人要生活在故事里,才有意义。那么,为什么讲故事如此重要?因为讲故事让人重复最初的叙事情境。美国心理学家尤利安·延斯(Julian Jaynes)在《意识的起源》(UrsprungdesBewusstseins) 一书中明确写道:“我开门见山地说出我的观点:最早的诗人是神。”(Jaynes, 1994: 440)而我们最早的诗歌就是荷马史诗,口头流传的叙事性诗歌。虽然今天的德语作家不一定都读过荷马史诗,但是荷马史诗影响了西方一代代作家,叙事这一情境也在一代代传承。
而比克瑟所说的由通过叙述而达及的“寂静”更是与永恒、上帝连在一起的沉默无声。用比克瑟的说法,人讲故事就是在回忆,而回忆就是走向内心深层的过去世界:曾经走过的路,自己的青春与童年。如果考虑到岁月更迭带来的代代回忆,这一回忆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最早开始的叙述。叙述与倾听让人停下劳作,忘却烦恼,走出自我的世界,进入历史之流。这一生命的联结让人汇入生命的洪流,有了自己的根。歌德在《遗嘱》中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现在马上转向你的内心,∕你会在那里找到中心,∕任何高贵的人都不会不信。”(Eibl, 1988: 685)
当一个人成为叙述的主角,与一个愿意倾听的人重复古往今来的叙述情境,叙述者和倾听者就进入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交流模式,叙述者感受着受人关注的美好,倾听着也随着对方的叙述走出了自己的生活,进入另一个真实的世界,二者在这一刻融为给予与获得所构成的和谐的一体,达成交流的喜悦。如果能够抓住倾听者的心,讲述者就有了吸引人的魔力与光环。在比克瑟的一篇小故事《只言真相》(UndschonnurdieWahrheit)(Bichsel, 1993: 55-58)里,一个女招待萝希反复尝试给酒馆的客人讲故事,却总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当她再次要讲故事时,听众们依然聚拢来听,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怀有期待:对敲击灵魂的期待,对忘我之境的期待。
于是,按照比克瑟的想法:我们必须要讲述,因为人要学习叙述,叙述让人的生命有了意义。这意义在笔者看来便是神性情境的重复,叙述的情境将我们和原初连在一起。这一点,比克瑟作为实践者虽然有所体验,却并没有明确说出。当人问到他为什么写作时,比克瑟的回答是:“‘您为什么写作?’并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而是一个可能完全关乎存在的核心问题。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大概就放弃写作了。”(Bichsel, 2003: 20)在专栏文章《我毫无想法》(Mirfälltnichtsein)中,比克瑟一方面说自己写作是为了不让主编陷入困境,是一种为了交差而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说“写专栏就是写作本身,就是和字母打交道。”而这种看似毫无必要的事情对他来说恰恰是专栏写作最美好的地方。更为有趣的是,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写作标准:如果终稿就是他动手时想到的,他就会把它扔到废纸篓里。他需要的是意外之作(Bichsel, 2003: 21)。前一个理由是他写作的外在动力,把写作视为与字母的交流则将写作的目的拉回到语言本身,而语言是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字母的摆布便是异彩纷呈的思想与文化。不同的开头便会引出不同的思绪之路,唤醒不同的情感,成就不同的故事。如果主编不对终点做出要求,作者所期待的最终意外也就不是件难事了。维特根斯坦有句话非常耐人寻味:我的确是用羽毛笔在思考,我的头脑常常不知道我的手在写什么(Wittgenstein, 1977: 39)。或许,比克瑟就这样不着痕迹地道出了写作的神奇。
此外,对字母的迷恋、词语的热爱也是一种对神性的热爱。高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就曾在另一首诗《创世纪》(Schöpfung,1929)写道:词语是密码,包含着来自天空的秘密:一个词,一个我,一根绒毛,一丛火,/ 一点火把的蓝光, 一道流星。从这两行诗里关于词语的隐喻中我们可以看出,词语是永恒与短暂的结合体,虽然渺小,却显现在浩瀚的背景下,源出于无际的神秘。“词语……一方面是精神,另一方面也具有大自然的事物的本质和两面性。”(Benn, 2003: 1075)这些隐喻让人看到,词语虽然是光,却倏忽而逝。根据“光是知”这一概念隐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词语”:词语虽然能够给人带来知识,这知识不是永恒的真理,它是永恒与短暂的结合体。由此看来,独角犀牛就像不断看到流星的人一样,无休无止地思考,却一世不得真知。想想我们突然看到黑洞照片的欣喜若狂,我们或许会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多么巨大的无知境地。
(二)叙事方式:让读者参与神性创造
比克瑟的故事以短小简单著称,在《去巴黎》这部故事集里甚至发展为几近沉默的简短。这本故事集一百一十五页,包含四十八个故事,其中最长的一个十四页半。在这四十八个故事中有三十四个篇幅不到一页,其中又有二十四个连半页的长度都没有。有些极短的故事只有两三个句子,譬如《爱情》:“她帮了一个自杀的人好几年。现在,她没那么大力气了,便坐下来,捂住了耳朵。”
那么比克瑟是如何用这样少的词语来完成一个故事的呢?用他的说法就是充分运用固定的想象模式(Klischee),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典型模式(Stereotyp)。受具象诗的影响,比克瑟擅于运用固定模式唤起不同读者对同一个词语的联想。具象诗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种欧洲诗风,其概念源于造型艺术,所谓“具体”最初指的一幅画的构成元素,即点、线、面和颜色。所有具体艺术流派的一个共性就是分离出各种艺术的构成元素,将对这些元素的展示视为一种独特的真实。具象诗的艺术对象便是词语,其中的一个个概念并不指向诗外的某一具体实物。用具象艺术理论家海恩茨·迦普迈尔(Heinz Gappmayr)的话来说:每个概念都是一个理念,包括无数可能的物体,譬如“房子”这一概念就可以指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房子。我们要借助特别的标志来辨认出一个概念所指的物体(Durongphan, 2005: 54)。比克瑟不仅像具象诗人那样钟爱词语,钟爱词语创立的真实,也在创作中充分运用了可以调动无尽具体想象的概念。譬如:他笔下的故事通常发生在酒馆里,每个地方的人都可能有自己对酒馆的想象,而说到流浪汉,读者也可以调动自己头脑中流浪汉的形象。读者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在作者的引导下在接收中配合完成了一个故事的创作。关于拼命拉住缺少生命力量的爱人的故事,世间也已有许多。如果一个人把爱情视为救命稻草,拼命抓住自己的伴侣,而其伴侣也极尽所能相帮,爱情变成了伴侣的重负,令其身心俱疲。当他或她疲惫不堪时,便会选择自救,像小说中的她一样捂住耳朵。小说到此为止。读者会知道:捂住耳朵就意味着不想再听任何呼救的声音,那是无奈地放弃,那是面对现实,开始自救的信号。只一个捂耳朵的动作,真正的读者就会想到这个人有多累,有多痛。此处无须多言。比克瑟的故事有了诗的浓缩,几近沉默。就这样,寥寥几笔,比克瑟就让一个故事在一个能够与之交流的读者心中开始,读者也在这想象、反思与回忆中拥有了叙述者的身份。比克瑟没有事无巨细的描摹,便是让有能力的读者从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创造者,而“创造”这个词则把人和上帝连在了一起。当比克瑟心目中理想的读者在阅读比克瑟的故事过程中完成自己的创作,也便有了创造者的身份。
(三)叙事对象:让小人物的生命具有神性
比克瑟的故事主角基本都是无名的人,极为普通的人。他认为,“不是生活不再值得讲述,而是我们缺少讲述的时间和技巧。”(Bichsel, 1997: 91)比克瑟认为,文学“要为平庸之事找到叙述模式。”(Bichsel, 1990: 222)“要把越来越多的事件纳入文学,让他们发现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件都是故事”(Bichsel, 1997: 95),让读者在自己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可以称之为故事的事件。比克瑟说“我觉得文学的意义不在于传递内容,而是坚持叙述”。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模仿的不是现实,而是叙述的情境。所谓叙述的形式指的不是文本的特征,而是叙述行为本身。在比克瑟看来:“之所以存在叙述,就是要把讲述展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造出自己的故事。我们便可以默默地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生存。”(Bichsel, 1997: 88)这就是说:作家的讲述是为了教人讲故事,不忘记叙述。当比克瑟把社会中的无名小人物纳入故事时,也就给了他们讲故事的模式,给自己生命以意义的方式,与此同时也赋予更多普通人参与创作,发现自身神性的机会,从而让其平凡的生命具有神圣的意义。
1. 比克瑟作品中不同类型的小人物
从比克瑟所捕捉的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物来看,对书里书外的一个个小人物,比克瑟都饱含怜悯与宽容,而这都源于一份大爱。他让人看到小人物的不幸,看到得不到社会承认的人如何努力让自己的生命拥有一个意义。《布鲁姆夫人》一书有二十一个故事。德国最知名的文学评论家莱希-拉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给出的评价是:“比克瑟在这本书里写的都是小人物的日常之事,他描述平淡无奇的场景,回忆种种情形,讲述微不足道的事,道出几乎无法捕捉的情绪,展示各种反应。”(Reich-Ranicki, 1967: 91)而蕾古拉·迈耶尔(Regula A. Meier)则写道:“比克瑟所写的是数以万计的普通人,没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去向何方。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没有自己的传记。只有少数几个人物有名字,或者说是被赋予了一个名字,但是毫不引人注意,很快也就忘了”(Meier, 1974: 47)。这些无名者我们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即孤独的人;像孩子一样思考,不畏嘲笑努力践行自己想法的人;默默生活在渴望中的人。
第一类人:孤独的人。这些人所体现的最大不幸便是现代人的通病:孤独。比克瑟曾说:有人对你讲他的故事,是一种亲近的表现,一种交际的需求,不管那个故事多么简单。而听者的故事则是一种回应,一种宽容、相助,一种爱的表示。但是,现代的生活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没有了回应的时间和心情。在《布鲁姆夫人》的故事中,孤独生活的布鲁姆夫人通过写纸条的方式与送奶工交流,但是送奶工没有给她回复,因为他觉得那样就是一种通信了。或许对他来说通信就意味着缩短两颗心的距离,而这份亲近他无法,也不想给一个陌生的服务对象。
在另一个故事里,一个女人收到一封来自海边的信,刚从信箱里拿出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阅读,看完才打开家门。而这封信的内容和无数从海边写来的信一样简单:……。作者在写完看信的女人之后,就转而去写那个发出信的男人了。虽然应该是男人写信在前,女人看信在后,但是作者都用了现在发生的时间来描述。查理特对此的看法是:……。在笔者看来,这种手法是在描述两个可以无限复制的人:写信发出问候,远方急切地看信。他们的故事超越时空,成为两个典型的为交际而叙述、倾听的人物,是爱打破了时空的壁垒,心的隔阂,而这爱本是可以放大,减少更多孤独的。
第二类人:像孩子一样思考,不畏嘲笑努力践行自己想法的人。(1)一个人固执地说自己有个叔叔叫尤斗科(Jodok),虽然家人不予相信,他却自得其乐,不断用无意义的语言游戏说着关于尤斗科的故事。(2)一个人要亲自丈量世界,证明地球是圆的,其方式是开着车,载着船,从自己家门前开始,笔直向前,直到走回到自己的家。(3)一个男人按照自己的体系重新命名了周围的事物,结果却导致人们再也无法与之沟通。(4)一个男人把自己关在没有光线、拔掉电话的房间里,想要忘记一切却最终宣告失败。(5)一个男人能够熟练地背出列车时刻表,此后又去数台阶。这些人在安排自己时间的同时,给自己的生命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任务,看上去只有闲得极其无聊的人的突发奇想、异想天开,对人类,对社会都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但换个视角来看,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充满勇气与好奇,他们敢于挑战社会的固有观念,敢于不同,能够坦然面对周围的不解和嘲笑,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去给自己的生命一个独特的意义。毕竟,今天的文明时代虽然不再有远古时期成就英雄史诗的环境,但对不凡的崇拜之心依然藏在人的心底。
第三类:默默生活在渴望中的人。《去巴黎》故事集中有一篇名为《渴望》的故事:在埃门塔尔丘陵地区的朗瑙曾有一家商店。店名是:去巴黎。或许这个渴望就是店主的,现在他或许就生活在巴黎。在比克瑟创作的另一个名为《圣萨尔瓦多》的故事里,比克瑟写了一个男人或许永远不会实现的渴望。作者用极短的篇幅描述了一个名叫保尔的男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当妻子去教堂参加合唱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家里打开新买的钢笔,像每一个试用新钢笔的人一样写几个字,画几道波浪线。突然他写下一句话:我要去圣萨尔瓦多,这里好冷。继而他思考了一下,如果自己现在马上动身离开,妻子回来后会是什么表情,什么动作,会说什么话。从他的想象来看,他的离去对妻子不会是什么重大打击,只是个慢慢适应的状态。没有痛哭流涕,没有悲痛欲绝,也没有发疯的寻觅……两个人的感情在保尔看来就是单纯的相伴,也就是没了什么热情的、不知所向的继续。接下来无所事事的他收拾桌面,看钢笔使用说明书。然后慢慢等到妻子熟悉的开门声,进门后必有的一系列动作。这看似简单的情节告诉我们,他已经不知多少次观察妻子的行动,他们的距离亦是显而易见。他没有让自己忙碌的责任与义务,没有兴趣和爱好,没有暖心的陪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自然可以很多,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考虑,也可以通过推想给自己一个警告。就在这无数的推测中,读者再次悄然扮演了叙述者的角色。
2. 小人物的无名与普适性
从上面三类无名人物的生活片段来看,比克瑟笔下或滑稽荒唐或简单平凡的小人物的生活,只要遇到理想的读者,就可以起到不凡的作用。只要读者能够耐下心来,慢慢地提问,慢慢地寻找答案,就会慢慢靠近作者的内心,成为比克瑟所期待的理想读者。此外,人物的无名性造就了比克瑟故事的普适性,他们用平凡人的寻常场景接纳每一个想走进这一世界的读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物虽然没有名姓,却因为比克瑟的文字有了生命,成为一个个给人启迪、让人难忘的人。对比克瑟来说,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不仅有自己的真实性,而且是可以交流的对象。他的短篇故事集《去巴黎》就是献给两个小说人物妮娜·阿尔麦耶和佩罗尔先生的。妮娜是著名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第一部长篇小说《奥尔迈耶的愚蠢》(Almayer’sFolly)中老奥尔迈耶的女儿,佩罗尔则是他晚期作品《海盗》(TheRover, 1923)中的主人公(Durongphan, 2005: 197)。康拉德是比克瑟最敬慕的作家之一。虽然他们的作品的篇幅相距甚远,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通过文字传承叙述,传授叙事方式,让故事在各个时代继续,在各种不同的人心中响起。
四、结论
与读者共同思考平凡人的追求与渴望,无奈与痛苦,让无声的读者群体在阅读中成为创造者,反思者,继而成为叙述者,让平凡的生命因为叙述而获得意义,步入神性,这便是比克瑟对世间无名者充满宗教情怀的爱。
“讲述,是一种声音。阅读,这是听取声音。阅读无法理解的、神圣的东西,我后来失去了多少,因为我以为一定要读懂,也能够读懂,以为自己懂了。”(Bichsel, 2009: 174)这是比克瑟在《关于上帝与世界》中写下的一段话,我想,比克瑟看似简单的故事我们或许还要一次次读起。不仅是因为要慢慢读懂比克瑟,也是因为叙述和永恒的关联,正如比克瑟讲道的那样:“叙述有时也是沉默。叙述最终会通往沉默。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从妈妈那里学到了这个,妈妈会在我们睡前讲故事,在我们进入沉默之前。”(Bichsel, 2009: 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