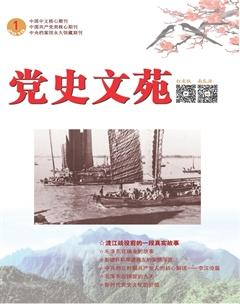渡江战役前的一段真实故事
张家康
1954和197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两次来到安徽省繁昌县,拍摄黑白和彩色故事片《渡江侦察记》。军事顾问是当年的参战指挥员慕思荣和高锦堂。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渡江战役发起前,华野第二十七军先遣渡江大队强渡长江天险,活跃在江南敌占区,并策应大军顺利过江。电影只是这段惊心动魄战斗经历的艺术再现,毕竟受影片时长限制,不可能是战斗经历的全记录。先遣渡江大队在江南的15天,是一段身处龙潭虎穴、一发千钧的惊险战斗经历。
军部批准先遣大队渡江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第二十七军组建一支先遣渡江大队,与江南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以执行侦察任务,策应大军过江。第二十七军立即在军侦察营基础上组建先遣渡江大队,由侦察营第一、第二连和第三连六○炮班,加上第七十九师、第八十一师的3个侦察班组成,总计300余人。大队长由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参谋长亚冰担任,副大队长由军侦察科科长慕思荣担任。大队成立了临时党委,亚冰和慕思荣为正副书记,军侦察营教导员车仁顺、副营长刘浩生、第二连指导员王德清为党委委员。这支队伍除亚冰是皖南人、新四军老战士外,多是北方人、老八路。他们刚从淮海战役下火线,就接受了这项新任务,慕思荣和刘浩生回忆: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第二十七军侦察营在安徽省宿县东北的灰古集休整。春节刚过,就受领了渡江战役侦察任务。2月上旬,我们从驻地出发,经两天徒步行军到达蚌埠,休息一天。第二天换乘火车运行,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第一次乘火车,干部战士高兴极了。多数人还是第一次乘坐火车,虽然乘坐的是拉煤用的车……蚌埠至合肥这么一段不长的距离,运行了近一夜才到达。我们在合肥休息一天,又繼续徒步走了两天才到达无为县东南沿江一线。
这支队伍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不谙水性,见水即怕,可他们偏要打破“木船不能渡江”的陈旧论调,使解放军成建制的过江成为现实,这无疑是对这些北方战士的挑战。经过新式整军运动,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指战员们,阶级觉悟和战斗力大大提高,在勇士们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战士们以前多在平原和丘陵山区作战,南方纵横交错的水网和稻田,对他们是陌生的,而要由“旱鸭子”变成“水鸭子”,没有一番艰苦训练是不行的,他们抓紧时间在内河学习划船、操舟、掌舵、撑篙、泅渡、救护等本领。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初识水性,掌握了乘船坐船的要领,而且还会撑篙掌舵、划船操舟。
为检验渡江训练成效,也为侦察江南敌情,3月21日和23日,大队先后派出第二连第一排第三班和第二排第四、第六班偷渡过江,捕获俘虏,侦察敌情。两次偷渡捕虏都获得成功,先后俘敌10名,缴获机关枪1挺、步枪8支。更重要的是,初步了解了江南的敌情,这就是“敌88军指挥所于繁昌,144师师部于桃冲,其所辖之445、446、447三个团,分守油坊嘴、黑沙洲、旧县(今新港)、荻港、太平街、太阳洲江防”。敌人所筑工事薄弱,兵力呈带状分布且间隔很长,30多里的江防只有一个师,沿江只布了一道防线,只要突破这道防线,就可以长驱直入,向纵深发展。
充足的船只和水手是顺利渡江的先决条件,军部想方设法为他们挑选了三十几只小船,每只载重在两吨左右,并挑选出最好的水手。在物资准备上完全依照战时需要,尽其所能,给予配备,比如浮水竹筒、木筏、船橹、船桨、船杆。为防止船漏,准备了补漏用的棉花和黄泥。为避免木船行进中击出水声,准备了稻草、绳子,将其铺挂在船头。捆绑木桨的小皮带也事先用油浸透,以防摇桨时发出大的声音。
船工是先遣渡江关键帮手,要使船工乐意为渡江效力,既要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更要相应地采取经济措施,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先遣渡江大队协同当地党政机关,研究制定了船工家属生活困难补助办法及船工伤亡优抚条例和船只损坏赔偿规定等。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已是一目了然,船工们并没有多大思想顾虑,眼下家属子女的生活有了保障,他们都愿意把部队送过江去。
军部在武器装备上也尽量给予保证。“增加弹药基数,步枪每支一百五十发(子弹),机枪每挺一千发(子弹),冲锋枪二百五十发(子弹),每班带小包炸药,及六○炮弹两枚,火箭筒两个(每连一个),六○炮每连一门,自带四天给养。干部携带银圆一部(分),并有电台一部及地图等其他必需之用品。此外个人之笨重物品及可能泄密之文件全部放在江北岸。译电员准备汽油洋火,以便万一情况下焚毁密本(密电码)。”
根据多日的观察,先遣大队知道江南的敌巡艇多在夜晚8时前活动,于是决定在夜晚9时过江,登陆点选择在对岸繁昌荻港十里场至夹江口20余里的地方。整个大队分为两队:一队由大队长亚冰率领,由大队机关和第二连组成,分四小路成一字形,以十里场、皇公庙段为登陆点;二队由副大队长慕思荣率领,分三路成一字形,以北埂王至夹江口段为登陆点。过江的原则是力争偷渡,准备强渡。登岸后分别迅速穿插到戴公山和狮子山隐蔽。
军部批准了渡江的计划。4月4日,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副参谋长李元、政治部主任仲曦东来到先遣渡江大队驻地,进行战前动员。聂凤智宣布作战命令,他说:“你们是渡江的先锋,军委、三野、兵团首长和广大指战员都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战士们握紧拳头高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渡江立大功,江南比英雄!”亚冰代表全大队指战员向军首长表决心说:“我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决排除万难渡过长江,完成任务。”
狮子山上遇敌军
电影《渡江侦察记》将渡江侦察的建制由营缩小为连,而且渡江指战员的着装都是解放军制服,显然这是艺术创作与观赏的需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深入敌后的解放军必须进行伪装。据亚冰回忆:“部队还进行化装,三分之二改穿国民党士兵服装,三分之一穿便装。”4月6日,军部下达了渡江的命令。这天是农历三月初九,那皎白的月亮高悬在天上,江面波光潋滟,真是“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晚9时半,亚冰等率一队,分乘8只木船,以四路成一字形,從无为县石板洲叶家墩东南侧的鲤鱼套启渡,目标繁昌县的十里场、皇公庙。月色下,敌人的碉堡、铁丝网越来越近。就在即将靠岸的时刻,突然响起了“吧吧”枪声,敌人发现了渡江的船只,偷渡也随之变为强渡。亚冰在《先遣渡江的日日夜夜》中说:
我马上意识到,敌哨兵已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如不急速登岸,就有人船被击沉江中的危险。我命令:“全速前进,强行登陆!”战士们迅速拿起备用的木桨和铁锹,全力划水,飞速前进。这时,枪炮声已响成一片,炮弹爆炸激起的水柱像山一样高,落下来能把人打歪,小船在风浪中颠簸前进。在纷飞的弹雨中,战士们用身体掩护船工,对船工说:“子弹打不着你,只管用劲划!”船工们很受感动,划得更快。
离岸越来越近,第一排第三班所乘的木船却被埋设在江中的木桩卡住。三班是前卫,直接关系到后续船只的行动。三班长张云鹏翻身跃入江中,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来!”大家紧随其后跳入江中,欲泅渡过江。这里水流湍急,一个漩涡连着一个漩涡,他们七人中除王长仲、宋希文,全都被湍流和漩涡吞没。
排长范玉山急中生智,他伸直了胳臂将船篙尖钩钩住近岸的木桩,战士们顺着篙杆,一个个地攀缘上岸。登岸后,他们在繁昌荻港大成圩会合,清查完各班人数,重新恢复建制,把负重伤和牺牲的同志搬至船上,让船工将他们送回北岸。随后,部队又马不停蹄,按照预定的方案,向铜陵境内的狮子山穿插。次日清晨,他们登上了狮子山。大队长亚冰立即发报给第二十七军军部,报告已顺利过江,并占领了狮子山。就在此时,他发现东面山头上驻有敌兵,此地不能久留,亚冰立即命令第二连连长高锦堂、副指导员徐万礼和王春生在顶峰警戒,负责牵制麻痹敌人,一定要和敌人纠缠至黄昏,以掩护一队继续向南穿插,到南陵塌里牧村集中。这场与敌斗智斗勇的经历,几十年后,高锦堂说起来还是那么的扣人心弦,他说:
经过细致的观察,我们发现敌人穿的是灰军装,肯定不是国民党的主力军,而是自卫团的杂牌军。而我们穿的是黄军服,响当当的“国军主力”。心中有了数,我们便大胆地与敌人周旋。敌人向我们喊叫:“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下来和我们联系。”徐万礼指示王春生同志回他们的话。王春生头戴“国军”大盖帽,身穿军官服,威武地站起身来。这时一颗子弹从他耳边擦过,王春生端起美式卡宾枪向敌群扫了一梭子,大声骂道:“奶奶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随便向老子开枪?如果你们打伤我们一个人我们非消灭你们不可。我命令你们派人上来联系……”
敌人看到答话的是国民党军官打扮,说话口气很大,被唬住了,但还不断地朝天放冷枪壮胆。过了好一会,一个敌军官模样的人,伸长脖子在山下喊了起来:“喂!别误会,我们是繁昌自卫团。贵军是哪一部分?”王春生傲慢地答道:“老子是88军149师搜索队的,昨晚在江边追击共军到此。你们他妈的怎么搞的,把共军给放跑了。”这家伙委屈地说:“我们也是昨晚奉命来此追击共军的,请你们派人下来联系。”王春生骂道:“你混蛋,你们上来和我们联系,你们地方部队要听我们长官指挥,现在你们派一个人上来,我们派一个人下来。”
几句简单的回话,把敌人懵住,他们不打枪了,但还不敢上来与我们联系。徐万礼乘机指示王春生:“你下去,我们掩护你。你和敌人保持五六十米距离。”王春生吸着烟,边走边骂:“奶奶的!自己人联系一下都畏缩不前,还能剿匪?你们自卫团都他妈的是草包!”敌人不得已才派一个人上山联系。双方相距五十多米远站住,开始对话。
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方有意拖延时间,一方仍是将信将疑,一直挨到太阳下了山,山上山下都被黑幕所笼罩,高锦堂估计亚冰他们早已撤至安全地带,这才悄无声息地下了山。没走多远,后面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枪声,我们的战士幽默地说:“不用放鞭炮送行!”
慕思荣率领的二队,处在长江上游,当他们听得下游传来密集枪声时,慕思荣立即命令起渡,时为晚上10时左右。当船行至江心时,敌人发现目标,立即用轻重武器予以射击。他们奋力划船,实行强渡,船速极快,“嗖嗖”飞来的子弹,多数落在船尾。强渡中,五班的船只因迷失航向,而被敌弹打中,多名同志光荣牺牲。
到达铜陵迪龙冲时,已是7日凌晨。慕思荣安排干部战士轮换值班站岗,其他人员就地休息待命,并封锁了村子,人员只准进不准出。同时,找来当地的村长和保长,让他们收养一名伤员,并给足了银圆和药品,在大军过江时交给部队,还答应为他们向新建立的人民政府报功。下午5时左右,亚冰派人送来信,要二队向南陵县塌里牧村靠拢。晚7时,他们从迪龙冲出发,于次日凌晨到达塌里牧村,两支队伍又会合成一支队伍。
向北纵深穿插侦察
在塌里牧村,亚冰就部队的位置、状态和下步行动,给军部发了一份长达1000字的电文,为防止敌军无线电侦听,电文分两次拍发。当晚,他们又向铜陵、南陵间的张家山进军,于8日晚到达张家山。部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人地生疏和粮食短缺,如果再不与地方党取得联系,这么一支300余人的队伍,在江南很难立足。在江北组建时,就已经在中共无为县委的配合支持下,找了近10名向导,并把他们编为宣传组、借粮组和联络组。联络组专门负责与江南的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络接头。
10日一大早,亚冰就找来联络组的何道纯,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找到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同时派了1名参谋和3名侦察员随同行动,并规定会合地是南陵县戴公山老庙。何道纯是无为县姚沟区中队排长,家住南陵,来无为前在南陵县工山区当过民兵。他们一行五人找了两处地下联络站,都没能接上关系。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地下交通员罗玉英,从她的口中得知,江南形势十分险恶,国民党实行“砍山并村”,一家通“共”五户连罪的手段,有些人叛变了,更多的人隐蔽起来,想找到自己的同志十分困难。就在跟着罗玉英进山的过程中,何道纯意外地看到正在田里种地的叶显金,以前他们曾在一起打过游击。何道纯回忆说:
我正准备上前打招呼,他却溜上田埂,隐到家里去了。我随后跟去。他装作不认识,带理不理。我一再说明情况,并把手枪交给他(因罗玉英说过叶显金未暴露,是我们自己人,所以我才敢这样做),他这样半信半疑地给我们带路。出门后,叶显金告诉我,游击队就在南陵县板石岭的俞冲。
——搜救转移400多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