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华贸易立场的转变与应对
陈浩
经过2018年的曲折,中美正重新坐下来讨论贸易摩擦和解决之道。外界期待双方能达成新的协议。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贸易引起的收入分配效应逐渐累积,中美基于前期共识而达成的贸易关系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同时,日美贸易摩擦尽管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但其发生、发展、消退的变化规律值得借鉴。因此,认清美国对中美贸易态度的转变,吸取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正确处理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挑战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立场的重大变化
(一)从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是双赢转向零和
一是中美贸易是零和游戏,而非双赢。从传统的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来看,无论生产效率高低和资源禀赋状况,贸易双方都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这是二战后各种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迅猛发展,也是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甚至认为即使中国不对美国开放,美国也可以对中国开放的主要原因。
但目前美方的态度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自由贸易完全有可能是零和游戏,而非双赢,因为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的前提条件已经丧失。当年,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要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只存在商品的流动,而且规模报酬不变。但在全球化之下,除了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都可以跨境流动。两方做生意,如果做到连家都搬过来了,那搬走的一方还有什么收益可言。
同时,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外部经济愈发明显,而这完全可能给贸易的进口一方带来净福利损失。美国认为,在对等条件下,其能以比中国更低的潜在成本生产不少产品,并在中美贸易中成为这些产品的出口方;但由于中国实施一系列重商主义行为(如补贴、汇率操纵等),使中国能够在这些行业建立起大规模生产,获得规模经济,从而以比美国更低的价格生產这些产品,并成为中美贸易中的出口方。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就不是双赢,而是受损方。
二是跨国公司难以代表美国的立场和利益。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快速发展。但美国等认为,这些跨国公司名义上是美国的,但实际上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
这是因为:跨国公司代表的是企业自身的利益,而这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跨国公司在中国有着庞大的分支机构和雇员,当地政府要求其致力于帮助地方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把研发、生产、销售等转移到中国,使美国丧失了数万亿美元的产出和数百万的工作机会;跨国公司的管理者成为中国的说客,影响美国政府制定出对中国更有利的贸易政策等。
三是无法同化中国。美国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初衷之一是通过扩大贸易和交往,既能使美国获益,也能使中国变富,财富能创造资本主义,这样中国会往美方预期的民主、自由方向发展,也就不会有冷战。但现实是美国的预期完全落空了。此外,比较优势等带来的贸易利益是长期的,短期看效果不一定明显。这也导致美国无法充分认识到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甚至成为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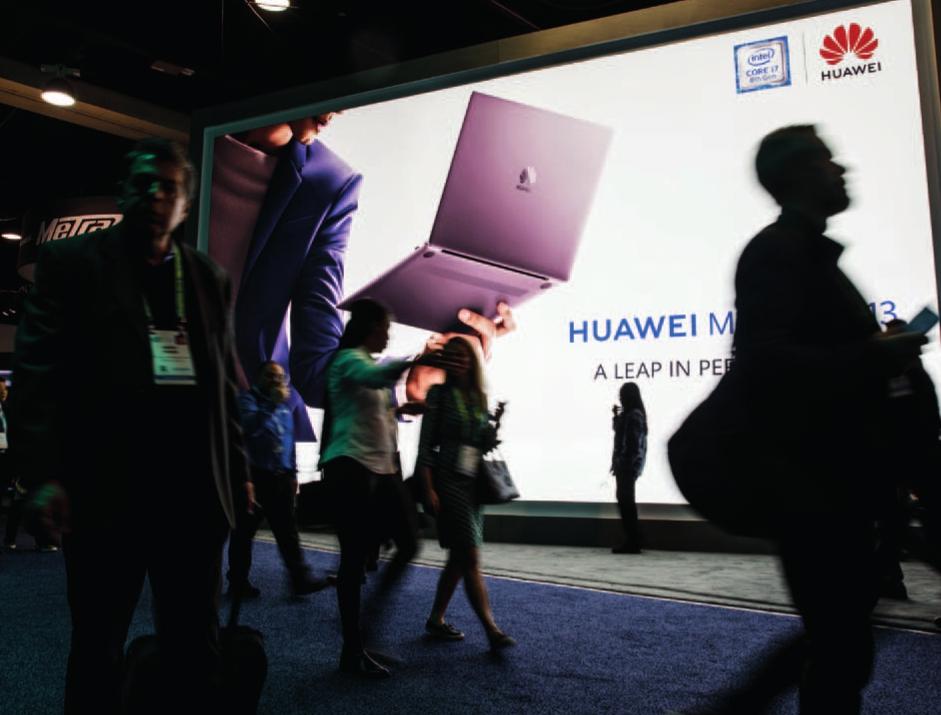
(二)从关注精英阶层转向更多关心中下阶层收入增长停滞
一是中下阶层收入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美国的主要关切。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让支持政客的精英们变得富有,却给百万工人带来了灾难;美国中下阶层收入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曼昆被罢课、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事件都表明,收入不平等的矛盾在逐步积累。最终,代表铁锈区工人和中下阶层的特朗普战胜代表传统精英的希拉里而当选美国总统。
二是美方认为中美贸易是导致美国收入增长停滞和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赫克歇尔-俄林的贸易理论显示,国际贸易将产生收入分配效应:一个国家相对充裕资源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益,稀缺资源所有者因贸易而受损。就中美两国来说,美国资本更充裕,工人相对缺乏,中国则相反。这意味着中美贸易使得美国的资本家获益,工人受损。对工人来说,美国的高技术工人较充裕,低技术工人更稀缺,因此,中美贸易会提高美国高技术工人的工资,而低技术工人受损。
三是美国的政策重点已经开始从精英政治转向更多关注中下阶层。随着美国主要关切的变化,美国的政策重点开始从国际转向国内,从顾全大局转向美国优先;在国内从主要考虑华尔街、精英阶层的利益,转向更多关注工人和中下阶层的诉求,从注重增长和效率,转向更多关注公平、增加中下阶层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三)从尊重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和国际分工转向鼓励制造业回归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理论,并接受了由此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因此对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和由此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近些年来,美国愈发认为强大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维系其国力的根本,完全依赖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将无法保持霸权地位。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意识到即便拥有绝对的货币霸权和超级的金融能力,如果任由制造业不断衰落,产业空心化蔓延,同样逃不过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表明,普通民众无法接受制造业衰败和工资收入远远低于金融业的事实。
因此,近些年美国提出“再工业化”。其手段除了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维持较低的融资成本外,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提高进口关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这样维系其夕阳产业,类似于刚开始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保护其幼稚产业。
(四)从纵容消费、支持强势美元转向扩大投资、倾向弱势美元
二战后,美国有1500万退役军人需要安置,而其他国家当时很穷,靠出口拉动不现实,因此美国出台军人安置等法案,转而依靠消费拉动。这种鼓励消费的做法在当时是对的,但后来一直延续并固化了利益集团,导致美国的消费率从上世纪50年代的58%,增加到现在的70%多,而储蓄率偏低。这不仅是导致美对华巨额逆差和本轮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也严重拖累了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与纵容消费逻辑一致的是以往美国政府大多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认为强势美元对美国利大于弊。因为只要其他国家接受美元,美国就可以印美钞,就可以换东西,也不用担心赤字(无论是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
近年来,美国愈发认识到过度消费和强势美元的危害,因为:一是这样使中、日等国能够顺利让本国货币贬值,压低其出口价格,获得对美国同类商品的价格优势,从而挤占市场,削弱美国的制造业;二是强势美元使得美国人变得不负责任。滥发货币、过度支出,短期看是占了便宜,长期看将入不敷出,最终使美元和美国丧失主导地位。因此,近些年来美国政府并未刻意维持美元的强势,而是努力提高储蓄率,扩大招商引资。
(五)从消极对待中国的新重商主义行为转向积极对抗
美国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新重商主义行为。包括:制定复杂的产业政策;遵循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操纵人民币汇率,使其低估以降低出口价格从而鼓励出口;大量补贴,有选择性地大量出口退税,促使企业将生产转向政府想要鼓励的特定商品;大量实施鼓励在中国开发新产品的政府项目;违反签订的贸易协议,从多方面作弊……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新重商主义行为大多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包括允许中国加入WTO等。
对于中国的新重商主义行为和美国政府的消极反应,特朗普认为这导致了美对华巨额逆差,美国GDP降低了数万亿美元,流失了数百万工作机会等。为此,特朗普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是配套的,而且大多得到了兑现。比如:重新谈判贸易协定(NAFTA)、实施高关税等,压迫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减少美国巨额逆差;减税、扩大招商引资,吸引外国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制造业回归;退出TPP、巴黎协定等,减轻美国的国际义务,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修建边境墙、颁布禁穆令、限制移民,维护本国公民利益等等。
(六)从防范中国转向全面遏制
一是对待此次中美经贸摩擦,美国朝野态度较为一致,甚至跨国公司等受损群体愿意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这表明特朗普制造经贸摩擦不仅有短期选举和连任的需要,而且还有修昔底德陷阱的因素。
二是美国以知识产权为借口,并不完全是出于经济角度,而是还有长期遏制中国的需要。因为特朗普多次指责中国的补贴、汇率操纵和作弊,造成了美国数万亿美元的GDP损失,而“偷走”的知识产权数量在几十亿美元。并且,从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已有的加征关税科目看,许多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项目,而这些科目的贸易量并不大。
三是打击中国的供应链能力,削弱其长期竞争力。美国认为,中国目前的要素价格优势已不存在,主要的优势是完整产业链带来的快速反应能力。如果没有这些,中国不断攀升的土地、运输、劳动力成本,不能自给的资源现状、庞大的人口压力和沉重的企业税负将导致中国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因此,特朗普要打击中国的国家项目发展模式,打击中国企业的出口,逼迫产品供应链转移,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七)从注重多边贸易体制转向双边协定
一直以来,美国非常注重通过GATT和WTO这样的多边贸易体制来维护经济利益、推动世界贸易。但近年来美国愈发认为像WTO、TPP这样的大规模国际贸易协定,会把美国绑起来、拖下水;会把美国的谈判优势送给一个国际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把国外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上;会破坏美国的独立性,因为美国不能否决WTO、TPP相关委员会的决定。
美国需要的是若干个小的双边协定,这样掌握主动、方便控制(如修改协定等),有利于发挥谈判优势、各个击破,且不会有一个组织凌驾于其上。
日美贸易摩擦镜鉴
日美贸易摩擦始于上世纪60年代,激化于70年代,80年代达到高峰,90年代还有大量的贸易争端。期间,美国的进出口逆差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在广场协议签署后达到最高峰,之后大幅较快下降的过程。中美经贸摩擦是否会经历相似的过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深刻反省。
(一)合理使用货币宽松政策
日本当年为缓解日元升值帶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大幅下调利率水平,货币条件过于宽松,结果过多的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相反催生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最终导致了“失去的十年”。
中国在遇到类似中美经贸摩擦这样的外部冲击导致经济增长承压时,如果恐慌性地出台宽松货币政策,则类似于日本将日元升值视为国难,导致政策反应过头。目前,中国防控金融风险的任务较重,美国完全有可能在中国转向去杠杆时加码经贸摩擦,以使中国政府加深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推迟去杠杆,甚至继续放水,从而催大本已危险的房地产泡沫,使得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产生无法修复的损害,最终削弱中国的长期竞争力,并且彻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中国一是仍要坚持去杠杆、稳杠杆,主要是中国去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为保证去杠杆平稳进行,政府可以加杠杆,住户部门加杠杆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小,主要是居民消费增长乏力,还贷压力较大。二是坚决清理不良债务。不良贷款要真实地面对,切实地处理,必要时政府要出手。如果不处理不良债务,或假装处理好了,则经济活力一定无法恢复。当年日本就是过于相信市场能使得经济从危机中复苏,导致政府在2000年以后才向银行业注资。
(二)妥善应对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罪魁祸首,也是导致我国目前杠杆率较高、金融风险较大的主要原因。中国房地产业的长期单兵冒进,给政府带来了一点土地收入,却严重扭曲了激励机制(大家都炒房,没人干实业),导致了经济内外结构的严重失衡:一二线城市房价相对三四线城市偏高,房地产价格相对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偏高,国内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相对国外偏高。这些失衡带来了巨大的重估压力。
为此,我们要认真吸取日本的教训,妥善应对。一是不刺穿泡沫。泡沫破裂导致经济在短时间内调整,经历剧烈波动,很痛苦,不适合中国,应避免使用。但这样做的坏处就是调整需要很长时间。二是多管齐下。化解高房价带来的重估压力,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房价,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房价下跌消化一部分;工资、物价水平上涨弥补一部分;汇率贬值消化一部分。另外,可以引导一二线城市房价趋降、三四线城市房价趋升,以使房价的结构趋于合理。
(三)保持汇率平稳变动
将汇率升值一棍子打死,拒绝让人民币汇率升值,是没有真正理解和吸取日美贸易摩擦的教训。事实上,汇率升值、贬值都是有两面性的:升值的坏处是不利于出口,短期内不利于制造业;好处是能够提高消费者购买力,有利于进口商,长期看,对制造业也有好处,有利于海外收购,有利于国际化。但可以肯定的是,非常剧烈的汇率升值和波动,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让汇率相对平稳的变动非常必要,政府在这个范围内干预是合理的。
这一次中美经贸摩擦,美国未像当年日美贸易摩擦那样逼迫人民币升值,也暂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可能的原因是其认为人民币当前依然面临贬值压力。
事实上人民币升值也不一定能减少美对华逆差。因为首先要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进口和出口的需求弹性之和要大于1,而中国对美进出口产品中很多是初级农产品和消费必需品等,这些产品的需求弹性多半不大。另外,美对华贸易逆差很多是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等造成的,这部分也无法通过升值来消除。
(四)搞好产业调整升级
当年日本在日元升值的压力之下,除了反应过度以外,事实上,其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而制定的目标基本实现,比如:走出去、产业升级、扩大内需、扩大投资等。中国要抓住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机遇,集中精力完成产业调整升级。
一是要拓宽出口市场,推动自主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可以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拓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出口目的地,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要加大自主创新和研发力度,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坚决走出去。绕开贸易壁垒的方法之一就是跨國设立企业。从日美贸易摩擦看,日本最有成效的应对就是借着日元升值,将大量制造业转移至美国和其他国家,结果再造了一个海外日本。但中国走出去要注意平衡。一方面可以鼓励先进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在海外开拓,另一方面要注意引导企业向中西部转移。避免企业都跑到东南亚等地去了,中西部地区没能承接上,而东部地区又出现了产业空心化。
另外,当前有观点认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措施之一是引进来。需要指出的是,引进来、扩大开放是长期战略,短期内不但无助于缩小美对华逆差,相反还会扩大。比如我们引进美国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办企业,多半要么是替代我国的进口,要么是生产的东西又出口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无论哪种最终都将扩大美对华逆差。
(作者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为人民银行党校34期学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编辑:袁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