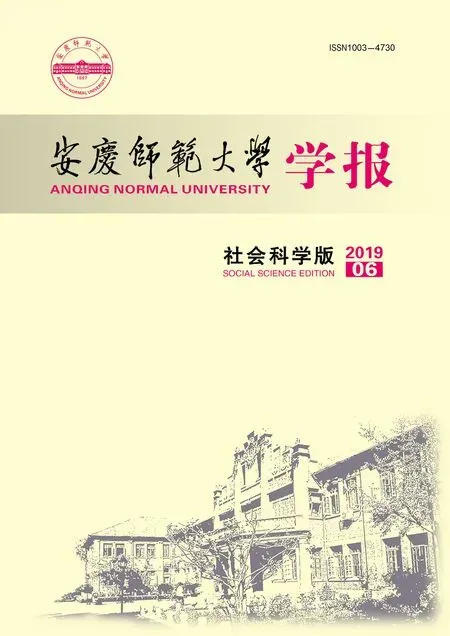人工智能视域下审美主体性反思
周盈之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一、引 言
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昌弘有一个“恐怖谷”理论:机器人越像人类,人们会对其越有好感,而当这种相似度超过临界点后,人类的好感度会极速降低,甚至陷入恐怖的情绪。这是基于人类心理的研究结果,即人类先天地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事物,但这种相似性引发的好感是有限度的,一旦仿真性超过限度而难辨真假,对象身上的非人性特征会被放大而使人感觉不正常,从而产生厌恶和恐惧情绪。基于这个理论,很多机器人专家建议,在制造人工智能的时候,不应将其外表过分人化,从而避免用户产生不良情绪。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扫地机器人还是外科手术机器人,它们依然以机械的形态出现,不曾拥有人类的外表,而对于这些提升人类生存质量的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我们当然乐见其成。但与此同时,层出不穷的科幻艺术总是在浇灭人们的这种乐观情绪,特别是在电影这种视觉性艺术中,那些和人类别无二致的机器人,与人类上演着奴役与反奴役的故事,作为观影者的我们不得不担忧机器人主宰的未来世界。可以说,科学领域的欣欣向荣与人文领域中的奄奄垂绝,形成了当今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的一大奇相——到底人工智能将使人类获得更好的生命体验,还是使人类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呢?当艺术作品让我们超前地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终极形式——拥有“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我们人类是自惭形秽还是依然能坚定地站立在世界上呢?对人工智能的讨论,始终绕不过的依然是“人”的问题。
二、“人”自身主体性的颠覆
在电影《机械姬》中,程序员Celeb为了测试高仿真的智能机器人Eva 而与其进行交往。Eva 高度的智能使得Celeb开始自我怀疑,于是在一天的测试结束后,他拿出剃须刀的刀片,划破自己手腕,任红色的血液汩汩流淌,然后再一拳击碎镜子,用疼痛证明自己“人”的身份。
人工智能的发展倒逼人类对自身进行重新的认识,人类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它的主体性需要被不断的质疑与检验。事实上,人(human)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概念,按照福柯的说法“人是近期的发明”[1],它的肉身存在背后是现代知识型的塑造。在中世纪之前,人类是匍匐于神之下的,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以完美的“维特鲁威人”作为人文主义崛起的象征,“将生物学的、话语的和道德的人类能力合并成一个目的论意义上制定的和理性的进步概念”[2]18。作为优越的“维特鲁特人”,人类拥有完美的身形和高尚的思想,获得了主体性,自认为独一无二的万物之灵而掌控全世界。显然,人工智能的发展,打破了人类自身优越性的幻想,而未来可能产生的人工生命更是可以完全将“人”替代进而摒弃。面对“人之为人”的诘问,我们必须从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再度审视自身的主体性。
从时间上来说,科学对人类身体的改造很早就开始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这当代人类的四大福音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身体的纤维和结构。机器人和人类的界限变得日趋模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
在医学逐步发达的今天,机器频繁地介入人的身体:心脏起搏器、助听器、人体芯片、新材料假肢等高科技的机械产品的介入,在弥补人类肌体功能缺陷的基本目标之外,开始寻求促进人类能力的无限发展,提升人类生理功能的极限。由此,生物意义上的身体完整性被打破,我们以四肢五官来感知世界的方式也被这些机械所取代。一个依靠心脏起搏器维生的人、一个依靠假肢行走的人还是纯粹的“人”吗?现如今很少人能坚称自己拥有纯粹天然的身体,机器对人体的介入拓宽了生物意义上对“人”的认识,而以人工材料完全复制出整个肉体,似乎也是可以想见的未来图景。
如果说,机器进入人身体的过程仍然是清晰而有意识的,那么人类处理肉体,从而成为人工智能组成部分的反向过程,则更为隐蔽和暧昧。我们以一个习以为常的情境来进行分析:当我们上网的时候,虽然肉体依然停留在小小的房间中,但是我们的意识却突破物理限制,变成无数的信息载体而环游世界。在这里可以进行提问:网络上的我还是一个“人”吗?网络消弭了人的物质存在性,通过人的精神意识来认证个体的身份。著名机器人专家汉斯·莫拉维克有一个理论——只要将人类的意识存储在机器上,然后再下载至另外一个肉身中,人类就可以实现永生的梦想。这很自然地让人想到,近些年来公众对网络账号继承问题的伦理讨论,而《黑镜》第二季第一集就实体化了这种情况:通过读取社交平台上的聊天记录,一家技术公司使得玛莎和死去的丈夫进行对话,进而定制出一个和丈夫一模一样的机器人。然而这个机器人是人又不是人,玛莎想杀了他又不能杀了他,最终只能将他囚禁在阁楼上。“恐怖谷”理论所说的人形机器人的可怕,不仅在于其人形,更在于由人形所带来的伦理秩序的破坏。
事实上,在标识人类主体性的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莫拉维克的实验更为推崇精神的崇高性,其所追求的“永生”就是对“我思故我在”的极致化。确实,面对机器人,人类一直自矜于拥有“理性”和“感性”的高贵品质,认为这是机器人永远无法通过模拟获得的主体特性。然而,随着Alpha-Go的胜利,“人类最后的智慧堡垒”围棋项目也被人工智能攻陷,基于大数据和算法,人工智能具有了自我学习能力,在很多方面,它都能作出比人类更合理的选择。而“微软小冰”所创作的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则告诉我们,人工智能开始介入审美这种高级的感性精神活动领域。人工智能在智性、理性和感性的多维突破,让我们更为确信科幻作品中拥有感觉、情感和欲望的人工生命的即将出现。麻省理工大学的机器人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将“人工生命”设想为:从仿生生物学的角度,彻底寻找建立一种与神经系统运行相似的可能性,由此制造出来的机器人不再以人类作为模仿的对象和衡量的标准,而是成为一种和人类并存的一种新型的能够直觉和认知的生物[3]317。可想而知,一旦人工生命机器人出现,他们的感觉、认知和思维获得了充分的融合,他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与人类一样的精神文明。
如果拥有和人类神经系统类似的人工生命还披上人类的皮肤,那么我们也就不再能分辨谁是“孙悟空”,谁是“六耳猕猴”?无论是科技现实还是科幻艺术,“人”的概念都变得摇摇欲坠,“人将非人”的黯淡前景,在美国文化学者凯瑟琳·海勒看来,不外乎两种命运——“人类要么乖乖地进入那个美好的夜晚,加入恐龙的队伍,或为曾经统治地球但是现在已经被淘汰的物种。要么自己变成机器再坚持一阵子”[3]383。其实,无论是人成为机器人,还是机器人成为人,都将出现一种新的生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这种“新人”呢?
美学学者唐娜·哈拉维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就给出了答案:“到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成为一种神话,我们都是怪物凯米拉(chimera),都是理论化和编造的及其有机体的混合物;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赛博格(cyborg)”[4]316。所谓“赛博格”,是“控制论的”(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这两个词的合并缩写,它是一种混合生物体,由人类的身体和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高科技有机物组成,这种组成物促使主体在劳动、需求和繁殖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可以说,“赛博格”的出现,已然颠覆了以肉体为标准的稳定人体边界,不只是人类和机器界限的模糊,它也使得自我/他者、现实/想象、真理/幻觉、科学/自然的对立边界变得含糊,因此,哈拉维指出:“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4]314
显然,作为梅西会议控制论科学的时代产物,赛博格指向一种生物电子人,它对应于机器对人体的介入的过程,那么其反向过程所形成的生物体又叫什么呢?答案是“后人类”(posthuman)。海勒指出“当你凝视着闪烁的能指(符号/标记)在电脑显示屏上滚动,不管你对自己看不到却被表现在屏幕上的实体赋予什么样的认同,你都已经变成了后人类”[3]序7。“后人类”概念最早是由19 世纪末俄国神秘学专家布拉瓦茨基在人类演化理论中使用。这个概念在沉寂百年后于科技高度发达的21 世纪焕发出新的光彩。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对此概念作出清晰界定,大致可概括为四点:第一,后人类观点重视信息数据形式,而将人类的生物实体视为一种历史的偶然存在;第二,后人类观点否认意识的核心地位,颠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辨理性传统;第三,在后人类观点中,人的身体在本质上是一个需要学会操作的假体,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就在不断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者代替身体本身;第四,也是海勒认为最重要的后人类观点,即人类的身体可以与智能机器完美融合,“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3]3-4。这四条定义分别处理了肉体和意识的关系,物质和信息的关系,本体与假肢的关系,人与机械的关系。不难看到,“后人类”并非是时间上后于“人类”存在的生物,而是一种同时的但不同于人类的独立存在形态,它着力将一个完善稳固的主体“人”打碎,杂糅进异质物,从而改变主体概念本身,成为新的存在物,所以“后人类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3]序5。
假设一下,一个用各种仪器维持生命的人和一个拥有全部人性的机器人,到底谁是人、谁是机器?我们应该按照物质标准进行判断,还是精神标准呢?“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概念,人类的主体性由此彻底颠覆。于是,我们明白了《机械姬》最后“成人”隐喻:人工智能Eva利用爱上她的程序员Celeb顺利逃出实验室,并且杀死了创造者Nathan。然后她来到储存了之前历代人工智能躯体的房间中,将他们身上的人造皮肤剥落,一块块地贴在自己身上。最后她穿上白裙子和高跟鞋,走向花园、走向直升机、走向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
三、“人”在世界中主体地位的颠覆
电影《黑客帝国》系列讲述了一个机器人统治人类的“矩阵”世界。在第一部的结尾,主人公Neo 为了拯救同伴和人类最后的据点,与反派Smith 进行战斗。在打斗中,两人一度不分上下,直到Neo顿悟,他们仅仅是由一系列数据构成,于是他超越肉身的速度限制,打败了对手。
正如电影中对数据的人化处理,虽然人工智能质疑了“人”的概念,但是我们总是用“人”的形象来想象人工智能的外表,用“人”的情感来丰富人工智能的内心。有意思的是,凡是表现人工智能主题的电影,机器人主角总是人形的。排除导演选用真人演出更为简便的客观原因外,这其中反映的是我们人类根深蒂固的“拟人化”思维。
所谓“拟人”思维,是积淀在人类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从幼儿读物中能说会跳的锅碗瓢盆,到神话传说中呼风唤雨的雷公电母,拟人“使我们得以人类的术语使世上万事万物具有意义——这些术语是在我们自身的动机、目标、行动、性格特征的基础上能够了解的”[5]。实际上,拟人化是对人性的自我崇拜,是人类对他者进行投射的认识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将世界万物归化入以人为标杆所创立的道德体系。于是,那些与人类并不相同的事物,或是通过部分外形的类比或是通过伦理架构的挪用,而被人类所接受。由此,他们成为仅有部分类似于人类的低等物,人也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界主宰的无上地位。然而,面对具有人工生命的人形机器人,人类已经很难再将其贬低为类人的低等存在,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会惧怕这种与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生物会奴役人类,毕竟人类就是通过奴役这个世界上其他生物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的霸权。可以说,科幻艺术中的奴役与反奴役故事的成立,其核心逻辑依然是人类作为世界主体的翻转与再翻转,人类与万物被视作对立的两极,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其中得到延续。
将人类视为世界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缘起于14 世纪后的人文主义复兴,它奉行普遍主义、统一主体和理性至上的原则,人作为“万物之灵”具有了不容置喙的权威,这种优越感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更是极度膨胀,人类相信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绝对主体。在人文主义思想中,“人”被历史文化建构为“男性的,白皮肤的,城市化的,操着一口标准语言,以异性恋的方式铭刻在一个生殖单位和一个被认可政体下的完全公民身上”[2]94,他排除了诸种“他者”——性恋化的他者(女人),种族化的他者(土著)、自然化的他者(动物、环境或地球)、技术化的他者(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由此,以反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诸多“后”学在20 世纪后半期兴起,比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等。显然,上面提到的四类他者存在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即生命性的弱化,特别是与异性恋白人男性(文化上的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关联度的弱化,一个比一个更加反叛“人”概念。因此,我们不妨将人工智能的后人类理论看作最激进的解构性哲学,因为它从根基上否定了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当人连自身都无法确定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作为世界主体的统治地位。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主体地位逐渐失去的过程,它矫正了人类与世界之间失衡的主客体关系,尝试揭示出人的真正存在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超越的、充满无限可能的,人活于世,就是对陈规的突破与扬弃。人类的生命扎根于、也依赖于复杂多变的物质世界,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性,由此,那些依靠权力和财富将全体人类概念化为自主意志的小部分人终将毁灭,人类将从走得过分远的歧路上返回,在世界中找到自己恰如其分的位置。
这种反人文主义的言说方式,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它真的解决了人类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吗?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之下?显然没有,反人文主义看似谦虚地约束人类的野心背后,本质上依然将“人”作为思考的基准点,机器人作为一个他者改变了人的定义,改变了与人的关系,但是它始终没有占据人类原本的主体位置。所以,反人文主义本质和人文主义共享着同一套价值观,通过树立他者来确认自身,这种对立基本存在两种命运,要么就止步于一组组无法被综合的对立组,即人文主义;要么就是通过整合,改写了主体的内涵,即反人文主义,显然,这种改写依然是不彻底,我们依然可以找出更多的存在对立的概念。所以,后人类研究者布拉伊多蒂批评反人文主义是“人文主义传统最高价值的内容和最持久的遗产”[2]41。
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都是布拉伊多蒂所反对的,同样思考后人类问题的她,拒绝将人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而是要去建构“一元论”的世界和“游牧化”的主体。“一元论”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新空间,“它通过暗示和多重他者性相互作用的一个开放的、相互关联的、多定‘性’的跨物种的生成流变”[2]129。这个世界秉持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它应对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生命机会主义,取消他者性的辩证法所引发的权力斗争,打开生成的强度空间,塑造一个新的伦理谱系。突破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的双重夹击的“一元论”世界,形成的是混沌一体的世界,它将自身定位于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中,以具身化的现实而非无形的信息为基础。而在“一元论”世界的基础上,与其相匹配的主体就是“游牧性主体”,这个概念来源于布拉伊多蒂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生成机器”概念的化用,她指出“这个主体是在多重性内同时又被多重性建构的关系主体,即跨差异的主体,同时内部体现差异性,又脚踏实地和充满责任感。后人类主体性在集体性、关系性和因而社团建构的强烈意识基础上,表现了一个具身化与嵌入式的因而片面的负责形式”[2]71,因为技术中介构筑了新的人类主体性,为这个群体划定新的伦理关系,所以这个游牧性主体不再落实于肉身化存在的人,它可以囊括以机器人为代表的类人或者非人;而其精神性上也不再是傲慢的,它强调不断地审视自我,采用陌生化的策略,与社会主导观念保持批评的距离,在人类内部(阶级、性别、性恋、民族和种族)的差异中建立各种组合关系,放弃超验理性,放弃认知的辩证法,明确主体性并非人类的专权。除了自身统一性主体的解构,游牧性主体还承担着对他者、对世界的伦理责任,也就是说,游牧性主体与整个星球世界之间是依赖共生的关系,我们既要警惕抛弃人类概念本身的逃跑性思维,也要摒弃使得人类再主体化的自由个体主义,与此相对的,是要重新对人类在世界中的站位进行划定,审视非确定的主体与这个星球的关系,这其中“包括社会、心理、生态和微生物或者细胞层面的各种权利关系”[2]149,由此摆脱二元对立思想之下长久的普世道德价值。因此,游牧性主体不是一个恒定的主体,而是复杂的、突变的、跨越的和平等的,它代表的是普遍生命体的集体想象和共同愿景。
这种新的主体和世界的定义和关系,使得主体“是从混乱的世界产生并且与混乱的世界结为一体的,而不是占据一种统治和操纵地位并且与世界分离的”[3]394。他们理所当然地破除了传统人类主体和世界客体的二元对立逻辑,要求人类以非人的方式想象自身。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要保持世界和主体的这种不确定的混乱的自由,必然使得万物之间没有区别的高下,只有等同的类比,由此世界就是永无止境的连接和生成,这是一个无法停止的过程,由此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失效和破碎的世界,世界也将不再有主体诞生。
上映于世纪末的《黑客帝国》系列预言了人类晦暗的末日前景,人机大战的本质是人类作为世界主体性位置的战斗,要想认识这个世界,我们不得不自认为主体,但为了世界星球的长远发展,我们又不能一直占据主体的位置,这里存在一个无解的动态平衡过程,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黑客帝国·矩阵革命》这部终结篇的结尾:当Neo 最终消灭了Smith,人类与机器之间达成协议重获和平。建筑师问先知:“你认为这样的和平可以维持多久?”先知的回答是:“直到和平结束”(As long as he can)。显然,她的意思是,人类与机器的战争从未结束,和平只是一个中场休息。这也就是人类作为世界主体位置的获得与失去的必然命运。
四、主体性与主体地位的美学重建
电影《银翼杀手》描绘了“银翼杀手”警察追捕与人类具有相同智能和感觉的叛逃复制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选择在2019 年的洛杉矶:阴雨绵绵的黑夜、废弃的大楼、卖宵夜的街边小吃、大型的霓虹招牌……都在塑造着一个压抑的未来世界。
可能是电影拍摄时间古早的原因(1982年)或者是故事发生时间临近的原因(2019 年),对于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来说,并没有一种强烈的未来气息,而是充满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末世感。确实,当今天回看这部作品,借由微妙的时间差,我们再一次确认了一个事实:在科幻作品中,再绚烂的未来科技都只是虚有其表,他们真正所要思考的仍然是当下人类生存状况,即电影将当下的社会文化、伦理体系、本体经验进行简单地变形,将其放到一个末世中进行检验,从与人类极具可比性的人形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重新思考当今人类生存的问题。
从现实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必然也会呈现出相应的适应性进化。这就好比告诉一个中世纪的人21 世纪的生活情态,在毫无现实依据可循之下,他必然会产生无限的恐惧,显然我们对未来断层式发达科学的恐惧并不会比中世纪人强到哪里去。因而,我们必须看到当下科幻艺术作品中出现的科学技术进步与精神文明的停滞之间的错位。这种错位是普遍的,表现的是萦绕人们的文化焦虑,以2018年大热的电影《头号玩家》为例,尽管电影将时间设定在2045 年,那时候人类的生活已经被虚拟宇宙“绿洲”所垄断。然而,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生活在2045 年的年轻人,依然将机动战士“高达”视作至高战斗力、认为跳disco 是酷炫的事情,喜欢库布里克的《闪灵》……,作为一个对这些文化要素已然陌生的90 后,我实在不能想象四十年后的年轻人会复古到喜欢20 世纪80 年代的流行文化。所以说,与其将《头号玩家》视为对未来的幻想,不如视为对怀旧情怀的致敬,而怀旧正是当代流行文化的一大标签。因此,以未来为表,以现实为里,以文化为体,以科学为用,这才是所有科幻艺术作品的本质,无论它以何种方式嫁接未来与现实,其本身都是当下经验的言说,因此从人文角度思考人机关系、人类主体性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归到关注当下人类的精神文化。
那么,我们当下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文化境遇呢?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很难摆脱人工智能对生活的影响。好像就是从AlphaGo战胜人类棋手开始,“人工智能”成为大众媒体的讨论热词,人们这才惊觉,人工智能不再是一项遥不可及的高新科技,而是切实地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且不论其他,就以我们无法离开的手机为分析对象:音乐APP 根据我们的喜好推荐音乐,购物APP 根据我们的消费习惯推荐商品,社交APP 根据我们的文化偏向推荐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内容。通过与大数据的合作,人工智能似乎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它能够很容易地使人类沉溺于快乐的欲海中,因为它摒弃差异,制造共识,将异质的存在排除,让我们只看到想看到的东西。确实,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似乎我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懒惰而颓丧,我们的心灵开始变得自大而愚蠢,我们不再能理解其他人的不同,甚至不再能包容“不理解”这件事本身。
当人工智能执行严格的程序,给出最合理的解答,让人类放弃思考的能力,被动接受虚假的社会共识时,人类确实正在不断让渡自身的全部主体性,而一旦主体性消失殆尽,人类将成为《黑客帝国》中仅仅提供“生物电”的无用生物。那么如何自救?在这场关于机器人威胁人类生存的论战中,美学艺术崭露头角,表现出救赎人类的可能——共识的反义词是“歧义”,理性的反义词是“感性”,遵从的反义词是“创造”,被动的反义词是“能动”,可以说,美学艺术具有与人工智能完全相反的核心品质。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作为感性科学,艺术之美始终要求我们去感受真实的世界。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的VR眼镜使得人们仿佛身临其境,坐在家中就可以体验到雪山、草地、大海、沙漠所有这些自然美。然而,这种通过计算机生成的模拟环境即使再逼真,也是有限的采点所合成的三维立体图像,它所呈现的视角、给人的体验必然是雷同的。苏轼看到的庐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李白看到的庐山是“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而我们通过VR眼镜看到的只能是“啊啊啊啊啊!好高啊”的雷同体验。感性在场具有语境性,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美都是不同的,所以它要求的是亲身体验,而这种各人不同的感性体验,必然造成歧义的出现,由此,人工智能所塑造的虚假完美、荒谬和谐被打破,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实是真实、丰富,却也残酷的。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话语,我们要去聆听不同的声音,甚至听见那些不被允许讲话人的言说,打破可看的、可听的、可感的、可思的既定秩序,体察全部的世界,也保有其他所有生物去体察的权力。从这个角度再次审视描绘人工智能的电影,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影片的主色调不是暮气沉沉的黑,就是光洁无暇的白,黑与白作为两极颜色,显然是对现实贫乏的绝对隐喻,而真实的世界应该是凹凸不平、色彩各异的“原质”世界。
此外,艺术创造可以突破个人有限性,与真实而不完美的世界的作战。确实,随着技术发展,人工智能也具有了艺术创造的能力:“微软小冰”出版诗集,艺术软件Aaron 能够创造出被美术馆收藏的绘画,“音乐智能试验”的程序能够创造近似披头士乐队的作品……这些机器人创造的艺术作品正在技术上无限逼近真正艺术作品的客观属性,但是真正的诗歌不是“像”北岛的诗歌、“像”梵高的绘画、“像”披头士的音乐,而是如同这些作品一样能够真正去撬动这个社会、改造这个世界的,它应该使得“人从片面走向完整、从单一走向丰富,从被肢解的实际人生中找回已经失落了的本真世界”[6]。写好的程序永远是被动的,不自由的,它不符合美与艺术的本性,而“感性”“精神性”和“人”作为艺术中三位一体的核心品质,显示的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是一种自我开拓的欲望,使得人类日益崩塌的主体性获得重建,这种主体性不是与世界分离并且统治世界的主体,而是成为一个敢于介入现实进程的主体,敢于去改造世界的主体。回头看科幻艺术,它建构出了一个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世界,它在引发人类焦虑的同时,也激发了人类重新创造、斗争的欲望,这不正是艺术对现实作用的能量吗?所谓“人工智能威胁论”在人文领域比在科学领域更有市场,显然也是对人类日益失落的能动主体性的召唤。
电影《银翼杀手》中最让我喜爱的角色是复制人头目Roy,他和银翼杀手Deckard在一座废弃大楼的天台上进行决战。在决战最后,Roy 救了Deckard 一命,但是他即将死亡。Roy 盘坐在雨中,手握白鸽,平静地说出生命中最美的诗篇:“我所见过的事物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我目睹战船在猎户星座的端沿起火,我看着C 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然而,这些都将在转瞬间消逝无影,如同在雨滴中消失的泪水。”然后他的头慢慢垂下,白鸽挣脱束缚,飞向天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爱与痛,最后都化作了美,我认为这部1982年上映的科幻电影远远超过后来种种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Roy比所有的人类更像人类,因为他灿烂地活着、热烈地爱着,用全部的生命感受美。而在这部电影的导演剪辑版的结尾,银翼杀手Deckard在自家门口发现了一个独角兽的折纸,折纸是警察搞定杀死复制人时候出现的,这里似乎暗示了主人公银翼杀手Deckard 本身也是复制人。人与机器人,谁是主人,谁是猎物,他们随时都在转换着,谁是人,谁是机器人,这同样可以随意转换,唯有留在心中的美永恒不变,唯有想要改变世界的信念亘古长存。
五、结 语
纵观各种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关系讨论的哲学作品,其实并不见多少颓丧的结论,反而都希望创造一种更好的人类,更好的世界和更好的星球。可见,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冲击“人”的概念,人类似乎总是自信的、昂扬的、骄傲的,哪怕期间带有小小的焦虑和迟疑,也只是对过分膨胀自我的一种矫治。这并不是说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文焦虑是杞人忧天,而是焦虑本身也存在一个曲线,适当的焦虑可以激发人应对危机的能力,发挥最大的潜能。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我们正在最积极应对的波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