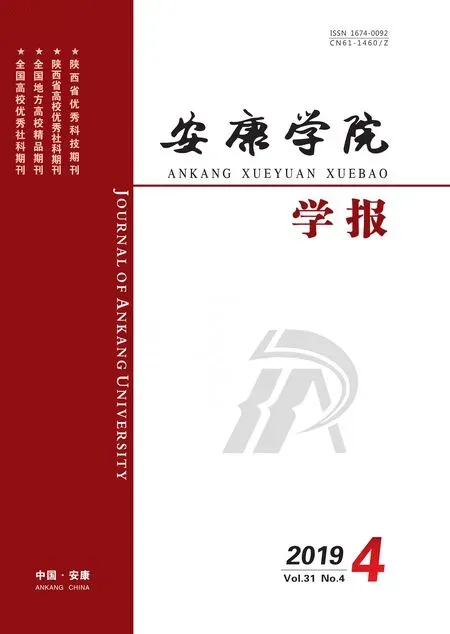阴影里的人:《耻》的后殖民生态女性书写
张 兰
(安康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后殖民生态女性批评“通过探究女性、环境与动物间的相互关系,致力于解构男性/女性、文化/自然、人类/动物、殖民/被殖民等二元对立概念,颠覆(新)殖民主义所构建的各种父权概念及话语霸权。”[1]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或是跨文化的角度,抑或两者兼之,许多学者都认为由于女性的社会角色及心理特点,使她们更接近自然。女性和自然之间有着深远的联系,贯穿了历史、语言和文化。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权主义的方法和态度使得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与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自从霸权主义占据父权社会的首位之时起,女性和自然环境便遭受了殖民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双重虐待。在西方的传统意识下,女性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处于支配的概念结构中。正如金(Y King)所说的:“生态危机与仇恨系统有关。而这种仇恨是白人、西方哲学的男权意识、技术和死亡发明对自然和女性的仇恨。”[2]掠夺自然就像强奸女性一样,这已经成为对自然的各种掠夺行为的一种隐喻。对自然的各种掠夺就像找各种借口强奸女性一样。强奸的隐喻体现在许多其他的地方,尤其是人类对于土地的占用、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欺凌。
库切的小说《耻》表面上看似乎是关于一个大学教授引诱其女学生,然后被学校辞退不得已投奔自己的女儿,在与女儿并不融洽的相处中女儿又被三个黑人轮奸的故事。实则其在小说中所关注和思考的主要问题却是殖民父权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给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南非人民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恶果。在《耻》中,库切将殖民父权意识对黑人女性的威胁、黑人父权殖民者对白人女性的报复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把殖民战争、父权统治、女权问题与自然生态等众多议题互相杂糅,集中展现了其后殖民生态女性思想。
一、殖民父权意识下不可发声的女性
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她的《底层人可以说话吗?》说底层人是无法言说的,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底层遭受双层压迫的人。正如斯皮瓦克在书中所提到的这种双重压迫所造成的非生态正义是由殖民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男性沙文主义所引起的。斯皮瓦克认为:“在父权制和帝国主义之间、主体建设和客体形成之间,女性的形象并没有变成一种原始的虚无状态,而是陷入了一种暴力的穿梭中,即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流离失所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3]因此,父权制和殖民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最终使得底层女性无法让自己的声音清晰地被听到。
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表明,女性受到帝国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统治,就像殖民地的臣民一样,被置于他者的地位,受到不同形式的殖民和父权统治。因此,男性主导的声音经常可以听到,而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的声音则永远不可能被听到,因为她们是白人殖民者控制下的并且黑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的弱势群体。库切在其小说《耻》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现象:卢里把女性当作是从属于男性的群体。在他看来,女性不过是被男性使用且只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物品而已。小说中卢里会见各色女性,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自己的男性权力,展现其男性地位。在与妓女索拉娅的相处中,卢里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展现他的男性话语权:“他不喜欢她的化妆,嫌它太生硬了,要她把唇膏和眼影都擦掉。她按他说的做了,后来就再没有用过化妆品”[4]16,他对此的评价是:“真是个听话的学生,顺人意,听人劝”[4]1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卢里与索拉娅的交谈中卢里略有一些无拘束的感觉,偶尔甚至是无所顾忌,但是对于索拉娅的回应我们知之甚少。这是库切在小说中第一次展现女性被迫失声的现象。
在卢里与其女学生梅兰妮的关系中,我们只知道梅兰妮是卢里所任教大学的一名女学生,与卢里相识是因为她选修了卢里的文学课,而其他有关她与卢里的信息我们知之甚少。在卢里与梅兰妮保持关系的这一段时间里,梅兰妮的声音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相反,卢里的声音从始至终都是清晰可见的。从他们的关系一开始,梅兰妮——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学生,卢里——一个中年白人男教授,身份地位的不对等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一个标志。事实上,卢里的话语权以及他内在的对于梅兰妮高高在上的权力控制就是如此,以至于梅兰妮的声音根本不可能被听到,这实际上也是对南非无数被强奸的黑人妇女的经历的准确反映。通过让卢里发声,而同时让梅兰妮保持沉默,库切在梅兰妮周围构建了一种失语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南非被强奸的妇女身上是普遍存在的。
在卢里和梅兰妮发生关系之后,库切在小说中提到此次强奸案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学校所举行的听证会。然而不幸的是,听证会所讨论的并不是“强奸”而是性骚扰,并且听证委员会的男性委员们似乎对于导致卢里被解雇的调查根本不感兴趣。在听证会开始前,其中的一名男性委员艾拉姆·哈金对卢里说:“戴维,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要告诉你我完全同情你。这样的事情真的麻烦透顶”[4]49。然后听证会在没有梅兰妮出现的情况下开始了,因为她在前一天已经被委员会叫去陈述详情。在听证会举行期间,令人吃惊的是卢里并没有阅读梅兰妮的陈述,而是直接认罪:
“我已经陈述了我的立场。我有罪。”
“什么罪?”
“就是指控我的那些罪。”
“卢里教授,你在领着我们兜圈子。”
“我犯有艾萨克斯小姐指控我的所有罪错,还有,在学生成绩记录上做手脚。”
此时法罗迪亚·拉苏尔插话了,“卢里教授,你说你承认艾萨克斯小姐的指控,但是你有没有读过那份指控书?”
“我不想读艾萨克斯小姐的指控书。我全部承认。我看艾萨克斯小姐没有理由撒谎。”[4]57
诚然,以上对话似乎表明卢里诚心诚意地接受了梅兰妮对他的指控。但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卢里拒绝阅读梅兰妮的陈述充分表明他拒绝听到她的声音,他使她失声。此外,在小说中,库切让卢里在被解雇后去向梅兰妮的父亲道歉而不是直接向梅兰妮道歉,则进一步构建了梅兰妮的失声状态,她被完全置于事件之外了。由此可见,卢里并不承认梅兰妮具有独立自主的权力,而是把她看作是依附于她父亲的一个物体,这充分展现了卢里顽固的宗法观。对于梅兰妮而言,作为老师的卢里和作为白人的卢里分别代表男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二者身份集于一身,使得梅兰妮没有发声的机会。库切通过解读殖民话语权,把第三世界女性的后殖民状态呈现在大家面前。由于殖民霸权及父权的压迫和统治,使得女性处于边缘地位。
许多人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非源自女性对动物的本质认同,而是源自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被边缘化和被剥削之间物质联系的认知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滥用。由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支配,都是社会构建的结果,而这种社会构建是“建立在一套基本信念,价值观、态度和假设之上,它们塑造并反映了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5]。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从殖民时代开始,殖民霸权和男权主义的方法和态度使得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与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倡导环境教育和环境伦理的学者们通常认为,基于二元论的统治行为是造成当下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因为这种统治行为把性别排除在外。
二、后殖民时代下被迫失声的女性
在小说《耻》中,不仅是梅兰妮,一个黑人女孩是无声的,而且露茜,一个白人女孩也被迫失声。在露茜被三个黑人残忍的强暴之后,在她处理伤口之前她就已经下定决心不去控告强奸她的那些人。因此,在被强奸之后,露茜立刻告诉卢里:“你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4]116。她是这样解释的: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件与公众有关的事。可在眼下,在这里,这不是。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就是南非。”[4]131
在此非常明确的是露茜退却了,因为她对于发生在南非的事情并不抱任何幻想,并且她很清楚地知道她之所以可以待在自己的房子里是因为佩特鲁斯允许她待在那里。
同样的,对于露茜遭受强暴的描写其实也是库切对殖民、父权、女性和生态之间各种关联审视和思虑的体现。正如小说中所暗示的一样,佩特鲁斯肯定是这起强奸案的始作俑者,因为他想控制露茜从而攫取她的土地。这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由于佩特鲁斯在黑人社区地位的上升,他所主导的这起强奸案从某种程度上使得露茜无法反抗,无法发声。事实上,这些强奸犯以及他们的帮凶运用他们的权力使得露茜无法发声,因为露茜知道要想待在这里,她就不得不把她的土地出让给佩特鲁斯,就像南非其他许多女性一样依附于像佩特鲁斯这样的男人。从而,露茜退却了并且接受了她的命运,说道:“不错,我同意。是很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但是……开始,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4]237对于露茜来说,沉默是她在当代南非所付出的代价。在一次与露茜的交谈中,卢里试图理解露茜的沉默,他说:“你是不是想搞什么秘密解脱?你以为忍受现在的苦难就能偿清过去的罪恶?”[4]131露茜反驳说:“不。你一直都在误解我。什么罪恶感,什么解脱,那都是抽象的概念。我做事不按抽象概念来。你要是不能明白这点,我什么忙都帮不了你。”[4]131
因此,在露茜看来,并不是罪恶和救赎让她对自己所遭受的强奸保持沉默,而是因为库切让她在当下的南非现实中保持沉默。在小说《耻》中,露茜对于男性侵犯的被动反应、沉默,以及把自己和自己的财产交给黑人佩特鲁斯的行为是与当时南非社会权力的不平等脱离不了关系的。即使是在当下的新南非,尽管种族权力结构已经被推翻,但是父权制仍旧存在,只是这一次黑人男性在选举运动或其他领域赢得了胜利。
露茜凄惨的处境以及所遭受的侮辱实际上揭示了南非的殖民历史。正如卢里在安慰露茜时所说的:“他们的行为有历史原因,一段充满错误的历史。就这样去想吧,也许会有点儿帮助。这事看起来是私怨,可实际上并不是。那都是先辈传下来的。”[4]181斯皮瓦克认为女性已经被经济、文化、政治边缘化。由于男性主导社会中的性别角色,妇女被排除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之外,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中被剥削,女性遭受着双重殖民。由于被男性社会所拒绝,她们则被迫从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在小说《耻》中,露茜被迫失去了她的土地、权力和其他东西。更为讽刺的是,她不得不给他的老板,也就是强奸她的人工作。库切试图在《耻》中向读者展现在后殖民时期由于父权制及殖民历史的影响,所谓的新南非白人女性的生活状况,以此展现妇女受到了双重压迫,被迫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萝斯玛利·路瑟认为,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使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对妇女的压迫合法化,其允许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在她看来,这种社会等级结构根植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即超验二元论。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认为他们有权开发自然,同时也就有权利用女性。”[6]这意味着女性和自然被男性当作是他者,都可以被男性所利用。因此,女性和自然之间有着一种象征关系,即女性—自然的隐喻,它成为西方文明中女性歧视和自然歧视的象征性联系。卡特里奥娜·桑地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曾说过:“那些提倡她所称为‘母性的环保’的人认为只有女性才能提高对生态破坏的认识,因为女性是孩子和‘家庭尊严’的守护者。”[7]
三、殖民父权意识下的话语权之争
库切在评价希拉·佛卡得(Sheila Fugard)的小说《一个革命女性》时指出:“南非是一个崇拜男性上帝的父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女性是不可见的。”[8]在此,库切所说的“不可见”旨在强调南非女性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小说中的梅兰妮、露茜都是被边缘化了的女性,因此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莫伊·托瑞尔(Moi Toril)指出:“唯有让被压抑的女性重新找到一个主体位置,重新找到一个发言的位置,她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9]在小说《耻》中,库切一如既往的书写了殖民父权体制对女性的压迫,也同时书写了女性在殖民父权体制面前所展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露茜离开父母独自来到乡下,“坚实地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4]73。她“护养狗,忙菜园,看星象书,穿没有性别特征的衣服”[4]105,试图摆脱南非社会下父权的阴影。在她遭受三个黑人的欺凌之后,面对卢里的安慰,她无动于衷;当卢里试图说服她报警的时候,她说这是她自己的私事。露茜首先承受了来自白人父亲的干涉和压制。“父亲”的身份使卢里试图改变女儿的生活方式。他觉得露茜身为自己的女儿,不应该在小镇经营农场,和黑人、土地、动物打交道,而是应该做些更上等的事情。暴力事件发生后,卢里要求露茜离开南非,开始新生活。露茜颠覆了传统父权制下顺从的女儿形象,通过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决定对父权中心主义展开了回击:“我不能根据你喜欢不喜欢我做的事来过自己的生活”[4]228。她对父亲说:“我不会永远都是一个小孩,你也不会永远都是一名父亲。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我不需要你的指引,尤其是现在。”[4]187
库切在小说中通过描述卢里同露茜的父女关系,展现出女性试图拓展生存空间并开始要求掌控话语权。当卢里责备露茜没有告诉他自己怀孕的事情时,露茜如是说:“你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我的生活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似的。你是主角,而我只是个小角色,直到故事讲了一半才出现。哼,同你想象的正相反,人是不能被分成主角和小角色的。我不是个小角色。我有自己的生活,这生活对我十分重要,就像你的生活对你十分重要一样。而在我的生活中,做决定的人只能是我。”[4]228这是露茜的声音。库切通过描写露茜对其父亲展现出的话语权,凸显了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加强,在抵制殖民父权压迫、追求平等和自由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南非的女性在殖民及后殖民时期饱受压迫,殖民霸权及男权主义对殖民地女性产生的统治等同于对自然的统治,产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以及环境问题,从而危及生态公正。格兰特·法瑞德(Grant Farred)强调:“男性话语和话语方式充满着战争和暴力的破坏性和强制性,女性必须为了自己的崛起和人类的发展前景,创造女性的话语权。”[10]许多学者认为女性是绿色社会和改善自然环境的关键,“女性必须意识到,在一个依然以统治为基本模型的社会里,女性是不可能得到解放,生态危机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11]。
四、结语
女性主义研究者麦茜特认为:“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而顽固地持续下来。”[12]一直以来,被誉为“我们的传统中所产生的第一位蓄意使自己具有女性身份的作家”[13]的库切,以其对殖民问题、女性问题与环境问题,尤其是殖民统治带给后殖民时期的诸多负面影响等富含实际意义的关注,在其后殖民文学作品中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其对女性、生态的关怀融入其后殖民书写中,将后殖民书写、生态书写和女性书写互相杂糅,表现出明显的后殖民生态女性书写的特色。库切以其敏锐的目光、非凡的洞察力和睿智的思维,始终坚持作家必须回应时代和社会要求并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姿态,积极关注南非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始终致力于发现和揭示殖民父权话语影响下南非社会的真相,以真实的笔触描摹南非人民的生活,尤其是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导致的种种冲突和后果。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理念的烛照下,库切把殖民问题、生态问题与女性问题交织一起,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了对南非乃至整个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思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关注后殖民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生态和社会问题对于推进后殖民社会的发展和生态保护大有裨益,同时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