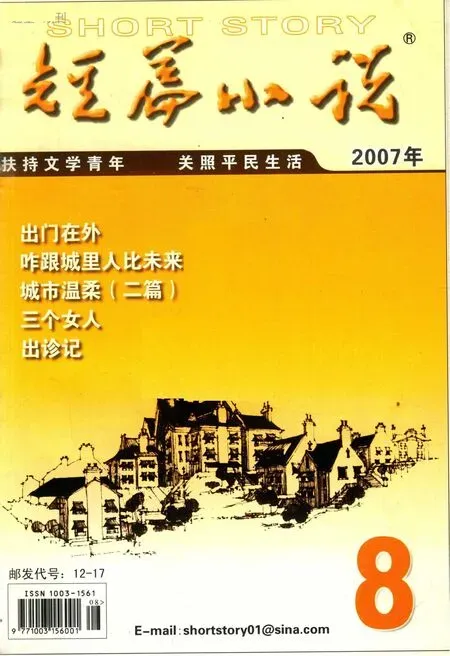有一种情义叫割舍不断
◎闫 岩
责任编辑/文媛
从我十几岁开始发表文章到现在,在各类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大大小小已不计其数,要数最有感情的,最值得感恩的,最割舍不断的,非《短篇小说》莫属。
我与《短篇小说》的相识已有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了。那时我还在县城上中学,县城与回村的路口有一个很小的书亭,那个书亭一直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风景是让人来欣赏的,我也只能是欣赏而已,我是买不起书的。书亭的玻璃窗上挂着许多的杂志,印象最深的就那么几本,《青少年文学》《华夏少年》《读者》《青年文摘》《辽宁青年》和《短篇小说》。别的价钱我记不起来,只记得《辽宁青年》是一毛七一本,回忆起来真是不敢相信,我竟然买不起一本一毛多一本的杂志。
写这篇东西之前我打电话问过母亲,我说妈,我怎么不相信呢,怎么就忘了呢,一本一毛七的杂志我竟然买不起,这是不是真的?母亲回答,是真的呀,就是买不起,她每天做一模豆腐才挣不到两块钱,能让我们兄妹三人上学就很不错了,买其它的东西哪儿能呢。母亲说,有一次家里没有钱买盐,她从我们院的杏树上把所有的杏都摘下来卖了,卖了一块钱,买了一小簸箕的盐,够我们吃两个月的。我和母亲说着说着当初,母女俩忍不住都哽咽了,赶紧终止了回忆。
那时还小,眼里的杂志还是青少年的,班里有个同学有一本《华夏少年》,我说了好多好话同学才借给我看,而且只能看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后我把书还给了人家。从那时起,我爱上了写作。开始只是一种模仿,后来觉得不模仿也能写成了,就想把写出的文章寄出去让它变成书上的字。我买不起杂志,也找不到地址,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我在书亭那儿装作买书,然后偷偷地把地址记下来再说不买了,我没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一次记不全,又怕卖书的人认出来,就过几天再去记,就这样我记下了《华夏少年》和《青少年文学》的地址,写好了文章,买不起邮票,我就一分一分地攒,攒够了8分才把文章寄出去。我很幸运地在《青少年文学》上发表了文章。那时《短篇小说》我是不敢涉及的,因为我不懂什么叫小说,《短篇小说》在我眼里是那么高大上的一本刊物,每次去了都得多望几眼。后来有了发表的经验,就把写小说当成了一种目标。
敢往《短篇小说》寄稿子已是几年以后,我已经不上学了,出来打工。为了学习《短篇小说》的风格,我转了几条街才买到这本书。读了又读,还是不能把握。踌躇了多次,写好了一篇五六百字的小文章放在信封里寄出去了,是王立忱老师给我回的信,稿子退了,但他退稿的内容似乎比我文章的字还多,读着这封退稿信,我非常激动,甚至捧着那封信哭了许久。后来,我在王老师的鼓励下又写又寄,终于发表了。当看到自己的文章终于上了《短篇小说》,那种难以抑制的心情只能用眼泪来表达。
在我最困苦时,王老师不但在精神上鼓励我,还支持了我很多邮票、稿纸甚至信封,他说,你生活这么艰苦还如此热爱文学,作为一个编辑这叫我感动,我会永远支持你。那些邮票,那些稿纸和信封的样子永远都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都是我最难忘的一部分,如今想起来我还是会感动得落泪。
那时没有网络,只有邮路,从河北到吉林,一封信要走一个星期左右,当我发出一封信就开始遥首盼望王老师的回信,盼望能看到他写的留用或者是退稿的指导,还有王老师的鼓励,《短篇小说》就是我整个人的精神支柱。现在看来,《短篇小说》并不是大刊物,有些著名的大作家对它也并不在意,但对于我这个草根来说,却神一样存在。有时受委屈了,有时出意外了,每当我顶不住生活的压力时,它就会及时地出现,给予我坚强生活下去的勇气。王老师是极有耐心的一个人,一篇稿子退来改去,来来回回能耗上三四个月。很多时候我都等不及,算着王老师给我回信的时间在路口等邮递员,那些年我和邮递员混得很熟,他看到我停下来那说明有我的信,没有我的信就只摇一下头就笑着过去了。
过了那么几年,我省吃捡用装了一部固定电话,看着那部电话,我心潮澎湃,考虑都没考虑,我把第一个电话打给了《短篇小说》的王立忱老师。那么多年来,我是和王老师第一次通话,我激动得说不成整句话,哭了。王老师安慰着我,说让我再努力,一定会有成绩的。
在王老师的支持、鼓励与教导下,我写小说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每年都能发上两三篇,渐渐地使我有了些底气,敢往别的杂志投稿了。《短篇小说》寄来的稿费我都买成书来读,也是渐渐地,我对写小小说有了一定的底气,发表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在小小说界也有了些名气。
最早时,王老师和我的通信我都珍藏着,可那时候生活不固定,也可以说居无定所,搬来搬去,所有的信居然都找不到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弄丢的,想起那些珍贵的信被弄丢,我的心就扎扎地疼。
因为底子薄,读的书不多,写小说也进步得没那么快,我把自己归于没有天赋,也不勤奋。在生活艰难的日子,想到未来没有希望就会放弃一阵子,等过那么一阵子突然再发表一篇文章又有了继续下去的勇气。期间,有那么几年,我凭自己发表的文章到了一个国企干宣传工作,生活总算稳定了下来,结婚生子,工作再忙一些,对写作这件事就没那么用心了。当孩子长大一点,再看看一些同时期的写作者,他们和我一样出身卑微,一样出来打工,一样经受苦难,但他们却没放弃自己的追求,登上了荣冠。比如《微型小说选刊》的主编陈永林,《知音》的邹当荣,淮安文化馆的创作员王往等,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本来我们是好朋友,可他们的努力已把我远远地甩在后边。
我对自己不那么勤奋,不那么拥有天赋总耿耿于怀,所以我努力地读书学习,近年来也取得一些成绩,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群支付》发表在2016年《小说界》4期上,2017年被评为河北省的最高文学奖“孙犁文学奖”,也是获得的这个奖项后,省文联和省作协的领导发现了我,不断地鼓励我,让我对文学有了更远的目标和认识。
然而,发表再多的文章,刊发的刊物再大,《短篇小说》在我心中依然是伟大的,磨灭不了的。多年后当我再一次和王老师联系,年逾七旬的他依然在为《短篇小说》推荐稿件,这使我惊喜。他说,你有稿子就发过来吧。我说,行,我发。随后,我接连不断地给王老师投稿,王老师对于稿子看得还是很认真,我的稿子会经常被他枪毙。现在网络发达,手机方便,每次枪毙了我的稿子他都会说出一大堆的理由,或短信,或微信,或打电话。现今,我把《短篇小说》推荐给了我的很多文友,有的发表了,有的没发表,但他们都表示很喜欢这本杂志,也对王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日久生情,我和《短篇小说》有着将近三十年的交往,不仅仅是恩师对我的扶持,我对这本杂志也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过那么几个月,我总情不自禁地写篇小说发给王老师。《短篇小说》开辟了“说长道短”栏目,我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写。我自认为,我和《短篇小说》是众多作者中感情最深的一个,那种感情,别人无法体会。
有一个遗憾,和王立忱老师认识二十多年,我们从未曾谋过面。下一步,我就要抽个时间,抽个空闲,去东北走一趟,亲眼看一看我敬重的王立忱老师和《短篇小说》编辑部。这是我迫切的期盼!
当然,我还有一个迫切的期盼,也是大家所期盼的吧,《短篇小说》稿费发放标准二十年前千字五十,现在还千字五十,真是执着如一啊!或许,《短篇小说》不像那些大刊物有政府扶持,有企业赞助,完全凭借自身的发行量维系刊物的生存,这样一想,她就更了不起呢。衷心希望她越办越好,凭借自身的独特魅力,永远立足于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