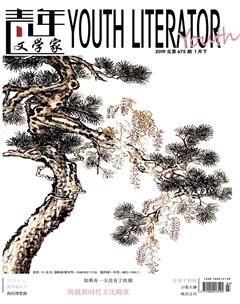论《妇病行》中病妇的思想奥区
摘 要:女性形象一直是汉乐府与南朝乐府诗歌中主要描述的对象,学术界历来注重对妇女人物形象层面的解读,但对其思想层面的解读尚有可完善之处。本文以同题共咏中古辞与江总的《妇病行》为例,分别论述其处于特定人文与自然场域下“病妇”的思想奥区。古辞中病妇的思想层面主要表现为怜念子女、心怀歉疚、孤孑黄泉;江总笔触下病妇的思想层面主要表现为幽怨、自怜和空虚;且分别从历史场域、阶级地位、社会风尚揭示其思想奥区形成的缘由,对研究女性思想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妇病行》;病妇;思想奥区;
作者简介:韩淑萍(1994-),女,汉族,山东潍坊人,苏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2
乐府诗中有诸多描写女性生活的篇章,女性形象一直是汉乐府与南朝乐府诗歌中着力描述的对象,该同题共咏诗辞 虽处于不同的历史场域之下,但其所揭示的女性思想却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通过对两首诗歌中女性思想层面的分析,可一窥底层妇女在汉代社会背景下遭受的思想磨难和南朝社会的痼疾在妇女思想层面施加的影响,对研究女性思想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是汉代乐府诗歌中揭露封建黑暗社会的精品,它向我们真实地展示了 徘徊在生死边缘线上的底层妇女形象。对于“病妇”思想层面的揭示,古辞和江总所作诗辞 皆深度不一,《蔡宽夫诗话》云:“齐梁以来,文人喜为乐府词,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意。”明代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亦云:“古乐府命题,俱有主意,后之作者,直当因其事用其题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则失之矣。”故总体看来,江总乐府诗失其古乐府本意,而究其原因,在于古辞为汉代无名氏即时性创作,而江总则处于与之悬殊较大的人文历史场域中。兹列以下两首诗歌,将其所包含的“病妇”思想奥区分别进行论述,并分析该同题共咏诗辞 产生以下不同思想层面的原因。
妇病行
古辞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日: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
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妇病行
(陈)江总
窈窕怀贞室,风流挟琴妇。唯将角枕卧,自影啼妆久。羞开翡翠帷,懒对蒲萄酒。深悲在缣素,托意忘箕帚。夫婿府中趋,谁能大垂手。
一、古辞中“病妇”的思想奥区
首先,诗中病妇第一个层面的思想奥区在于为母之痛,怜念子女。《乐府诗集》古辞中提到:多年染病的妇人,在贫病交加之下已步入死亡的边缘,在其生命的残留之际,心中依然对自己三个孩子担心不已,还未及留下遗嘱,早已泪眼翩翩,面对心爱之人经历着灵魂与身体的双重折磨,诗中的丈夫自然痛心不已,然却无可奈何。“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诗中病妇第一层面的精神奥区展露无遗:莫让我即将夭折的孩子们忍受饥寒交迫之苦,若他们犯有过错,莫用竹条鞭打他们,慈母情怀根深蒂固。但面对眼前的三個孩子,现实情况却只能令父亲愧对妻子的遗嘱。由此,可一窥汉代底层病妇令人唏嘘的悲惨命运,同时也是其身为人母思想光芒的展露。
其二,为妻之痛,心怀歉疚。古辞中“传呼丈人前一言”,“累君两三孤子”,“传呼”与“累”字,凸显了病妇自己即将离世,但夫君未在身边照料,不得不将其“传呼”到自己身边,但当“病妇”将抚养与照料孩子的责任全部委托于夫君时,萌生了怜爱与亏欠之意,由此折射出病妇家庭地位之低,这是病妇思想奥区的第二个层次。虽是夫妻关系,但病妇仍需用尊敬的言语来央求夫君善待幼小的孩童,对丈夫生发愧疚之意。汉代,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拥护,其关于纲常伦理的思想弊端也随之彰显无遗。因此,“病妇”的思想奥区亦折射出汉代妇女社会地位的卑微,封建伦理对她们人性上的禁锢首先造成了男人与女人之间在思想上的不平等地位。
其三,为民之痛,孤孑黄泉。在汉代黑暗与薄情的社会背景下,病妇自身数年疾病缠身且出身社会底层,家庭极端清贫与惨淡,当客观的压力与自身的病情结合在一起,使得病妇已失去对生的希望,涌现在其即将奔赴黄泉的时刻时,“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还未及诉说衷肠病妇便已泪眼模糊,无语凝噎,悲叹自己一生命运的凄苦,即便到了生命的尽头也仍是孤身黄泉,只得在弥留之际提醒夫君“思复念之”,这是病妇思想奥区的第三个层次。身处飘摇的乱世之中,在物质上的贫乏,灵魂上的枯竭,诗中病妇作为汉代社会中的一员,临近生命的尽头,却仍孤孑一身,无法得到身体与灵魂的救赎,亦是汉代诸多底层妇女在思想层面的折射。
二、江总《妇病行》中妇人的思想奥区
首先,为妻之病,病在“幽怨”。《妇病行》同题共咏中,江总采取突变的方式,将古辞中“病妇”的形象脱胎换骨,写成艳情诗的风格。且诗中的“病妇”其在思想层面的表现与古辞中的病妇悬殊较大。其所作《妇病行》中提到“窈窕怀贞室,风流挟琴妇。唯将角枕卧,自影啼妆久。”风雅洒脱的妇人,拥有娴静美好的容貌,胸怀坚贞不屈的情操,完全脱离下层民众的贫苦生活,迎合了宫廷文人的趣味与审美。但“唯将角枕卧,自影啼妆久”因身体不适的贵妇只得在卧榻上对着镜子里的倦容流泪,夫君却不在身边,敢怒不敢言的她只得独自幽怨,由此可以窥探出,诗歌中病妇的全部生活重心在于能否得到夫君的宠爱,而失去自我在精神价值方面的追求。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诗中的贵妇只顾迎合心仪之人的低级趣味,如若失宠,便只会以郁结于心的愁怨来抒发不满。这亦是古代妇女在男权社会下思想的普遍反映。
其次,表现为病在“自怜”。江总乐府诗在表现宫廷怨妇的虚靡生活时,不仅表现了其对物质生活浮华与繁艳的向往,且折射出她们在精神与情感上的自怜意识,“羞开翡翠帷,懒对蒲萄酒 。深悲在缣素,托意忘箕帚”,翡翠的帷帐,葡萄美酒,一“羞”一“懒”,将病妇的生活情态一览无余,物质生活上的富华却难以掩盖住其精神上的空虚与悲哀,故常常用细绢来遮住自怨自艾的泪滴,怜惜自己如飞鸟一般失去自由,却又不得心爱之人的关心,乐府诗中有诸多怀有如此般自怜意识的诗辞 ,如《怨诗行》、《班婕妤》、《昭君怨》等,她们无不因自己个人爱情的失意而自我怜惜。病妇个体的情感意识是从群体意识中剥离出来的一种对于个人境遇的体验,当这种情感的体验被过度放大之后,便会成为禁锢其人生发展的桎梏,产生怅然若失感,使得自身不仅无所作为而又多愁善感。
其三,为民之病,病在空虚。受社会痼疾的影响,诗中妇人属于当时社会关系网中的一员,而当时南朝社会奢华与浮靡之风已在众多贵妇周边蔓延,诗中妇人自然成为社会弊病的一种折射。江总诗歌中的“贵妇”处于南朝陈时期,肖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说:“南朝则纯为一种以女性为中心之艳歌讴歌,几乎千篇一律……总之千遍万转,不出相思。”故南朝陈的历史场域中,众多女性皆如诗歌中的“病妇”一样,对爱情与人生充满自怨哀怜情怀,自身成为依附于男性的附庸。南朝陈的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文人享乐、妇人幽怨的习气,社会上流传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也不出儿女情长,且多以女性视角抒发闺幽怨情怀,这是一种社会弊病的折射。
三、《妇病行》产生如上不同思想奥区的缘由
该同题共咏中江总笔下病妇的生活状态与经济状况远胜于古辞中贫苦的病妇,为何诗中“病妇”的思想精神会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与诗人所处的历史场域、阶级地位、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是历史场域的不同,一为汉代,一为南朝齐时代。汉初,汉高祖刘邦制订了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策略,但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统治者对百姓的压榨和剥削日益严重,在“文景之治”时期,统治者就“急征暴敛,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其债者”,在此之后,统治者更加荒淫无道,东汉时期统治阶级“熬天下之膏脂,斫生人之骨髓,……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过着浑浑噩噩、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腐朽生活,老百姓却是“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上述种种,皆是古辞中“病妇”所处历史场域的真实反映。江总写作《病妇行》时处于南朝陈时期,陈后主“不知稼穑艰难”,“复扇淫侈之风”,耽于享乐,颓废政治,陈代文坛诗歌创作既没有建安时期高扬的政治理想,也没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故文人们选择佛教、艳情和诗酒享乐作为自己情绪的宣泄点,故处于当时历史场域中的江总亦是如此。
其次为阶级地位的差异,一为下层民众,一为达官显贵。古辞中《妇病行》的作者虽然为无名氏,但是不难推测其应属于汉代的下层市民,诗歌中对于“病妇”、“丈人”、“孤子”形象的刻画,对当时的下层民众社会环境的揭露,皆真实的揭露了汉代黑暗的社会与腐朽,只有感同身受的社会经历才会使他谱写出具有如此深刻的意义的诗歌。江总,一生历经梁、陈、隋三朝,是南朝陈一位重要的作家和大臣。其中,陈后主陈叔宝在位时,江总任宰相,所以,他的仕宦生涯决定其所出入之处必然与宫廷有关,得到朝廷的优礼和照顾。长期的养尊处优使江总这样的南朝文人纵情于诗酒艳歌,对政务漠不关心,所以,江总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诗歌中难以流露出对下层民众的关心,他的生活经历的局限性决定了他难以写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
其三为社会风尚的迥异,一为儒家文化的熏陶,一为浮艳之风的熏染。儒家思想作为西汉时期的指导思想,一方面需要对时人“精神遭礼制束缚,学术深受政权独尊儒术之宰制”,另一方面也在后期不断的自我发展完善,但汉代男尊女卑和夫尊妻卑仍占主导地位,婚姻中的女性居于从属地位,故当时的社会推崇纲常伦理之风。陈后主时期,宫廷充满浮艳与享受的风气,《陈书·后妃传》曰“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押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 ,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南史·后主纪》曰“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押客'。先令八妇人璧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故当时的文人在创作时普遍推崇浮艳柔糜之风。
以上采用多边互镜的交叉模式,分别对特定生态场域下“病妇”的精神奥区作了进一步的 剖析,病妇之“痛”在于怜念子女、心怀歉疚、孤孑黄泉,贵妇之“病”在于幽怨、自怜与社会痼疾的影响。且以及论述了该同题共咏诗辞 产生以上不同精神层面的原因:历史场域的不同,阶级属性的差异,社会风尚的迥异。分析《妇病行》中病妇思想的典型特征及其成因不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汉代与南朝社会女性主体的生存困境,而且对男权社会下女性主题的整体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華书局1980年.
[2]朱承爵《存余堂诗话》,《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4]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二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