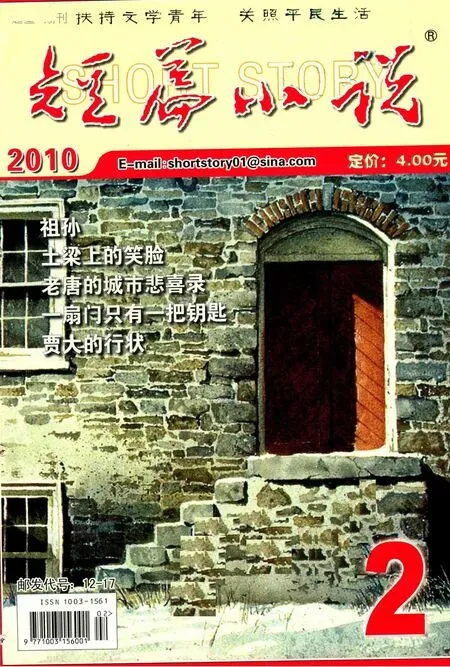奔跑

这个学校有很多名人,有人以贱出名,有人以傻逼出名,田田是因为她的性格强硬出名,被许多同学称为牛人。她喜欢参加各种风光无限的公益活动,譬如向灾区募捐,尽管只募捐到一千零一块钱。再如她号召大家去地震灾区当志愿者,结果只有自己一人跑到四川,又被维护秩序的警察以帮倒忙为由给撵了回来。
有回学校开联欢会,几位男生起哄捣乱,往台上乱扔东西,甚至扔了一只臭鞋。田田作为报幕员,走到台前,下意识地捂了捂鼻子,然后用比老鹰还锐利的眼睛扫视一会儿台下,瞄准,踢,臭鞋准确无误地击中了鞋的主人,激起好大一阵喝彩。
厉雷夜里做了个梦,一颗大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直冲地球而来,他在地面上颠儿来跑去左躲右闪,还是没躲过去,结果被撞醒了。
田田绝对是一狠角儿,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学的,很可能又天生又后天,狠上加狠。她生在一个传统家庭,她爸性格温顺,大大的良民。她妈性格暴烈,还有外遇。她爸隐忍很久,终于崩溃,夫妻分离了。上小学的时候,田田非常要强。学习一定要得第一,要是得个第二,她会急得哭鼻子。聪明的田田渐渐明白,哭鼻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她又一次得了满分,发现有个男生和她并列第一,而且这个男生不服她,她一挽袖子,扑上去把人家打哭了。这个倒霉的男生不是别人,就是厉雷。
田田获得了全市中学生歌咏比赛第一名,不久又获得了中学生作文大赛第一名。之后,她偶尔拉着电子琴弹得蛮好的厉雷混迹于地下摇滚乐队,出入于一些小酒吧或小型演唱会,挣些小钱贴补家用。更多时候,她都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闲暇偶尔写点小文章向报刊杂志投稿,捞几张稿费。偶尔,田田跟厉雷勾肩搭背哥儿俩似的去她家玩音乐。她爸对她的兴趣爱好一向持保护态度,至于她妈,她不提,厉雷更不提,他俩约定过,为免生郁闷,避开不谈各自妈妈这个话题。
田田的同桌叫小松,有天凌晨四点他就醒了,很困,却再也睡不着。这并非他第一次失眠,每次失眠,他都要思考一些事情,每次都是越思考越糊涂。到学校才想起兜里没装钱,早餐和中午饭怎么吃呀?
田田把小松拍醒时,他睡眼朦胧,一脸字迹,是桌面上的刻字印上去的,仿佛图章。她递给他一巨块面包和一巨袋酸奶:“你是不是没吃早饭啊?听你肚子呱呱响跟叫魂儿似的,吵得我都不能补作业!”
“你以前肚子响得也够厉害,怎么耽误不了我睡觉啊?”
“别和人类比行不?我们地球是很危险滴,还是回你们火星去吧。”
小松看到面包和酸奶都是没开封的,就问:“是厉雷巴结你的吧?”
田田眨巴眨巴眼:“你不是在睡觉么?怎么知道的?”
“猜的。”吃了人家的嘴短,小松一边狂啃面包,一边替厉雷说好话,“其实厉雷挺帅的,对你忠心耿耿,干吗老冷落人家啊?”
“我冷落他,可没拒绝他啊。我几乎每天冷落他,他都练出免疫力了,脸皮厚得跟城墙似的,我算没辙了。”
“那就不要冷落人了,我也能多沾点光。”
“沾什么光?”
“这不,面包会有的,酸奶也会有的!”小松啃一口面包,啜一口酸奶,津津有味的样子,把田田逗笑了。
这天傍晚,厉雷非要请小松搓一顿。小松吃得很 HIGH,左手一个鸡腿,右手一个鸡屁股,狼吞虎咽,大嚼特嚼,真应了那句俗话,不是自己的吃着最香。
厉雷很快喝高了,面红耳赤,打出一个又一个响亮的饱嗝:“想当初认识田田那会儿,我在县城刚上初一,和她分到了一个班。田田长得比我高,我就想,这女生长这么高,太缺德了!又想我要是能拥有她,天就不会塌下来,有她顶着呢!哪个男孩还敢欺负我啊!我预谋了好几天,然后跟田田说了我的想法,结果被她打了一顿。男孩们见我被女孩打了,连以前被我欺负的都开始欺负我了。”
“你跟人说什么了?”
厉雷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坦白交代了:“我说,田田,咱俩结婚吧。”
“该打!”小松不解气,“你这人老坏了,该狠打!”然后想打破沙锅问到底,“怎么打的?打的哪儿?”
“拳头,捣我小肚子,几下就把我捣趴下了。”
小松惋惜地摇摇头:“换我就拿砖拍,直接照脸上盖个戳,证明是进过肉联厂的免检产品,谁想吃猪肉了,不用跑猪肉摊,直接跟你身上片两刀,新鲜不说,还绝对没注过水,正儿八经的笨猪肉!”
厉雷肯定把那杯啤酒错当成茶水了,一口灌下去:“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事儿么?”
“想证明你从小就很倒霉?”
“不是,但我确实够倒霉的。今儿咱不说这个,我想说,我整天一门心思琢磨怎样接近田田,却屡屡功亏一篑。那时我学习一般,我拼命学习,就为让老师排座位的时候让我和田田同桌。我学啊学啊,学得头昏脑涨糊里糊涂,终于被老师安排到第一排,田田却被扔最后一排了。”
小松来了兴趣,连吃都忘了:“为什么?田田也有过不及格的时候啊?”
厉雷又灌了一杯茶水(还是啤酒):“田田何止不及格,平均分数三十不到。之后我坠着屁股不学习,任凭老师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唾沫横飞。我爸开家长会回来,皮带飞舞,我的小屁股差点爆裂,你说我容易么?”
“真不容易!”
“唉!”厉雷叹口气,“有回我找茬把班主任的儿子打哭以后,我的既定目标终于达成,老师把我扔到了最后一排,可你猜怎么着?田田又给搁第一排了!”
“你那班主任扭劲儿不叫扭劲儿,叫麻花儿!”
“也不能那么说,把田田搁回第一排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的成绩上去了,全班第一。这事儿成一谜了,我揣摩好久也没揣摩明白。”
“你怎么不问问田田?”
“我担心她是故意那么做的。”
厉雷又要灌茶水,小松拦住他:“你看看清楚,那是冰镇啤酒,不是凉白开,别喝了,再喝就崩了。”
厉雷搭着小松肩膀往外走,一脸的感激。
“哥们儿,”小松问,“你喜欢田田到什么程度了?”
“比滏阳河水还深。”
“滏阳河水至多一米五深吧?”
“不!一米六深呢!”
高处的阴云多了起来,炽热的太阳渐渐被淹没。风起沙飞,视野一派混沌。
田田旷课五天,厉雷请假寻找她四天。
厉雷来请小松,说田田正在一个叫“爆裂”的迪厅唱歌,求他过去帮忙解劝田田。
进入迪厅之前,小松直接往售票口走,厉雷说不用。两个人高马大的保安见到厉雷摆摆手,直接让他俩进去。走了几步,其中一个保安突然对厉雷吼了句什么,噪音太大,小松没听清。厉雷拉着小松往回走,出门后才说:“田田刚走。”
厉雷忧郁地朝四下望着,点燃一支香烟,顺手递过来一支,小松摇头不接。
“下次抽烟的时候,你应该留意一下熏倒了多少无辜女孩儿。”
“好吧。”厉雷把才抽几口的烟掐灭,扔在草丛旁,踩了一脚。
两人来到市中心新华书店旁边的一个小酒吧,在角落里一张条桌前坐下。厉雷点了些菜和稀奇古怪的鸡尾酒。
“田田来过这儿。”厉雷说,“这几天,她什么地儿都混,在书店里喝酒,在电影院里撒酒疯被赶出去,然后去火车站找警察,问票贩子在哪儿,说要买飞机票去美国德克萨斯当农民。要不是我明里暗里保护着,恐怕她连牢底都坐穿了!”
吃喝罢,厉雷去付账。小松走出几步,回头朝厉雷看了一眼,惊诧了,厉雷后面几米外的男厕所里突然走出一个女生。我的个神呐!是田田。厉雷也转过身。田田的衣服脏兮兮的,脸上和头发上还滴着水,目光涣散,往这边看看,眼神才开始聚焦,猛地跑过来,扑在小松身上,小拳头捣了几下他的胸口。
“我好不容易快忘掉你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啊?”
小松的脸憋红了,不知是因为被打太重还是因为田田糟糕的眼神,他无奈地像试西瓜生熟一样使劲弹弹田田的脑袋:“喂!该打的人在那儿呢。”
田田趔趔趄趄走近厉雷,问:“这世界怎么如此颠荡啊!”
厉雷架着田田去到一个小药店,问一个正坐在电脑前剪指甲的年轻女营业员:“有解酒药么?”
女营业员拿来解酒药。
田田突然一手捂嘴,一手拉住厉雷的衣袖说:“我想吐。”
厉雷问女营业员:“卫生间在哪儿?”
女营业员不无担心地瞅着田田说:“我们巴掌大个药店哪儿来卫生间啊,可别吐这儿啊,一吐就淹了!”
田田憋得鸭蛋脸通红,厉雷一看势头不妙,就把自己的太阳帽摘下来,犹豫了零点零一秒后,他戴上帽子,翻手摘下了田田的针织太阳帽。田田捶了他一拳,可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口气朝帽窝吐了个半满,旁边的女营业员看着看着干呕了几下,跑柜台后面找了个塑料袋,也呕吐起来。
女营业员呕吐罢,疑惑地打量端着太阳帽窝接田田呕吐物的厉雷,问:“你怎么不吐啊?”
厉雷告诉她:“我在想,她都快吐满了,这帽子明明是针织的,为什么不漏呢?”
女营业员又开始大吐特吐。
厉雷发现田田的身体有点虚脱,走路有气无力的。虽然还没吃解酒药,田田已清醒许多。问她累不累,她没甩他。过一会儿,田田突然冷冰冰地问:“你干吗到处找我?吃饱撑的啊?”
“快高考了,你要这样到什么时候?”
田田一把推开他:“管得着么你!”
“就算我多管闲事了,可你也得为自己想想啊,你这样下去连一般大学也考不上的知道不?你不是一直想上音乐学院么?去实现你的理想,那才是你该干的事,而不是整天喝酒泡吧,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渣?如果是的话,你就继续胡闹下去……”
“我是走投无路了,只能自暴自弃。”
“还有个词叫绝处逢生,也许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旁边是电影院,厉雷指了指,田田点了点头。里面正在播放香港导演彭浩翔的作品《依莎贝拉》。光影闪烁,两人在空荡荡的后排位子坐了下来。看到女主人公正焦急地寻找自己丢失的小狗时,田田的神情中闪过一丝落寂。
从电影院出来,厉雷小心翼翼地说:“我送你回家吧。”
“我不想回家。”
“那你想去哪儿?”
“我想去哪儿是不是你就能把我送到哪儿啊?”
“是。 ”
“我想去天堂找上帝玩玩儿,你送我去吧。”
“那咱们得先打的啊。”
坐在出租车上,他偷看她的时候,她也在偷看他。他想清一下嗓子,她却先清了一下嗓子。他等她说话,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总得说点啥,可他没想好下面该说啥。
第二天,田田又去上学了,不料下午上体育课时,她扭伤了脚踝。放学后,厉雷背着她,在一片废墟旁停下,废墟上只有两面破墙还立着。她坐在半块水泥板上,面对那片萧条,默然无语。
厉雷说:“难受就哭出来吧,老规矩,借给你肩膀。”
田田直视着厉雷的眼睛:“我老跟你发脾气,你干吗还对我这么好呀?”
“不知道。”
两人一起看那片废墟。一面残墙轰然倒塌,灰尘弥漫。
田田揉了揉眼睛:“去年暑假我家来一客人,是我老家的幼时伙伴。我们坐在客厅调侃各自上小学时许多好玩的事,比如有个老师打喷嚏,喷了前排某女生一脸唾沫;有个男生在厕所打瞌睡掉进茅坑里……我俩乐得肚子疼。我爸做好了午饭,留他吃饭,可他硬说有事,我送他到门口的时候,他奇怪地背朝我挥了挥手。后来听说他跳河自杀了。原来他得了白血病,家里穷得叮当响,没法治疗,寻了短见。这是我一位女同学告诉我的,她说他生前喜欢我。”
厉雷听得目瞪口呆:“你该不会也想寻死吧?”
田田摇头,看着残墙倒塌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件事。”她用肩膀碰碰厉雷,“这些日子谢谢你。”旋即面无表情地说,“告诉你句实话,我不喜欢你。”
田田一瘸一拐往家的方向走。
厉雷追上来:“为什么?你总得说出个一二三吧?”
田田停住,皱着眉头搜肠刮肚:“一、我学习好,你忒差劲儿了。”
“我会努力的!二呢?”
“没有二。”
厉雷怔了,倒不是因为田田离他越来越远,是他看到了一个恐怖画面:田田像刚才她讲的故事里那位男生一样,在背后朝他挥了挥手。
黑板右上角赫然写着一行红字:“距离高考还有30天。”
田田近来学习很认真,但走神的事情在所难免,这不,她目视作业本,用夹着钢笔头的手指去挠嘴唇旁边的痒痒,挠罢,嘴唇上边多了片黑,像只有一半胡子的希特勒。
小松乐得不行,问她:“这是第几节课了?”
“第二节?第三节?要不就是第四节。”田田见教室里只有他们两人,觉得不对劲,看一眼手机,恍然大悟,“已经放学了哟!”
小松说:“你这儿有片东西,我给你弄掉。诶!你看天花板!”
田田抬头那一瞬间,小松飞快地用已经沾好炭素钢笔水的指头肚往她上嘴唇这边抹一下,把希特勒的另半边胡子好看地完成。
“干吗?吃我豆腐哟?”田田从小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样子,惊叫一声,转回头想掐小松。小松已跑出教学区。她的嚎叫声回荡在空旷的校园,“猪!猪!”
田田把所有的书与本子都放在学校,高高低低造房子一样垒在桌子上,整个一鬼子炮楼。她就这样埋在书堆里,眼睛累了揉一会儿,作为仅有的休息。这天,田田居然戴了一副漂亮的紫框近视眼镜。
“呵!”小松惊呼,“多俩眼的田田帅呆了!博士后也就这般摸样吧!”
半天,田田一点反应也没有,原来压根儿没收他的台。只见她眼不离书,手在另一摞教科书后面摸索着什么,摸呀摸,终于摸到一瓶炭素钢笔水,拧开瓶盖,咕咚咕咚一气喝完。小松目瞪口呆,以为她要喷呢,没想到,她吧唧两下嘴,觉得味道不错?
周五下午放学的时候,田田在座位上手托下巴看着黑板上的高考倒记时,那个数字越来越小了。发了一会儿愣,她拿起书包,在里面装满沉甸甸的教科书、教辅和厚厚一叠卷子。走出教室的时候,小松看着她瘦弱的身体和庞大的书包,觉得她整个人矮了不少。
他扯过她的书包替她背着:“装这么多东西?逃荒啊这是?”
田田把书包夺回去:“多管闲事。”
厉雷走过来,神秘兮兮地拉住田田:“那什么,我借给你的那本书呢?”
田田一脸疑惑:“哪本书?”
“就那本啊,有书皮儿那本。”
“废话!没书皮儿那是卫生纸!到底哪本?”
厉雷不再作声,从田田手里夺过书包就跑。
田田纳闷了:“你抢我书包干什么呀?”
田田不得不去厉雷家。
开门的却是刘洋。
“厉雷暂时不会见你的。”说罢这话,刘洋就关上了房门。
“咣当!”田田一把将房门推开。
厉雷光着身子从卫生间冲出来朝自己卧室跑。
田田的脸“唰”一下涨红了,忙不迭往外退:“刘洋你个臭玩意儿!他裸着也不说一声儿!”
“嘿嘿嘿!”厉雷穿戴整齐出来,作揖打躬道,“没想到你来这么快。这不今儿我家空调坏了,都快热崩了。”
田田红脖子涨脸,嗓门天大:“滚!给我滚出去!”
厉雷一路狂颠儿,黄鼠狼似的逃出了自己家,只剩跑丢的一只拖鞋在屋门内地板上转圈。
厉雷看罢自己的高考分数,不由热汗淋漓,弯下腰猥琐地钻出人群。背后田田的声音犹如晴天霹雳划破长空:“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
厉雷没敢回头,拔腿就跑。他怕田田讽刺自己是个只扛枪不装子弹的家伙。
田田追厉雷把鞋都跑掉一只,跑回去抓起鞋接着追:“你个臭玩意儿!跑什么呀跑!我又吃不了你!”
厉雷上气不接下气:“追什么呀追!我又不是双汇王中王!”
“我有事跟你说!再跑我生气了啊!”
“我不想跟你说话!拜托你别再追了!”
眼看厉雷越跑越远,田田来了个急刹车:“敬酒不吃吃罚酒!”将手中那只鞋瞄都不带瞄朝厉雷扔了过去,那只刚踩过狗屎的硬底鞋在空中划过一个充满艺术性的弧线,准确地砸在厉雷脑袋上,家伙登时晕了,跌个四仰八叉。
田田跑过去,见厉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一副狗熊样,用脚踹一下:“死了没?”
“没。”厉雷坐起来,擦一把冷汗,“有病啊你?”
田田穿上脏兮兮的鞋:“没病跑个球呀?”
厉雷叹口气,表情突然死了。他把手放在田田的肩膀上:“拜托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话,最好下次见面我们像从来不认识一样。”
田田惊异地望着厉雷,气得嘴唇直哆嗦。
厉雷颤抖着手点燃一支香烟,烟雾弥漫,空气黑了许多。
田田幽灵一样飘回了家。她找出自己的旅行包,嗖嗖嗖嗖往里面塞了许多衣服,塞进一本书又掏出来,毫不犹豫地扔进垃圾桶。那本书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从进门起,田田的爸爸就不远不近沉默着站在客厅注视着女儿的一举一动。田田走过爸爸身边的时候没有告别,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
爸爸平静地问:“很久是多长时间?”
田田拉上旅行包的拉链:“不知道。”
“你要去哪儿?”
田田背起巨大的旅行包:“不知道。”
爸爸低头沉思了两秒:“你,不会不回来吧?”
“不知道。”田田向门口走去。
“能不走么?”
“不能。”
厉雷蹲在田家门外一个垃圾箱旁边,拿截小树枝拨拉着地上一只硕大的毛毛虫玩,玩着玩着毛毛虫就给玩死了。他蔫儿吧唧走到田家房门前,举手刚要敲门,门突然打开,差点儿把他的鼻子碰塌,一阵闷疼,抬头见田田的爸爸正愁容满面地打量他。
田田背着一个巨大的旅行包走出来,见到厉雷,皱起了眉头:“那天不是说让我以后不认识你么?”
厉雷慌乱中结巴起来:“田田……那个……叔叔好。”
田田的爸爸不理厉雷,转脸对田田说:“路上小心,到地儿了给我打个电话。”
厉雷跟着田田走,田田一脸焦躁:“别烦人了!再烦人我一脚踹死你!”
厉雷笑了:“我被老爸打多了,皮厚,你要不是香港脚我还真不怕你踹。哥儿们,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带咱一块儿去呗。”
田田横厉雷一眼:“你管得着么?”
厉雷锲而不舍:“你到底要去哪儿?不告诉我,你就是小狗儿。”
“我谁都告诉,就是不告诉你!气死你!气死你!”
厉雷嗲声嗲气:“哎呀喂!我好生气好伤心啊!”然后摆出一脸无赖相,“你不告诉我,我就一直撵着你问,问到你撞墙。到底去哪儿?到底去哪儿?到底去哪儿?”
田田急了,朝厉雷的屁股踹过去,结果踹空了,自己差点摔倒。她气呼呼地盯着厉雷,发现了他那只熊猫眼。两人沉默着往前走。包太重,她出了不少汗,衣服贴在身上特别难受,只好用一个肩膀背着,这边肩膀酸了再换另一个。厉雷上来夺她的包,她夺不过他,愤怒地把包扔了过去。
田田舒展一下肩膀:“你眼睛怎么弄的?”
厉雷茫然地望着前方:“高考落榜被老爸打的。”
田田气愤地说:“榜上有名又怎样?没钱上还不是白忙活?”
厉雷苦笑:“我挺羡慕你的,天大的难事也能扛。”
田田别过脸:“不扛咋着,去死?死也要唱着歌死,那才叫悲哉壮哉!”她是借贷无门,又不想眼睁睁看着身患胃癌的老爸不去医院买药打针输液做化疗,就那样蔫儿吧唧,日复日月复月,坐天等死,于是凭借自己有歌唱天赋,打定主意出去拼一把。
“哦,”厉雷说,“我明白你要去干啥了。你先走,我回家取点东西麻利赶往火车站。”
两人在火车站售票处会合。
田田用手轻轻触碰一下厉雷眼睛周围的淤青:“疼么? ”
“不怎么疼了。”厉雷望着田田的眼睛,从她的瞳仁里看到了被泪水洇湿的自己,有点模糊不清。
田田的手机响了,打开瞥一眼,干脆把电池抠了。
到售票口了,田田问售票员:“最快发车的是哪趟车?”
售票员一脸的不耐烦:“你到底去哪儿啊?”
“随便。”
售票员瞪一眼田田:“44次,到终点站硬座一张票一百块。”
田田把一张百元钞递给售票员:“一张票。”
厉雷也掏出一张百元钞递进去:“一张票,44次终点站。”
田田木然地接过一张票,又接过一张票。
刚从售票处出来,就听到喇叭广播:“44次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没有检票的旅客请赶快检票进站!”
两人不敢怠慢,撒腿跑动起来。可惜厉雷跑不快,他背负得行李太多,尤其那个米把长的电子琴盒老碰腿,本来是他拉着她,现在倒过来,是她下死力拽着他在奔跑。黑发飞扬,灿烂的笑容在阳光反照下亮得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