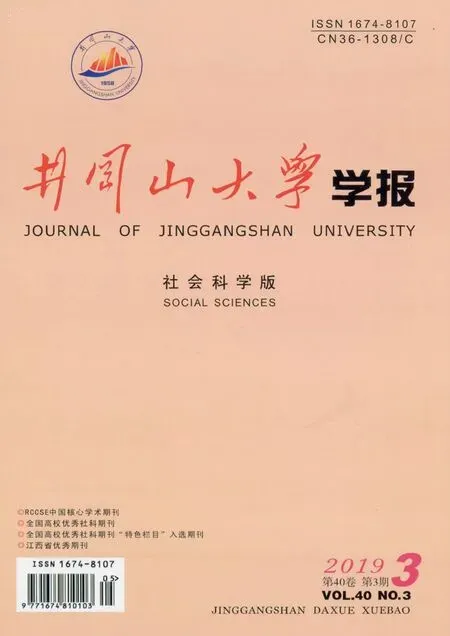在场批评、史识关照与学理拓展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苏区戏剧研究
李洪华,周 晶
(南昌大学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苏区通常是指1927年11月中华苏维埃诞生到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更名改制期间,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工农武装割据”方式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区域。苏区戏剧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开展的主要文艺宣传形式之一。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军中的宣传队就利用活报剧的形式编排了《打土豪》《活捉肖家壁》等剧目,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苏区戏剧日益成熟,自1929年古田会议后至1934年红军进行长征,苏区戏剧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
苏区戏剧研究是伴随苏区戏剧产生而发生的,最初主要表现为苏区时期有关戏剧的理论批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文艺的发展,苏区时期的戏剧经验在解放区戏剧运动中得到传承和发扬,但关于苏区戏剧的研究很少。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挖掘革命文艺资源和重述历史的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苏区戏剧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五六十年代有关苏区戏剧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苏区戏剧的收集整理,二是相关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对苏区戏剧的介绍。“文革”时期,除样板戏外,真正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研究几乎出现空白,苏区戏剧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文革”结束后,文艺在改革开放的文化语境中迎来了春天,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苏区戏剧研究进入到全新的阶段,无论是文献整理还是系统研究都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根据上述情况,本文主要分四个时段,即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新世纪以来,对苏区戏剧研究进行梳理概述。
一、在场的批评:三四十年代苏区戏剧研究的滥觞
据赵品三回忆,苏区戏剧活动最初是从部队中开始的,那时候每逢打了胜仗,总要召开群众大会,演出各类戏剧,这为苏区戏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教育工作,争取更广泛的人民群众支持,苏区在开展各类文艺运动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以指导革命文艺实践尤其是戏剧创作。初期的戏剧理论批评几乎与戏剧实践同时进行,具有鲜明的在场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革命文艺工作领导者为指导戏剧实践活动的种种尝试,如各类决议中的相关规定和号召。其次是苏区各文艺报刊发表的一系列极具时效性的戏剧评论和指导意见。再次则是为了确保戏剧思想倾向正确性和演出时效性而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首次明确了红军宣传工作的重大意义,从方针政策上明确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并将文化艺术与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苏维埃政府、各地方党委及群众团体在部署工作的同时也愈发重视文化艺术工作。为了促使戏剧艺术性与革命性相统一,戏剧理论研究工作显得尤为急迫。1933年11月15日,在瑞金正式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化研究组。据《红色中华》报道,该研究组的工作方向“主要侧重于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具体问题”,同时“拟定讨论提纲和供给材料给组员”,目的在于通过理论研究活动 “创造和培养我们工农兵大众自己的文化文艺作家”[1](P191),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戏剧理论,指导苏区戏剧运动,使戏剧更好地为革命斗争服务。
文化研究组成立之后,戏剧评论工作得以迅速展开。1933年5月23日,《红色中华》刊载了关于《蹂躏》《无论如何要胜利》剧作的评论。苏人的《工农剧社的转变》对上述剧作的悲剧题材和效果大加赞赏,认为“这两个剧本非常紧张的场面,悲壮的表演艺术,使台下观众怒吼起来……获得了相当成功”,充分肯定了在取材方面“工农剧社有了相当的进步”,并对未来创作能够“满足我们观众的需要”的戏剧表现了更大的期待[2](P185)。 1934年1月22日,《红色中华》以《一个精彩的晚会》为题,称赞为全苏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演出的《我——红军》一剧表现出“群众尤其是白区的工农劳苦群众斗争的坚决刚毅,与红军作战的坚决英勇,白军内部的动摇,与士兵革命化,以及各反动派在革命怒潮的汹压之下的鼠窜狼狈、末路”等,称赞其真正做到了“尽善尽美”[1](P209)。 虽然文艺服从于革命政治在苏区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戏剧评论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戏剧艺术的要求。1933年由两千余名从国民党军队叛逃出来的新战士演出了《暴动之前夜》,《红色中华》充分肯定了该剧对新战士发挥了 “充分的政治武装”的作用,然而《红星报》则以《这样的宣传是要不得的》为题,对该剧的两段唱词展开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空洞抽象的描写,是敌不过生动的反革命的煽动的”[1](P208)。此外,《红色中华》在 1933 年底到1934年初,还发表了系列反对旧戏的通讯,提及个别地区上演封建旧戏和封建迷信的行为,揭露地主、流氓等坏分子大肆宣传“许仙真君”、“南无慈悲大士”的鬼话,同时也报道了各地政府机构同封建旧戏的斗争情况[3](P118)。
苏区时期,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戏剧事业产生了较大的破坏性影响,较为严重的是1932年对《工农剧社章程(草案)》展开的斗争和1933年对戏剧《谁的罪恶》的批判。前者仅因草案中的几句“短短的序言”就被认定为具有“托洛茨基”的反革命政纲,把起草者的思想认识问题当成重大政治立场问题加以严厉打击,使得部分革命干部和青年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沙可夫创作的三幕话剧《谁的罪恶》因其“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而遭受到各方面的批判,剧中人物发出的“战争真是可怕的东西”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呼声,被指责为 “没有把握住反对战争的列宁观点”,“没有鲜明的指出欧战中无产阶级反对战争的实际斗争”,“陷入人道主义的泥坑中去”,“偷运了社会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作者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剧作 “没有有力的描写出非洲黑人对法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的战争”,使得“戏剧效果走上了歪曲的道路”[1](P207)。 然而,这种检讨在《红色中华》的编辑看来似乎还不够深刻,紧接着又于1933年9月15和18日在109、110期连载了阿伪的批评文章《提高戏剧运动到列宁的阶段》,文章犀利地指出剧本作者推卸责任,没有反省自身存在的和平主义意识问题[4]。在今天看来,这两场戏剧批评运动是当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制造的“肃反扩大化”政治事件的一部分,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虽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戏剧思想内容上的纯洁性,但其无端上纲上线和对戏剧工作者的恶意攻击都是有失偏颇的。
为了更好地引导中央苏区戏剧运动,苏区中央局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法则来保证戏剧实践活动的政治性和纯洁性。首先是在话剧发展日益稳固的基础上于1932年5月在瑞金设立了筹备委员会,经过了四个月对《工农剧社章程草案》的酝酿与激烈讨论,最终推出了新的《工农剧社章程》,该章程明确规定了工农剧社的机构和功能,其中作为常委组织之一的编审委员会,对剧本材料的编著和内容展开审查,开启了苏区戏剧活动的专门研究工作。随着戏剧运动的发展和壮大,由工农剧社和蓝衫剧团演变而来的苏维埃剧团如燎原星火遍布于中央苏区,因此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于1934年4月批准并颁布了《苏维埃剧团的组织法》,对苏区各省、县及革命根据地苏维埃剧团的组织机构、规模形式、演出任务及教育经费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为苏区戏剧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除了戏剧社团,各地方基层组织和乡村俱乐部也是戏剧创作演出的主要阵地,它们积极响应上级组织和领导的号召,为红色戏剧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中央对此也颁布了相关文件,如1934年的《俱乐部纲要》就规定了“戏剧及一切表演的内容,必须具体化,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采取当地群众生活的材料,不但要一般的宣传红军革命战争,而且要在戏剧故事里,表现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暗示妇女解放,家庭及生产条件等的革新,揭破宗教迷信的荒谬,提倡卫生及一切科学思想,发扬革命的集体主义和战斗精神”[2](P135)。 这些针对戏剧创作和组织制定的规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苏区戏剧研究的一部分。
从以上提及的各类会议决策、文艺报刊发表的一系列戏剧评论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可以看出,此时的苏区戏剧理论批评始终都围绕着“戏剧如何为革命服务”这个中心问题而展开,明确提出了革命戏剧必须重视社会效果,政治标准第一、革命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统一等原则。这种极具时效性的在场批评,一方面扩大了戏剧活动在苏区的影响和传播,使得苏区戏剧创作和演出等实践活动走向更加规范和制度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在极度敏感的政治环境和极左路线的双重影响下,戏剧批评难免有失偏颇,常常把戏剧作品在艺术和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上升到政治立场的高度加以挞伐,这对苏区戏剧的发展、戏剧人才的培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均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踏上了艰难的长征道路,存续了九年又十个月的苏区翻开了新的篇章,苏区时期的戏剧经验则进一步在解放区戏剧运动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苏区戏剧研究也随之告一段落。
二、使命的担当:五六十年代苏区戏剧研究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挖掘革命文艺资源和重述历史的工作迫在眉睫,苏区戏剧也因此受到各方关注。1950年李伯钊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回忆瞿秋白同志》,首次向人们介绍了苏区时期活跃的戏剧运动,为苏区戏剧研究提供了一些生动详实的材料。五六十年代苏区戏剧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苏区戏剧的收集整理,二是相关现代文学史著述对苏区戏剧的介绍。在戏剧的收集方面,由于苏区时期唯一一本由工农剧社创作、经瞿秋白同志编辑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剧本集《号炮集》因战乱而被遗失,至今仍下落不明,资料的缺失和交通的阻塞使得收集的工作难以有效展开,因此该时期只有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收录了赵品三、李伯钊和石联星等三篇亲历者的回忆性文章,首次较为完整地再现了苏区戏剧运动的艰难岁月。其中,赵品三的《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5],梳理了苏区话剧在革命队伍中的兴起及话剧活动从业余走向专业的发展道路,介绍并肯定了瞿秋白同志在剧本集体创作、审查预演、剧目出版、戏剧工作者培养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贡献,高度赞扬了苏区时期艰苦奋斗、集体参与的话剧工作作风。李伯钊的《为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议演出的剧目》[6],详细介绍了戏剧《最后的晚餐》《黑人吁天录》的故事梗概和演出效果。随后在“反右倾、鼓干劲”口号和江西省委宣传部的指示下,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在广泛调查、走访的基础上与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西分会于1960年合作出版了《红色戏剧》[7],收集了包括话剧、歌舞剧、活报剧、快板、双簧等形式多样的25篇完整作品,首次展现了苏区时期老革命根据地群众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但令人惋惜的是,上述史料收集和出版工作后因“文革”而被迫中断。
虽然这时期的史料收集成果寥寥无几,但是作为苏区文艺主要形式之一,苏区戏剧在相关文学史编著中受到关注,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及苏区戏剧的是1959年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集体编著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8],该书梳理了苏区文艺与抗日根据地文艺之间的关系,将其归结为“文艺第一次与工农兵相结合”,并为苏区戏剧设立单独一节,介绍了中央根据地戏剧运动的一般情况,概括出苏区戏剧由党领导、与现实联系紧密、群众参与、战斗与宣传并行等四个特点。此后出现的相关文学史著述,如1961年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和1962年吉林大学中文系编写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均简单介绍了苏区戏剧运动的发展和创作情况,并且都重点突出了瞿秋白对苏区戏剧的指导意义。除了以上集体编写的文学史著述外,这时期出现的少量个人编写的文学史著作也不同程度地关注了苏区戏剧,如刘绶松195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9],将苏区戏剧放置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框架下加以考察,认为它上承左翼戏剧下启延安戏剧,具有浓厚的革命意识形态色彩。丁易 1955年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0],则将苏区文艺运动归置于左翼文学运动中,重点介绍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学活动及根据地群众的文艺活动。可见,上述文学史著述大多是将苏区文艺放置在整个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内进行梳理,苏区戏剧并未单独获得重视。值得提及的是,由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1960年编写出版的《江西苏区文学史稿》[3],将苏区戏剧运动分为初创时期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两个时期,总结出苏区戏剧的六大题材,即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扩军运动、革命战争、抗日反帝、城市工人斗争和婚姻自由等,并归纳了苏区戏剧形式上短小灵活、气概上豪迈乐观等特点,是这个时期苏区戏剧研究的重要收获。
“文革”十年浩劫,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提出了严格的“一体化”要求。在此期间,除了作为极左政治产物的革命样板戏外,其他形式的戏剧艺术发展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苏区戏剧研究几乎空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红军撤离苏区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在一次围剿活动中收集了一些苏区文献资料,后被制成显微底片流传到国外。因此,“文革”时期国内有关苏区戏剧的研究工作被迫停顿,但海外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却颇有成果。在论著方面,主要有日本福冈大学秋吉久纪夫编写的《江西苏区文学运动资料集》[11]和东京大学中野淳子编著的《江西苏区红色戏剧资料集》[12]。前者辑录了大量苏区报刊登载的戏剧作品、戏剧评论和党内文件等珍贵资料,其中还收录了我国已有的研究成果,力图呈现出江西苏区红色戏剧发展的历史图景。后者则收录了当时尚未在国内出版的25个红色戏剧剧本。此外,在论文方面,也有樋口进、秋吉久纪夫、中野淳子等人发表的研究苏区戏剧的文章。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工作,不但弥补了这时期国内苏区戏剧研究的空白,也对今后苏区戏剧的史料挖掘和研究活动做出了贡献。
三、史识的关照:八九十年代苏区戏剧研究的发展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进行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文艺领域也在八十年代解冻并迎来了新的春天,第四次文代会强调了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各种文艺新潮开始涌现,学界也出现了“重写文学史”的浪潮。苏区戏剧作为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战时产物,在二三十年代因其通俗性、时效性和战斗性备受推崇,然而在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八九十年代,苏区戏剧又因以上特性而受到“另眼相看”。因此,苏区戏剧作为革命文学传统一脉,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并未得到重视。如果说冯光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13]、田仲济和孙昌熙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4]还将苏区戏剧放置在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体系中加以考量,而孙中田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5]、邓英华和于寒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6]则有意抹去了苏区戏剧的存在,只简单介绍了上海左翼一批剧社的发展始末。钱理群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7]虽将苏区戏剧同左翼戏剧和熊佛西等人领导的农民戏剧实验一起纳入“广场戏剧”的大范畴,某种程度上拓宽了苏区戏剧的研究视野,但是“广场戏剧”这一概念却模糊了三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并且对苏区戏剧的介绍也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展开论述。
虽然苏区文艺在当时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苏区文艺和苏区戏剧在这个时期学术研究领域的进展。首先在著作方面有了较大突破,如1985年汪木兰和邓家琪合编的《苏区文艺运动资料》[18]、1987 年左莱和梁化群合著的《苏区“红色戏剧”史话》[19],均收集了大量苏区文艺史料,分析了苏区戏剧运动的现实状况和主要特征。1988年全国文化系统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成立,使得革命文化史料的收集工作得到全面展开,苏区文艺也在史学范畴内得到了进一步重视。其中,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8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20]就有“红军时期”的珍贵史料;1994 年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写的《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21]则是目前为止内容最为详实的一本苏区文艺史料集,书中汇编了自1929年到1935年中央苏区相关部门发布的文件及材料,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文化法规、社团和戏剧活动,并在前言部分较为粗略地梳理了整个戏剧运动的发展经过、戏剧社团的建立、戏剧创作的方式及题材等。1995年由刘国清编著的《中央苏区文学史》[2],则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梳理诗歌、散文、戏剧、小说这四种文艺形式在苏区的发展概况,并在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左”倾路线给苏区戏剧创作带来的危害。1998年刘云主编的《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1],将中央苏区戏剧史放置在本书最显著的前端,详细介绍了苏区戏剧在不同时期的艺术形态及前进方向,并且重点突出了戏剧理论和文艺批评。通过对以上著作的翻阅和整理,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苏区戏剧研究仍然未从整个苏区文艺的范畴中独立出来,均是作为革命文艺形式之一穿插其中。只有1992年汪木兰和邓家琪合作编著的《中央苏区戏剧集》[22],完全以苏区戏剧为研究重点,并收录了现存完整的74种剧本材料,弥补了长期以来戏剧文本研究的空白。
在论文方面,论者多为一些长期研究苏区文艺的专家学者和苏区运动的亲历者。汪木兰的《活跃在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剧团和高尔基戏剧学校》梳理了苏区剧团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的章程和教育方针,并对戏剧的巡回演出也做了详细介绍[23];何宇的《苏区“红色戏剧”》特别突出苏区戏剧中的苏联特色[24];刘国清的《中央苏区工农戏剧大众化简论》分析了苏区戏剧的大众化特征[25];邵葆《中央苏区戏剧与瞿秋白——访老红军韩进》[26]、胡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苏区“红色戏剧”史话〉序》[27]、方志纯《忆赣东北苏区的戏剧活动》[28]等,分别以亲历者的身份回忆了当年的演出盛况和戏剧工作者的努力。总之,八九十年代的苏区戏剧研究无论是在队伍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果上都较此前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一些部门和专家在史料整理及其相关研究方面明显增强了史学意识,为后一阶段的苏区戏剧研究提供了更为充实的史料和开阔的视野。
四、学理的拓展:新世纪以来苏区戏剧研究的深入
新世纪以来,苏区革命精神和原苏区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2012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旨在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在上述背景下,苏区研究成为学界热点,苏区戏剧研究也得到全方位学理性的拓展。
苏区戏剧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创作和演出活动十分注重大众化和时效性。新世纪苏区戏剧研究重视从实践角度对苏区戏剧运动尤其是一些剧团活动展开研究。黄涛涛的硕士论文《论江西苏区的戏剧运动》[29],对苏区戏剧运动的背景、特点、作用、意义等各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归纳。何立波的《中央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30],从整体上梳理了苏区专业化剧团的发展演变之路。黄文华的《论蓝衫团与苏区文艺建设的繁荣》[31],重点介绍了蓝衫团的相关活动和主要特征。谭宁佑的《“工农剧社”是“中国文联”的雏形》[32],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从成立背景、工作宗旨、指导原则等方面展开分析,认为“工农剧社”是“中国文联”的雏形。这一结论新颖而颇具启发性,为今后苏区戏剧社团研究提供了新角度。
新世纪以来,苏区戏剧创作研究主要围绕创作主体、创作形式、创作题材等方面展开。苏区戏剧大多由集体合作完成,也有少数独立完成的,其中贡献突出者有李伯钊、瞿秋白、沙可夫、胡底、钱壮飞、李克农等。郭珊珊的《从苏区到延安——李伯钊与根据地戏剧发展研究》[33]、杨会清的《红色戏剧的拓荒者——李伯钊在中央苏区》[34]、何立波的《第一次将长征题材搬上舞台的“红色戏剧家”李伯钊》[35]、 贾翼川的 《论红色戏剧家李伯钊》[36]等,都从不同方面探讨了李伯钊在苏区戏剧创作中的经历和贡献,贾翼川还进一步分析了李伯钊戏剧创作中的某些公式化、教条化倾向。瞿秋白也是苏区戏剧创作主体研究的重点,郭珊珊与刘文辉的《从左翼到苏区——瞿秋白大众戏剧理论的建构》[37]、刘云的《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的卓越贡献》[38]、傅修海的《瞿秋白与文艺大众化思想的中国化进程》[39]等,多以瞿秋白从精英知识分子到革命政治家的身份转化及其大众化戏剧理论为中心展开论述。傅修海的《瞿秋白与中国现代集体写作制度——以苏区戏剧大众化运动为中心》[40]还进一步探讨了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戏剧集体写作制度构建的作用及影响。此外,王学海的《生命不在骨架的承载——论沙可夫的戏剧创作》[41]、许爱珠和闵庆莲的《“龙潭三杰”对苏区戏剧发展的贡献》[42]、何立波的《红军将领与苏区戏剧运动》[43],探讨了沙可夫、胡底、钱壮飞、李克农等在苏区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
苏区戏剧艺术形式丰富多样,不但有活报剧、歌剧、舞剧,还有地方戏剧、木偶戏、皮影戏和京剧唱词等。当前有关苏区戏剧创作形式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活报剧和舞台剧,如廖华英和苏英伟的《红色体验与苏区活报剧的发展》[44]、刘文辉的《活报剧在苏区:历史与形态》[45],分析了活报剧在苏区的演变及其特点。胡敦伦在 《试论苏区活报剧的灵活性、新闻性和综合性》[46](P365-373)中进一步对活报剧的数量和题材做了详细的分类,区分了活报剧与戏剧在综艺性上的不同。李上、李启福的 《中央苏区戏剧舞蹈在革命战争中的重大作用》[47],围绕戏剧舞蹈的政治性、群众性、生活性等特点分析了苏区戏剧舞蹈的历史意义。苏区戏剧大多取材于苏区革命斗争和群众生活,这些方面也受到研究者关注,如贾翼川的《论20世纪中国“红色戏剧”》[48],将苏区戏剧分为工农红军革命斗争题材和革命群众揭露旧社会黑暗罪恶题材两大类,此外也涉及了《最后的晚餐》《黑奴吁天录》一类具有知识分子特征的戏剧。
苏区戏剧的政治效用也是新世纪以来的研究热点,其中以王永华的《苏区戏剧与中央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互动》[49]和周建华的《意识形态视域里的小故事和大历史——中央苏区戏剧审美意识形态化考察》[50]为代表,两者均把苏区戏剧看作意识形态的表征符号,后者还从美学角度分析了苏区戏剧在故事选择、人物刻画、斗争性语言、对立性思维、舞台布置等方面暗含的革命政治因素。此外,郑紫苑的《苏区戏剧教育功能:大众化与化大众》[51]分析了苏区戏剧的教育功能,刘魁、江明明的《革命性与娱乐性:中共与民众互动视野下的苏区戏剧》[52]则分析了苏区戏剧的娱乐功能。
苏区戏剧与民间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熊岩、谢玲的《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的文化人类学思考》[53]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分析了苏区戏剧的敞开式演出形式、军民共演参与形态、戏剧与生活的同构性等特征,认为这是对戏剧本原状态的回归。刘文辉在《仪式的“复活”:民间泛戏剧形式在中央苏区的遗存与再造》[54]中认为,一方面革命者极力反对传统旧戏并致力于瓦解传统文化秩序,另一方面民间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使得苏区戏剧在宣传革命时也要“入乡随俗”。对此,江明明、刘魁的《新与旧:中共与民众对苏区戏剧的取舍研究》[55]也持同样观点。郑紫苑的《民间戏剧“政治化”与乡村日常生活的变迁——以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客家民间戏剧的改造为例》[56]、《论中央苏区戏剧对客家民间文化重构与客家民间文化的自我保存》[57],将苏区戏剧与客家文化联系起来,分析了苏区戏剧在形式、意象、语言等方面对客家民间文化的渗透和重构。
纵观近百年来的苏区戏剧研究,我们作出如下结论和瞻望:一、苏区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倾向和特征,早期主要表现为注重政治时效的在场批评,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史料的收集整理,上世纪末至新世纪以来有了进一步的学理性探讨。二、苏区历史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苏区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环,戏剧是苏区最重要的文艺形式,在文艺大众化、文艺与革命相结合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苏区戏剧研究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三、苏区涉及范围广,除中央苏区外,还有鄂豫皖、湘鄂川、鄂豫陕等苏区,目前苏区戏剧研究多集中于中央苏区,系统、全面、深入地挖掘苏区戏剧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构建苏区戏剧研究的完整体系应该是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