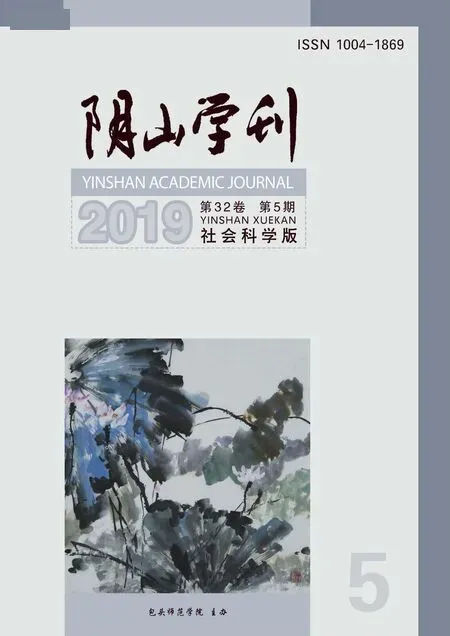王安忆《富萍》中的空间书写 *
潘 妍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当代西方学术知识界从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趋势,这种转向针对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空间阐释传统,颠覆了传统时空观念中空间的从属性与同质性。“它将要显示,空间不是单纯的社会关系演变的舞台,反之它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解构和转化。故空间说到底也是社会和文化的空间,包括身体在内,它们都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产物。”[1]337成为显学的空间理论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学作品往往是现实生活最直观的反映,许多作家都注目于自己所熟悉的空间地域进行书写。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现代都市之一,有着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作为城市空间,它的形成与变迁都极具代表意义。作家王安忆对于上海一直进行着孜孜不倦的书写,她自身的成长经历就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而其对于空间的敏感以及对于城市精神的洞悉使得她的书写为解读上海城市空间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富萍》描述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在小说中王安忆关注了上海较少被人提及的底层空间和底层劳动人民。王晓明在《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中将《富萍》解读为对于90年代在新城市形态笼罩下的有关“老上海”消费主义式的“想象的怀旧”的一番抵抗。[2]在空间理论的视野中,可以明晰地看出王安忆有意地拉开与传统老上海空间的距离,并将认同的价值观和态度倾向普通劳动者。在被遮蔽的底层空间中,王安忆对于上海进行了别样的书写与思考。
一、典型空间意象的书写
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不同的空间约束着我们的行为和感受,同时,我们的集体性、社会性也产生了巨大的空间和场所。大卫·哈维在其著作《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里指出城市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空间区隔,“新空间的建构与区隔从根本上影响了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秩序,在此基础上又将形成新的阶级意识形态与认同表述。”[3]所以说,空间的变化是一个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的过程。人对于空间意象的特定经验往往取决于空间特性及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富萍从扬州乡下来到繁华的上海,经历了巨大的空间变化,在全新的空间中,她的思想观念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富萍始终用带着乡下人经验的眼光观察上海,其空间体验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表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面貌。
如果想从空间解读人的生存状态,街道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在一个城市中溜达闲逛就是在发现空间位置的意义。在街道上溜达的人,成了这个都市的阅读者。富萍通过城市的街道来熟悉上海,在街道上有了对上海最直观的空间体验,她的目光不仅巡视了“弄前街道”,还勾联了弄堂与弄堂之外的世界。淮海路的街道都是整齐干净的,两边是林立的华丽建筑,但上海人所喜爱熟悉的摩登、繁华并不能打动富萍。“走在街上,就像走在水晶宫里似的,没有一星土,到处是亮闪闪的,晃眼”[4]33。富萍觉的好看,但到底是与她隔了一层,和她关系不大,她真正感兴趣的是摩登繁华的水晶宫之下的劳动和生活空间。在李天华的事情上与奶奶矛盾激化了之后,周围的人都孤立富萍。于是富萍就在街上闲逛,走在街道上,城市的天空都是逼仄的,被楼房划成一块儿一块儿,压得人透不过气。马路窄小且昏暗,还有不怀好意的人藏在阴影之中,在这样的空间里,富萍丧失了安全感,她意识到自己的孤苦无依。而在闸北和梅家桥,作者所描写到的街道就是另一番模样了。闸北的街道不像淮海路的巷道那样狭窄拥挤,也不像商业区的马路那样精致摩登。闸北的街道不够平直整顿,缺少规划。梅家桥的街道更是凌乱曲折,周围全是低矮歪斜的房屋。但走在这两地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是各种各样的劳动场景,或是街坊邻居聚在一起洗衣服做饭,或是各家忙碌着自己的营生,或是大大小小的家庭经营的小店。由于靠近河边。这里的街道往往通向河岸,在街道上随处可见自然风光,路边的水塘野草都昭示着勃勃生机。富萍走在淮海路的街道上只感受到了不真实的繁华,在闸北和梅家桥才有了空间的实感,在空间所呈现的表面样态下的是人们的生存状态。位于底层的生活虽然不够繁华富有,却有着内在的充实。
列斐伏尔说,空间看起来是中性的,但就其本质来说,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空间的占有与划割就是政治经济地位的体现,继而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即便在同一个大城市的内部,中心城区的发展与其郊区的城镇化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反映在发展规模与发展模式等方面,而且也同样反映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上。”[5]15大都市是巨大财富与奢侈消费的聚集地,城市中心有摩天大楼、富人住宅区、五星级宾馆,有为精英和有钱人提供的休息娱乐场所,但是城市边缘却都是棚户区和穷人。“更重要的是,棚户区通常是处在豪华、富裕的丰碑所产生的阴影里。”[5]16《富萍》中城市中心与棚户区的空间对立也十分鲜明。
小说一开始就讲述了各种各样的上海市中心住房。有侨民公寓、弄堂公寓、军区大院等等。不同的住房空间昭示着不同的等级组织、生活样态。富萍的舅舅住在闸北的一片棚户区中。棚户区位于城市边缘的贫民聚集地,建筑比较杂乱。相比城市整齐的居住空间,棚户区更像聚集在城市周围的村庄。上海繁华地带寸土寸金,人们的生活空间相对拥挤。富萍和奶奶共用一张床铺,和奶奶吵了架也只能到外面的公共空间去。而在闸北,生活空间就相对宽敞了。舅舅家是独门独户,拥有自己的厨房,富萍住在阁楼上,那是属于她自己的空间。宽敞与拥挤是相互对立的概念,而“宽敞与实现自由的感觉密切相关,自由意味着空间,意味着有力量和足够的地方去活动。”[6]42过完年,孙子来上海接富萍回去。当富萍向李天华提出分出来单过的请求时,李天华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我父母亲怎么办?”这次对话直接导致了富萍的不辞而别。李天华家中有众多亲戚与弟兄姐妹,他本人生得柔弱,身体方面就缺乏作为劳动者应有的结实和硬朗,再加上性格温顺,他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占。自幼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富萍厌倦了孩子和没完没了的亲戚,她与李天华两人的矛盾焦点在于富萍想谋得一份独立的生存空间,但李天华没有办法为她提供。而当富萍在梅家桥与残疾青年结婚之后,“挨着小披屋的山墙,新搭了一个更小的披屋。”[4]254富萍在城市中有了自己的房子,拥有了独立的生存空间。
除了街道和房屋这两个最容易体现空间差异的意象,小说中还有一个空间意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女中。整本小说都以人物或剧情事件命名,唯独有“女中”和“剧场”两个以空间命名的章节,而关于女中的空间体验鲜明地反映了富萍在城市中的心理,在整个小说中有特别的意义。在淮海路,富萍感到最愉快的时光是在一个产妇家中洗尿布的日子。与之前描写在奶奶那里的家长里短不同,富萍在产妇家做活时,王安忆着重描写了女中这个学校。富萍做工的地方在女中的后边,隔着一排篱笆墙可以看到一块沙坑和一些健身器材,时不时就有一些女中的学生来这里做游戏或者聊天。在这片空间中,富萍显得放松了很多,对于周遭的一切也带上了这个年纪女孩应有的好奇和愉悦。她一边干活一边听女中的学生聊天做游戏,“那里的动静有一股子生气,解除了一些富萍的寂寞。”[4]57由于处在陌生的城市中,再加上长时间待在亲戚堆里,富萍总是感到沉闷,而在外做工的这个空间对于富萍来说是独立的,没有认识的人的目光注视,同时又是在创造收益。因为女中是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富萍在这里可以接触到一些陌生的同龄女孩,女中的普通女生也让富萍感到亲切,从而有了很好的空间体验。所以当后来奶奶和富萍说女中学生的坏话时,富萍还有些愤懑不平。当富萍与奶奶吵架之后,她都会走到女中这里散心,期望和这里的什么人交谈一下,但这时候的女中往往是寂静的,有一次晚上富萍走到学校来,听到篱笆墙那里有人在哭泣,她试图想要和那个人交谈,但里面的人在听到动静之后就走远了。这一个细节描写将富萍寂寞失落的内心刻画得十分鲜活,女中这个空间也因此变得生动了起来。
二、小说中空间意义的获取和定位
空间意象构成了空间的符号意义,语言构成了文学的符号意义,空间与文学有着天然的同构关系。《富萍》中的诸多空间意象串联起了整部小说的一个主题——在城市中立足。不仅仅是富萍,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想在上海谋得一个生存空间。每个人境遇不同,所处的空间就有所不同。小说围绕众多人物的生活,对空间的意义进行了定位。
奶奶从扬州乡下来到上海,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成为被上海所接纳的普通市民中的一员。虽然奶奶做的是保姆的职业,但却住在位于上海中心的淮海路。奶奶在不同的地方做过保姆,最后决定只在淮海路做工,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物、生活都与奶奶合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空间氛围使得奶奶选择了淮海路。在淮海路,有很多像奶奶这样的人,比如同为帮佣的吕凤仙。吕凤仙之所以在那片居民中受尊敬,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她有自己的房子,和奶奶那种吃住在东家的保姆不同,吕凤仙和做的人家分得很开。每天工作结束,吕凤仙会在自己的屋子里给自己烧晚饭吃,吃过晚饭又精细地记账,小说对吕凤仙晚上在家中做的琐事描写得充满了仪式感,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有着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因此她在这座城市生活得更有底气。相较于吕凤仙,奶奶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后路着想。虽然奶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老上海,但是她在上海并没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就连睡觉也是和东家的两个小孩共用同一间屋子。之前奶奶对于做工的人家的挑剔,多半因为她住在那样的家中感到不适。在城里没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奶奶终归要告老还乡,因此才认了李天华这个孙子,尽力地给亲戚帮忙,在安排婚事上也是尽其所能拉拢更多关系,为的就是以后回到乡下可以名正言顺地住到孙子家去。
如果说奶奶这样的保姆能够在城里立足多是因为依附于做工的东家,那么富萍的舅舅舅妈能够在上海边缘生存下来,就完全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富萍的舅舅孙达亮十二岁就跟着大伯离开家乡做了船工,行走于苏州河上,“终年在水上漂流的人,做的梦也是岸上的房子。”[4]122他们在1963年终于上岸,用辛苦攒来的积蓄买了一个船老大的破屋,在小说的叙述中,这是开始全新生活的标志。这种空间体验是处于淮海路那种流光溢彩的消费空间、甚或柴米油盐的弄堂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人所不熟悉的,“就像是在上海空间的整一想象中打入了一个楔子”[7],虽然没有像奶奶那样住在繁华的城市中心,但岸上的房子为他们提供了独立的生存空间,他们因此能够在上海立足,世辈繁衍下去。
富萍在上海的漂泊轨迹也体现了她在上海寻求立足和发展可能的过程。富萍刚来到奶奶家,就尝试着谋求自己的空间。一开始富萍只能在出去买菜或者送小孩子去电影院的过程中看一看这座城市。有时她会借买菜为缘由走得绕远一些,去看看在城市中真正引起她兴趣的东西。虽然她渐渐地开始熟悉淮海路的街道,但是始终与这座城市有着隔膜。在奶奶家,她只能和别人分享空间,而上海的弄堂又充满了流言和各式各样的议论,让富萍怎样都不自在。然而在舅舅家,她有自己的小房间,没事了也可以去找小君或是到河边、梅家桥散步。她的活动范围变广,与周围的人交往与接触更加自如,相比起来更加自由。富萍最后在上海这座城市扎根下来,虽然处在边缘,但还是拥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奶奶终归是依附于做工的人家,她最后还是得回到乡下。富萍在上海的漂泊从淮海路到闸北再到梅家桥,看似是走了下坡路,逐渐远离了中心地带;但实际上,她是远离了老上海那个繁华、虚无的空间,而进入了一个平凡但充实的劳动空间,成为了城市中最平凡的一名劳动者。虽然上海城市中心拥有“老上海”想象式的华丽和璀璨光韵,但光韵终归会褪去,还是回归踏实的劳动空间最为可靠。
在淮海路,唯一可以引起富萍亲切感的恐怕就是充斥在日常生活中的劳作和忙碌。“富萍虽然与‘繁华的街道’有着隔膜,不过却从市民日常生活的踏实中找到了心理上的补偿”[7]。小说对富萍通过橱窗看商店伙计工作的场景描写得十分细腻。例如在布店,扯布的声音、打算盘的声音、发票在铅丝上滑过的声音都在富萍的心中激起了回响。在这样的商场中,富萍的注意力并不是在商品上而是在其间人们的劳动上。当后来吕凤仙为她介绍工作时,她很感动,一改之前对于吕凤仙不好的观念,吕凤仙给了她在这个空间中立足的可能性。比起那些小恩小惠,富萍更相信劳动的力量。淮海路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空间,像奶奶这样的人虽然有着小市民的习气,但却都是凭借劳动而谋得生活,这也是富萍虽然有隔阂但一直尊重奶奶的原因。
相较于对城市中心空间的敏锐与挑剔,闸北、梅家桥这样的棚户区被写得充满诗意,在这个地方,全然没有了之前的犀利,而都是理解和同情。别人对垃圾船上的船工抱有偏见,说他们是吃苍蝇下饭。王安忆为船工辩护道:“苍蝇是有的,而且很不少,但不见得是下饭吃。”[4]105实际上垃圾船的工作确实是有些腌臜的,但是垃圾船的船工都很勤劳也爱好干净,所以与其说王安忆是将这样的空间写得诗意,不如说她态度鲜明地赞美了这些劳动人民。棚户区的房子十分凌乱,巷道也是七拐八折,“但在低矮歪斜的屋檐底下,却也钉着正式的,蓝底黑字的地址门牌。”[4]229本应该呈现的破败、贫穷场景都变成了平和、热闹的劳动场景。里面的人操着各式各样的营生,但是芜杂琐碎的营生难掩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王安忆似乎有意地避开贫民生活拮据、腌臜的一面,将生活的艰难隐藏在心无旁骛的劳动后面,描写甚至带有了牧歌情调。最后作者用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大水结束了小说,表明富萍成功在城市中立足的同时暗示了生活的延续,显现了生命的韧性与可能,给读者留下了诗意的想象空间。
三、小 结
不同于当时普遍的描写上海的小说,《富萍》没有写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没有写新式的公寓酒店,即使写到了,也是从另一个角度,通过保姆的眼光、通过市民们的议论、通过街道上的橱窗或是通过富萍这个乡下人的体验。空间并不是均匀的、单一的,上海城市空间有着诸多的层次,而《富萍》所采取的视角使上海失去了那样光鲜亮丽的浮华表面,充满了烟火市井气,其中渗透着作者对于人情世故的洞察和敏锐。整篇小说围绕底层空间,勾勒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劳动场景。书中每个人都勤恳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城市边缘地带的人们为谋取生存空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这些各样的生存空间背后,是王安忆对于劳动人民及劳动本身的赞美。
小说中富萍选择逃离自己嫁到一个更糟糕的家庭中去的命运,在城市边缘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王安忆通过富萍的漂泊与选择表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可贵,热烈地赞美梅家桥人朴素的生活状态,赞美没有被贫困、粗俗所损伤的人性的美好。富萍最终在梅家桥扎根,并且孕育了后代,生活得以延续下去。正如与富萍的名字音同的浮萍一样,漂在水面上无依无靠,但是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富萍在上海漂泊了一番,最终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土壤扎根。除了《富萍》,王安忆在很多小说中都有关注过普通劳动者,例如《骄傲的皮匠》《妹头》《悲恸之地》等等,但多是聚焦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某一单个劳动者,所书写的也是她所熟知的市民生活。其作品中关注一个形成整体区域的贫民空间的小说并不多,《富萍》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上海是王安忆成长并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处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消费主义方兴未艾的时代,王安忆敏锐地发现了浮华的上海发展中所存在的不合理不安定因素。贫富的分化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在城市的空间规划中。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也是这样,形式主义发展到顶峰之后遭遇了困境,各种各样的主义已经没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是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不断地刺激着作家们敏感的神经。王安忆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中坚守着,努力挖掘日常生活中的批判力量。她将目光放在劳动者的身上,就是在试图寻找一种力量可以对抗因社会变动而带来的虚无和功利。王安忆不惜牺牲自己的敏锐观察力及细腻精致的口吻,就是因为更愿意相信劳动的力量,在《富萍》中营造的诗意空间也是希望以富萍的选择来凸显当下生活应该有的前进方向。而小说《富萍》也因其独特的空间特点而区别于普通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给我们呈现了不同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别样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