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者
汤成难

《2018.壹捌.028》徐勇民纸本9.9×13.6cm20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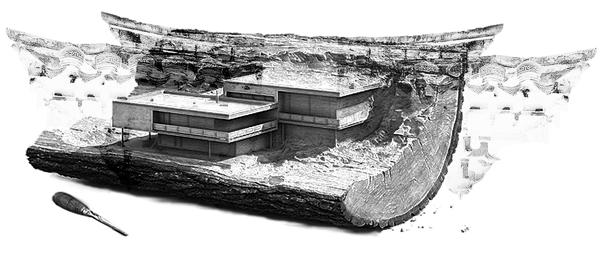
1
父親杨泉水第二次从城里回来,是我去村口迎接的。刘彩虹不允许我和妹妹去,说谁去就打断谁的腿——她没有一双好腿,见谁的好腿都想“打断”。当然,她并没这么干过,只是说说而已。
秋天刚刚结束,离春节还远,我们不知道杨泉水为什么又回来了。他像个孩子一样,一次次地被我们送离,又一次次地跑回来。那天我们正在给猪喂食,看一头懒洋洋的黑猪从草灰上爬起来——尽管懒,但在吃食上毫不含糊。阳光刚好,风也轻柔,刘彩虹似乎很高兴,伸出拐杖拱了拱黑猪的脊背,脸上的褶子便聚起来了。就在这时,路上有人对我们说,你家杨泉水回来了。我和刘彩虹都愣了一下,好像一时想不起杨泉水是谁似的,我看见刘彩虹脸上的笑容被风吹走了,皮又松塌下来。
杨泉水是走回来的,包裹比离开时多了一个,它们参差不齐地挂在身上,猛一看,像是被包裹劫持着似的。小官村离车站有十七里路,那些从城里回来的“老板们”(我们这里喜欢称去城里干活的人叫老板)都喜欢坐着“放屁虫”,那是一种行驶起来发出“哒哒哒”声音的电动三卡,光是声音的震耳欲聋,就很威武。也有一些不坐放屁虫的——毕竟需要十五元的费用,便选择车站门口的摩的,也能发出一点代表疾驰的声音。但杨泉水是走回来的,就这一点,便叫人气愤。当然,最气愤的人应该是刘彩虹,她咬着牙把一张脸拉得很长——这个时候回来算什么呢?为什么不等到年底呢?
刘彩虹的问句是不需要回答的,她也不会像泼妇那样跟杨泉水吵架,对于令她生气的事情,刘彩虹喜欢以回娘家或者躺在床上绝食来表示。杨泉水回来的时间的确有些尴尬,在我们小官村,除了老人和小孩,平日里很难看到这样的劳力,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年,人们似乎都不喜欢待在村子里了,背上包袱离开村庄,小官村的人也不清楚他们都去了哪里,仿佛小官村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城市。出去了就很少再看见他们,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回来一次,也有的三四年才回来一次,看到的时候人都变了样。于是小官村的过年便更像过年了,热闹得恍若幻觉,那些哒哒哒的放屁虫不停地载着从城里回来的人们,拖着长长的声音驶进村子。越临近春节,哒哒哒的声音越络绎不绝,此起彼伏,仿佛也成了年味之一。
杨泉水没有在那样的声音中回来,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沮丧。他从村庄的尽头缓缓走来,太阳将他的影子一直送到我的脚下。杨泉水腾出一只手在我头上摩挲着,好像把要说的话都从脑袋上揉下去似的——而实际上,杨泉水原本就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我们默默往家走,阳光在背后推着我们。
杨泉水是个篾匠,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刘彩虹说她看上杨泉水正是从他的一双手开始的。“你们那时还小,记不得了,” 刘彩虹对我和妹妹说,“你父亲整天就坐在那棵槐树下给人编篾器呢。”
我怎么会记不得呢,杨泉水坐在一堆竹篾之中的样子,那样的画面,仿佛定格在春天——槐花开得正欢,香气四溢,槐花下面是杨泉水,认认真真地编着篾器。杨泉水的手很巧——篾匠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劈篾,一筒青竹,对剖再对剖,剖成竹片,再将竹皮竹心剖析开,分成青竹片和黄竹片,再根据需要,竹皮部分,剖成青篾片或青篾丝。剖出来的篾片,要粗细均匀,青白分明,再把它不同的部位剖成不同的篾。劈篾时,杨泉水更加安静,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场的,他送给我的竹篾球可以作证。编篾的工具很简单,篾刀,小锯,还有一件叫“度篾齿”的特殊工具——这玩意儿不大,却有些特别,铁打成像小刀一样,安上一个木柄,其中一面有一道特制的小槽,它的独特作用是插在一个地方,把柔软结实的篾从小槽中穿过去后,篾的表面会修饰得更光滑和圆润,起到打磨作用,这叫刮篾。
附近的几个村子也找杨泉水编篾器,他们把竹子扛来,支在老槐树上,给杨泉水点上一支烟。杨泉水不爱说话,听着,把对方的要求记下:一只鱼篓子,一只淘米篓,要是料多的话,再加一只竹篮子。也有人带一张纸片过来,纸片上画着一只圆匾或八角篓子。他们递过去,问他这样的能不能编?杨泉水看两眼就明白了,回说,能呢。
刘彩虹说你父亲只要赶几个早就能将它们做完。这些我是相信的,杨泉水的手很大,但灵巧,锯、切、剖、拉、撬、编、织、削、磨,一双大手在竹篾上如行云流水。
2
刘彩虹在院子里扫地,杨泉水跟她说话,她头也没有抬起来,但扫得更用劲了,好像跟笤帚怄气似的。杨泉水小心翼翼地进屋,打开包袱,拿出几样小玩意递给我和妹妹,然后歪着脑袋看着我们傻笑。这时刘彩虹进屋了,杨泉水又拿出一只木梳子给刘彩虹,说这是他做的,枣木的。刘彩虹没接着,继续虎着脸进进出出。每次刘彩虹跟杨泉水闹别扭,都让我们为他们捏一把汗,仿佛刘彩虹扯着的一根绳子,越来越远了,远得杨泉水花很长时间才能将那根绳子拽回来。
吃饭的时候刘彩虹告诉杨泉水,木梳已经不兴时了,现在没人用木梳,都用塑料的,五颜六色,特别好看。
杨泉水愣了一下,将梳子在手里摩挲半天,好像一时不能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每天都在天翻地覆地变化。
杨泉水是在1990 年不做篾匠的,那时候一年也编不上几个篾器了,有人从外面带回来了很多塑料篓子,红的、黄的、蓝的……颜色鲜艳,轻巧。杨泉水第一次看见塑料篓子时十分惊讶,他不明白究竟怎样的手艺才能将这些塑料编出来。后来才知道,它们都是模具制成的。“先将模具做成篓子的形状,再进行挤压。”有人对杨泉水说,其实他们也没见过制作流程,但告诉他的人就是这么说的。
刘彩虹说父亲手巧,手巧还怕吃不上饭?1990年后杨泉水不做篾匠了,当然,这里的“不做”也由不得他去选择。他把工具收起来,隔三差五地又拿出来磨一磨,劈一根竹子,剖成篾丝,用几个白天时间做成一只竹匾或竹篓,这些做好的东西塞满了屋子,使人有种被淹没的感觉。
杨泉水说,他怕手生。但刘彩虹不乐意了,一张脸就撂下了,杨泉水便知趣地收起来,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抽烟。
我大一点的时候,杨泉水还教过我如何编篾,我们假装去大堤上挖野菜,杨泉水把篾刀、度篾齿放在篮子里,上面盖上铁锹。爬上大堤,就看见竹林了。“竹子要挑结疤少的,做出的竹器才漂亮,”杨泉水砍断一根翠竹,削去枝叶,锯断,再用篾刀流畅剖开。“青篾丝柔韧,弹性大,可以剖成比头发还细,适合编织细密精致的篾器;黄篾柔韧性差,难以剖成细的篾丝,只能用它编竹椅或竹匾了……用对了材料,编出的东西才会好。编的筛子,要精巧漂亮,方圆周正;织的凉席,要光滑细腻,凉爽舒坦……”。
这时候的杨泉水变得特别善谈,早晨的阳光被竹叶筛成无数光斑,在他脸上闪闪烁烁。风吹来,竹林沙沙作响,我突然感到杨泉水不是在说给我听,而是说给自己听,说给风听,说给竹林听……
3
杨泉水去学木匠的那年,我已经读小学了。有手艺还怕吃不上饭——刘彩虹说得对,杨泉水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出师了,很快从一个篾匠变成了一个木匠。杨泉水的身上总是带有淡淡的木香,鞋上,或者衣服上偶尔会沾着一个刨木花,他看见了,便用两个指头捻起来,轻轻丢下。看得出来,杨泉水还是很喜欢现在这个行当的,你要是问他为什么喜欢木匠这活儿呢?杨泉水会嗤嗤地笑,告诉你木头香,跟竹篾一样香。
村里有人要做家具了——往往是一些快要办喜事的人家,早早就来“请”杨泉水了——这个“请”也是讲究的,家中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谈妥了,定下吉日,开张那天是要放鞭炮的,六百响的小鞭炮,噼里啪啦地好一会儿,主家便在这时递给木匠一个小红包,大小随主家,但一定是吉利数字。杨泉水羞涩地接过来,不看,便塞在上衣口袋中。找他的人多,活儿能从第一年春上排到第二年仲夏,小官村的人喜欢“请”杨泉水,相信他做出来的家具和他做的篾器一样漂亮又耐用。
杨泉水给杨国柱家做的家具是他十多年木匠生涯里最得意的作品,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可谓巅峰之作。打婚房家具整整用了六个多月——小官村的人喜欢把做家具说成打家具,斧头,榔头,刨子……在木头上敲敲打打,家具就有模有样地出来了,也算形象。杨国柱家的活从春天一直做到秋天,杨国柱说,不急不急,慢工出细活。他是小官村最早外出打工的,在外干什么也说不清楚,反正每年过年回来一次,衣锦还乡。杨国柱年轻的时候因为穷,没娶上老婆,人到中年,突然发了横财,便从城里带回来一个女人。杨国柱要把祖上留下的房子翻个新,给自己打一间婚房,逢年过节回来住一住。杨国柱是头一年的春天来“请”杨泉水的,他骑着一辆摩托车出现在杨泉水家门前的槐树下,槐树绿得正欢,荫着树下暗红色的摩托车,摩托车叫“八零”,也没人明白这个名字的意思,总之比那些凤凰啊双狮的自行车牛气多了。杨国柱见杨泉水正捧碗喝着粥,便上前奉上两支烟,说作兴,喜事逢双。他们在老槐树下比划了几句,杨泉水便丢下碗坐上摩托车急匆匆离开了。
杨国柱带杨泉水来到大堤上,这是他刚刚承包下来的,大堤下有梨园和桃园,是每个生产队的,逢到丰收时候,每户都能分上很多。这是小官村孩子们最喜爱的地方,可以说这里承载了所有孩子的童年时光。大堤上是水杉和胡桑,杨泉水有记忆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林林立立了,现在都长得很粗壮了。大堤与运河搭界的地方,还有一片杂树林,几年前也有人说要承包下来用来养鸡养鸭,后来不了了之。杂树林里野草葳蕤,石蒜簇拥着树根;木香肥大的叶片扇子一样地打开;贝母的灯笼花打出苞儿来了;野葡萄奋力向上生长,像要填满所有空隙似的……现在这片地方,包括大堤上整整齐齐的水杉都是杨国柱的了。杨国柱把烟熄了,钻进树林里,杨泉水也跟着进去了,他们一左一右,像阅兵似的,打量着两侧的树木。打家具当属硬木好,硬木木性比较稳定,做出来的家具也耐用,杨泉水说,橡木、桦木,、赤杨、樟木、黄杨,都是上好的材料。他们在几棵樟树前停了下来,仰着头看着,树干挺立,不枝不蔓,杨泉水拍了拍树干,說,这几棵打衣橱,再好不过了,樟树有气味,正好能驱虫。杨国柱也学着在树干上拍了拍,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小红绳系上做标记。后来他们又挑了几棵水杉,杨泉水说这些属软木,比硬木稍微次一点,但是轻,用来打凳子,搬着方便。杨国柱又在几棵水杉上系上红绳。选好木头,就等着找人伐倒了。新砍的木材不着急打家具,先在河里沤上一年,等木头吃饱了水,再捞上来风干,这样做出来的家具才不会变形。等选好所有木材,也快晌午了,他们从树林里钻出来,点上夹在耳朵上的烟,站在大堤的最高点进行着极目远舒,远处河水涟涟,阳光照着河面碧光闪闪,杨国柱对着河水喊了一声,好像以此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而杨泉水一直看着远处,脸上慢慢舒展了。
这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站在大堤上的两个人的话,大概就是意气风发了。杨泉水说他喜欢从林子里吹出来的风,带着木头的香气。第二年的春天,杨泉水已经坐在这堆散发着香气的木头中间开始他的“作品”了——用“作品”一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杨泉水在杨国柱新砌的毛坯房子里从春天一直干到秋天,那些灰不溜秋的木头羞涩地露出最好看的木纹,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墙角——衣橱、高低柜、三门橱、梳妆台、床……我常常在放学后跑过去玩一玩,杨国柱家偌大的房子里只有杨泉水一个人。我将院门敲上好久,杨泉水方才听见。他正坐在一堆小木条之间,专注地用砂纸打磨,脚下已经堆了很高了。我问这是干什么用的?杨泉水说是窗上的木格条。我想起看过的连环画,画上大户人家的窗户都是这样的,再将这些木格条榫接得严丝合缝,很是讲究。我一件一件地看过去,用手抚摸,打开抽屉或者柜门,再轻轻合上。樟木的气味,松木的气味,还有水杉的气味,把整个屋子填满了,就连杨泉水的头发里和衣服布缝里都夹藏着这样的气味。
我离开的时候,杨泉水并无察觉,他仍然坐在那堆木头之间,旁若无人。很多年后,我都能记得这一画面,无穷无尽的木头像要把他淹没了似的。
杨国柱的婚礼是在那年冬天举行的,新房里的家具成了婚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少邻村的人骑着自行车赶来,倒不是来一睹新娘风采,而是想摸一摸这些别致的家具,平整,光滑——床角的圆润、墙裙线的流畅、梳妆台的别致、抽屉的轻巧等等,都让人赞不绝口,最后,人们的目光落在三门橱的门把手上,这竟然是用木头雕成的一朵花,花瓣次第开放,栩栩如生,又恰到好处地落在门腰处。
这套家具着实让杨国柱风光了一把,但凡小官村的人家要打家具了,都会带着木匠来看一看,也有的直接请杨泉水——他的工期都排满了,活儿一家挨着一家,杨泉水没有因为活儿多了就毛快起来,他照样每天有条不紊地将工具——锯子,刨子,榔头……装进白帆布包里,帆布包挂在后座旁,骑上车不慌不忙地出门了。
4
这个帆布包现在还挂在阁楼的木梁上,隔三差五地就被杨泉水取下来在阳光下晒一晒,拍拍灰尘,常常天要黑了,杨泉水才将帆布包挂上去——他用一根叉杆勾住包带,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挂到梁钩上,他仰起头,很长时间都没有动,好像一根看不见的线将脑袋固定了似的。
后来,帆布包还一度成为我的书包——杨泉水为此跟刘彩虹吵了一架,但刘彩虹认为这包结实,给我做书包一定很耐用。我说过,对于吵架,刘彩虹从没输过,她用绝食的方法就赢了这场争吵。我还记得杨泉水把包递给我时的神情凄然,他叮咛我一定要爱护,不要弄坏了,甚至每天早晨为我把书包认真绑在后座上,起初我还以为是对我的关心,后来才发现是对帆布包的不舍。那时我已经在镇上读书了,是班里为数不多来自农村的人。我的书包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有调皮的学生常常趁我上厕所的时候,把书包拿到讲台上,用红色粉笔写上“木匠专用”。一开始我还感到生气,后来也习惯了,便从讲台默默把书包抱回来,用袖子擦掉粉笔字,再塞进桌肚里,认真听讲。这一点上,我完全遗传了杨泉水的内向和老实,我对此从未心存憎恨,而是更疼惜这个书包,我把脸伏在课桌上,书本上略带着的木屑气味使我感到丝丝的难过。
第二年春天,小官村的人开始背着包袱往外跑了,像被一阵风刮走了似的。我的同学也纷纷辍学外出打工了,他们去南京和上海,更远一点的,到了深圳。刘彩虹也想出去,当然也只是想想,她听从外地回来的姐妹们说,上海的饭店特别多,饭店里需要服务员呢,端端盘子——端盘子谁不会呢。我的姐姐也去了上海,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在一家服装厂上班——给衣服剪线头、缝扣子——工厂有宿舍和食堂,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平时也没机会出去逛一逛,但她们知道人在上海,这一点令她们欣慰。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回来的人都这样谈论着,当然从他们身上的穿着也能看出来,他们总是在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被叫停下来,刘彩虹一瘸一拐地迎上去,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听的机会,关于外面的世界,刘彩虹充满好奇,或者说,她对小官村人在外的情况充满好奇。
据说那一年,上海一家工厂直接开着辆中巴车下来招人了,车停在村西的打谷场上,招聘启事就贴在车玻璃上。一些刚刚识字的小孩大声朗读着,把“包吃包住”几个字读得抑扬顿挫。那时油菜花已经蹿得老高,柳条儿柔软起来,风里都是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一切都要蠢蠢欲动的样子。打谷场四周的麦苗被踩得歪歪咧咧,要在平时,肯定有人要站出来吼几句。但那天没有,谁会注意这些呢?再说这点麦苗又算什么呢?他们认为地上的麦苗在城里人面前真是太乡气了,恨不得将它踩到泥土里,踩到看不见为止。
一天,中巴车带走了小官村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人,他们来不及跟窗外的亲人们挥手,叽叽喳喳地挤在中巴车上,向城市出发了。
小官村变得异常安静起来,陆陆续续地又有人离开了,去了上海或南京,好像那里有挣也挣不完的钱。我的姑父和几个邻居去了上海一家工地,我的舅舅则去了南京的一个工地,他们回来和杨泉水谈起城里的时候,总是将话题落在各自干活的工地上——五十六层,都爬到天上去了,风一吹,摇摇晃晃的。另一个说,地基就浇筑了一百多天,地下全是房子。他们相互赞扬又彼此争执,好像整个工地都是他们的。这个时候,杨泉水并不说话,低着头一丝不苟地磨着榫头。
这些年小官村需要打家具的很少很少了,加上邻村的一年也就一两个活儿。从外地回来的人告诉杨泉水,打家具已经不兴时了,谁还自己锯树打家具?都用三合板了,轻巧,方便。杨泉水抬起头,看说话的人,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在槐树下告诉他塑料篓子的人了。
真正使杨泉水受到打击的应该是姐姐的嫁妆了。原本杨泉水计划姐姐结婚时,他要亲自为她打一套家具,但從上海回来的姐姐一口拒绝了。难看死了,她说。姐姐看中了仙城百货大厦里的一套家具,粉红色的,特别好看。姐姐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可见对这份婚姻的重视程度。家具用一辆小货车运了两次,直接送往男方家中去了。家具很轻便,像积木一样,只须半个钟头便组装成功,真是令人喜悦。杨泉水去“会亲”的时候,家具已经摆放整齐了,一进门就被这突兀的颜色给吓愣住了,来来回回看了一番,把抽屉和柜门打开,一股强烈的胶水气味扑鼻而来,他皱了皱眉,坐在一张塑料凳子上抽烟。那一晚,杨泉水没和人说话,低着脑袋,像是跟谁生闷气似的。
5
杨泉水第一次进城找的活儿就是在一个工地上推小车,他大概算是小官村最后一波进城的了。那时的小官村人口比以往少掉了大半,很多农田荒芜起来——谁愿意每年从城里赶回来种地呢。当然也有一些喜欢与泥土打交道的,把大片的田地承包下来,说要种植草莓和甘蔗,但都不太理想,还有的把大堤承包下来,折腾上一年半载,又继续荒芜起来,好像土地已经不能再给人们提供食粮了。他们迅速地背上包袱跟着进城的队伍,他们在土地上最后的努力只是为了离开的脚步更加坚定。
杨泉水在工地上干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回来时正是晚春,槐花懒洋洋地开放着,小官村像酣睡了似的,极其安静,杨泉水从村东走到村西,只有两个流着鼻涕的小孩和一条狗之外,他没有遇见任何人。刘彩虹不知道去哪里了,门没有锁,大敞四开着——小偷也喜欢城市吧,杨泉水想,他拿了一把刷子便去了河边,从前热闹的河码头——小官村人更喜欢称作水板凳,用木板或者几块石头铺就而成——变得冷清起来。他记忆中的早晨仿佛是从水板凳上的浣洗声开始的,岸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等候着,夹着一只盆或挽着一个篮,说着和小官村有关的人和事,在水板凳上洗着一年四季的衣裳和食物,从春洗到冬,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以这片土地为生,以这条河流为生,现在不知为什么,都迫不及待地逃离了。
他蹲在水板凳上用刷子刷着裤腿上的混凝土渣子,猛一抬头,天都快黑了,好像那些铅灰色的混凝土跑到天上去了。
杨泉水在家待了十多天便又进城了,这次是去了一家家具厂——刘彩虹从一个老乡那儿打听来的消息,杭州的一个家具厂正在招工呢。刘彩虹认为没有比这更适合杨泉水的了,杨泉水把自己的锯子、刨子、榔头等一一擦干净,装进帆布包里,帆布包斜挂在身上,从镇上乘了最早的一班车离开了。
我和刘彩虹都以为杨泉水这次会安顿下来了,毕竟他是个木匠。刘彩虹说那家家具厂很大,每天都有卡车来装货——这些她也是听来的。怎么说呢,总之,我们都为此而感到高兴。刘彩虹说要不是我每个礼拜回家(妹妹也打算和姐姐一起去闯世界了),她肯定也去城里打工了。那会儿我在仙城县里读高中,每个礼拜都要回家“带菜”——当然刘彩虹没有进城并不是因为我。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喜欢上学,好像对上学以外的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刘彩虹每天都在盼着我毕业,盼着我进城打工,这样她就可以离开这里了。你看看小官村,刘彩虹总是这样对我说,还有几个人待在这里呢?只有好吃懒做的才不愿出去呢。她常常畅想进城后的生活——她可以去菜场或商场门口卖唱,那里人多,她的歌声凄凉,人们一定会被歌声打动,然后在她跟前的塑料盆里脆生生地投上几个硬币。
就在刘彩虹畅想美好未来的时候,杨泉水又回来了。现在,他就坐在我和刘彩虹对面,把锯子、榔头、刨子一一从帆布包里拿出来,放在木箱里,帆布包空了,又被郑重其事地挂在了木梁上。用不上的,他对我们说,都是机器操作。据说家具厂没有刘彩虹描述的那么大,但效益的确很好,车间里各种机器的声音震耳欲聋,电锯的吱吱声,电刨的刺刺声,还有空压机轰轰的声音,车间里的工人说话都要扯着嗓门,尽管如此,彼此也不能听清。
是不是木匠,厂里并不在乎,只要有力气就行,所有的一切都是机器制作,机器把三合板、木工板裁开,气排钉和胶水把它们固定起来,真的,轻得很。杨泉水说。
整个晚上杨泉水都在小声咕哝,这怎么叫打家具呢,用胶水粘的,木板也不是木板,是木屑壓成的,这算什么呢。他自言自语道。
6
杨泉水回来的这几天,刘彩虹也不和他说话,脸比韭菜还绿。杨泉水也不提进城的事,每天起得很早,显得十分忙碌,似乎要证明他在家也能有所作为一样。早晨,他把自行车推出来,把帆布包又挂在后座上,在明媚的晨曦中出发了,他穿过小官村尘土飞扬的土路,一直骑到附近的小吴庄、小王庄、小杭庄,车轮呼哧呼哧地响着,他摁着铃铛,也发出清脆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寂静的村庄中显得更加寂静。自行车慢慢绕过每一户敞开或紧闭的门,“打家具哎”,他朝着门洞喊着,声音飘进去,空荡荡地,又逃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杨泉水又出门了,他比第一天骑得更远,经过小镇,一直到达最远的杨家桥,他穿过整个村庄,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只有一条狗若无其事地叫了一声,村庄死寂一般。各种藤蔓爬上院墙和屋顶,地上的巴泥草四处蔓延,绿色好像就要统领村庄。杨泉水说,人都没有了,这哪还像是个村庄哟——
一连很多天,杨泉水都这样早出晚归,初冬的风吹在脸上,已经有了寒意。自行车经过村头的时候,突然看见一辆农用车,车上载着两三个大人,风一般地驶过去了,他们的笑声像豆子一样洒落下来。杨泉水也加快速度,他多想追上这阵笑声。农用车拐了弯,向南去了,杨泉水死劲踩着脚踏,生怕不小心跟丢了。突然,在大堤脚下,农用车停了,车上的人跳下来,手里扛着铁锹,将大堤的泥土铲到车上去。杨泉水连忙走上前,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能随便挖我们的大堤。对方并没有因为他的质问而停下动作,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告诉杨泉水,这片大堤被人承包了,土都卖给建筑工地了。老头又说,我们都挖了一个多月了,今天又不是第一次来。杨泉水这才发现身后的大堤已经被挖出一道隘口了,堤上的水杉林也被砍伐了不少。杨泉水冲上去抢过老头手中的铁锹,扔了出去,当他要再抢一把铁锹的时候,已经被推倒在地了,杨泉水的脸正好埋在沙土上,呛了一嘴。他感到身上一股重重的力量,是铁器与骨头的较量,他抬起头,刚要站起来,却又被推倒了,他看见大堤缺口的部分,那片他和杨国柱找木材的杂树林已经不见了,堤口缺得像一张嘴。
那晚,杨泉水推着自行车一瘸一拐地回来了,身上都是泥土。刘彩虹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话,埋头在河边洗着帆布包——被踩在泥土里而脏兮兮的——他勾着头,整个身子仿佛要栽到河里似的,一直洗到天黑,洗到帆布包白如月色。
刘彩虹认为杨泉水每天在村子里晃来晃去,还是很丢人的,哪个年轻力壮的不在外挣钱呢,她说如果杨泉水不愿进城的话,她可以出去。
刘彩虹说完这话第二天杨泉水就进城了,没来得及背上他的帆布包。但这次只呆了十天又回来了,他的手指被家具厂的电锯锯掉了。是我去镇上接他的,差点没认出来,杨泉水的头上还戴着干活时的帽子,那种周围像披肩一样的帽子。他说车间灰尘大,每个人都有帽子,不戴的话灰尘全跑到头发里去了。他用一只手将帽子摘下,头发上仍然是木屑的白色。我接过他手上的包,这才发现他的右手包着厚厚鼓鼓的纱布。疼吗?我问,刚问完就觉得有点多余,十指连心,怎么会不疼。
不疼,杨泉水突然说,他把手抬起来,晃了晃,说,还有两个指头呢。
我推着自行车,杨泉水不肯坐上去,说自己能走呢。我们一前一后向小官村走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他不停地看着两边,那些曾经苍翠的大堤已经夷为平地了。对岸的村庄一览无遗,小官村也仿佛失去庇护露了出来,胆怯,慌张,猥琐地缩在一旁。我好像是第一次发现小官村的变化,那个从前记忆里的模样不复存在了。据说不久以后这里将建几座工厂,小官村的责任田也要浇上水泥,成为工厂的一部分。
杨泉水走得很快,仿佛久别归来。我想问他还去不去城里?还去不去家具厂?但忍住了。他自顾着向前,像要把我甩掉似的,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认为杨泉水是故意把自己的手弄坏的。
7
这年的冬天来得很早,西北风一刮,寒劲儿就来了。杨泉水每天都去南大堤,在空荡的沙土地上来回走着,走累了便坐在一只树桩上,远处夕阳衔山,河水静默,风夹着细沙拍打在脸上,他顺势躺下来,恍若从前的草叶又把他整个儿包围起来。草的波浪不断拂动,他的脸贴在树桩上,截断的树桩散发着淡淡的木香,然后,他的泪水无声地流了出来。他就这样躺着,看黑暗一点点地降临,星星跳上青灰色的夜幕,这时,仿佛整个世界都变成草地,每一颗星星都跳跃在草梢之上。
第二天再来的时候,杨泉水便带上绳子,把倒在地上的树,以及一些根部架空的树拖了回来,再把木匠工具拿出来,用左手慢慢锯开。刘彩虹知道杨泉水要干什么,因为几天后院子里堆着的齐整木料足以说明一切。我很久没有闻过木头的香味了,淡淡的,飘散在院子里。地上铺了一层刨木花,松松软软的,木头又露出好看的花纹来,曲折婉转,像流水一样。杨泉水每天坐在木头之中,忘了我们似的,刘彩虹常常扯着嗓子朝他喊,她把杨泉水做好的凳子、椅子气急败坏地扔到墙根下。有一次夜里下雨了,杨泉水要下床搬木料,却被刘彩虹拦住了,似乎有意跟他作对似的——杨泉水搬回来一块,就被刘彩虹扔出去;他再搬进来,她再扔出去。黑暗里木頭和木头在来回跑着。后来,刘彩虹扔出去的东西里增加了杨泉水的衣服、鞋子以及锯子和刨子,当杨泉水又一一拿回来的时候,突然看见黑夜中出现一道白光——帆布包被扔出去了。杨泉水箭一样地冲进雨里,刘彩虹迅速用拐杖勾住他,他们在离帆布包一尺远的地方撕扯起来,泥浆甩到脸上。刘彩虹咆哮了,像狮子似的扑在杨泉水身上,拳头和雨点一起落下来。她用拐杖跺在帆布包上,把多日来的怨气通通发泄出来,又用帆布包抽着杨泉水。我要你要,啊,我要你要,直到浑身没劲了,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帆布包被她套在杨泉水的头上。我要你要,你要啊,你永远别拿下来。
你们一定不会相信,杨泉水再也没有把帆布包从头上拿下来过,我试图为他取下,总被他死死按住。刘彩虹说,别理他,让他戴一辈子好了。那晚之后,杨泉水就病了,他不停地咳嗽,像要把五脏六腑咳出来一样。
杨泉水不做家具了,而是每天把木料铺在地上,坐在上面发呆,一直到半夜。有时我回家很晚,屋子里一片漆黑,我蹑手蹑脚进去,尽量不发出声音,经过堂屋的时候,差点被杨泉水绊了一跤。他披着棉衣,套着帆布包,蹲坐在木头上。
我说,怎么还不睡觉?
他的嗓子哑了,喉咙里嘶嘶的声音。等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杨泉水仍然岿然不动地坐在那里。有好几次他都是这样地使我吃一惊,我忘了他会每天坐在黑暗中。他的嗓子没有好转起来,说话时只剩气声了。当我半夜起来的时候,仍然会看见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我从他身边经过,去厕所或者去厨房喝水,他都没有察觉。春节将近时,杨泉水已经不再说话了,刘彩虹说他嗓子坏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能发出气声。但我不相信,脑子里总是出现杨泉水坐在杨国柱家毛坯房子里时的画面,他的身下是长短粗细的木料,干净,柔软,沉默而本分。
那年我也辍学了,突然对上学失去了兴趣似的,迫不及待地跟着村里一个包工头去了建筑工地。我向杨泉水告别,他并没有抬头,帆布包像长在脖子上一样。他慢慢举起手向我道别,他的手早已愈合了,但断掉的指头再也不见了,纱布拆了,露出红彤彤的手指桩。断掉的是中指、无名指、小拇指,齐刷刷地从指根处没有了,剩下的大拇指和食指有点孤零零的,甚至有些怪异,像一支随时扣紧扳机的手枪似的。
责任编辑 张 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