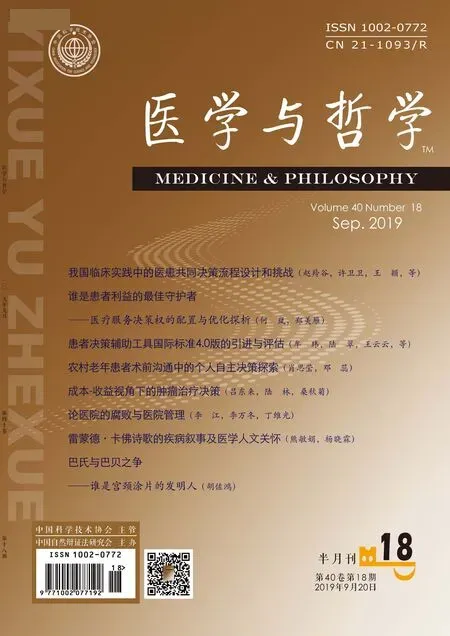雷蒙德·卡佛诗歌的疾病叙事及医学人文关怀*
熊敏娟 杨晓霖②
诗歌叙事是最古老、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文学在叙事医学人文教学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叙事文类。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年~1988年)是美国最著名的极简主义短篇小说作家之一,然而,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也非常有造诣,只是没有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在医学人文领域,他的诗歌作为非常有价值的阅读和阐释的素材,能够有效地引发医学生和医学教育者的深度反思。本文中卡佛的诗歌主要参考克莱普(Sandra Lee Kleppe)在《卡佛诗歌中的医学人文》一文中所列诗歌,诗歌的中文翻译引自舒丹丹译的《我们所有人:雷蒙德·卡佛诗全集》,部分译文有细微调整。
卡佛自20世纪80年代从“生存现实主义”向“人文现实主义”转变[1],从这一时期开始,他的诗歌作品中开始大量出现后现代元病理人文元素。本文从医学人文视角对卡佛的诗歌进行研究,并分析作为一名诗人,他是如何背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创作出充满医学人文关怀的诗句。
1 疾病叙事:疾病类型与叙事视角
卡佛的前半生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晚年又罹患肺癌,50岁便英年早逝。他曾说:“我觉得诗要比其他作品更接近我、更特别、更难能可贵……所有的诗都有一个‘自传’的成分在。有些情节的确很像某个时间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情。”[2]因此,他的诗歌中涉及到酗酒、癌症、失眠症等疾病题材的作品占了相当的分量,甚至有些诗歌以此为标题,如《驾车时饮酒》(DrinkingWhileDriving)、《酒》(Alcohol)、《干杯》(Cheers)、《冬季失眠症》(WinterInsomnia)、《患癌的邮递员》(TheMailmanasCancerPatient)、《烟斗》(ThePipe)、《药》(Medicine)、《烟灰缸》(TheAshtray)等。
卡佛诗歌的叙事视角也灵活多变,内视角、外视角交替出现,或是第一人称的回顾性视角,如《运气》(Luck):“那时我九岁。/我的生活里一直/离不开酒。我的朋友们/也喝,但他们能节制”。或是第一人称的旁观视角,如《巴尔扎克》(Balzac):“我想起戴着睡帽的巴尔扎克,/在他伏案写作三十小时后,/雾气从他脸上升起,/长袍睡衣黏着他毛茸茸的大腿”。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变换自如,卡佛笔下的人物是丈夫、妻子、儿子、女儿,也是朋友、陌生人,甚至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如《解剖室》(TheAutopsyRoom),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他们大多数都是蓝领阶层的穷人——推销员、侍者、理发师、清洁工、看门人等。他们喜欢蜷缩在家里,或躺在沙发上,或看电视,或吃零食;或听人讲故事,或给人讲故事;即使在外工作,也或是销售员,或是酒吧招待。这些人没有宏大理想,但真实得如同你我;这些人一般不试图思考生活的哲理,即使偶尔尝试,也往往无果而终。这些人按理进不了神圣的文学殿堂,但由于卡佛,他们生动地存在着,照亮了读者内心暗存的卑微和无奈[3]。
2 疾病隐喻功能的构建
2.1 社会与生命困境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认为现代的疾病隐喻与传统不同,“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癌症作为一种“伴随情绪消沉而来的疾病——这既指生命力的萎缩,又指对希望的放弃”[4]。卡佛[5]95在《患癌的邮递员》中生动地记录了一个垂死之人的困境:
患癌的邮递员
成天闲在家里
那个邮递员从没笑过;他容易
疲劳,身体正在消瘦,
只是这样;他们为他保留那份工作——
再说,他需要休息。
他不愿听见大家谈这事。
他走在空空的房间里,
想起一些疯狂的事,
比如汤米和吉米·多西,
在大古力水坝
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握手,
还有他最喜欢的新年派对;
他告诉妻子的事
多得可以写一本书,
她也爱想一些疯狂的事,
但能照常工作。
有时候在夜里,
邮递员梦见他从床上起身,
穿上衣服,出门去,
高兴得发抖……
他恨那些梦,
因为醒来后
一切都不曾留下;仿佛他
哪儿也没去过,
什么事也没做过;
只有那房间,
那没有阳光的清晨,
门把手慢慢转动的
声音。
此诗刻画了一个潦倒的劳动人民的形象,邮递员表现出的疼痛、焦虑、厌世、恐惧等情绪就是对社会和生命困境的重要反馈。梦与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诗歌充满抒情力量的简单意象。比如,“门把手慢慢转动”营造了紧张的气氛,邮递员“梦见他从床上起身/穿上衣服,出门去/高兴得发抖”,他却想保持清醒,因为梦让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因疾病导致的疲惫不堪的生活,门把手代表着从生命到死亡的通道,代表着走向另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大家对他的议论更暴露了温暖的匮乏、人情的凉薄,卡佛就曾在《你们不知道爱是什么》(YouDon'tKnowWhatLoveIs)的诗歌里发出这样的质问:“你们有谁知道生活是什么/你们有谁懂得哪怕一丁点儿?”
2.2 精神的暗疾与隐喻
失眠症作为一种心理疾病,是作家钟爱并藉此来探索人性和精神图景的方式。卡佛把失眠作为他的一个文学主题,同时也是一种暗喻的符号。他在诗作《冬日失眠症》中这样写道:“脑子想从这儿跑出去/跑到雪地上。它想要奔跑/跟随一群粗毛野兽,满口利齿。”失眠者在黑夜中有一种全然的清醒,这是正常人所没有的清醒,失眠者沉浸在黑暗世界里做着痛苦的空想,然而“在月光下,穿过雪地,不留下/任何脚印或踪迹,身后什么也没有”。卡佛笔下的失眠者常常会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无助,所以沉睡就成了避难所,一个暂时能获得片刻宁静和安全的空间,把自己与身边的人群隔开,以此来逃避生活,驱散内心的纷乱。如《睡眠》(Sleeping):“他睡在公共汽车上,火车上,飞机上。/睡在岗位上。/睡在路边。”甚至,卡佛在《旧时光》(TheOldDays)中写道,“上床睡觉时/真希望就这样一睡不醒”。
酒在卡佛的人生中占据着重要意义,亦在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虽然确切地定义“酗酒症”并非易事,但众所周知,生理特性、负面生活事件、文化因素、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或人格障碍都可能导致酒精成瘾。因此,酗酒症可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6]。卡佛笔下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酗酒行为的描述生动揭示了他们对心碎回忆的逃避、难以忍受的孤寂和面对生活中那些迫在眉睫的困窘时的无能为力。对于处在现实重压下的人来说,酒就是一服具有安慰效用的精神药剂。《驾车时饮酒》描绘了两个男人一路饮酒作乐的场景:“我很快乐/和我兄弟驾着车/喝了一品脱‘老鸦’酒。”《干杯》中的酒鬼像是在喃喃自语:“喝了伏特加之后用啤酒漱口/……他们不明白,我很好/我在这儿好着呢,现在每一天/我都会很好,很好,很好……”而酗酒者清醒之后又会陷入到痛苦挣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个阶段的心理活动会更加复杂、丰富,显示出一种与生活融合无间的立体感与真实感,能够令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人物的焦灼不安与迷惘。如在《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PhotographofMyFatherinHisTwenty-SecondYear)一诗中,卡佛表达了他与父亲一样都是酗酒者的绝望之情:“父亲,我爱你/但我怎么能说谢谢你?我也同样管不住我的酒。”而在《给我的女儿》(ToMyDaughter)中有这样的诗句:“你必须这样——就是这样!/女儿,你不能喝酒。/它会毁了你。就像它毁了你妈妈,毁了我。/就像它曾经毁了我们”,人物的愤怒与无助跃然纸上。
3 医学人文关怀的彰显
3.1 医患沟通
卡佛的诗歌提供了许多有关医护人员与患者如何沟通的例子:为什么,怎样,在哪儿,沟通成功还是失败,等等。如在《医生说的话》(WhattheDoctorSaid)一诗中,当医生要告知病人面临死亡的讯息时他并没有选择专业术语。医生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接近患者面临死亡的现实,而且更要超越这个现实。在诗中,医生说道:“你信教吗,你会不会跪在/森林的小树丛里让自己祈求神助?” 通过使用“神助”这类的语句,医生对治疗和愈合进行了区分。治疗可以消除疾病,但愈合却能帮助患者成为一个健康而完整的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患者没听懂,“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跟医生握了握手,说了些感谢的话。这是一个异样的,甚至尴尬的反应,但它表明,患者已经接受了医生的说法,甚至认为“是他刚刚给了我/这个世上别的人不曾给过我的东西”,——面对死亡时一个似是而非的生命礼物。通过握手这个动作,医生和患者都从自己的空间里跨出了一步[7]。
与《医生说的话》中成功的交际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首《求婚》[5]287。诗歌的第二节这样写道:
几天前一些事情变得清晰
我们一直憧憬的未来的这些年月
都将不复存在了。医生终于谈到我将留下的
“这副躯壳”,他正尽最大的努力带我们逃离
眼泪和凶兆的深渊。“但他爱他的生命。”我听到一个声音说。
她的声音。年轻的医生,几乎没有停顿,“我知道。
我想我们不得不经历那些生老病死。最终
你们会接受。”
在诗中,尽管患者和他的家人非常痛苦,医生还是顽固地、一板一眼地告知事实。这首诗表明,这位医生受过的培训以及他的年轻不成熟让他面对患者时就像阅读一本教科书似的古板,而不是以适当的方式回应患者的情况。
3.2 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是对濒死患者进行的治疗和护理,其本质是缓释或者消除患者死亡时精神上的恐惧与肉体上的痛苦,让他们保持着人的尊严,接受死亡,平静地迈向死亡。《我的死》(MyDeath)一诗非常形象地展示了濒死患者临终前的渴望:“我希望,某人会给每个人打电话/说,‘快来,他不行了!’/他们就来了。”这首诗写于卡佛去世前四年,它为亲人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他们应该如何回应?患者又希望他们对那即将到来的痛苦作出怎样的反应?卡佛在诗中写道:“如果幸运,他们会走上前……/他们会举起我手说‘鼓起勇气’/或‘会好起来的’……/为我庆幸吧,如果我能在朋友和家人的注视下/离去”。卡佛通过创建这种死亡模式,呼吁家人能够给予临终患者充分的情感照顾和生命尊重,更希望人们能够坦然无畏地面对死亡,就如诗中所说的那样——“我多么爱你们,多么高兴/这些年有你的陪伴。无论如何/别为我太悲伤”。
3.3 解剖室人性再现
在卡佛的好几首诗里都可以找到对尸体的描述以及尸体对凝视者的情感冲击,如《给普拉特医生,一位女病理学家的诗》(PoemforDr.Pratt,aLadyPathologist)、《照片上的威斯·哈丁》(WesHardin:FromaPhotograph)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卡佛在萨克拉门托的一家医院做过一段时间的看门人和护工。《解剖室》[5]32一诗对尸体解剖室的情况描述可能源自卡佛自己的这段经历,他以“元病理书写”的方式描述了解剖室的内部人员面对现代医院中尸体的处理方式表现出的痛苦矛盾之情,诗歌的第一节这样写道:
那时我还年轻,像十岁孩子一样精力充沛。
对任何事都是如此,我以为,尽管我夜间的部分工作
是等验尸官的工作完成后
打扫解剖室。但偶尔
他们下班太早,或太晚。
老天作证,他们会把东西遗漏
在他们特制的桌子上。一个小婴儿,
安静得像块石头,冷得像雪。另一次,
一个白头发的黑人大高个,胸部
已被打开。他所有的生命器官
都摆在他头部旁边的一只盘子里。
软管里的水在流,头顶的灯发出白光。
还有一次是一条腿,一条女人的腿,
摆在桌上。一条苍白的线条优美的腿。
我知道是什么。从前我看过。
但它仍使我透不过气来。
此节对解剖台上发现的内容的描述是从一个整体转移到部分:先是一个婴儿,然后是一个男人的部分躯体,最后是一条女人的腿。同时,这三具尸体代表了不同的年龄、性别和种族,因此也代表了人类的形象:为了进行科学的研究,人类逐渐衰退的躯体完全暴露在解剖室光亮的“头顶灯”的照射下。随着现代诊断和治疗的高科技设备的出现,患者变得越来越物体化,人性的成分越来越少[8]。以尸体举例,医生和研究与采取行动的科学“对象”(即尸体)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宽,并且对“患者”人格的漠视的倾向也愈加强烈。然而,《解剖室》这首诗的叙事者并不是一名医生或医学生,他只是“看门人”和清洁工,在他看来,摆在他面前的不是专业人士口中所谓的研究对象,而是独立存在的主体。所以,尸体摆放方式(物体化的、非人性的残肢)所展示的残酷现实与他人性的本能产生的冲突使得他非常震惊和困惑。
第二诗节中,主人公回到了现实,当他看到一个真正的女人的腿,活生生的腿时,他奋力做了两个动作——“我会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或者/地板。然后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伸向她的腿”——紧跟着说:“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切都正在发生。” 他对妻子抚慰的话语和亲密的举止表示出抗拒,似乎完全不想跟妻子倾诉自己的痛苦。
然而,这首诗通过转喻和共情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重拾人性的过程。残肢代表整个人是一种本能的感觉,这种充满怜悯的情感让主人公有足够勇气去面对那冰冷的解剖台展现在他面前的残酷现实。正是这种姿态,如同悼念中要尴尬地表现出“悲伤”一样,与试图将破碎的肢体与一个完整的身体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同等重要。同样,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经历所导致的笨嘴拙舌以及手足无措也被认为是沟通中努力人性化的表现[7]。
《解剖室》精确描述了一个外行人如何在医学背景下与非常具体的死亡场景做斗争的情况,是个体对重拾人性所做的努力。与解剖相关的诗歌,医学生还可以读到诗人西尔维尔·普拉斯(Sylvia Plath)的《尸解室的两个画面》(TwoViewsofaCadaverRoom)和医生戴安·罗斯登(Diane Roston)的《学习解剖》(OnStudyingAnatomy)。伯纳德·莫克汉姆(Bernard Moxham)曾指出:“对于今天的许多医学生来说,熟悉人类尸体将是他们第一次接触死亡。这种经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是非人性化的。然而,如果制定一些对策,就可以使它成为一个积极的经历。”[7]卡佛的这首《解剖室》可能有助于找到解决这种困扰的对策。
4 结语
诗歌阅读能够帮助医学生构建共情想象空间,促进医学生感受故事和情绪的力量。阅读叙事诗歌或抒情诗歌所获得的共识不是经由推理(reasoning)而来,而是经由感同身受的认同和想象得来。雷蒙德·卡佛的诗歌中对人性的冷静拆解其实是对20世纪后期的医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根据医学人文学家的观点,这个时期的医学已经禁锢在科学术语的误区,患者的人格和身体被简化为隐喻文本一般,供冷漠的专业人士“阅读”。
卡佛在访谈录中曾提及自己的写作目的,是“要证明每一首诗或每一部小说都可以被视为……作者的一部分,被视为他对他那个时代的世界的见证的一部分”[9]。卡佛作为短篇小说家因其后现代极简主义风格而声名鹊起,但在21世纪的今天,研究学者看到了作品中展现的医学人文主义要义。同样,他的诗歌也是一种人文关怀的抒情表达,这种医学人文关怀的体现有助于重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共情联系,有助于重拾现代卫生机构背景下“将患者看作完整个体”的人性化理念。
叙事医学人文教育提倡医学生广泛阅读甚至创作与生老病死、疾病和疗愈相关的诗歌,达到提升自我职业认同、患者心理状态理解和职业压力自我缓解等目的。除此之外,叙事医学还提倡医生在必要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向患者有针对性地推介诗歌进行阅读,在某种意义上,达到患者健康素养提升和自我疾病状态认同等功效。每天推荐患者读一首十四行诗虽然不能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但可以帮助患者预防糖尿病倦怠——亦即糖尿患者对控制病情感到精疲力竭的心理状态。诗歌不仅能够帮助连接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鸿沟,而且对患者心理上的治愈具有重要的作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