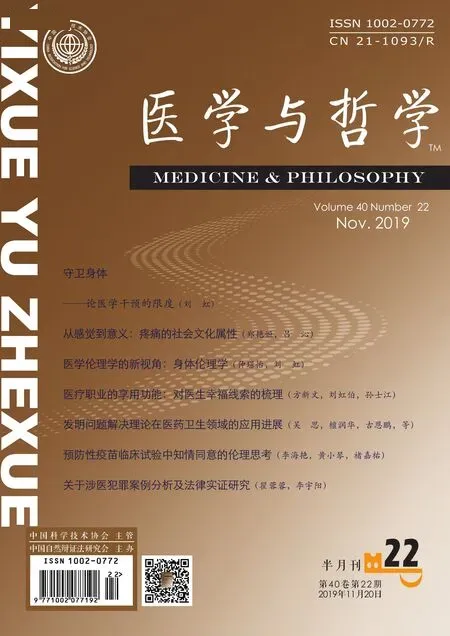从感觉到意义:疼痛的社会文化属性*
郑艳姬 吕 沁
疼痛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一项负面的生理体验,通常给人类带来难以愉悦的感觉。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定义疼痛(pain)是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的不愉快感觉和情感体验;国际疼痛学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IASP)也指出:疼痛是与组织损伤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主观感觉和情感体验[1]。同时,疼痛也是继体温、脉搏、呼吸、血压之后的人类基本生命体征的第五大体征,已被广泛运用于生命迹象及生活质量的医疗诊断、治疗及评估范畴[2]。疼痛不仅是一项有关身体的事项,还夹杂着大量与社会及文化有关的诸多因素,罗塞林·雷伊(Roselyn Rey)[3]2在《疼痛的历史》一书中说:“疼痛被发现和承认的历史,就是现代医学知识体系的边界和内容不断厘清的历史,科学与玄学分野的历史,个体的意志得到彰显的历史。”这不仅揭示了疼痛的痛苦性,同时也表明它是与人的思想、情感、认知等相关的精神活动,是一种复杂的“身体”感受。医学人类学素来将文化视作整体,并通常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讨论疾病与治疗的观念与行为,本文将在此框架内分析疼痛的生理、文化及社会属性。
1 疼痛的感觉特性
疼痛(ache,pain,soreness)在生理学范围内的讨论多是指“疼痛感”,通常也被简称为痛感(英文为nociception,源自拉丁语中的“伤害”),是引发疼痛的刺激从受创部位或者病灶部位发出并传导至中枢神经、使人产生疼痛感知的过程[4]。从现代医学的观点而言,疼痛感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理特征,被人体普遍感知。威曼(Weinman)曾经指出:“疼痛是对组织损害或生理功能障碍所产生的一种信号,当神经或神经末梢受到来自体内或者体外有害刺激时,便出现疼痛。”[5]
首先,疼痛是人类身体在与外在环境互动中产生的一项自然生理反应,显现出了其生物属性的一面。在体质人类学家看来,疼痛是人类进化的一种“副产品”:为了适应直立行走,人类在骨骼、牙齿等方面的改变导致了一系列身体基本疼感的来源。其次,疼痛对外界造成的身体伤痛有预警的效应。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难免要与自然界的物体发生互动,当人类遭受到外在伤害时身体也会发生疼痛。对于长期以来都要与自然界的危险做斗争的人类而言,为了长此以往的繁衍生息,疼痛感具有决定性的防御意义,人类的身体对钝器、锐器、极冷和极热条件的刺激有着极其敏感的反应,疼痛感的出现在提示与警醒人们,从而让人们避免了有可能进一步的身体伤害,因而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最后,疼痛还是疾病的重要征兆,疼痛不仅预示着疾病的发生,强烈程度也成为了疾病激烈与否的一个评判标准。不同的疾病也会伴随着不同方式及不同身体部位的疼痛,疼痛感也会伴随着疾病诊断以及治疗过程的发生而产生,最常见的如注射、外科手术、各类“镜”检查、活检,甚至静脉切开术等。可以说疼痛感本身是人的身体发生生理变化的指示,是损伤过程发生之时身体内部应激的一种反应。
与疼痛感作为一项直观的感受不同,对于疼痛发生机制的探究则属于历史的范畴。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人们都没能很好地理解疼痛,对疼痛原因的解释五花八门,并且由于其带来的不适体验,往往充满神秘的宗教色彩。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认为,疼痛的大部分原因是魔鬼随着流血的伤口进入到人体内部而引起;其学生柏拉图(Plato)将疼痛看作是情绪而非感觉;现代生物医学的创始人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遵循其体液理论的步伐,认为疼痛是因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体液不平衡而造成。诚然,我们的目的不仅仅只在于解释疼痛感本身,围绕疼痛在主观感觉和情感体验两方面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更多的目的在于试图控制疼痛的发生。正如以Engel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所主张的,需要从“痛知觉”和“痛反应”两个方面来认识疼痛[3]8。
而真正对疼痛机制的集中探讨,发生在医学生理学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不仅将对疼痛发生原理的研究从一种神秘的、不可寻的角度带到了依托于神经传导学的理性解释,也由此,对疼痛感受机制发生中心的关注从心脏转移到了大脑。特异性学说(specificity or labeled line theory)、强度学说(intensity theory)、模式学说(pattern theory)和闸门控制学说(gate control theory)从不同方面解释了疼痛发生的原因,是自17世纪以来较为流行的四种疼痛解释理论[6]。至今为止,由于理论逐渐被淘汰,强度学说和模式学说已经逐渐退出疼痛医学的视野。外周特异性伤害性感受器(nociceptor)的发现虽确立了特异性学说的主导地位,但其中枢通路的特异性仍然受到质疑。从否认存在特异性伤害性感受器这一点来说,闸门控制学说显然是错误的,但其提出的中枢调制(central modulation)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当代慢性疼痛机制研究[6]。因此,即便是剩下的这两门学说,也发生了极大的争议,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仍未平息。不可否认,从宗教到医学,从对魔鬼的揣测到对神经元的研究,是人类对疼痛研究从感性踏入理性的过程,但是只有生理学部分的解释还远远不够,其社会文化性是必须考虑的“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2 疼痛的公开与表达
事实上,疼痛不仅是人类可以体验和感知的一种存在,疼痛在历史不同时期的价值与意义的建构也随时空与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个体忍受痛苦的一些能力和品质也可能因社会背景而异。与疼痛有关的表达方式与行为不仅与文化密切相关,也与具体的情境有着巨大的联系。不同的文化语境和不同的疼痛表达相关联,鼓励其中一些表达,隐蔽和禁止另一些表达[7]。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否将身上的痛苦表达出来?何时会表达疼痛?通过怎样的方式传递疼痛的感觉?人在什么时候会选择忍受疼痛,什么时候又会选择公开?由疼痛牵扯出来的问题,都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否将疼痛公开通常与文化的价值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文化中,都将疼痛看作考验意志与增添荣誉的时刻。巴里巴人(Bariba)是生活在西非贝宁与尼日利亚部分地区的一个少数族群,在他们的文化中,有一句著名的谚语:“sekuru ka go buram bo”,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与死亡比起来,耻辱更让人难以忍受”。每当妇女要分娩的时候,她们会选择独自找地方生产,刻意向周围的人们回避这一过程。而对于男人们,当遇到打仗或者遭遇事故受伤时,他们会刻意表现的跟平时一样,看不出任何痛苦的成分。一旦有人因疼痛表现出痛苦的神情或者呻吟,则会受到周围人的鄙夷与耻笑;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忍住疼痛,这样的事迹与经历将会享誉四方。很显然,能够忍受疼痛对应的“荣耀”与不能忍受疼痛所对应的“屈辱”形成了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忍受疼痛赢得更高的荣誉是文化中受到鼓励的,会尽量避免因为痛苦和懦弱的行为而招致耻辱[8]。不仅如此,巴里巴文中只有少数词语用于讨论和表达痛苦。
同时,疼痛的公开及表达往往还受到文化情境的影响。Johansen[9]对居住于挪威的索马里难民女性的研究发现,在挪威社会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些古老的割礼传统所带来的疼痛,女性们会大胆的将割礼带来的疼痛描述为极为痛苦、难以忍受。而在母国索马里,对于疼痛的厌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诉说,诉说疼痛也是被予以谴责的。当她们离乡背井后,脱离了曾经熟悉的文化情境,就从道德上和法律上对传统的仪式进行批判与谴责,并开始反思幼年时期所遭受的阴蒂切开术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不难看出,疼痛的表达方式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人们对待疼痛的态度也有可能大相径庭。
此外,人类学家Zborowski分析了意大利人、犹太人、爱尔兰人和美国人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下的痛苦经历差异[5]。虽然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有类似的痛苦行为,如允许哭泣、咒骂和使用情感词,但他们控制疼痛的方法和目的并不相同。意大利人需要止痛药来缓解疾病发作时的疼痛,如果医生能够成功治疗他们的疼痛,则会对医生的信任大大增加。而相反,犹太人不大愿意接受止痛药,认为止痛药会影响健康并使人上瘾。与此同时,他们对医生持怀疑态度,经常会进一步询问诊断和治疗的计划。可以认为意大利人注意到在现有情况下身体所感受到的疼痛,并希望疼痛的感觉能够立即得到缓解,并且疼痛态度更偏向于当下取向(present-oriented)。犹太人倾向于希望别人关注他们的健康并同情这种疾病,而不是表面疼痛。他们更关心治疗的长期影响,并期望家庭成员和医护人员治愈自己的疾病,且使他们的身体完全康复,其疼痛态度较偏向未来取向(future-oriented)[5]。
由此可见,疼痛的表达不仅反应了文化的固有模式,不同类型的文化也引导着个体疼痛表达的方式,更进一步的是在不同的文化中,与疼痛有关的经验与话语体系也受到文化的塑造。疼痛的表达与行为是一套相对独立且独特的“疼痛语言”(language of distress)系统,无论是隐忍还是以激烈的方式向外表达,抑或是极度的悲伤和抑郁,都受到文化所赋予方式与意义表达的限制[5]。由于文化具有多样性,因此疼痛的概念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往往要根据当时社会文化可接受的标准下定义,这些标准或行为规范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10]。
3 疼痛的意义建构
关于病痛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有着独特的“隐喻”(meniaphor)这一点,美国批判主义文学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1]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就对肺结核、癌症和艾滋病的社会隐喻做了深入的探讨分析。然而,疼痛在社会隐喻方面与疾病相比显得更为隐蔽,但值得肯定的是,疼痛的隐喻很大部分是针对社会的隐喻,并且其根源往往就是生活环境不利的指涉。例如,胃部的疼痛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饮食时间不规律,饮食方式过于急促等,而这背后则是生存空间狭小,生存压力太大的缘故。因此,身体的疼痛正是对不良社会生存状况进行提示与预警的方式,甚至是最直接控诉的媒介。
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文化体系中关于疼痛的隐喻还与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圣经》中,长时间地让身体处于疼痛之中被视作一种对上帝虔诚的表达模式。在《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sseia)中,疼痛是上帝的旨意,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要么是遭受了报应[3]9。疼痛与“受难”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联,疼痛的发生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惩罚。在一些更激进的想法当中,身体的不适被视作生病主体自我生成的,德国身心医学家格奥尔格·格罗德克(G.Groddeck)认为:“病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疾病,患者本身就是病的病因,而用不着从别处寻找原因。”[12]类似的思想也表达出疼痛的道德隐喻,将疼痛与惩罚联系在一起,创造出的忍受疼痛的能力与人格的关联,体现出人类区域将病患个体边缘化、异化以此来对社会、对个体进行控制的目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疼痛的主体并不值得同情,因为他们在道德上出了问题,甚至有咎由自取的意味。可以看到,疼痛的患者和健康人具有的社会意义并不相同,当身体被贴上了标签之后,健康对应着正常,拥有疼痛则对应不正常,这在语义学上几乎成了同义词[13]。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某些场域中疼痛的意义被视作对社会结构禁忌的一种规训,并具有权力的意涵。以坐月子为例,产妇因在生产中忍受了巨大的疼痛诞下婴孩,对家庭的绵延做出了贡献,因而疼痛会变为一种权力的武器,要求家庭对自己的功绩进行认可。如果在月子期间,此种认可的行为得到明确的表示,那么产妇能够借此机会很好地融入夫家,但若月子期间产妇没有受到良好的照护,那么将会为今后家庭的权力格局的变化留下隐患。在许多案例中,产妇关于生产疼痛的叙事大部分是关于异议和不满的表达,同时也会变成争取家庭权力的最好时机。由于没有被好好照顾,发生在产妇身上的各种隐性疼痛就是身体对此种家庭境遇的控诉[14]。不同之处只在于,这种疼痛和一般的躯体化的区别在于这是一种难以被发现的隐性表达。由此一来,疼痛背后所代表的权力关系彰显无遗。
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进一步把疼痛的定义从生理领域延展到了社会领域,他区分了“疾病”与“疾痛”,认为疾痛是一种个体更深层次生活体验,是患者对疾病引起的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15]。身体部位的“疼痛”实际上与某些个人“痛苦”的生活体验具有相关性。因此,个体的以往失败的经历、所遭受的不公正、参与过的冲突都会在某些时候以“疼痛”为契机转化为主体关于“痛苦”的身体障碍话语以及情绪的困扰。这种疼痛的“躯体化”(somatization)实际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16]87。“疼痛”也由此实现了从生理层面的“痛感”(pain)延伸到社会文化层面“苦痛”(suffering)的转变[16]49。而“社会苦痛”(social suffering)则把痛苦放入了更大的宏观叙事框架中,认为个人生活中的痛苦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有着莫大的关联,疼痛有时会青睐某一群体。
美国医学人类学家法默(Paul Farmer)等[17]提出“结构性暴力”的概念,指出不仅要关注身体层面的苦痛,还需要考虑社会阶层、性别、收入情况等影响因素,因此往往这些因素才是导致苦痛发生的外部根本性力量。由此,在深邃的历史维度中发生的殖民掠夺、战争、饥荒、暴乱等社会结构性的力量对于生命个体能够造成惨绝人寰的未可预期的后果,这也就是“结构性暴力”的实质。同时,《世界的苦难》(Lamisèredumonde)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18]。个体所承受的疼痛、烦闷,看上去是主体情感与身体上所遭遇困境的直观反映与结果,但是背后深层次的因素往往是社会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即个人痛苦的社会性,由此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之下由苦痛的隐喻典型的社会学批判[19]。不仅需要关注疼痛的微观层面的个体环境因素,更重要是将疼痛放到宏观的历史及政治经济因素中考量。
4 疼痛的主体叙事
当社会苦痛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个体(individual)作为疼痛的主体(subject)被越来越深入到其中,当他们自己也意识到疼痛的来由与社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开始进行自我认知与反思的时候,问题也随之而来。许多情况下,疼痛可能仍然是私密性的、潜在性的,没有任何的外在迹象表明个体正在体验疼痛。在Zola的研究中,在对待痛经(dysmenorrhea)的态度上,低收入组中认为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并不需要临床医治[5]。所以个体是否选择将疼痛公之于众以及叙事的方式都会影响外界对其疼痛的处置方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个体的疼痛置之不理,而是需要掌握识别与聆听疼痛的技巧。帕特里克·沃尔(Patrick Wall)[20]认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疼痛一词至少有感觉性的、情感性的和评价性的多层意思。”疼痛往往不是单纯的被感受到,而是伴随着由疼痛而带来的负面情绪及文化意义,包括难以承受感、孤独感,甚至是被遗弃感。很多临床经验告诉我们,疼痛者在描述疼痛体验的时候,往往是在描述以个体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感受为核心的情绪的表达与倾诉。关于疼痛的叙事至少有以下特点:首先,这样的叙事是以患者为主体,在进行描述时是以他们为中心,建构出一套图景来说明自己与周围世界关联的过程,并由此生产出关于他们自身的“新知识”;其次,不仅在内容的讲述上是以他们自身的身体感受、遭遇为核心,从方式上来讲也是通过他们的身体在讲故事;再次,在讲述与叙事的背后能够感受到宏观社会环境下,个体与时代互动,心理及身体渐变过程的一种展示,也就是社会如何影响到意识以及人们意识怎么构建这个过程故事的描述[21]。
兹比格纽·齐利克兹(Zbigniew Zylicz)[22]在考察疼痛者时,通过观察提出了更为形象的“疼痛房屋结构需求理论”。他认为,疼痛者在叙事过程中,通过叙述的内容主要想表达的目的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表达出的是对身体状况的担忧,这也是所谓的房屋的基层结构。在这个层次的目的中,疼痛者会通过对疾痛的叙事表达出想要延缓身体变化以保证身体机能能够不受到过多损伤的需求。第二层次的目的是为治疗效果的实现,这相当于房屋结构中的梁和柱子,它们撑起了房屋的整体结构。在这个层次,患者将自己在治疗上的需求明白无误地传递出来,期待医生运用专业知识满足他们对症状控制的需求。第三层次则是对人文关怀的渴求,这也是最内在、最高层次的需求,相当于房子的屋檐。疼痛者渴望以沟通的形式缓解疼痛给心灵带来的疾苦,同时它通常包含患者以往的患病体验,医生、药物或者治疗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拒绝某些治疗,或者他们已经接受的治疗为什么收效甚微的答案[23]。
不难看出,在疼痛的感觉中伴随着大量的个体主观意义建构,通常这种意义的核心内容与疼痛者本人所具备的文化或者价值观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尽管人们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也可以感受到痛苦。因此,要理解处于疼痛困扰的人们的疼痛感受与疼痛状态中的处境,必须揣摩在这些有关于情感与情绪的语言背后的意义,在这些意思的相互映衬、相互组合下,个人有关于疼痛的经验和体验才能立体地呈现出来。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每一种疼痛对于个体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并且这种独特性也是疼痛的本质之一。由此不难看出,对疼痛的解读,关注的不仅仅是其身体层面的痛苦与不适,更需要解读其疼痛叙事之后的需求与期待。并且,疼痛主体对疼痛的诉说其实就是他们表达诉求、寻求帮助与求得关怀的一个过程。
5 结语
疼痛绝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感觉与表现,它还具有“情绪”层面的意义,因此它是生物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结合体。它存在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空间,具有不同生活经验、拥有不同痛苦感受能力的个体身上,不同的历史时期饱含着对疼痛的不同价值取向及意义的建构。当个体表现出他人能感知的疼痛行为以后,这时候的疼痛变成了一种社会事件,疼痛者希望社会对这种疼痛有一种反应的开始[24]。当把疼痛放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境况中时,疼痛作为人类“苦痛”的一部分而存在,彰显了权力与社会结构两层意义。同时,疼痛又永远不会局限于身体与心理的认知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感觉与情绪,由于它的不良体验,将它放置在社会中引起了独特的身体隐喻与社会象征。作为承载这种独特感受的个体而言,疼痛带来的表达方式又受个体所在文化的熏陶以及个体对疼痛的认识有关。每一种疼痛对于个体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并且这种独特性也是疼痛的本质之一。对疼痛的解读,关注的不仅仅是其身体层面的痛苦与不适,更需要解读其疼痛叙事之后的需求与期待。并且,疼痛主体对疼痛的诉说其实就是他们表达诉求、寻求帮助与求得关怀的一个过程。如何发现疼痛及其背后的意涵,这不仅关乎解除疼痛的方式,也是认识个体对人生经历理解与表述的途径,对疼痛本质的认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