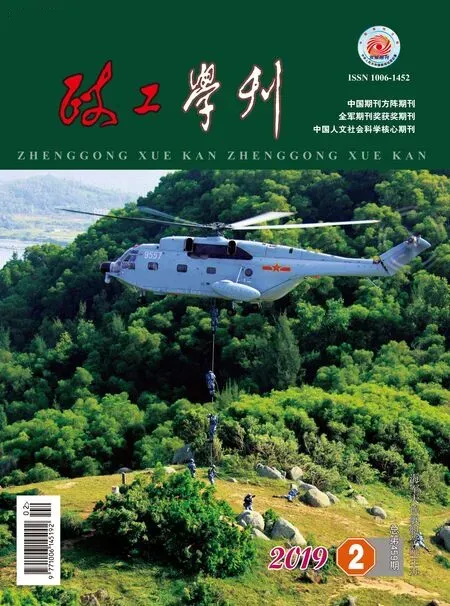难忘那“冬青”
☉葛 欣
鹅毛般的雪花自天穹簌簌落下,天地间浑然一片银白。巍巍的哈达岭一改往日严峻陡峭的面孔,此时如一头憨厚的北极熊静卧在雪野中。山岭上那几个孤独的哨位,被积雪覆盖,仿佛成了“熊背”上的点缀。刚刚下连的我此时无心欣赏周边的雪景,跟在班长后头,踩着厚厚的积雪默默走向哨位。

我自小生长在繁华都市,见惯了车水马龙,本以为能留在城市部队里,没成想新训结束后的一纸分配命令,让我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偏远哨所。站岗、巡逻、挑水、劈柴、种菜,没有一样是我拿手的,在这里城市兵似乎找不到一点用武之地。我站在哨位上,任风雪呼啸着经过耳畔,遥望那连绵的远山,对着家乡的方向迷失在乡愁中……
雪越下越急,天色变得更加灰暗,一股股的寒风裹挟着刮落的枝叶一起冲进哨位。“降温了,把大衣捂严实点!”班长的声音从对面哨位飘来。
在哨所,班长是唯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信任的人。自从我踏进哨所营门那一刻,班长就像见到亲兄弟般,又是提行李,又是打洗脸水。吃面条时,还往我碗里夹了一个大荷包蛋。往后的日子里,班长又主动跟我站一班岗,一路巡逻,一路天南海北地侃大山。虽然,班长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和他在一起,我总能感到几分开心。
又一股寒风吹得哨位“吱吱”作响,我猛然从思绪中醒来,感觉两只耳朵火辣辣的又疼又痒,便下意识地用双手捂住。班长走过来,仔细看了我的耳朵后说:“怎么不把帽子放下来,耳朵都冻伤了!”
生平第一次被严寒冻伤双耳,肿胀感一阵阵袭来,我感觉又委屈又无助,泪水盈在眼眶中。这时,只见班长迎着寒风走向哨位旁的一棵大杨树,干净利落地爬了上去。当他再次回到我面前,手里多了一团发绿的叶子。我很奇怪,在这种风雪严寒天气里,除了松树竟还能看到绿色。班长说,这是冬青,挂在叶间的果实叫冬青果。班长把冬青叶和冬青果捣碎,小心翼翼地涂抹在我的耳朵上。那股清凉柔顺让人感觉很舒服,耳朵上的疼痒消减了许多。
班长告诉我,虽然南北方都有杨树,但只有北方寒区的杨树上才生长冬青,它是治疗冻伤的特效药。冬天,风雪严寒瞬间就使杨树枝叶无存,而正是这种恶劣天气“赐”给杨树又一片新绿。更巧妙的是,这片新绿还具备了治愈严寒创伤的特性。“人有时就跟这冬青一样,遇到逆境并不一定是坏事,说不准它本身就是一剂催化成长的良方!”班长拍拍我的肩头说。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能来到这大山之中,结识了班长,见到了冬青,分明就是一种幸运。心底产生这样一种信念:自己一定要像这冬青一样,突破严寒,傲立风雪,展现灿烂夺目的本色!摘下一团冬青叶带回哨所,耳朵上的冻伤渐渐痊愈,几乎冰封的心灵也开始解冻。
第二年年底,班长退伍了,即将回到南方老家。我由于各项工作成绩突出,成为哨所的下任班长。临别时,我把珍藏了许久的几片冬青叶夹在日记本中,送给了班长。
多年后,我当上老连队的指导员。每当看到战士因生活艰苦而抱怨,因孤独寂寞而烦恼,或因工作无果而灰心,我就会带他们来到哨位旁的杨树前,给他们讲冬青的故事……
——致坚守奋斗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