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的年
刘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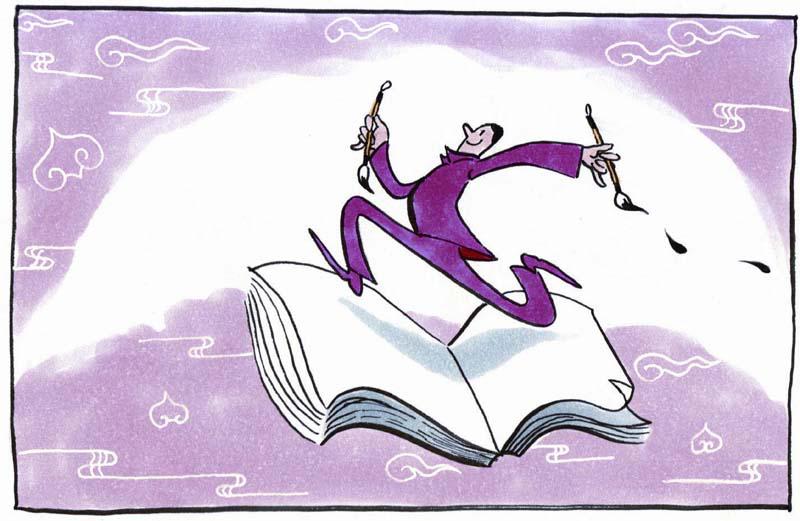
游子生涯几十年,身影若飘飞风筝,故乡是一缕拴牢的丝线。每逢过年,我必回湖北大冶老家过。当年,要從苏州坐火车到南京,辗转下关码头,半夜迷迷糊糊登江申号或江汉号江轮,逆长江水而上,很慢。后来是汽车,提速不少。再如今是动车和高铁,更快。我深刻感受了四十年中国交通的变化,不断缩短游子与故乡年的距离。
往返期间,我一直有个“经典形象”:嘴叼车船票。我曾在一首小诗中写道:“左手提着苏杭/右手拖着天堂/背上驮着舀来一瓢的北上广”。并且还有这样的句子:“我这认家的狗/叼一根骨头乐得直摇尾巴/我这恋巢的燕/衔一坨春泥飞向我的旧梁”,都与嘴相关联。也透露了我的一大特点:喜欢大包小包往家乡带土特产,带吃货,年在嘴上。行李多,分手乏术,在鱼贯而入的队伍中,我只好用嘴叼着票,检票进站。
家乡亲戚多,十几家人,还有左邻右舍,带少了还真的不够分。于是,我就成了苏州特产的“搬运工”,知名特产中的“采芝斋”“黄天源”“稻香村”,都被我一年一年往故乡搬。早年,我是晚辈,我仰视的目光中领略长辈品尝我的孝敬。一晃,我仰视的目光变成了俯瞰——长辈都一个个走了,我就成了长辈。于是,从孩童嚼食异域的香甜中,我弯腰打捞做长辈的呵护。老家的年就像一个水缸,我带回的一小桶外地水,注充入水缸,滋润着亲情树下的孩童。
但是,孩童吃了我的嘴软,除了嘴上道谢,除了嘴上拜年,还有别的有用嘴之处。那就是,读书!
我有地域的比较。我所工作的这个城市,文化氛围浓郁,家家都把孩子读书学习看成头等大事。故乡则多有人家玩麻将。走在乡村,似乎满世界都是搓麻将的哗哗声。这让我深恶痛绝。
但大过年的,不玩麻将玩什么?他们就好这一口,咱总不能夺人所好吧?没问题,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别人家的孩子咱管不了,自家的孩子我要管管的。我也让他们跟我赌一把,一小时内能背诵出三首古诗的,奖励一百;背诵出四首的,奖励两百……重赏之下必有勇孩!
于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在孩子们哇啦哇啦的吵嚷声中,几分钟就搞定。再来一首,“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又是几分钟搞定。厉害啊,眼看奖金就要到手了,再来再来,于是,年过罢就会迎来春天,那春天的好诗就更多啦,看看这一首怎么写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很快,称我“大伯”的,称我“表伯”的,称我“细爹”的,一个个都排队来领奖金了。没问题,言必有信,崭新的百元大钞,在一阵琅琅书声中,哧溜进了各人的口袋。
于是,孩子高兴,大人更高兴,俏皮话也来了:“有本事啊,我们挣钱是卖苦力,动手挣钱。你们呢,靠嘴挣钱,动动嘴皮子钱就来了。”“哈哈,这就是古人说的‘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家出了这么多的小君子,简直就是祖宗积德了啊!”
第二天,小家伙们又排着队,还要再挣“动口钱”……
没问题,继续读书,继续动嘴,还有钱挣!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在家族中形成一个爱读书的风气,尤其是辞旧迎新的过年时节。若干年后,他们都长大了,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定会有这“嘴上的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