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各圈层的人都在读什么书
曾勋
2018年,知识付费、媒体融合甚嚣尘上,网络的喧嚣在图书的次元掀起了波澜。这一年,纸媒寒冬令出版人愈加担忧,也有人于风雪中破冰前行,在“互联网+”时代寻求纸质书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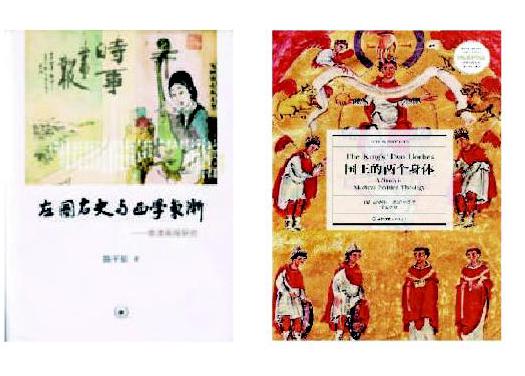
几年前,读者能在书市上看到作者是App的书吗?2018年,一本作者为“××云音乐”的《听什么歌都像在唱自己》横空出世,惹得不少音乐粉情怀爆棚。这本书精选200余条云音乐上的优质评论,脑洞大开,不设页码,选用字典式独特的分类检索色块设计,大量留白可供读者随手记录心情和生活感悟,将碎片化阅读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说到网络文化登堂入室,《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一书更加纯粹。这本网络文化辞典,网罗了近几年风行的二次元、宅文化、网文、游戏和流行文化等元素,将另类思想植入传统文化载体,将“潮流”与“学术”融合。有人说,进入电子文明后人类将重新部落化。如今,在网络空间以“趣缘”而聚合的各种“圈子”,数量恐怕早已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因血缘而繁衍的部落。这些网络新部落有着自己的生态系统和话语系统,其繁殖力和流通力都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创造的文化同样不该被忽視。
不过,正如《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中的破坏王一样,网络文化有属于自己的“代码”,而出版人的人文坚守也从来没有缺席。
2018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分别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考工记》《缮写室》《遥远的向日葵地》《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奥古斯都》《加缪传》《米沃什诗集(套装)》《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美国学者马修·德斯蒙德创作的非虚构作品《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获得了评委投出的18张选票,在十部好书中名列榜首。北京大学知名学者陈平原所著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则获评“年度推荐书”。
图史研究的入围似乎预示着这样的阅读趋势:哪怕是学术读物,也在寻求图文搭配的视觉冲击。
实际上,连环画在古代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鲁迅上私塾时,老师甚至禁止他们带有图画的书进学校。今天抖音等视觉娱乐媒介的盛行与画报在晚清走红,有异曲同工之妙。世俗娱乐与精英读本虽然历来走的不同路数,却在不同维度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
2018年还有一件让图书界“津津乐道”的事情,那就是削减书号供给,不少出版社削减了40%到50%。出版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正蓄势待发,也有书评人不太乐观,认为2018年的各大图书榜单普遍亮点不足,人文关怀与锐利度逐年消解。所以,到年末,一些学人晒出2018年自己的读书单,对那些不随大流、对图书榜单不感冒的读者提供了参考。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说,有的书读起来还是得正襟危坐,那就叫它“坐读”类。这一类书有,费拉里的《城邦与灵魂》、尤金·罗根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和卡洛·罗韦利的《现实不似你所见——量子引力之旅》等。而有一类书是闲而又闲的阅读,可称之为“卧读类”,比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弗里曼·戴森的《天地之梦》。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2018年对三本书做了深读:一是论述中世纪晚期神性化国王问题的《国王的两个身体》;二是介绍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三是揭示纳粹以毒品助战争的著作《亢奋战:纳粹嗑药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专栏作家毛尖则表示,应该再看一遍朱迪丝·施克莱的《平常的恶》,它会让我们为即将大量涌现的“次级文化”做好准备。其中就包括“平常的恶”,这些恶的重要性、它们的危害以及价值和重要性,都将在2019年后显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特别推荐刘统的《战上海》,此书以极为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从1949年5月到1950年5月,大上海如何在各种惊心动魄的时代关卡中突围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