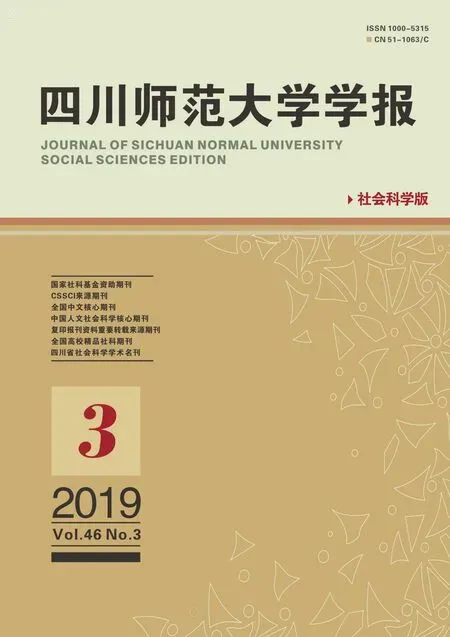康德哲学中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之关系新释
——批判的建构性道德哲学之基石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区分是康德自由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性的区分,是理解康德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钥匙,也是其解决本体理念实在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它对于把握康德的整个体系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对于其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又是种种关于康德哲学的争论的一个根源。
康德断言,先验自由是独立于一切经验性条件而绝对自发地引起因果序列的能力,而实践自由只是意志独立于感性的爱好而依据理性引起行动的能力。但实践自由是否有超经验层面,两种自由之间是否具有依赖关系,这一直是国际康德学界争论的焦点,其中有本体主义、自然主义、主观主义和拼凑论等相关解释。笔者提出一种先验主义的新解释,认为实践自由是一种先天的自由,并且它有现象层面而未必有本体层面,它不依赖于先验自由,而在实践的眼光下,对行动者而言,实践自由有本体和现象两个层面,先验自由构成了实践自由的条件。而这种在实践眼光下的实践自由,以及它与先验自由的关系,都不是单纯主观的。在实践的眼光下,人是自由的,不仅意味着我们主观地相信自由理念的现实性,而且意味着自由理念现实地影响着我们的经验性行为。我们可以在自由的理念下行动,而不必在实践中考虑我们是否有先验自由的理论问题。康德在始终坚持其严格性的哲学本色的前提下,创建出建构性的道德形而上学,在理论上为道德和规范性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基础,形成了西方自由理论与道德哲学的一座高峰。澄清其深刻而微妙的自由思想,对于当代的自由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一 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内涵
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区分对于理解康德的自由理论而言至关重要。在康德看来,先验自由是超自然、超经验的能力,而实践自由属于经验世界的层面,但也可能有超经验的层面,心理学的自由则完全是经验性的能力。根据德文版《康德全集》数据库,康德对实践自由及其与先验自由的关系的讨论在康德全集中的页码主要为:A534/B562;A802-803/B830-831;4:346;5:6;5:93;8:13-14(作于1783年);18:420(作于1769-1771或1766-1768);17:589(作于1772-1775或1769-1770);17:688(作于1773-1775年或1776-1778年);18:443(作于1783-1784年);19:258(作于1783-1784年);29:900-903(作于1782-1783年)。
心理学的自由指存在者独立于经验中的外在对象的直接决定而根据自身的主观意识而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现象层面的“心理学的属性”,是“按照经验性原则来解释的”[1]94。据此,人处于一个必然的因果链条之中,其中我们每一瞬间的观念都是被之前的观念所决定的。
先验自由本身是理论哲学中的宇宙论意义上的自由,体现在不被任何其它的原因所规定,而构成了宇宙中因果序列的根本原因的能力,它不在于经验的因果序列之中,却构成了这种因果序列的根据。这种存在者是一种本体的原因,而不是那些服从经验的因果律的原因。先验自由是“能够自行开始行动的某种自发性的理念,这种能动性不允许预先准备一个另外的原因再来按照因果联系的法则去规定这个自发性的行动”[2]A533/B561。先验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无条件的独立性,而且是一种“自行开始一种状态的力量”[2]A533/B561。
就实践自由而言,《纯粹理性批判》将其解释为是人独立于感性的冲动并根据理性所设立的原则(不仅仅包括道德原则)而行动的能力,它不仅使人能按照长远的实用目的而行动,而且使人能按照普遍的道德法则而行动[2]A802/B830。而在之后的著作中,康德基本上都把实践自由理解为人独立于感性的爱好和冲动并根据理性所设立的道德原则而行动的能力。实践自由概念内涵的转变,乃是基于后来康德对自由与道德有了更独特、透彻的理解。他论证了这一观点:他律的行为在其根本的层面是不自由的,换言之,它们在根本上是不自由的。以满足感性的爱好和冲动为最终目的的行为,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的自由,因为它体现出人对当下感性冲动的独立性和根据理性规则行动的能力,但是,它在根本的层面上说是不自由的,因为这些爱好和冲动是被自然界给予我们的,而不是我们主动形成的。
实践自由包含自身给自身原则(自我立法)的能力,而不是单纯以根据被给予的原则而行动的能力。根据第一批判,实践自由体现在“理性本身在它由以制定法则的这些行动”中,也包括“在感性冲动方面”的自由,即包括(积极的)立法的能力和(消极的)对感性冲动的独立性[2]A803/B831。“因为德性原则惟一原则就在于对法则的一切质料(也就是对一个欲求的客体)有独立性,同时却又通过一个准则必须能胜任的单纯普遍立法形式来规定任意……纯粹的且本身实践的理性的这种自己设立法则是积极理解的自由。”[1]33在此仅仅独立于欲求客体而自律的自由是实践自由,因为独立于一切经验性因素的自由才是先验自由。
康德指出,一方面,我们不一定有先验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不仅仅有心理学的自由,还有先天的实践自由。康德也从其它的角度分别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表达同一观点:在理论的眼光下,先验自由是不可知的,在实践的眼光下,我们是现实地自由的;自由理念没有理论的实在性,而有实践的实在性。据此,在理论的眼光下,实践自由是否以先验自由为根据,这是不可知的,在实践的眼光下,实践自由以先验自由为根据。
下文将表明,在理论的眼光下,实践自由有现象层面而未必有本体层面,而在实践的眼光下,实践自由有本体和现象两个层面。但是,在实践眼光下,人有本体层面的自由、有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自由,只是意味着我们在实践中有权利、也不得不设想人是自由的,并在自由的理念下凭借关于自由的信念而行动。现实的行动赋予了(指向本体的)抽象自由理念以实在性,这种实在性是实践上的实在性,而非理论上的实在性。
二 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的区别
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的区别,在于理性独立于感性的冲动与理性独立于一切自然原因的区别。先验自由只属于本体界,而实践自由肯定有一个现象的层面,但也可能有本体层面。实践自由是“相对的自发性”,先验自由是“绝对的自发性”[3]443。实践自由只是对感性的独立性,而先验自由是对整个自然和(基于自然的)宿命的独立性,后一种独立性是实践自由未必具备的。体现着实践自由的活动可以在时间上先行的条件作为根据,而先验自由背后必定没有任何先行的条件作为根据。而且,理性在设立法则后通过法则规定抉意,这必然需要理性引起的敬重作为中介。实践自由的有条件性的根据在于,体现实践自由的理性及其自律的活动有经验的层面,该层面必然被先行的自然原因所决定。但由于理性与自律的活动可能也有(不可知的)本体层面,因此,它可能也是基于先验自由的。实践自由为人所拥有,但先验自由不一定为人所拥有;而人有实践自由和人不一定有先验自由,这两点并不矛盾。
第一,先验自由是超经验的能力,实践自由必然有经验性的层面,可能没有超经验的层面。前者是对整个自然及其宿命的独立性,后者只是对动物性的独立性。“摆脱动物性的自由(spontaneitas practice talis[实践类型的自发性])/摆脱宿命[fatalitaet]的自由(transscendentalis[先验的]”[4]317。
先验自由体现于“独立于感官世界的一切起规定作用的原因”而“开始现象的序列”,它当然就绝不可能通过任何感官世界的原因来解释,因而不可能通过自然的法则来解释;毋宁,先验自由“看起来是和自然律,因而和一切可能的经验相违背的,因而所以仍然是一个问题”[2]A803/B831。
先验自由是无条件地引起某种状态、并由此引起相继的因果序列的能力;先验自由的原因性体现在,某物(可能是理智)不仅仅构成了事件序列的第一开端,而且它并不是基于某种既定的特殊本性而成为这种开端,而是自己给自己设立根据,自己赋予自己以原则,并由此引起某些因果序列,因此,并没有任何外在的原因作为先行的条件,而使得该物的活动得以可能,并按照经验的因果律而决定了它的活动。“这样,就不单是一个序列将通过这种自发性而绝对地开始,而且是导致产生这序列的这个自发性本身的规定性、也就是因果性也将绝对地开始,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先行在前而使这一发生的行动按照常住的规律得到规定”[2]A445/B473。
实践自由是意志独立于感性的冲动而对意志作规定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本身有其经验性层面,因而有其先行的自然原因,可以用经验的因果律来解释。“但理性本身在它由以制定法则的这些行动中是否又是由别的方面的影响所规定的,而那在感性冲动方面被称作自由的东西在更高的和更间接地起作用的原因方面是否又会是自然,这点在实践中与我们毫不相干……实践的自由是自然原因之一,也就是理性在对意志作规定时的原因性,而先验的自由却要求这个理性本身……独立于感官世界的一切起规定作用的原因……”,这里的法则是指上文的“客观的自由法则”,即“自由意志的一般必然的道德法则”[2]A803/B831;A55/B80。实践自由体现在“制定法则的这些行动”和对“感性冲动”的独立性;据此,究竟实践自由是完全被自然所引起和决定、还是背后还有一个绝对自由的本体层面,这是无法认识的。
实践自由(设立和遵循道德法则的能力)有其经验性的、被自然决定的层面,而它是否有超经验的层面是不可知的。根据康德的经验决定论,所有经验性的事物与活动都是完全被决定的。“……假如对我们来说有可能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一旦它通过内部的或外部的行动表现出来就具有如此深刻的洞见,以至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每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动机、连同一切对这一动机起作用的外部诱因也都为我们所获悉,我们对一个人在未来的行为举止就有可能如同对一次月食或日食一样确定地测算出来……”[1]99。由此也可看出,我们的所有经验性活动,我们在时间中通过抽象的思考而建立先验原则,以及我们按照这种原则而来的行动,本身也是经验原因造成的。而且,在人的内心中,有许多我们难以认识的隐秘动机,在严格意义上,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我们是否真的出于道德法则而行动。即使“通过最严厉的自省”,我们仍然“……根本不能有把握地断定,确实完全没有任何隐秘的自爱冲动,藏在那个理念的单纯假象之下,作为意志真正的规定性的原因;……但事实上,即使进行最严格的审查,我们也绝不可能完全走近背后隐藏的动机”[1]99。当然,实践自由背后有没有经验的原因,这是先验自由的问题,是一个理论哲学的问题,而不是实践的问题,实践哲学可以置之不顾。
第二,实践自由要发挥作用需以情感为中介,而先验自由可以不借助这种中介。道德的敬重感和精神快乐等情感是我们以实践自由规定行动的主观性条件。道德法则不仅仅是行为的客观的规定根据,“也是该行为的主观的规定根据,因为它对主体的感性有影响,并产生一种对法则影响意志有促进作用的情感”[1]75。他在下文指出这种情感就是对法则的敬重。康德在此指出,道德法则能够有充分力量规定主观意志,并非因为它与情感无关,而是由于它能引起道德情感。由于我们的道德行为有来自感性的“内部的阻碍”,通过敬重的情感来推动道德行动就是必要的[1]79。因此,“即使意志独立于刺激(stimulis),它也不是完全地自由的”[5]899。当然,在道德行为中,道德情感只是理性本身的结果以及其作用的中介条件,道德情感倾向只是道德活动的一个辅助性的必要条件,它也并不能被看作理性的目的和根据,而理性本身是独立于这种倾向的,情感因素不是道德活动的最根本的根据。没有独立于理性的道德动机。
第三,两种自由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先验自由可以体现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而实践自由只是在实践领域中的自由。首先,康德认为,纯粹理性是独立于感性而凭自身创造理念、形成先天综合判断并通过这种判断进行推理的能力,这种能力如果背后没有自然作为原因,它就是独立于一切外在因素而引起事件序列的能力,因而就是那种体现先验自由的所在。其次,纯粹理性既能够运用于认识活动,也能运用于实践活动(并为意志提供准则的普遍形式),因而,如果纯粹理性有先验自由的话,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都有先验自由。纯粹理性能够设立道德法则并对抉意提出命令,并由此引起敬重的情感。尽管这种法则及敬重不能规定人的抉意,它毕竟完全自发地产生了某些影响,引起某些后果,因而是某种本源的原因性。而显然,实践自由是实践领域的一种行动的能力,它不属于认识领域。
先验自由属于思辨哲学研究的对象,而实践自由是实践哲学研究的对象。“所有这些关于自由的先验概念的争论都在实践上没有影响。因为我在这里并不是关注最高的原因,而是终极的目的。”[5]903在自律的行为中,人们在追求道德的善,在此之上没有更高的目的。对于道德的行动者的意志而言(或在这种行动者看来),他并没有任何道德法则以外的根据,他完全独立于一切的经验性因素,单纯根据定言命令而行动;然而事实上,追求善的目的作为一种时间中表象,其背后还是可能有其它经验性的原因(如先行的事件序列),因此,他的道德意识可能是幻象,而他的行为则完全被经验原因所决定。
三 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一致性与联系
自由就是自我决定,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作为康德哲学中两种基本的自由概念,不仅具有许多的共同点,而且有着内在的关联。康德宣称,实践自由的概念和先验自由的概念无非是“自由的实践概念”和“其思辨概念”,前者运用于实践,后者是形而上学才考虑的宇宙论对象[6]13。先验自由也有理性的规定根据,可能体现于人的意志,从而构成实践自由的根本层面。而且,人有实践自由意味着人能根据先验自由的理念而行动。
第一,两种自由的共通点在于,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一样,也是以理性为规定根据的。先验自由要具体发挥作用,也是要有规定根据的,只不过自由的行动者通过自主设立“理知的根据”而引起事件的序列[2]A545/B573。康德说,先验的自由“要求这个理性本身(就其开始一个现象序列的原因性而言)独立于感官世界的一切起规定作用的原因”,或要求独立于一切先行的原因;但是,没有任何先行的、被给定的根据,不等于没有任何规定根据[2]A803/B831。康德在《形而上学演讲录》中批评了“由于自由不服从物理的诸法则或感性的诸法则,人们就认为它不服从任何法则”这一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推论”,“但我们在根据知性的诸法则而行动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因为这些确实是由我们产生的”,这时我们就不是被任何外在的事物决定,而是被自我所决定,并因此具有自发性[5]902。
第二,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一样,可以体现在意志的自由之上。因为人可能通过其本体的层面上的理知品格而有先验自由,因而对其行为具有负责任的能力,并在实践上成为可归咎的。首先,在探讨意志的先验自由与自然决定论的相容性时,康德这样评论一个关于居心叵测的谎言的例子:“这一行动被归于他的理知的品格,他在现在正在说谎的这一瞬间中完全是有罪的;因而理性不顾这一行为的所有那些经验性的条件而完全是自由的,而这一行为完全要归咎于理性的失职。”[2]A555/B583在此,意志的自由独立于一切经验性条件,因而就属于先验的自由,人有可能具有作为本体的理知的品格,以此引起经验性的品格和自然事件序列。人只能成为构成宇宙中事件序列的部分原因,无法像大写的创世者(如果有的话)那样引起所有的现象的序列,这并不否定,由于人的本体层面能够独立于一切经验性原因,人的行为“永远是一个第一开端”[7]346。其次,康德说:“但是,作为本体,也就是说,按照纯然作为理智的人的能力来看,正如它就感性的任性而言是强制的那样,因而按照其积极的性状来看,我们在理论上却根本不能展示它。”[8]226这里康德把先验自由和作为本体的人的能力的自由等同起来,可见先验自由和人的意志自由的一致性。
第三,先验的自由,可以体现于自律的能力(意志设立和遵循客观原则的能力)之上,因而可能体现在实践自由之上,因为实践自由恰恰就是这种自律的道德能力。“除了自律、即那种自身就是自己的法则的意志的属性之外,意志的自由还能是什么呢?”[7]446-447这里的意志自由是先验的自由,因为它被界定为“独立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的属性,而不仅仅是独立于感性的爱好的属性;意志自己是自己的法则,就是说意志自己建构了意志的因果关系的普遍原则,意志按照自由的因果法则(而不是自然的因果法则)来引起某种后果,就是自律[7]446-447。在《奠基》中康德认为,先验自由体现在独立按照法则去行动的能力之上,而并非不能有规则和规定根据的。我们所能够解释的,只是“可能的经验中被给予”的对象,“但是,自由是一个单纯的理念,它……不能在任何可能的经验中被阐明……它只是作为在某个存在者里面理性的必要前提而有效,这个存在者相信自己意识到一个意志”,“也就是说作为理智、从而按照理性的法则独立于自然本能去规定自己的行动的能力”[7]459。这种非经验的、作为单纯理念的自由就是先验的自由,它被看作理性存在者所能具有理性的前提,这个作为自由的前提就是独立按照理性法则去行动的能力。
因此,实践自由可能以先验自由为其基础性的层面,从而也可能体现人的本源的自发性和绝对的独立性。因此,有一种可能的观点认为,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区别在于,前者以任何先行的规定根据为条件,而实践自由则相反,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康德的思想。
第四,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的内在的联系体现在,实践自由之所以可能,是由于理性能够根据先验自由的理念而行动,但理性并不一定根据先验自由本身而行动。
关于两种自由的依赖关系,不少研究者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中的法规论中的观点是与其辩证论中的观点相矛盾的,并认为在法规论中的实践自由不以先验自由为条件,而在辩证论中则相反;而也有很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
对于这个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辩证论中以下论述是争论的焦点。康德认为,实践自由“以这个自由的先验理念为根据”,“因为实践自由的前提在于,虽然某物并没有发生,但它本来应当发生,因而它的原因在现象中并没有如此确定,以至于在我们的抉意中不包含有某种原因性,这种原因性独立于那些自然原因,甚至违抗自然的强制力和影响而产生某种在时间秩序中按照经验性规律被规定的东西,因而完全自行开始一个事件序列”[2]A533-534/B562。以下,笔者先正面阐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然后与其他解释者进行商榷。
笔者以为,由于康德在“辩证论”中所提出的关于某物“应当发生”这一理由是实践方面的,他的结论也应当是在实践的意义上说的:只是在实践的视角下(对行动者而言),人有先验自由,它构成了实践自由的基础,换言之,由于人的先验自由的理念(即纯粹概念)现实作用于行动、并能(连同道德法则)规定行动,人才有(独立于动物性的)实践自由。只是在这种实践的意义上,“辩证论”声称实践自由以先验自由为前提。我们只有在实践的理解中的自由,或者说我们只是在实践的眼光下是自由的,我们有根据先验自由的单纯理念(但不是先验自由本身)而行动的能力;而这又意味着,仅在现实的行动者的意志看来,人有先验自由,有完全的独立性和无条件的原因性。但是在理论上、就其自身而言,人未必有先验自由,实践自由也不以先验自由为必要条件。实践自由是指根据自由的理念而行动的能力,因而是根据道德法则而行动的能力:“自由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根据这种理念去行动,就是在实践上自由的……”[5]898在《奠基》和第二批判中,康德把实践自由理解为在实践视角下的先验自由(独立于一切自然原因而根据道德法则行动的能力),理解为某种先天的、但未必是超经验的能力。
具体而言,实践自由对先验自由的(单纯)实践意义上的依赖性体现在:人们只有把自身看作对一切经验原因具有独立性的,因而能够体现出尊严和崇高性的,人才能在行动中形成对自由理念和道德能力的现实性的理性肯定和感性敬重,从而能够按照道德法则去行动,因而才具有实践自由。每个有普通人类理性的人都有道德的关切和意念,这种道德意识使我们设想自身具有先验自由,并能根据自由理念原则而行动。但这并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关于自由的知识[7]455。
可见,关于实践自由及其与先验自由的关系,康德在独断论的意志自由论和宿命论之间,选择了先验主义的立场。他坚持,人的实践自由未必基于作为物自身的绝对自由,但也不是以自然原因所规定的、纯然主观的自由;实践自由有被自然决定的经验层面,但也可能以先验自由作为内在根据。我们必然在自由的理念之下行动,就是说我们有实践地理解的自由(Die Freiheit im praktischen Verstande)。我们之所以在实践中设想我们为先验地自由的,是由于我们设想我们应当遵循道德法则。根据《奠基》,在实践中,我们必然会把自身看作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体,因此必然把自身同时看作理知世界和感官世界的成员,其先验自由构成了经验性的行动的根据。
但是,人有实践自由与人可能在存在论上没有先验自由并不矛盾,我们只是在实践视角下才有先验自由。首先,在发表于1783年的关于舒尔兹的书评中,康德论述了尽管自由的思辨概念无法被认识,但即使最顽固的宿命论者也会在实践中把自身看作是自由的,因为在关于舒尔兹的评论中,康德论述了尽管自由的思辨概念无法被认识,但即使最顽固的宿命论者也会在实践中把自身看作是自由的,因为我们不得不在不同的行为准则之间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本身预设了不同的行为可能性和自由,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对自由的肯定中行动,即在自由的理念下行动。“因为我现在应当在其中行动的状态原初是从哪里来到我这里的,这可以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我只问我现在可以做什么,而在这里,自由就是一个必要的实践预设,是我惟有在其下才能把理性的诫命视为有效的一个理念。”[6]13其次,这一点在《奠基》中又得到了肯定:我们在实践上是自由的,只是意味着自由“被理性存在者仅在理念中当作其行动的根据”,尽管在理论上,先验自由的现实性问题无法被认识[7]448。
对康德辩证论中的关于实践自由及其与先验自由的关系的观点,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根据柯尔(Kohl)等人的本体主义解释,实践自由和先验自由一样,也是超经验的自由,并且,它依赖于先验自由。“只有当存在(一般而言的)一种非自然的原因性,它不被自然原因所决定而起作用,才会有这样的意志的原因性,该原因性不被感性的冲动所决定而起作用。”[9]316他认为,“辩证论”和“法规论”的观点并不矛盾。尽管康德在“法规论”中肯定,“为了实践的目的我们可以……在实践中忽略我们是否先验地自由的问题”,但是,“这不意味着,康德相信实践自由与物理学原因的必然的强制相容”[9]328。
根据盖斯曼(Geismann)的自然主义解释,实践自由是属于现象界的自由,这种经验性的自由却依赖于本体界的先验自由;先验自由是理论上的宇宙论对象,实践自由是实践哲学的对象,人们在理论上需要先验自由理念,在实践中会忽略这个理念。盖斯曼说:“康德的立场可以预先概括如下:当人们在思辨的(理论的)视角下把握自由,也就是当人们把自由建立在其可能性上,那么不诉诸它的先验理念就是不够的……与此相反,当人们仅仅在实践的眼光下把握自由(或自由作为实践的概念),那么人们就可以忽视这个理念;它“在实践上”完全不被需要。下文将会表明,无论在《纯粹理性批判》之中还是在其之外,之前还是之后,康德一再都把他的立场表达得清楚明白”[10]284。他认为,“康德基本上也在其他的地方,并且在授权出版《纯粹理性批判》之前和之后都另外作过在这两段话中让人感到混乱的断言”,但第一批判的“辩证论”和“法规论”的论述并不矛盾[10]283。他声称,实践自由只是“自由的现象”(libertas phaenomenon);行动者知道他有实践自由,但不知道它与这种先验自由相始终,不过这对他来说也是“完全无所谓的”,因为他不设立“能够自行开始行动的某种自发性的理念”,也不提出关于“更高的和更间接的起作用的原因”的“思辨的问题”[10]301。但我们不能像很多人那样认为“康德在法规论中最终把自由还原为自然。‘在取消先验自由的同时就会把一切实践的自由也根除了’这个论题,‘法规论’没有反驳一个字,法规论中所断言的,辩证论也不与之相矛盾”[10]301。
但这与康德的观点并不一致。首先,《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实践自由并不仅仅是经验性的。它确实也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原因,但这只是它的现象层面,但它可能也有本体层面。
然而,这只是从现象的视角看才是如此,这种视角下人对自我和对象的认识都通过主观的先天直观形式才得以可能,由此我们把握到的是人的经验性的品格,而人的本体层面的存在或理知品格毕竟并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又不能仅仅把先天的实践自由看作经验性自由的一类,所以康德指出,实践自由是否以任何先行的规定根据为条件,这是我们无法认识的“问题”[2]A803/B831。实践自由体现在理性行动者以自身为根据的行动中,它并不必然以先行的规定根据为条件。抉意固然是被动因所规定的,但是并不必然被某一种动因所决定,它也能够以“自由的法则”即道德法则为动因并被其决定。如上所说,实践自由不仅仅包括遵循法则的能力,也包括设立法则的能力。由于道德法则是意志或实践理性自身设立的,意志自我设立法则并遵循这种法则,这是自由或自我决定的体现,因此,只要意志或实践理性的立法背后没有自然作为根据,那么,实践自由就有一个超验的、本体的层面。其次,先验自由的本源性在于自主地设立根据,自发地设立法则而自我决定,而不是在于没有规定根据。先验自由的本质其实在于自我决定的自发性,而不是不被决定。
对于两种自由的关系,阿利森等人采取主观主义的解释。阿利森认为,在此康德只不过认为,在实践的眼光下,我们会把自身设想为有先验自由的,换言之,拥有先验自由不过是被主观设想的属性;而由于我们都主观地设想自身为理性的行动者,我们必然会主观地设想自身为拥有先验自由的。“无论如何,通过对自发性的‘契机’的坚持,它确实暗示,自由的先验理念何以可能被看作发挥着一个作为模型的或调节性的功能,该功能指向我们(或其他存在者)作为理性施为者(agent)的观念”[11]26。对阿利森而言,自由理念的调节性功能并不在于规定准则,而在于维持我们作为理性施为者的主观观念。因此,阿利森认为:“在‘辩证论’中康德只是断言实践自由对先验自由的一种概念上的依赖性而不是本体论上的依赖性”[11]57,换言之,我们主观上(通过概念)把我们设想为有先验自由的,设想它构成了实践自由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理论的意义上有先验自由,而只意味着我们有实践自由。
此外,还有玄耐克(Schönecker)等人持拼凑论的解释,认为康德把相互矛盾的两种观点拼凑在一起:根据第一批判的“辩证论”,超经验的实践自由依赖于先验自由,而根据第一批判的“法规论”,经验性的实践自由却不依赖于先验自由。实践自由在辩证论中是一个先验的实践自由(先验的-实践自由),相反,在法规论中的有条件的实践自由在本性上完全不是先验的[12]91。由此他认为康德在辩证论和法规论中对两种自由关系的论述是无法相容的。
笔者认为,对辩证论中的实践自由的本体主义的解释会面临许多困难。如果在强的、本体论的意义上,先验自由构成了实践自由的基础,那么,肯定了实践自由也就肯定了先验自由。首先,在逻辑理据方面,本体主义解释和康德基本的批判主义立场不相容。根据本体主义解释,我们能够以现实性、实在性等范畴来认识先验自由,通过经验界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经验来证明先验自由。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坚持,我们不能以知性范畴来认识本体,也无法通过经验现象来证明本体。其次,在文本依据方面,较强的解释无法与康德对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关系的一贯论述相一致。根据以上论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关于舒尔兹的书评和《奠基》等处一再说明,我们能够证明实践自由,但是人是否有先验自由,以及实践自由是否基于先验自由,这仍然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证明了实践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就证明了后者。
根据盖斯曼等人的经验主义解释,实践自由是经验性的,但它依赖于先验自由。除了上文提出的诸理由外,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和康德的一个基本观点不符合,即独立于感性的爱好和冲动无需先验自由,自然及其宿命就已经足以让人拥有现象界的实践自由,以至于只要知道了人先前的动机,“我们对一个人在未来的行为举止就有可能如同对一次月食或日食一样确定地测算出来……”[1]99因此,经验性的实践自由并不像盖斯曼所说,以先验自由为必要条件。
另外,盖斯曼的这一观点也并不恰当:先验自由的理念对于把握实践自由的概念而言不是必要的,这个理念并不构成实践自由的条件。“……当人们仅仅在实践的视角下把握自由(或自由作为实践的概念),那么人们就可以忽视这个理念;它“在实践上”完全不被需要”[13]284。但是,尽管先验自由本身不是实践自由的必要条件,先验自由的理念却是它的必要条件;如上所述,只有当我们设想我们有先验自由、并由此行动,我们才拥有实践自由。
阿利森对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关系作了主观主义的解释。对他而言,实践自由对先验自由只有概念上的依赖性。他把这种关系看得过于主观了。然而,先验自由理念的意义并非只是使我们可以主观地把自身看作行动者,却没有独立于我们的视角的现实自由。在康德哲学中,那种依赖性尽管不是本体论的,但也是具有现实性的,是相关于现实的经验世界和其中的实践活动的。而实践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我们把抉意(主观地)看作是有先验自由的,而且还意味着我们能根据这种设想去行动。实践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视角,而且也是某种具有实在性的现实活动过程,由此康德才建构了理性诸纯粹理念的实在性。
而且,阿利森认为,康德一开始就预设了人的施为能力(agency)和道德归因的正当性,他又对康德对道德法则和自由的论证进行了详细的重构,但根据这些预设,康德的自由理论就是独断论的,而且,从这些预设出发即可直接得出在实践视角下人有自由的结论,这使得他对其论证的繁复重构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澄清实践自由和先验自由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对于理解康德的进一步理论运思和论证都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玄涅克认为康德在辩证论和法规论中关于自由的论述是不一致的“拼凑物”,然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经过两个版本的长期的认真写作,很难说他没有意识到同一本书前后两部分、不同著作的不同论述的明显不一致,因而,他在辩证论和法规论中对实践自由的两种阐述更可能是在不同意义上说的。而且,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康德的实践的意义和理论的意义的区分,便会发现两处的论述并非不可调和。
康德道德哲学超越了传统的独断论的意志自由论和经验主义决定论,而建立了先验主义自由观,为道德与规范性的确定性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他以其实践自由的概念为实践哲学奠定自由意志的基石,形成了西方自由理论与道德哲学的一座高峰。澄清其深刻而微妙的自由思想,对于当代的自由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Volker Gerhardt教授、张传有教授、邓晓芒教授、宫睿博士、袁辉博士等学者的专业性建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