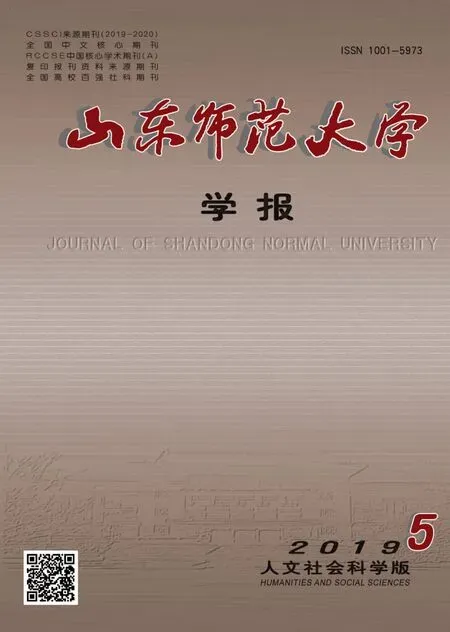鲁迅积累与创造的文学理论知识*①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
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家,鲁迅一生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文学理论知识,作为一位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他还根据自己文学创作的丰富经验以及所积累的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知识,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文学观念。这些文学观念由于能被逻辑或经验所验证,在属性上不仅仅具有主观性的“信念”,而且具有客观意义的知识,并且是具有创造性的新的文学理论知识。(1)关于信念与知识的关系以及鲁迅的模型信念与理论知识的关系,参见许祖华:《鲁迅的信念系统与知识系统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无论是鲁迅积累的文学理论知识还是创造的文学理论的知识,都不是以集中的形式(文学理论的著作的形式)得以彰显的,而是以分散的状态留存于鲁迅关于古今中外文学评价、研究、介绍的成果以及各类杂文和书信之中的,但鲁迅这些丰富多彩的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却仍然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体系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鲁迅关于文学的理论知识,关涉到了文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二是这些理论知识关涉到了他生存的年代及之前的古今中外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
文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果进行概括,不能不关注文学的来源、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人的关系(包括作家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性质(包括文学的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等)、文学的审美性质(如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等)、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如主题、题材、环境、情节与结构、情感、语言等)、文学创作的思维(如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文学体裁(如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的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风格、文学的继承与汲取外来文学营养,等等。关于文学的这些基本问题,鲁迅都有相应的论说。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如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文学思潮与流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启蒙主义、革命文学等)、文艺复兴运动、苏俄文学、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日本文学、魏晋文学、唐宋文学、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国防文学等,鲁迅也有相应的论述。这些论述直接彰显了鲁迅所积累的各种文学理论知识,也包含了鲁迅关于文学的一些真知灼见,正是鲁迅基于自己关于文学的各种模型信念,在既有的文学理论知识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文学理论的知识。
为了论述的方便和实证关于鲁迅积累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理论知识的判断,下面引用鲁迅谈文学的言论: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年)
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
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1934年)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鲁迅《给徐懋庸》(1933年)
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
这些言论,虽然只是鲁迅关于文学的“只言片语”,犹如文学理论知识大海中的“沧海一粟”,但从中我们能感受到大海的宏阔与壮丽;尽管它所针对的文学现象或问题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都不仅关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创作问题,如革命文学问题,也关涉文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如文学与社会(环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作家(创作主体)的关系,文学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文学的起源,文学审美的重要范畴悲剧与喜剧,等等。鲁迅这些“只言片语”所表达的关于文学的各种认识,有的并非是鲁迅的原创,而是他认可的别人的观点,属于他积累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知识,而有的则是鲁迅原创的,属于鲁迅在既有知识基础上创造的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虽然其存在形态是零散的,但其所关乎的文学理论问题却是成体系的。
刘中树在谈到鲁迅文学观的“体系”时曾经指出:“从改良人生、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革命目的出发,以对文学本质的唯物主义认识为理论基础,通过对中外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的历史考察,形成的文学本质观、为人生的文学观、现实主义文学观、‘革命文学’观、文学批评观、比较文学观以及文学史观等构成了鲁迅文学观的基本体系。”(2)刘中树:《鲁迅的文学观》,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页。刘中树虽然不是从知识学的层面谈鲁迅所积累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知识问题,更没有区别鲁迅“文学观”中的观点哪些是“积累”来的、哪些是原创,但他的观点却为我们论述鲁迅关于文学的理论知识“体系”提供了思路,即根据鲁迅关于文学理论的主要论题来透视鲁迅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及其特点。按照这一思路,鲁迅所积累及创造的与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包括价值)相关的理论知识,应该是本文要论述的主要对象。因为,这一类关于文学的理论知识不仅是鲁迅所积累和创造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知识中最为重要的知识,也不仅是包含了鲁迅独特眼光和特有的文学兴趣的一类关于文学的理论知识,而且还是与鲁迅创造的新的文学知识的成果,特别是文学创作的成果,如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等关系最为紧密的一类知识。这些知识或者直接、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或者本身就是从其创作实践及所形成的经验知识中高度凝聚提炼出来的知识。所以,聚焦鲁迅积累和创造的这两个方面的理论知识,等于抓住了鲁迅文学理论知识结构中的核心内容。
一、鲁迅积累与创造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知识
所谓本质,也就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根本的特征。文学的本质,即文学这种人类创造物与自然及人类创造的其他事物最重要的区别特征。文学的本质观,也就是认识文学的最主要特征的观念。那么,这些观念关涉文学的哪些问题呢?具体就鲁迅的文学本质观而言,应该关涉哪些问题呢?对此,刘中树有较为明确的论述:“鲁迅文学观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他的文学本质观,也就是他的文学起源论、文学的审美特征论和文学的审美功能论。鲁迅的文学观点和主张,都是建筑在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3)刘中树:《鲁迅的文学观》,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页。也就是说,鲁迅的文学本质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学的起源问题;二是文学的审美特性问题;三是文学的功能问题。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问题包含了文学的一系列重要的本质问题,如关于文学起源的问题,不仅关乎认识论上的唯物还是唯心的思想方法问题,而且关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的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还关乎文学有无功利性等本质问题。而文学的审美特性及其功能问题,又直接关乎文学作为一门艺术与其他人类创造物如哲学、宗教、科学等相区别的最主要特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三个问题入手,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透视鲁迅积累或创造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知识的主要状况。
关于文学的这三个问题,我们在鲁迅留存下来的文字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论述或观点。而这些论述和观点,有的是鲁迅积累的文学理论知识,按照学界较为通行的提法,也就是“借鉴”的别人的观点或学说;有的则是鲁迅在汲取既往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创造的文学理论知识。既往关于鲁迅文学观的研究成果,都没有对此进行相关的区分,而是统统归入“鲁迅文学观”中。这样的研究虽然也有意义,也能在相应的框架中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论述鲁迅文学思想的系统并收获相应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没有进行“借鉴”与“创造”的区分,所以,我们无法清晰地透视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在理论方面非凡的创造性以及其关于文学理论方面所作出的别人无法替代的杰出作用。而从研究的意义上讲,论述鲁迅接受或受到了什么人、什么文学理论的影响固然重要和有价值,但从鲁迅丰富的“文学观”中阐释鲁迅所创造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新知识,则似乎更有意义和价值。鲁迅创造的这些新的文学理论知识,正是鲁迅作为一个“伟大”作家、杰出的文学理论家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要区分鲁迅接受与创造的文学理论知识的直接而重要原因。
关于文学的起源,鲁迅在其相关学术著作或文章中所写的下面两段言论,是经常被人们引用的: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认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313页。
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5)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关于文学起源的这些言论及所表达的观点,我们如何来区分哪些属于鲁迅积累的文学理论知识,哪些又是鲁迅创造的新的文学理论知识呢?唯一的标准就是:在鲁迅提出相关学说之前,古今中外的作家、诗人及理论家们在相关文论中,是否有过相关论述。如果有,那就属于鲁迅积累的文学理论知识(即使拿不出直接的证据——鲁迅留存的文字证明鲁迅汲取了这些知识,也不能将这样的一些论述、观点、理论视为鲁迅的原创,最多只能用“英雄所见略同”来解释,而即使相同的见解,也有一个先后的问题,更何况鲁迅与既往关于文学起源的学说之间,少则相差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多则上千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则属于鲁迅创造的新的文学理论观念,而这些观念如果能够被事实或定理(逻辑)所确证,则属于“知识”,因为所谓“知识”就是被验证合理的信念。
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鲁迅关于文学起源的这些言论,那么,“文学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属于鲁迅积累的文学理论知识,因为在鲁迅提出这一观念之前,中外作家及理论家们早就有相关的论述。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里,就曾根据人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人类“劳动成果”出现的先后顺序:“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和航行。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5页。这段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不仅直接地揭示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历史过程,而且指出了艺术本身就是劳动的成果。具体就鲁迅所提出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的观点来看,诗歌起源于劳动的观点也早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有明确的论述:“工作如何进行——由一个生产者或者是由整个一群人——决定了歌的产生是为一个歌手或是为整个合唱团,而且后一种又分成若干种。在所有这些场合下,歌的节奏总是严格地由生产过程的节奏所决定的。不仅如此,生产过程的技术操作性质,对于伴随工作的歌的内容,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7)[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在这里,普列汉诺夫不仅直接表达了诗歌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并且具体地论述了诗歌的基本形式——如节奏由劳动的“过程的节奏所决定”与诗歌的内容也直接受到“生产过程的技术操作性质”的影响等问题。至于艺术起源于宗教,不仅在黑格尔那里有过这样的表达:“从客体或对象方面来看,艺术的起源与宗教的联系最密切……只有艺术才是最早的对宗教观念的形象翻译”(8)[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4页。,而且在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弗雷泽和法国人类学家雷纳克那里更有系统的关于艺术起源于人类最原始的宗教——巫术的学说,等等。虽然,鲁迅在论述文学起源于劳动,特别是1924年论述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的过程中,并没有引用既往任何一位学者、诗人等的理论学说,他系统接触普列汉诺夫“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观点,也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翻译、介绍普列汉诺夫的代表作《艺术论》的时期,但我们在鲁迅发表“诗歌起源于劳动”观点之前所留下的相关文字中却也能找到这一观点是“汲取”前人学说的根据。早在1913年,鲁迅就翻译了日本心理学家上野阳一的《艺术玩赏之教育》和《社会教育与趣味》两篇论文,并都撰写了“译者附记”。上野阳一在《社会教育与趣味》一文中,不仅提出了“艺术原始于存身保种”之说,而且陈述了“农人亦植秧有歌,牧畜有诗”(9)[日本]上野阳一:《社会教育与趣味》,刘中树:《鲁迅的文学观》,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页。的情形,明确地表达了“诗歌起源于劳动”而且是具体的劳动——植秧、牧畜的观点。固然,从影响的层面来说,鲁迅关于诗歌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并非只来自上野阳一的一家之说,作为一位眼光和视野都十分开阔的文化人、文学家,鲁迅常常是转益多师为吾师的,但这样的直接材料起码能够说明,在提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观点之前,鲁迅已经从上野阳一那里获得了这一方面的知识,鲁迅能够顺利地翻译上野阳一的论文并给予相关的评说,认为他的《艺术完赏之教育》一文“所见甚挚,论亦绵密”(10)鲁迅:《艺术玩赏之教育·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9页。,《社会教育与趣味》一文“立说浅近,颇与今日吾情近合”(11)鲁迅:《社会教育与趣味·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1页。,本身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事实上,不仅鲁迅关于诗歌起源于劳动的文学理论知识是汲取的,而且鲁迅对“无文字之前”人类文学创作的命题所进行的相关论述,也是汲取的。如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谈及的“‘杭育杭育’派”(12)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自发表以来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多方引用,几乎成为了一种经典性的权威话语。的确,鲁迅这段话及其列举的事例和所表达的观点不仅很奇特,也不仅十分形象生动,而且很新鲜,较之既往关于文学起源于劳动学说的论述,特别是欧洲或西方人的相关论述,要简洁、形象、生动很多。但这段话的内容,不仅其观点是汲取的,而且其“假设”的事例——原始人抬木头的事例,也是借鉴的。这样的观点和事例,早在中国西汉时期的文化典籍《淮南子》中就有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13)刘安:《淮南子》,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95页。这里记载的内容,至少有三个方面与鲁迅上述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完全相同:一是所描述的具体劳动的事例——原始人抬木头的事例相同;二是情景相似——抬木头者在抬木头过程中出于某种目的发出声音;三是都认可这些抬木头者所发出的声音尽管十分简单,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简单的声音就是“创作”(文学)或诗歌。那么,怎么样证明,鲁迅在《门外文谈》中的这段论述来源于《淮南子》呢?下面一些第一手的材料可以证明:第一则材料是,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开篇就论及了《淮南子》一书所记载的如“共工争帝地维绝”等事“仍谓寓言异记”的性质;第二则材料是,鲁迅还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专门介绍了《淮南子》一书的结构、内容及其字数,还专门介绍了这本典籍编撰的主持人淮南王刘安的大致情况以及其编撰《淮南子》一书的大致目的等,总之,介绍得较为详细;第三则材料是,鲁迅还分别在1921—1925年的日记中多次谈及《淮南子》的各种版本,等等。这些材料不仅能够说明鲁迅熟悉《淮南子》一书的内容,而且能够说明鲁迅对其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虽然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并没有标明自己这段话的材料、观点的出处,但通过上面的简要比较以及通过鲁迅与《淮南子》一书关系的材料,我们完全可以说,鲁迅这里所表达的关于文学起源的观点依然属于汲取的知识。
当然,在这段文字中,鲁迅也创造了新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其创造的新知识主要表现为三个相互联系的观点:一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出发,提出了文学是普通劳动者的创造物,文学历史的开篇并非是由圣贤们拉开的帷幕,而是由普通劳动者首先书写的观点;二是在这样的历史观下,肯定了这些目不识丁的劳动者“作家”的身份;三是从文学流派的层面提出了在人类文学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杭育杭育派”。这三个观点,不仅既往的中外文学家、理论家们没有提出过,而且即使与鲁迅同时代的中外作家、理论家也没有人如此肯定地提出过。这也许就是鲁迅这段话及其观点发表后之所以能产生巨大而长久影响的最主要的原因,它不仅承继了既往的文学观,更在既往此类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知识。之所以说这三个观点是知识而不仅仅只是观念,是因为它们都经受得起验证,特别是经受得起众所公认的这样的历史结论的验证:原始时代,人类还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也当然没有相应的所谓“身份”的分类,所以,作家也好,画家也好,这些后来被我们认为是精神劳动者的人在原始时代本身都是体力劳动者。
在鲁迅关于文学起源的众多观点中,最值得一提,也是最有新意的原创观点,是鲁迅提出的“小说起源于休息”的观点。这是鲁迅首创的观点。在鲁迅之前的中外文论中,找不到这样的观点。即使是欧洲人的“游戏说”理论,如康德的“艺术是一种游戏”的理论和席勒的“艺术起源于力量过剩的游戏”的理论等,都没有从劳动与艺术创造的主体人在劳动中或劳动后“休息”的层面进行过论述,更没有人明确地指出“小说”这种艺术形态起源于人生存的一种基本的状态——“休息”。鲁迅提出的这一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尽管可以讨论,甚至可以批评,而且这一观点也不一定就是最有说服力和最为精彩的,却是可以被验证的。鲁迅自己对自己所提出的这样观念就进行了基于经验与逻辑的验证:“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咏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1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这种验证,前半部分主要是基于劳动的过程和经验的验证,后半部分(即诗歌是韵文,小说是散文)则主要是基于逻辑的验证它在事理逻辑上没有什么漏洞,经受得起推敲并能自圆其说;在“事实”上,我们不仅提不出反例和反证,并且如果进行实践或者根据我们已经有的经验与经历来体会,那么还会有相应的“感同身受”。所以,它是“真”的,具有知识性(因为所谓知识本来就是被验证是“真”的观念或者信念)。
不仅如此,1927年,鲁迅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的文学观,将自己“小说起源于休息”的观点,从“起源”领域推广到“文学生产”的领域。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从“起源”的层面讲,诗歌、小说的起源不同,但从“文学生产”,特别是“写作”的层面讲,则所有文学都只有当人“休息”的时候才可能产生,无论什么时代,包括“大革命时代”也不例外。鲁迅还用生活的事例与“大革命”的事例对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15)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这样的论证,也就是对自己观点的验证。虽然鲁迅提出的观点可以讨论,但他基于生活常识与事实的“验证”不仅能自圆其说并形成较为典型的“一家之言”,而且也经受得起推敲。无论是基于经验还是逻辑,当一个人在从事某种别的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分身”同时从事文学创作这种精神生产的,即使他在从事别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的时候,可以进行文学创作的“构思”活动,但他要将“构思”的观念性成果变为实际的文学作品,也只能是坐下来“写作”才有可能。所以,鲁迅这样的观点不仅因为能被证明是“真”的,具有知识性,而且是鲁迅在自己创造的“小说起源于休息”文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关于“文学生产”的新的理论知识。鲁迅非凡的创新能力,于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提出“诗歌起源于劳动与宗教”“小说起源于休息”这些观点的同一时期(1924年),鲁迅翻译、介绍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两部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一部是纯粹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一部是文艺性的随笔《出了象牙之塔》。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翻译、介绍这两部著作的,鲁迅所做的这项工作的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为中国文坛输送了别样的、新颖的文艺理论,而且在于丰富并进一步地完善了他自己与文艺起源密切相关的知识结构。如果说,之前鲁迅所积累的文学起源于劳动与宗教的知识,主要关涉的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一关乎文学本质问题的知识的话,那么,鲁迅对厨川白村“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16)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学说的接受,则使鲁迅在原有关于文学起源知识的基础上,增加了人(作为创作主体的人)与文学关系的知识,从而使鲁迅关于文学的起源与发生的文学理论知识,由原来的二维结构,即文学与生活的结构,发展为生活、人、文学的三维结构。这个三维的知识结构,不仅较之二维的知识结构更为完善,而且也能更为有效地说明文学的起源与发生。虽然,早在系统接触厨川白村基于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所阐发的关于文学发生的学说之前,鲁迅自己就曾用创作历史小说《补天》的实践活动,“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17)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但那个时候,他毕竟没有系统积累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在小说中,他也只“解释”和生动地讲述了“人的缘起”的故事,却没有“解释”“文学的缘起”,而当鲁迅积累了关于人与文学关系的厨川白村所提供的文学理论知识之后,他也才有了这样的发声:“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18)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特别强调了人,尤其是人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对文艺产生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凸显了人的本质属性的“主体性”(即人的各种能力,如思维能力、认识能力、自主能力、创新能力等的总和)对艺术发生与生产的决定性价值。
正是在关于文学起源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完善的基础上,甚至就在完善关于文学起源知识的同时和前后,鲁迅不仅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积累了关于文学的社会性、阶级性、时代性及民族性的理论知识(此类例证众多且研究成果丰富,故不列举详论),而且也不断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一些新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如他关于有地方色彩的文学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观点,即是一例;“拿来主义”观则又是一例;至于其关于文学的审美特征理论的创新也是一例,而且是较为集中体现其创新成果的一例。
二、鲁迅积累与创造的关于文学审美特征的理论知识
关于文学的审美特征,古今中外的文学家、理论家从各个方面给予了论述,其观点可谓丰富多彩。鲁迅从“弃医从文”开始,就不断地从古今中外的文论中汲取这一领域的知识,并在其所积累的知识基础上奉献了一些创新性的成果,如关于文学的典型塑造理论;关于文学的形象性特征的理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情感性、倾向性理论,等等。而这些具有创新性的文学理论,大多与文学的审美特征有关。在这些与文学的审美特性相关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关于“高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关于审美范畴的悲剧与喜剧的理论创新成果,又是最值得关注的创新成果。
“高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悲剧、喜剧理论不是鲁迅首先论述的,而且,其概念本身也并非是鲁迅最先提出的,甚至大而言之,这些理论和概念也不是我们中国文论中既有的。它们都来自欧洲,是欧洲理论家、作家最早提出的概念,也是欧洲的作家与理论家首先论述的。如“高义”的现实主义概念,就是俄国的文学天才陀思妥夫斯基首先提出的,其理论也是他创立的。鲁迅曾经忠实地介绍过陀思妥夫斯基在自己的“手记”中所表达的这一观念或信念:“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巨制之一《卡拉玛卓夫兄弟》这一年;他在手记上说:‘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19)鲁迅:《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尽管现实主义学说在欧洲历史悠久,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但陀思妥夫斯基“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理论却不仅是一家之言,更是对欧洲现实主义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其突破与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这一现实主义理论不仅强调对人物的塑造注重性格、环境、细节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更强调“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二是不仅强调“反映”人的思想、情感等,更强调“拷问”人的灵魂;三是在强调拷问人的灵魂的过程中,不仅“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正是因为这种现实主义理论具有如此鲜明的创新性,加上陀氏的小说创作及其所形成的特色、倾向又以成功的实践的形态有效地彰显了这种“高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生命活力和审美魅力,所以,鲁迅十分欣赏甚至可以说是崇拜这样一位俄国小说家,认为“他太伟大了”(20)鲁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25页。,不仅崇拜他的小说创作,也崇拜其“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理论学说。但是,崇拜归崇拜,对于陀思妥夫斯基的这一文学理论学说,作为具有非凡创新能力的鲁迅,不仅有效地汲取了自现实主义理论以来这种最新的现实主义理论知识并热心地给予了介绍,而且还在解说其理论的过程中结合陀思妥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为“高义”的现实主义这种新的文学理论注入了“更新”的内容。这些“更新”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陀思妥夫斯基认为,“高义”的现实主义的思想与艺术追求主要就在于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而鲁迅则认为,不仅应该显示灵魂的“深”,还应该显示灵魂的“全”。这正是陀思妥夫斯基小说所表现的特点,但却是陀氏的理论所没有关涉的内容。所以,鲁迅说,陀氏主张文学要显示人的灵魂的“深”,“然而,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也就是小说创作中——引者注),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如果说,显示人的灵魂的“深”是陀氏“高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具有新意的学说的话,那么,鲁迅则在这个新的理论中或者说在这个新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显示人的灵魂的“全”的新内容。另一个方面是,陀氏否定“高义”现实主义者是“心理学家”,只认可是一个“写实”家,鲁迅则不仅认可“高义”现实主义者是人类心理的学者,而且认为:“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不仅强调人的灵魂的显示者需要有能力把握人的灵魂,而且强调这种“把握”还必须以“双重角色”分别从“审问者”和“犯人”两个角色的相互转换中来把握,并且认为,只有具备这样的双重角色并能够在两个角色之间进行成功的转换,“高义”现实主义者“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21)鲁迅:《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这就等于从理论上解决了创作主体如何实践或实现其“高义”现实主义的思想与艺术的追求,即显示人的灵魂的“深”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却是陀氏和别的人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也是鲁迅对陀氏“高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至于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与喜剧概念及其理论,是欧洲人最早提出的概念,也是欧洲人创建的理论。欧洲人不仅提出了悲剧与喜剧的概念并创建了理论,而且其创建的理论还十分丰富且精彩纷呈。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从戏剧类型的层面对悲剧与喜剧的特性等进行过经典性的论述,后经狄德罗、莱辛、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叔本华、尼采等,悲剧和喜剧则逐步从指称两种重要的戏剧类型的概念,升华为一对与“美”的本质紧密相关的美学的重要范畴并构成了多样的知识系统,如柏拉图的“痛感与快感”的知识系统;亚里士多德的“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模仿”,“悲剧是行动的模仿”的“模仿论”系统;黑格尔的“矛盾冲突论”知识系统;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系统;别林斯基的“诗的最高阶段(悲剧)和最后一型(喜剧)”的知识系统;叔本华的“解脱说”的知识系统,等等。同时,由于欧洲理论家们普遍认为,艺术的美不仅是美的形态最集中的表现者,也是美的本质最充分的凝聚者,而“美学的第一个问题和主要问题是艺术的定义”(22)[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页。,加之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与喜剧,本身又是欧洲人从研究戏剧这种艺术的两大类型中升华而来的,因此,悲剧和喜剧也就成为了与文艺审美特性紧密联系的一对范畴,甚至就是指称文艺的两种审美特性,即悲剧性和喜剧性、悲剧风格与喜剧风格的范畴。
尽管国内某些美学或文艺理论家认为,在中国古代美学家中,如写出“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的刘勰,“可以说是较早研究喜剧文学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喜剧观的美学家”(23)张玉能主编:《美学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但实际情况是,刘勰这位中国杰出的文学与美学家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既没有使用过“喜剧”(包括悲剧)的概念,更没有在本体论的层面对喜剧的基本属性进行定义、判断与推理,他仅仅只是从风格的层面谈论了中国谐戏类文学“悦笑”的特点、效果与作用。中国人引进悲剧和喜剧观念并真正参与关于悲剧与喜剧的理论建设,则是进入近代和现代之后。而真正从概念的层面对悲剧与喜剧进行定义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鲁迅。鲁迅关于悲剧的定义从问世以来,“几乎成了被许多人认可的悲剧定义”,鲁迅关于喜剧的定义从诞生以来,“也几乎成了许多人认可的喜剧定义”(24)朱晓进、杨洪承主编:《鲁迅研究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1-102页。。在中国,即使是那些以“西方美学理论”为蓝本和主要材料来源编撰的美学论著,也几乎于自觉或不自觉中引用鲁迅关于悲剧与喜剧的定义,如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张玉能主编的《美学教程》等。悲剧与喜剧这一对源发于欧洲、被欧洲一批又一批聪明的大脑进行了1000多年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学说和知识系统的美学与艺术学的范畴,为什么经过鲁迅的定义会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产生如此巨大的理论效果?答案只有一个:鲁迅关于悲剧与喜剧的定义不仅简洁明了,概括精准,经受得起文学(甚至社会)事实与理论逻辑的检验,而且角度新颖,具有创造性。就角度的新颖来看,既往欧洲或西方人关于悲剧与喜剧的定义与论述,或者从本体及效果的层面进行定义与论述,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或者从事物内部矛盾冲突的层面进行定义与论述,如黑格尔、柏格森,或者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的层面进行定义与论述,如马克思、恩格斯,或者从“目的”的层面进行定义与论述,如叔本华,或者从“命运”的层面进行定义或论述,等等。而鲁迅则另辟蹊径,从悲剧、喜剧构成对象的“价值”层面进行定义与论述,将“有价值的东西”与“无价值的东西”作为衡量悲剧与喜剧的构成性尺度,从而解决了如何为悲剧与喜剧定性的问题。就创造性来看,朱晓进、杨洪承在其编撰的《鲁迅研究教程》中,对鲁迅关于“悲剧”定义与论述的创造性列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鲁迅强调悲剧同社会生活的联系,从而与‘表现神秘的命运’的原始悲剧观以及与‘表现两种绝对理念的矛盾冲突’的唯心主义悲剧观划清了界限”;另一个方面是“鲁迅指出悲剧是一个‘毁灭’的过程,毁灭的对象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强调的悲剧性的毁灭,不是指以往一些美学家所概括的悲剧人物——‘好人’‘伟大人物’——的灭亡,而是不拘什么人物身上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而且,‘有价值的东西’也不拘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而扩大了悲剧表现的对象,使悲剧有了广阔的描写领域”(25)朱晓进、杨洪承主编:《鲁迅研究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对鲁迅关于“喜剧”定义与论述的创造性也列出了四点:“首先,他认为喜剧所描写的对象是‘无价值的’东西”,而这“无价值的东西”主要指上流社会的“伪”与下层社会的“愚”;其次,“指出了‘无价值的原因’”;第三,剔析了喜剧对象的独特性;第四,指出了揭穿“伪善”假象是喜剧的任务。(26)朱晓进、杨洪承主编:《鲁迅研究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2-103页。虽然这些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其对鲁迅关于悲剧、喜剧定义与论述创新的归纳也不一定全面与准确,甚至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与理由来说明这些观点是鲁迅在前人学说基础上创造的,但从其论述和归纳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到鲁迅在这一领域理论创新成果的概貌。
不仅如此,鲁迅还提出了与悲剧和喜剧这一对范畴密切相关的两个新概念:“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含泪的微笑”。这两个与悲剧、喜剧密切相关的新概念,前者是鲁迅通过评价现实主义作家果戈里的作品总结出来的,是鲁迅独特审美体验的理论性总结,也是鲁迅对悲剧理论的新贡献;后者是鲁迅引用普希金评价果戈里小说的话。
前者的创造性是显而易见的。既往欧洲或西方的悲剧理论几乎都是将“悲剧”归为轰轰烈烈的事件中英雄、名流的毁灭,关涉的几乎都是“轰轰烈烈的悲剧”和“英雄的悲剧”。欧洲悲剧理论之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27)[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诗学 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8页。这里所谓的“严肃”行动,只能是英雄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中的行动,不可能是小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因为,小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不具有任何“严肃”的性质,只具有庸常平凡的性质。至于欧洲著名的戏剧家高乃依则说得更为明了:“悲剧的题材需要崇高的,不平凡和严肃的行动。”(28)[法]高乃依:《论戏剧的功用及其组成部分》,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252页。俄国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也认为:“悲剧只集中最崇高的和富于诗意的生活片段”,“只适用于悲剧中的英雄或英雄们,并不适用于其他人”(29)[俄]别林斯基:《诗的分类和分型》,别列金娜选辑:《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187页。。而鲁迅却将“悲剧”归为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无所事事”或精神萎靡的状况,关涉的是“日常生活的悲剧”和“小人物的悲剧”。所以,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概念不仅与既往悲剧概念所指的对象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它是鲁迅基于自己鲜活的审美体验和独立的理性思考形成的一个关于悲剧的新概念,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并且也与自己关于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定义与观点统一起来。小人物虽然“小”,但他们身上同样是具备“有价值”的东西的,如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虽然庸常平凡,但也同样蕴藏着有价值的东西,如对爱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等。同时,这一关于悲剧的概念不仅新,而且具有可以操作的实践性品格,即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悲剧性的文学创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性作用。诚如鲁迅所说:“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30)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在实际创作悲剧的过程中,如果要创作“轰轰烈烈的悲剧”或“英雄悲剧”,很显然是较为困难的,因为其事、其人较少,作家的生活体验自然也少;反之,如果创作“日常生活的悲剧”或“普通人的悲剧”,则方便得多,因为其事、其人比比皆是,作家的生活体验也多。这也正是鲁迅创造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这一概念的价值之一,而鲁迅自己书写的一系列“日常生活的悲剧”和“普通人的悲剧”所形成的非凡的审美魅力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证明了创作“几乎无事悲剧”的可行性,更证明了鲁迅所提出的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理论的真性、知识性。
后者虽不是鲁迅创造的概念,但鲁迅高度认可这一概念,不仅反映出鲁迅特有的艺术兴趣,更反映了鲁迅敏锐的意识和对悲剧与喜剧这一对美学和艺术范畴的深刻理解。既往欧洲或西方人关于喜剧的理论,虽然也聚焦“笑”的审美效果,但其“笑”的本质都是对“丑”的对象——丑角、丑事、丑物等的否定甚至是鞭挞,基本不关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的“怜悯”情怀,而普希金的“含泪的微笑”的概念,却将喜剧的审美效果“笑”与悲剧的审美效果之一的“怜悯”结合起来。这一结合的结果,不仅渗透了事物普遍联系的辩证法,而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审美概念,即悲剧与喜剧交融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被鲁迅通过果戈里的小说的审美特征与效果验证过,而且也能被鲁迅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特征与效果所验证,如鲁迅所书写的孔乙己的悲喜人生、阿Q的悲喜人生等。所以,面对欧洲人和西方人提供的众多关于悲剧与喜剧的概念和理论,鲁迅在自己留存下来的文字中,几乎没有什么引用,唯独引用了极少被人引用的普希金提出的“含泪的微笑”的概念并给予了相应的解说:“听说果戈里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里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31)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3-384页。鲁迅的解说透出两点新意:一是肯定了由果戈里的小说开创的“含泪的微笑”的悲喜类型和风格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在别的地方也依然有用”,而这样的观点则是这一概念的创始者普希金没有论述过的;二是揭示了“健康的笑”与“含泪的微笑”相反的审美效果及其相反的转换,从而不仅进一步地肯定了“含泪的微笑”的杰出甚至“伟大”的审美效果,而且揭示了这种审美效果对读者的积极价值,即“果戈里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了健康”,以及对如作者果戈里一样“地位”(果戈里也是地主,与其在《死魂灵》中所讽刺的主要对象的地位一样)的人的“悲哀”。
三、鲁迅积累与创造的关于文学功能的理论知识
鲁迅关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理论创新可圈可点,而鲁迅关于文学功能(包括价值)的理论创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功能,无非是事物所能发挥的作用。所谓文学的功能,也就是指文学这种人类的精神性创造物所能发挥的作用。一般说来,文学的功能(也包括价值)与文学的本质是同质而异形的关系,即文学具有怎样的本质,它就应该具有相应的功能与价值。如文学是一门艺术,具有艺术(美的集中形态)的本质,它则必然具有审美功能及价值;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与表现,具有社会性本质,它也一定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与价值;文学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具有文化的本质,那么,它当然就具有文化的功能与价值。正因为如此,文学理论家们认为:“文学的功能问题也是文学本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32)姚文放:《文学理论》(修订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同时,由于文学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文学即人学”,因此,文学的功能也就主要表现为对人的作用,文学的价值也就主要表现为能满足人的某些需要,尤其是某些精神的需要。
鲁迅所积累的关于文学的功能与价值的理论知识,应该说也是十分可观的。这从他所涉猎的古今中外文论的事例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不过,鲁迅积累这些文学理论的知识并非是“掉书袋”似的积累,更不是“照本宣科”的吸收。面对古今中外浩瀚多彩的关于文学功能与价值的知识,他常常是积累中有消化,汲取中有新见。他所明确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就是这种状况的集中表现。
无须讳言,无论我们是将“文学为人生”作为一个关于文学的功能与价值的命题进行考察,还是将其作为一个概念进行考察,它们都不是鲁迅第一个提出并进行论述的,而是鲁迅从古今中外的文论中汲取的理论知识,尤其是从中国五四时期的第一个纯粹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们那里汲取的理论知识。“文学为人生”作为一个关于文学的功能与价值的理论问题或理论命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自从有所谓文学理论以来,就受到了各类先哲、名流、文学家、理论家的高度重视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学说。在中国,关于这一问题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应该首推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33)孔子:《论语·阳货》,《四书五经》,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第69页。之说;在外国,这一文学理论问题最集中的体现,则是影响深远的“寓教于乐”说,如古希腊的贺拉斯的理论:“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34)[古罗马]贺拉斯:《诗艺》,《诗学 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55页。中外的这些理论学说虽然没有使用“文学为人生”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地使用表达文学为人生的判断,但从其所针对的文学(文艺)的问题来看,莫不是关于文学(文艺)为人生(如孔子的学说)和怎样为人生的(如“寓教于乐”说)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文学为人生”作为一个概念,首先是由五四时期的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同仁提出的。1920年,周作人率先从文学本体论的层面提出了“人生的文学”的概念并进行了相应的论述:“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称它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跟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35)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文学研究会资料》(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同仁在总结一年来《小说月报》改革的情况时进一步强调:“我们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36)记者:《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文学研究会资料》(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7页。1922年,则有文学研究会的人明确地从文学的功能与价值的层面提出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今日底文学底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人生的,为民众的,使人哭和怒的,支配社会的,革命的,绝对不是供少数人赏玩的,娱乐的。”(37)之常:《支配社会底文学论》,《文学研究会资料》(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2页。在这个时期,沈雁冰、郑振铎、沈泽民、叶圣陶、朱自清等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也分别从不同方面对“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进行了相应的论述。茅盾1933年在谈文学研究会时指出:“现在看来,文学研究会团体虽然任何‘纲领’也没有,但文学研究会多数会员有一点‘为人生的艺术’的倾向,却是事实。”(38)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资料》(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9页。鲁迅自己也认可:“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39)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2页。鲁迅不仅认可文学研究会是一个以人生为本位并倡导“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团体,也不仅认可甚至赞赏其所提出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而且还在1932年直接使用文学研究会同仁提出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及其概念评说了俄国文学的主导性倾向:“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40)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3页。1933年,鲁迅更用这一主张及其概念总结了自己小说创作的基本价值追求并由此直接地表达了自己“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4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鲁迅对文学为人生主张、概念的认可和使用表明,他的“为人生”的文学观的来源之一就是文学研究会同仁的“文学为人生”的理论主张,其概念“为人生”也取自他们。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鲁迅虽然从古今中外的文论中汲取了关于文学“为”什么的理论知识,尤其从文学研究会的诸位成员的理论学说中直接地汲取了其“文学为人生”的理论知识,但鲁迅却也以自己的智慧,对这一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研究会同仁的理论贡献了自己的新知识,这种新知识主要关涉的是关于文学“为什么人的人生”的问题。
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不仅提出了文学要“为人生”的主张,而且也具体地论述了他们所要为的“人生”是谁的人生。沈雁冰就曾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42)冰:《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小说月报》1920年第11卷第1号。可见,他们所要为的“人生”就是“平民”的人生。对于“为平民”人生的文学主张,鲁迅不仅是赞赏的,而且在创作领域还是这一主张的最杰出的实践者。他收入《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中的作品就是证据。不过,鲁迅固然赞赏并切实地践行了文学为一般平民的人生的主张,但他并没有只限于文学为平民的人生的主张,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也没有只限于书写一般平民的人生并通过其书写践行为一般平民人生的主张,他所要为的“人生”要比文学研究会的同仁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
鲁迅在谈自己最初创作小说情况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4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1页。这段话很少被研究者关注并引用,却是十分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表明了鲁迅当初创作小说的时候“呐喊”几声的一个方面的目的——“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而且更表明了鲁迅当初创作小说的价值追求,是要“为”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的人生服务,“使他不惮于前驱”。如果说,在文学为人生方面,文学研究会的同仁更多强调、甚至“只”强调要为平民的人生的话,那么,他则不仅强调要为平民的人生,而且强调要为“前驱”与“猛士”的人生。如果说,鲁迅的《孔乙己》《药》《阿Q正传》《风波》等所要“为”的人生是平民的人生的话,那么,他的第一篇优秀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为”猛士人生的文学主张的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实践性成果。如果我们承认,《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精神界的战士”,他当然就是鲁迅所说的“猛士”,而且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因为狂人那些“离经叛道”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理解,更没有一个赞同,他只能在“孤独与寂寞”中自说自话、自做自事。而鲁迅对于其遭遇的书写,当然就是对他的“人生”的书写,鲁迅真切、生动而又深刻地写出了这样“猛士”的人生,按照鲁迅“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观点,不正表明在“观念”上鲁迅认为应该“为”像“狂人”一样猛士的人生而创作文学作品吗?或者说,鲁迅就是在他自己要“为”猛士的人生的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创作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创作的成功及其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这里。鲁迅“为人生”的文学及其观念的价值之一也在这里。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较之文学研究会同仁“为人生”的文学观更为深刻之一在这里,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的创造性之一也在这里。而这一切,恰恰又是既往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没有关注的。同时,鲁迅这一具有创造性的观念,由于有鲁迅自己的创作实践做根据,创作实践的成功又验证了自己观念的可行性和“真”性,因此,这一观念就不仅仅只是主观性的存在物,而是知识,并且是理论知识。这一理论知识,既是鲁迅对自己小说创作经验、体会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既往此类知识的丰富。
鲁迅最有勇气、最离经叛道地创造的关于文学的功能与价值的理论知识,特别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关于文学的功能与价值的有限性理论知识。
文学这种人类的精神创造物,自从诞生以来,几乎无人否认它的作用、认为它不重要。即使是给予文学(文艺)地位不高评价的柏拉图也仅仅只是认为文学与对象——理式世界“隔着三层”,并没有否定文学的功能与价值。相反,他还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优美的作品”对于培养青年们的健康、美的爱好、融美于习惯的美妙作用:“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们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从小就培养其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的习惯吗?”(4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62页。至于我们中国的先祖们,不仅竭力称道文学艺术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杰出而独特的功能与价值,而且还将其价值与功能提升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到了近代,梁启超更是在小说与国家、民族、民众等之间建立了一种直线的逻辑关系,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4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页。在这段激情澎湃的文字中,梁启超不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且将中国近代国家、民族、民众、社会以及政治、宗教、风俗、人心、人格甚至学艺革新的动力,都归结为小说的革新,甚至直接将近代中国的命运与小说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进入现代,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倡导者与建设者们,也莫不重视文学对人、对国民、对社会的重要而积极的功能与价值。郭沫若就曾指出:“有人说:‘一切文艺是完全无用的。’这话我也不承认。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有大用存焉。它是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圣箓,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46)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08页。还有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茅盾、巴金等著名的文化人与作家、诗人,也都充分地肯定并大力弘扬文学的积极价值与作用。
鲁迅则是一个例外。一方面,他也首肯文学的重要功能与价值,不仅与古今中外的作家、理论家们一样认为大业可消,文学生命长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47)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3页。,而且还常常对文学的积极功能与价值有新的发现,如上面所论述的鲁迅关于文学为人生的理论主张,就是一个直接的例子。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非凡创造力且特立独行的伟大作家,他又敏锐地洞察到文学功能与价值的有限性,并在中国近代与现代文坛一片赞扬、高歌文学伟大意义与价值的理论氛围中,提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由这样一些判断构成:第一个判断是“文章不用之用”,其意是指“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48)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第二个判断是“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第三个判断是“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49)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2页。;第四个判断是“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50)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这些观点的核心就是认为:文学虽然对于社会与人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文学的作用不是“全能”的,不仅在社会领域文学的作用不是全能的,即使对于人的精神作用来说也是有限的。如此的观点虽然出格,但却是经受得起检验的,因为无论是基于事实,还是基于文学的特性,文学的功能与价值也的确是有限的,并不如先祖们和贤达们所认为的那么“巨大”甚至无所不能。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哪个恶人、暴君或者侵略者(如德国法西斯与日本法西斯)会因为读了一首诗,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放弃侵略别国的;同样,历史上那些反抗压迫与侵略的英雄,他们的正义之举也并非就来自什么文学作品的鼓动;放眼当下,小而言之,那些沉溺于“网瘾”的“君子”们,没有谁会因为读了一首诗歌或者看了一篇小说就摆脱了“网瘾”的;大而言之,文学发达的一些民族与国家(如南美一些国家),其文学的成就并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并使本国的经济与文学一样发达;反之,一些经济很发达的国家,其经济的奇迹也不是由文学直接创造的,如美国。从文学的本性来看,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对人和社会虽然有影响,但任何影响,都只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基本和主要途径只能是“寓教于乐”,不具有任何强制的属性与能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历来谈文学的理论都不仅强调文学要有内容,更强调文学必须具有“艺术性”的重要原因。所以,鲁迅的这些观点虽然离经叛道,甚至惊世骇俗,却不仅是具有创意的观点,而且是知识,因为这些观点经受得起检验并能够证明具有“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