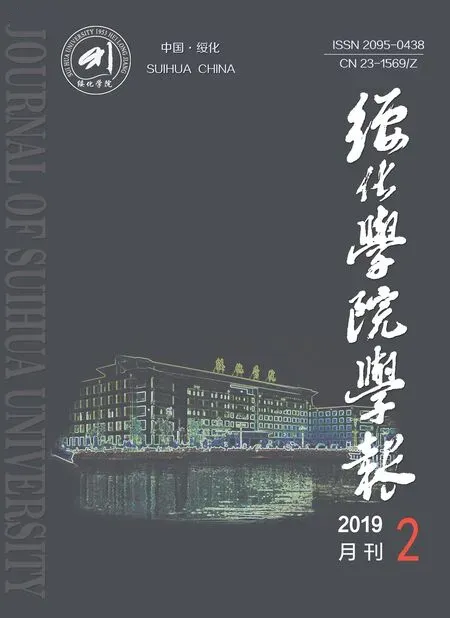月未圆 花已开
——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性别文化读解
宋为为 周丽娜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作为2017年的热播剧,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无疑有其吸引观众的多处看点,但其所传达的颇具现代色彩的性别文化观念应是最大看点之一。像曾经热播的《甄嬛传》《芈月传》一样,《那年花开月正圆》是孙俪主演的又一部典型的“大女主”电视剧。虽然后者仍然是一部女性成长的传奇励志故事,但女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却不再是“后宫”这一封闭的空间。《那年花开月正圆》讲述了清末陕西女首富周莹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女主人公的成长环境被移至一个更为开放也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在一个男权意识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环境中,一个女性如何突破重重障碍获得了经商权力和资格,并取得成功,这个故事本身蕴涵了极为复杂的性别文化观念。电视剧将现代性别观融入这个故事,从而将周莹的一生表现得活色生香。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年代剧。”因此也引起社会上对女性主义的热议。那么,该剧中的女主人公是否真正做到“女性独立”,其“独立”又展现出怎样的性别立场和性别文化观念,其所包含的女性观、女性解放意识又是表现在何种程度?周莹这朵已绽放的女性独立之花,处在封建男权社会环境下,又展现出怎样的冲突与和谐?基于此,从性别文化视角来审视这部电视剧,参照男权社会下女性难以独立生存的社会传统,以传统两性模式的转变、男权话语秩序的颠覆、人物的现代女性意识三个角度为切入点,探讨该剧所建构的性别文化内容。
一、从依附到平等:“花已开”之“双性和谐”
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所讲述的女商人周莹的故事有真实的历史根据,但它在原有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和虚构,用具有现代色彩的性别观念重新阐释了周莹的人生历程,使其仿若一支过早盛开于男权文化秩序中的现代女性之花。首先,周莹的婚恋追求中体现了强烈的两性平等意识和观念,表达了对“双性和谐”理想的肯定和认同。
周莹的历史原型是一个大家闺秀,奉父母之命与门当户对的吴家结亲,嫁入夫家后夫妻相敬如宾,度过几年幸福的时光,然丈夫英年早逝,没有留有子嗣,周莹最终以一个寡妇身份支撑起一个家庭。与历史事实相比,电视剧在人物身份、情感关系、社会矛盾等多方面都做了较大的改动,这些改动也是从大众文化需求、现代性别文化观等角度出发来更好地丰富周莹这个艺术形象,凸显人物之于特殊环境中所显现的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更能具有“陌生化”的效果,以吸引观众的眼光。著名女权主义者李银河说过:“男性将欲望对象投向女性,让女性被看成客体,这样的性别表述方式,总会塑造出一些理想化的魅力女性,从而使得女性主动去向那个理想化的形象学习,变得拥有美丽的容貌、性感的身姿,而把男人规范为具有攻击性、力量性以及聪明智慧的形象,进一步促使了男人凌驾女人,从而促使女人走向物化。”[1](127)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电视剧塑造出来的周莹是一个拥有主体意识的人,无论是在婚恋关系上、家族伦理秩序中,还是在经商道路上,都始终坚守自我,女性保有自己的主体地位,不同于同类商业题材电视剧把女性作为客体地位、展现其“男性”力量,周莹始终不为迎合男权社会的常规而改变自己的内心需求。
在周莹与吴聘的短暂婚姻中,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相对平等的夫妻关系,身为丈夫的吴聘尊重妻子的自主权利,没有用传统的三纲五常去约束妻子,在这样宽松自由的环境下,周莹的商业天赋被挖掘、放大。即便是一个如此完美的“暖男”形象,吴聘也不是一开始就完美无缺的,虽然他不囿于用传统伦理来约束周莹,但受于传统思维的影响,并不赞同周莹经商,在周莹言行的引导下,逐渐放下自己的“旧”思想,自身也变得愈加开朗。观众对吴聘的英年早逝大感惋惜,甚至“跪求”吴聘复活。基于创作团体的观点和此剧的整体走向来说,吴聘的“缺席”为周莹的“在场”提供了契机,吴聘可以说是周莹的人生选择的启蒙者,而周莹的出现也激起吴聘的性格的多方面发展,两人真挚的感情也为吴聘的短暂一生画上不圆满的句号。
周莹与沈星移之间的爱情将其女性主义的特质激发到极点:保持婚恋自主权,也冲破了女性贞操观念,她获得了与男权平视的权利,这也是现代两性平等观念的核心诉求。一开始被养父卖身到沈家当丫鬟后,沈夫人选她为少爷的通房丫头,这是其他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周莹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不愿他人左右自己的婚姻和生活。周莹始终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生活。她在丈夫死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沈星移的感情。这时,周莹面临更多阻力:寡妇的身份、神堂的誓言、吴沈两家的仇恨等等,这都是周莹与沈星移的挡路石。但无论外界如何评说,周莹总是遵从自己的心意,在这二人的关系中,她扮演了沈星移成长中的启蒙者角色。沈星移一开始是一个纨绔子弟,对周莹的“占有”是恃于少爷对丫环的理所应然,是基于男权意识对弱小女性的理所应然。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社会关系中,沈星移都是不成熟的,周莹的言行举止和经商方式都给予他极大的启发,在周莹主体意识的引导下,沈星移承担起对个人、家族、社会的责任,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
综上所述,周莹的几段感情线,无论是与吴聘的婚姻,还是与沈星移、赵白石、图尔丹等人的感情选择,与剧中吴老爷与吴夫人、吴漪与赵白石、吴聘与胡咏梅、沈星移与玲珑等其他传统的两性关系相比,她打破了从一而终的婚恋观,遵循自己的情感需求。这展现出周莹对两性平等观念和感情自由选择的坚守,不是以男性为中心,而是追求两性平等对话,相互之间共同影响、共同发展。周莹一直站在与男性平等的位置,遵从自身主体需求的选择,不受男性中心的压制,做到真正的双性和谐。
从依附到平等,从男性中心到两性和谐,是该剧赋予两性关系的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阐释,既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也向观众传达了先进的现代性别观念。对此,李银河也认为:“新女性主义的长期目标,应当从之前的男女二元对立到争取两性和谐,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充足发展,从而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2](185)
二、男权话语秩序的颠覆:“花已开”之“女主外”
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大众艺术领域,“主流商业电影的影像与叙事的基本构成原则,首先是男人看/女人被看;是建立在男人/女人、看/被看、主动/被动、主体/客体的一系列二项对立式间的叙述与影像序列”[3](122)。在传统男权文化中,女性始终处于一个“被看”的客体地位,大众艺术领域所呈现的性别文化也大都如此。而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遵循常规的叙事模式,而是选择以“女性独立意识”来组织结构,以女性为主人公,书写女性的成长历程,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模式,破除了男权社会为女性规划的囹圄,重塑女子之于家庭、社会、国家的存在意义。
周莹原本是一个江湖卖艺的为基本生存打拼的小女孩,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当地首富吴家,她想当学徒学做生意,但是吴家少爷因“没有女人做生意的先例”拒绝了她,周莹凭借其过人的经商天赋和对学习的执着感化了吴家掌门人,为她破例。又在阴错阳差之下嫁给吴家少爷,后来丈夫被害、公公蒙冤去世、家族生意遭到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境下,周莹最开始的权力来自男性的赋予——公公留下的印章让她接下掌权人的重担,但由于身份、性别因素难以得到家族的认可,因为利益的冲突被族人陷害后失去孩子、差点被沉塘害死,九死一生归来后,为自己洗脱冤屈;在家族生意日渐衰落的情况下力挽狂澜,促使家族生意起死回生,也慢慢得到了家族的认可和众人的信服。其最初被认为是僭越男权伦理的行为也得到谅解,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当家人。在经商道路上,面对竞争对手的阴谋暗害,周莹凭借其聪慧勇敢和超高的商业天赋以及为人处世的原则,信奉“诚信”二字和家国于一身的责任感作为经商法宝,一路上披荆斩棘,在商途中大展宏图,开创了股份制管理模式。此外,她还赈灾济民、兴修水利、办女子学堂、筹募军饷等,历经一系列波折与苦难,最终成长为叱咤商界的风云人物,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洗清家族冤情,实现人生的逆袭。
电视剧《当家大掌柜》中的女当家人史纨清和周莹处于相似的处境,同样的时代背景、两人同样打破社会分工,承担起一家之主之责,但史纨清只是父权社会选择的过渡人物,家族最终还是交给史家嫡孙,史纨清为史家献出了一切,为家族牺牲婚姻,牺牲健康和子女,但最后仍然被父权社会罢黜,仍处于男权社会中的“他者”,成为“祖制”的牺牲品。相比之下,周莹坚守自我,勇于挣脱传统男权话语秩序的困囿,颠覆社会为女性设定的“他者”地位,学者张岩冰认为:“这个‘他者’最终就是一种在主体内部又对主体进行颠覆的力量,女性就构成了男性的‘他者’。她被规定视为男性的一部分,是男性要证明自己的东西,又是男性想要逃避的东西,她从内部对这个牢不可破的男性的金身进行破坏,最终破坏那种根深蒂固的男女的二元对立。”[4](154)周莹的所作所为获得家族以及社会上的认可,突破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规范模式,稳固了自己的话语身份,肯定了女性的价值。
纵观全剧,在当时封建男权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中,周莹既是大家族少奶奶又是寡妇的特殊身份限制了她,想要走出家门、走入社会对她来说可谓是“步步惊心”,在封建社会中“男权制一方面夸大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规定了男性的统治与女性的从属,并建立起了一整套能使男性控制女性的社会权力体系;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层面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单一性别结构——男性主体与女性客体伪装成两性之间的必然规律。在男权制的精神控制中,女性被剥夺了大部分的主体性权力,并从内心接受了自己的客体定位,在男权制话语权力下,性别特质又被理解为男优女劣的自然禀赋。因此,无论是在家庭私领域还是社会公领域,男性的领导者和女性的从属者身份都被视为是自然合理的统治秩序”[5](38),“女子出嫁从夫”是当时环境的默认准则,但周莹没有选择做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而是施展了更为强烈的人生抱负,从女子的后院走向男子的前院——六椽厅,担任起重振吴家东院的重担。
周莹对传统社会分工的冲击与颠覆,在话语权上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反映出她不依附男性,追求独立自我的理念,也凸显了这一艺术形象的现代女性观念。从这个层面讲,该剧肯定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张扬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将现代的女性观念传达给观众。
三、男权文化环境:花开在“月未圆”时
虽然该剧让周莹这朵具有鲜明现代色彩的女性之花盛开在晚清的社会背景下,但观众仍能深切感受到人物生存环境中那种强大的封建男权势力。“月未圆”的社会环境给周莹的女性奋斗道路带来了重重障碍,人物与环境之间的激烈冲突从反面否定着男权秩序中保守落后的性别文化观。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首先是作为属于某个主人的“物”而存在的,周莹也难逃此厄运。她首先是养父用来谋取生存的工具,为了生存经常被养父卖来卖去,但她并没有自怨自弃,在常年痛苦生活的打磨下已经掌握一套足以自保的生存本领。动荡不安的民间成长环境养成周莹放荡不羁的个性,牢牢坚守自己人生的主动权,具有极强的现代女性意识。
进入吴家后,因性别差异不能当学徒,周莹据理力争,在男权意识统治的封建社会里,发出了“谁说女人不能做生意”的时代呐喊。“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性就是单一的性别群体,男性处于统治支配地位,并且经过反复实践为女性制定了贤妻良母的形象定位”[6](110),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女性被困囿在闺阁绣楼,言行举止都受到女德观的约束。波伏娃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判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7](23)也就是说,性别问题总是与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相关,是传统男权意识规定了性别差异。周莹嫁入吴家后,其不拘于礼节的行为令她的婆婆吴夫人大为不满。吴夫人是深受三纲五常教化的传统大家夫人,她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改造周莹,希望周莹遵循三从四德的妻子本分,但周莹仍不拘泥于传统礼法,特立独行、坚守自我,反倒是把吴夫人弄的哭笑不得。
在经商过程中,周莹的女性身份给她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和阻力:竞争对手用女子贞节去陷害她;当地官员以女子不能抛头露面来遏制她的发展;甚至吴家为了维护家族“脸面”,防止周莹改嫁,逼迫她在祠堂发誓……周莹克服每一道荆棘,为人处世始终秉承“诚、信”二字,与客户的合作一直保持互利共赢的状态,绝不会用次品代替正品蒙混过关,因此,她的商业版图越做越大;没有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去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与仇家言和。庚子国难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到陕西,当地官员号召富户为其提供费用,周莹平素赈济灾民不遗余力,但是不愿为太后的私人供给提供费用,虽遭当地官员陷害,最后她还是以个人勇敢机智的言行获得太后对她的认可。
烟台大学教授任现品认为:“在父权家族私有制的社会中,再加上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女性的存在是处于被剥夺、被压制的状态,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政治参与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同时在个性、情感、欲望方面又备受压制。”[8](184)放置在该剧的社会背景中,这种观念也的确存在,但正因这种强大的男权势力使周莹每一次冲破传统性别观念的行动都具有了超越当时的历史环境的意义。这也体现出该剧在性别叙事上的进步性,揭示女性在男权文化意识形态之下遭到压抑和阻挠的生命经验,也使这个人物表现出的女性自主意识更为难能可贵。
虽然该剧主打“女性独立”“女性主义”大旗,但还是存在许多争议。我们再回到《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剧情中,周莹从一开始处于弱者地位,是一个“灰姑娘”人设,成长的道路上也离不开众多男性的帮助,她的独特个人魅力获得众多男性的欣赏,但她并不依赖于这些男性,甚至发生反转——以自身的言行影响了这些男性、促进了这些男性人物的成长,这显现出现代大众文化处理性别叙事的进步性。周莹的成长之路既有社会、家族的诡谲波澜,也有情感上的缠绵悱恻,但无论是处在商业竞争还是身处情感选择中,周莹都能始终保持清醒,坚守自我。最终她不但得到了吴家家族的认可,还得到了竞争对手的认可,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认可,其灵魂的独立带来了所有人的尊重,这正是该剧创作主体所要阐释的女性独立。
总之,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对周莹这一人物的演绎虽也存在许多不足,但是,总体来看,该剧在周莹一生传奇故事的讲述中所呈现出的两性和谐追求、传统男权话语秩序的颠覆、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否定都显示出浓厚的现代色彩。相比同类题材而言,这部剧具有很明显的进步性,在电视剧史上可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也显示出社会主流意识对传统女性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全新诠释,体现了性别文化在大众艺术领域的显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