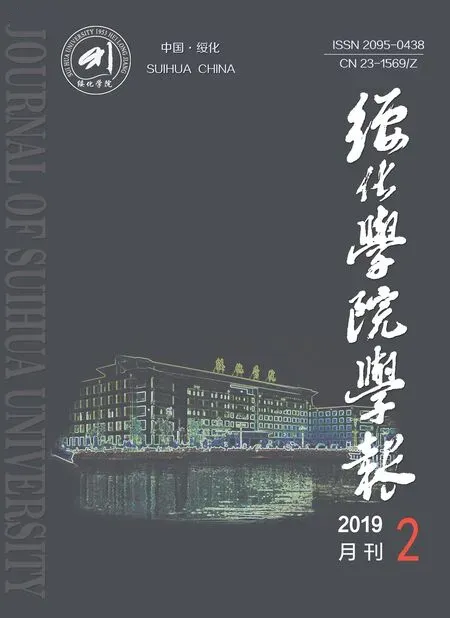无拘无束的黑色精灵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的美学精神阐释
朱文琦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1984年年底,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莫言创作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并发表在创刊不久的《中国作家》第二期上,小说发表后不久便获得文学界的热烈讨论,因此,这部小说也被视为莫言的“成名作”。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毫无顾忌的笔法塑造出一个浑身充斥着旺盛生命活力的黑色精灵——黑孩。作为莫言文学生涯的新起点,《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形象,黑孩身上更是隐含着莫言日后文学创作中的那股激越、狂放、浪漫的美学精神。1999年,莫言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演讲会上称:“黑孩子是一个精灵,他与我一起成长,并伴随着我走遍天下,他是我的保护神。”[1](P86)可以说,黑孩与莫言是一对存在于文本内外的共生形象,一方面,黑孩是莫言独特美学精神的具象化表现,另一方面,莫言又凭借黑孩形象的塑造获得了创作上的巨大成功和不断奋进的勇气,只有理解黑孩才能理解莫言的文学创作,黑孩已经成为解开莫言文学密码的重要钥匙。
一、苦闷下栽种的“红萝卜”
日本著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一书中认为文艺创作以两种力的冲突为基础,一种是创造生活的欲求的“生命之力”,另一种是服从生活的限制的“压抑之力”,二者的冲突必然导致“人生苦”,最终,“人生苦”借助文学创作得以发泄,因此,“文艺决不是俗众的玩弄物,乃是该严肃而且沉痛的人间苦的象征”。那么,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之前的莫言无疑也正处于人生的苦闷阶段。1984年,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军队到学校,环境的变化无疑对莫言的精神状态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那一届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的学生,有几位已经大名鼎鼎,最有名的如济南军区的李存葆、李荃,沈阳军区的宋学武,南京军区的钱刚,都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奖,其余的同学也都发表过很多作品”,[2](P272)相对而言,缺乏代表性作品的莫言便被置于军艺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笔者注:其他同学)当时在军队系统都很有名,瞧不起人。像我这种从农村来的,没有发表过几篇小说,被他(笔者注:同学)蔑视”,[3](P107)而对于自幼便拥有旺盛表达欲望的莫言来说,初入军艺学习时期渴望言说却遭受蔑视的处境又使得他倍感苦闷。
面对众多已经取得相当成绩的同学,莫言身上压抑着的言说欲望不断地涌现出来。一次系里组织讨论会,讨论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彼时的李存葆是当时军艺文学系35名学员中最有成就的代表,同时也是军队的先进人物代表,不仅《高山下的花环》名声在外,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屡屡获奖。因此,在讨论会上,大家的发言几乎全都是溢美之词,唯独莫言对李存葆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李存葆的小说“有点像宣传材料一样”,[4](P127)“在这个介于纪实与中篇小说的作品中,闻到了‘一种连队小报油墨的芳香’”。[5](P62)此番口出狂言的结果就是引发了同学们对他的强烈不满,莫言也随之感受到了来自同学的异常巨大的压力,“我自己把自己逼到一个悬崖上了。很多人都说你既然把人家得全国头奖的小说贬得一文不值,那你写一部作品出来让我们看看”。[5](P62)“假如我后来没有写出来的话,就成了一个笑柄”。[5](P62)
巨大的苦闷与压力使得莫言不断地对文学创作进行思考与探索,从而逐渐激发出隐藏于脑海深处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天刚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眼前出现了一片很广阔的红萝卜地,北方的大红萝卜,很鲜艳的。太阳初升,一轮红日,很大的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子,草棚子里出来一个红衣少女,很丰满穿红衣的姑娘,手里拿了柄鱼叉,叉起一个萝卜,举着,朝太阳走去。这时起床号响了,我醒了”。[6](P28)在极度的苦闷与压抑之下,来自山东高密的莫言无意识地梦到了自己的家乡,家乡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都因着梦的呼唤而汹涌地灌入莫言的脑海之中,构成莫言小说创作的丰富矿藏。醒来之后的莫言由此获得了写作的信心与勇气,“当天上午,我一边听着课,一边在笔记本上写这个梦境,一周后,写出了草稿。又用了一周誊抄清楚”。[6](P28)终于,在浓厚的苦闷与压力之下,莫言从“故乡血地”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以汪洋恣肆的笔法在自己的文学王国里种下了一颗“透明的红萝卜”。
二、莫言、黑孩与黑衣人
《透明的红萝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个骨瘦如柴、沉默寡言但又充满灵性和生命活力的黑孩。可以说,黑孩形象的塑造既是源于莫言独特的人生体验,更是来自于深层次的莫言对鲁迅所呼唤的“摩罗精神”的继承。
首先,小说中黑孩参与公社集体劳动和因偷萝卜被捉的情节全部来自莫言童年时期的亲身经历。出生于1955年的莫言,童年记忆中充斥着饥饿感,为了填饱肚子,莫言曾多次铤而走险。20世纪60年代,莫言以“半劳力”的身份到一个桥梁工地上参加集体劳动,在劳动间隙,他溜到萝卜地里偷了一个红萝卜,结果不小心被看门人捉住并受到了严厉处罚,这次惩罚在莫言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在文学创作中,童年记忆成为莫言书写的重要资源。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一文中,莫言指出:“我十三岁时曾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小工,给一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生火。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产生与我这段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小说中的黑孩儿虽然不是我,但与我的心是相通的。”[7](P39)从上述自白里可以看到,黑孩身上浇筑着莫言独特的生命体验,无论是在逆境生活中所流露出的迎合与顺从,还是在极度恶劣环境下的展现出顽强与坚韧,都是“童年莫言”的精神写照。同时,对黑孩身上发生的反常现象的描写——如黑孩对大自然产生的异于常人的独特体验——则是作家在个体生命独特感受基础上形成的追求生命意志和心灵自由的审美风格的形象展现。
其次,小说中的黑孩形象更显示出莫言对鲁迅“摩罗精神”的自觉继承。1927年,鲁迅在《莽原》上发表小说《眉间尺》(后改名为《铸剑》收入小说集《故事新编》),小说根据干宝《搜神记》中《三王墓》的传说进行改写,讲述的是黑色人宴之敖者立誓为少年眉间尺报仇,手持眉间尺的剑与人头入宫刺王,最终在金鼎的沸水中与王同归于尽的故事。对于《铸剑》一文的价值指向已经产生了多种观点,可谓是众说纷纭。1991年8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莫言的《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一文,文章认为《铸剑》是一个复仇的故事,眉间尺是复仇者,黑衣人是复仇者,鲁迅也是复仇者,眉间尺的复仇的动力是出于道德伦理的需要,而文本中的黑衣人与现实中的鲁迅是一组共同存在的形象,黑衣人与鲁迅的复仇动力都是源自对黑暗、苦难、生死无所畏惧的自由自在的“摩罗精神”,二人都是“看透了的英雄”,而这恰恰与莫言自身的个性气质与精神追求产生了强烈共鸣,因此,莫言感到“那冷如钢铁的黑衣人形象,今生大概难以忘怀”。[8](P109)这种无拘无束、超脱现实、视生死为无物的精神遂构成莫言的“生命伦理”,早年创作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正是对鲁迅《铸剑》中的黑衣人形象的变形置换。吴福辉先生也指出:“等到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一问世,扑入人们眼帘,让所有的读者最初是惊讶,然后发出惊叹的正是一个‘小黑孩’形象……‘黑衣人’的黑色外表和黑色精神也灌注到‘小黑孩’身上,沉默少语,自尊倔强,而且是反抗的、嘲讽的、超脱的。”[9](P10)
总而言之,黑孩身上显示出多层的意蕴。一方面,黑孩是莫言在自我生命体验基础上形成的追求生命意志和心灵自由的形象化表达,另一方面,黑孩又是莫言对鲁迅小说《铸剑》中代表着“摩罗精神”的黑衣人的变形置换。可以说,黑孩既传递着莫言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悟和审美追求,同时又维系着身处当代的作家莫言与中国现代作家鲁迅间的精神联系。
三、具有“邪劲儿”的黑色精灵
黑孩是解锁莫言文学创作密码的一把重要钥匙。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身上最大程度地浓缩了莫言的生命体验和鲁迅的文学精神,这种生命体验和文学精神构成莫言文学创作的巨大动力。
1907年,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摩罗诗力说》一文,文章的核心思想在于呼唤中国产生如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匈牙利的裴多菲一般的“精神界之战士”。上述作家虽然国别不同,但大致呈现出共同的创作风貌,即反抗传统、酷爱自由、对待生活保持真诚的姿态,艺术风格上崇尚刚健和悲壮。时隔近八十年,莫言在自我生命体验的基础上,以浪漫主义、先锋的姿态在文坛上崛起,可以说,莫言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明显地带有鲁迅所主张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气质。在一篇介于创作谈和散文之间的文章里,莫言写道:“创作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10](P88)其实,文章中所说的“邪劲儿”指的就是创作者要将“灵感”“灵性”“个人”看作是文学的最高原则,要敢于打破平庸,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打破一切束缚创作的教条。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具有“邪劲儿”的人物形象,首先,黑孩并非是一个哑巴,但在整部小说他中却没有说过一句话,无论是面对来自刘副主任严厉的批评还是面对来自菊子姑娘温切的关怀,黑孩都是以沉默作为回答;其次,黑孩浑身闪烁着一股不可思议的灵性,他能够听到黄麻地里响着的鸟叫一般的音乐、能够听到蚂蚱剪动翅羽的声音,能够听到头发落在地上发出的声音,甚至能够听到逃逸的雾气碰撞到黄麻叶子和茎秆而发出的声响,普通的红萝卜在他眼里变成了一个晶莹剔透的拖着如金色羊毛尾巴般根须的大个阳梨;最后,黑孩还拥有异于常人的忍受力,当羊角铁锤把右手食指的指甲砸成碎片,黑孩只是发出了一声“象哀叫又象叹息”般的音节后就不再作声,当从桥洞穿过的秋风使人感到从心里往外冷的时候,黑孩却还只穿一条大裤头子,光背赤足,但又看不出有半点瑟缩。总之,无论是对世界的感知还是本身的行为,黑孩都显示出与常人的明显不同。
黑孩身上涌现出的“邪劲儿”其实是来自于作家本人对生命意志的追寻和对鲁迅所呼唤的“摩罗精神”的继承。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生命意志论”,持悲观主义的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的支配只能导致永恒的虚无与痛苦,解脱的唯一路径就是禁欲主义,而尼采则在叔本华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生命意志论”,积极肯定生命的伟大与创造的美妙,力求打通个体向自然的回归之路,实现生命和灵魂的升华。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尼采借扎拉图斯特拉之口说:“我给你们教授超人。人类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11](P34)在“超人”的对立面,尼采还提出“末人”的概念,“末人”指的是丧失生命意志,无希望、无创造、信奉奴隶道德的病态的人,而“超人”则是敢于面对生之痛苦的、具有强力生命意志的人生欢乐的享受者。通过“超人”与“末人”的对比,尼采既否定了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又否定了叔本华“生命意志论”中的悲观因素,从而提出肯定生命、赞扬生命的“生命意志论”。
莫言自身的个性气质与尼采的哲学思想和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颇有“邪劲儿”黑孩就是在生命意志和“摩罗精神”影响下的产物。一方面,黑孩的“沉默”与“隐忍”源自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是一种超越性的姿态,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如小石匠、小铁匠和菊子姑娘三人间的紧张关系或是菊子姑娘的亲切关怀,黑孩持一种超脱于外的冷漠态度,既不给予什么,也不索求什么,始终沉浸在自我的生命世界之中,追求内在的生命和谐;另一方面,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悉反过来又表现为黑孩对自然的高度亲近,既然现实社会中充满着争夺和压抑,那么大自然则成为生命意志的最后栖息地,干瘪焦枯的心灵从广袤的自然之中汲取养分从而重获丰盈的活力,投身于自然的黑孩由此获得了异于常人的感受力。
结合莫言创作《透明的红萝卜》前的苦闷心境,可以说莫言塑造的黑孩就是他本人。面对已经成名的同学们,莫言备感苦闷与压抑,那个在桥梁工地上无比委屈的黑孩其实就是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学习的莫言的变形加工,而汲汲寻找出路的莫言终于在自我个性气质的基础上,从生命意志和鲁迅的“摩罗精神”中获得了丰沛的创作动力。因此,以“奇诡的浪漫主义”手法对人的生命价值进行探索,重视人的本真感觉,强调生命感受在生命中的重要作用,构成莫言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
结语
《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之后,莫言的文学创作进入到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阶段,自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间发表各类小说数10余部,而黑孩身上所散发出的“生命意志”与“摩罗精神”则是莫言文学创作的主要审美追求和创作动力。莫言认为:“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12](P29)可以想象,《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光着屁股、露着脊梁,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上蹿下跳、攀高爬低,将浑身上下散发着的旺盛的生命活力和自由叛逆的“摩罗精神”传递给了存在于莫言文学世界里的其他人物。
《红高粱家族》通过对“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日常生活以及抗日行为的叙述,以充满原始野性的美学风格展现出一种敢爱敢恨、自由不屈、永不停息的生命力量并将这种力量抽象为中华文明虽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能够绵延不绝的根本精神。《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农民高羊虽然已经失去《红高粱》中“我爷爷”余占鳌的那种强悍暴力的精神,采取一种忍气吞声的生存方式,但是在面对现实社会的黑暗与压迫时,体内所蕴藏的生命力量遂喷涌而出并从暴力的反抗行为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丰乳肥臀》中塑造出一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母亲,通过对母亲在残酷的处境下生儿育女、顽强求生等行为的描写,讴歌了母亲的伟大与无私,而其背后着意展现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
自发表《透明的红萝卜》以来,莫言的文字始终表现着他对生命的关注和忧思,对自由不羁的心灵的追求,对生命理想状态的向往。莫言是以“黑孩”为出发点、为根基进行文学书写的,黑孩身上所承载的生命意志和“摩罗精神”弥漫在莫言所营造的文学世界当中,只有理解黑孩,才能理解莫言文学创作中的那股激越、狂放、浪漫的风格,才能真正进入莫言的文学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