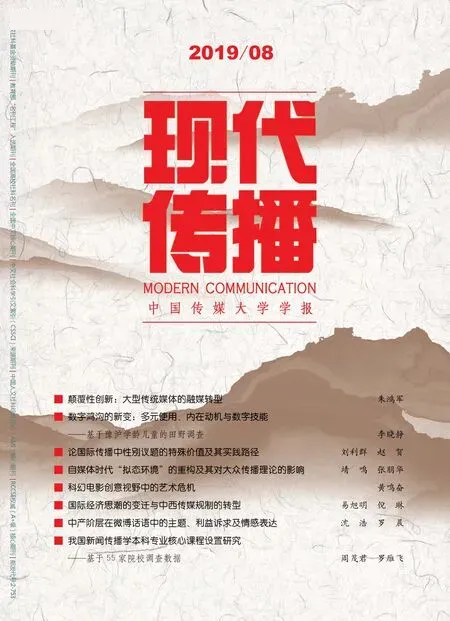营造“共同体”意识:论主流媒体话语调适的转向*
——基于电视文化类节目的思考
■ 吴 雁 袁 瀚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主流媒体的话语输出和传播效果存在着困境,制约着主流文化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融入。一方面,主流媒体固有的单向式话语传播力不佳,无法有效地融入民间舆论场。中心式话语过分强调、肯定、认同官方立场,采取灌输的传播模式让公众容易对政治传播产生疏离感、厌恶感,不利于执政党话语体系下沉。①同时,多元社会思潮的传播,消解我国官方的议程设置。自媒体的崛起、不同群体的意见表达导致正确与错误的思潮并存,“众声喧哗”的传播环境对主流媒体话语权造成一定的冲击。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的话语模式存在着娱乐化凸显、消费主义日益泛滥的趋势。随着我国主流媒体市场化进程加快,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媒介话语向市场和利润“献媚”,呈现出教育意义让位于商业属性的缺失。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今天享受不再是权利或乐趣的约束机制,而是公民义务的约束机制……消费者把自己看作是处于娱乐之前的人,看做是一种享受和满足的事业。”②主流媒体为了迎合社会大众的感官满足,导致选秀、竞技、明星生活等各类娱乐真人秀节目充斥于大众的视野,而社教类节目因模式固化、趣味不足等原因逐步离场。过度娱乐化的媒介话语稀释了主流价值观的政治传播效果。
主流媒体的话语困境推动其在新的社会环境和媒介语境下进行话语调适,重新获得文化领导权。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话语即权力,话语与权力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话语”是权力的外衣,只有依赖于“话语”才能实现真正的权力。权力并不仅仅局限于统治阶层或者执政党所掌握的强制力、征服力,而更多地指影响力、辐射力、说服力。③换言之,公众对于权力的认同和信任有赖于话语体系的致效。执政党、政府通过政治传播,使信息在共同体范围内扩散,沟通官方与民间的立场,使权力与执掌权力的代表具备合法性。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主流媒体需要进行话语转型,突破固有的话语体系的局限,在坚守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采取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模式进行舆论引导和价值引领,以实现缓和社会矛盾和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媒介功效。
二、电视文化节目中的话语转型
央视及地方卫视作为执政党价值传播的载体,承担主流文化输出和传播的功能。文化类节目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从发轫伊始就印上了全面而深刻的文化教育意识。④目前国内学者对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定义、功能众说纷纭,尚未形成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电视文化节目“以传承文明、宣传知识、教育大众为己任”⑤。一方面,电视文化节目具有社会教育意义,需要借助优秀文化进行价值引领、道德规范,从而影响社会公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另一方面,由于电视文化节目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因此在节目制作、编排中需要采取“大众化”路线,利用符合大众审美心理和媒介消费习惯的节目语态,推动主流文化在不同群体的融入与致效。
电视文化节目具备教育性和大众性,既承载了媒介的价值导向功能,又覆盖了广泛的受众人群,是执政党和主流媒体话语传播的有效载体。近年来主流电视媒体积极在文化类节目上发力,提升主流价值观和主流社会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鲜活性。《朗读者》《见字如面》《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信·中国》《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文化类节目蔚然成风、百花齐放,在社会上取得了不俗的传播效果。以《朗读者》为例,该系列节目是央视推出的中外文学作品朗读节目,一开播就成为新媒体传播的“现象级”节目,掀起社会的“朗读热”。⑥《见字如面》是全国首档书信朗读节目,挑选中外名人的信件,运用独特的电视话语展现书信中的人物内涵,彰显时代价值;《信·中国》则是对《见字如面》的继承与发展,将执政党建党以来收录的党员书信作为文本来源,挑选出其中的一部分加以呈现,旨在传递执政党的文化与价值。⑦
纵观近年热播的《朗读者》《见字如面》《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信·中国》等电视文化类节目,可以发现这些节目呈现一个大趋势:基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电视媒介话语中营造民族共同体。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小说、报纸等印刷传播媒介在不同社会人群间唤起“共同体”意识。安德森指出:“报纸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对于作为小说的报纸几乎分秒不差地同时消费(‘想象’)……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⑧电视文化类节目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挖掘并呈现优秀中华文化内涵,并创新叙事模式、传播语态,使观众参与到观看的过程中,激发文化认同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从而提高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具体而言,主流媒体话语调适的电视文化传播路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民族文化,展现民族特色。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提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⑨。一个民族的历史运行轨迹和社会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特殊的文化模式。反之,文化是不同民族和社会形态分野的标志,民族文化、民族符号折射出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
近年热播的电视文化节目,内容大部分来自中华民族文化。依据笔者对《朗读者》(第二季)中的演说文本进行的统计,其中超过六成的文本来源于中国古今的文学作品;《见字如面》(第二季)的演说文本超过八成来自中国大陆的作者所撰写的书信;《信·中国》的演讲书信来源则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信件。诵读类节目选取优质的中华媒介文本,呈现华夏民族不同时期的时代内涵,并通过演说者与主持人之间的话语互动进行情感抒发与价值传递,实现文化育人的传播效果。《国家宝藏》作为一档文博类节目,通过展现故宫博物院等九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及其背后的前世今生进行民族文化科普,让社会公众了解文物所承载的文明和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精神内核,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中国诗词大会》取材源自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的精粹,融合了竞技对抗的叙事模式,实现了中华优秀古典文化的全民普及。电视文化类节目展现优秀民族文化,利用全民族共同的文化瑰宝有机地联结“分散的”“孤立的”“异质的”社会大众,维系民族共同体。正如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所言:“它们在该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感情。”⑩
第二,凸显民族身份,彰显民族认同。国家是包含了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民族血缘的共同体,因此国家认同感的构建有赖于在政治、文化和民族三个层面进行。其中,政治认同指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国家方针政策;文化认同指认同国家的历史底蕴、灿烂文明、大好河山;民族认同指认同各族人民共属一体的国民心理。观之近年热播的文化类节目,在传播社会主流文化的过程中较少“直抒胸臆”地宣传我国社会道路、发展方向、政策方针的先进性和正确性,更多的是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意识,即每个社会成员同属于民族共同体,华夏儿女是大家的共同身份,在“统一”身份中提升民族认同感。美国学者M莱恩·布鲁纳(M.Lane Bruner)认为:“国家认同不仅仅是一种或者一套随后将促进一系列行动并且证明这些行动合理性的叙述,它也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修辞过程。相应地,在此所采用的修辞方法不是为了发现一个国家的认同,而是用以分析那些碰撞的时刻,也就是相互竞争的阐述在有关想象中作为国家的一名成员意味着什么的持续的话语协商过程中产生碰撞的时刻”。借助莱恩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电视文化节目除了对国家与执政党的认同与歌颂,更多地趋向让社会公众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属于中华民族,明确民族身份,并认识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以树立起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典型的体现在《信·中国》这档节目上。该节目选取的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信件,但是仔细阅读这些信件可以发现,节目主题不会局限在歌颂执政党,而是借助革命与建设的时代背景,展示共产党员对自己华夏儿女身份的深切认同,倡导一种民族身份归属的意识。比如开国元勋聂荣臻斥责日本侵略者的信件中,是这样写的:“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这实际上就突破了单一的执政党视角的局限,转而呈现了对民族命运的重视与人类和平的呼吁。
第三,倡导民族责任,实现国民教育。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提出,在发达工业社会,“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谬误的意识”。当前中国电视节目市场呈现出过度娱乐化、消费主义泛滥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娱乐真人秀节目的滥觞。真人秀节目通过生动的叙事和视听语言向观众提供观看的“快感”,丰富了大众的文化消费。但与此同时,真人秀节目也因娱乐性、虚假性、低俗性等消极因素冲击了电视媒介话语的良性教育功能,传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导致社会公众公共意识淡漠,沉浸于感官的满足而忽视了对社会、民族应承担的责任,并且观众并未察觉到自身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失。在社会转型期,多种社会思潮芜杂交错,主流媒体更应当发挥正面的价值导向以实现公众的良性教育。当下热播的电视文化节目倡导公民应该承担起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正是对消费主义思潮泛滥的规范和矫正。源自共和主义传统的积极公民观倡导公民参与到公共领域中,为共同体做出贡献、承担责任,因为这是精神升华、人格提升和自我实现的途径。
《朗读者》(第二季)开篇就邀请清华大学薛其坤等学者朗读了《礼记·大学》,表达了中国古代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达情怀。《见字如面》(第二季)中呈现了抗战时期“爱国县长”给日本侵略者田岛寿嗣的回信,表达自己坚决不向侵略者屈服的决心以及保全一方水土的勇气。《信·中国》里也呈现了一批共产党员在抗战时期坚持革命的故事,承担起对民族和对亲人的责任。
三、从“劝服论”到“共同体”:对主流媒体话语调适的展望
“劝服论”是古典修辞的中心观点,在此观点下,话语修辞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的策略性使用”,运用修辞的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言辞使一个团体获得特定的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因而带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劝服论”长期贯穿于主流媒体的话语模式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媒介体制秉持苏联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列宁新闻观所倡导的“喉舌论”,各级媒体长期作为执政党“宣传工具”而存在,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发挥了舆论动员和精神鼓舞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日益开放,社会文明日渐繁荣,传媒生态日趋丰富,单一的“劝服论”与“喉舌论”不适应新的社会文明生态,媒介体制与媒介管理理念亟待革新。基于上述电视文化节目话语转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未来主流媒体话语调适的一个发展趋向:营造“想象的共同体”,统合官方与民间二者的立场,在话语层面上传递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考察了在欧裔移民者移居美洲大陆、建立政治治理体系的过程中语言文字和印刷传播媒介发挥的作用。其中,以报纸为代表的印刷传播媒介淡化了官方的政治性,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呈现,让大众在媒介消费的过程中产生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他提出:“想要了解为何行政单元——不只是在美洲,在世界其他地方亦然——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会被逐渐想象成祖国,我们必须探究行政组织创造意义的方式……加拉加斯(Caracas)的报纸以相当自然的,甚至是不带政治性的方式,在一群特定组合的读者同胞中创造了一个这些船舶、新娘、主教和价格都共同归属的想象共同体。当然,可以预期的是政治因素迟早会进入到这个想象之中。”
借助安德森的观点,可以发现,近年来主流媒体在电视文化节目的话语调适的过程中发掘优秀民族文化,展现民族特色,彰显民族内涵,实际上是在突破“劝服观”带来的传播局限,克服民众对主流媒体话语模式产生的僵化、权威、生硬的消极刻板印象,营造一个“大中华”的传播共同体,有利于提升社会大众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据此,笔者立足“共同体”的传播理念和话语模式,针对主流媒体的话语调适和转型提出如下展望:
1.集体记忆:民族共同体历史遗产的再现
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是实现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记忆是一种重塑机制,借此可以构建作为整体的自我,“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同时,集体记忆也是根据我们的现实需求或对现在的关注而被形塑的。
主流媒体积极构建集体记忆,是对当前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涌动的矫正。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否认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主张民族是虚构的概念,长此以往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在媒介话语层面,民族虚无主义表现为照搬国外娱乐节目的制作模式,而忽视了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再现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创新集体记忆的叙事模式、传播风格,在营造民族记忆景观中唤起归属感。近年来主流的党媒、央媒在营造集体记忆上积极实践,除了央视等电视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也把握住国家公祭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5·12”汶川大地震纪念日等关键时间节点,利用短视频、H5、VR等新媒体技术再现民族集体记忆,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2.身份确认:缓解“他者化”的社会情绪
由于封建时代我国长期存在高度集中的皇权政治体制,这一历史因素导致中国人的思维易于形成官方与民间二元对立的藩篱。而到了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矛盾显露,社会成员面临着较多的“不确定性”,更容易产生“他者”的思维。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由于流动性、不确定性突出,“认同成了难题”。鲍曼提出,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后现代人深受感情的匮乏、边界的模糊、逻辑的无常与权威的脆弱等诸多因素的困扰。结合当前的社会实际,我国目前的发展尚未到达高度稳定的社会形态,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社会矛盾的暴露使公众容易产生“认同失焦”的情绪。
对此,主流媒体作为社会心绪的“调节器”和“矫正器”,在“认同焦虑”的社会背景下应该强化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确认,告知、确认和强化全体成员的归属,即同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将“分散的大众”嵌入共同体中,以缓解“他者化”的社会情绪。例如,在201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数字产品《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主流媒体在建军节这一节点推出的新媒体产品将落脚点放在“我”的角度,将人民解放军的象征符号与受众的阅读体验相勾连,旨在努力沟通官方和公众的两个舆论场,积极破除双方的隔阂。
3.情感动员:激发社会凝聚与集体行动的共同信仰
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建设与政党形象塑造上较长时间采用说理、灌输的权威式话语,较易给公众留下负面的刻板印象。民族情感动员正是应对这一弊端的有效工具。涂尔干说过:“就本质而言,社会凝聚来源于共同的信仰和感情。”情感性因素是集体行动生成的内在机制,兼具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其中,情感性因素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现为在集体行动中,欢乐、友爱、和谐的正向情感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所以,主流媒体在维护民族团结中应当克服一味说理、阐明利益的局限性,更应该重视情感在舆论动员中的作用。重视情感的作用近年来在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制作中得到了践行。在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在内容传播时大量采用情感语汇和符号,并吸收民众话语营造亲民、活泼的氛围。同时也有意识地淡化了官方的色彩,满足民众的情感诉求。
注释:
① 张宁:《政治传播中的“非传播”现象》,《新闻记者》,2016年第8期。
②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③ 赵欢春:《意识形态话语权及其当代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④ 颜梅、何天平:《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嬗变轨迹及文化反思》,《现代传播》,2017年第7期。
⑤ 刘晓欣:《电视文化节目研究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年第12期。
⑥ 过彤、张庆龙:《〈朗读者〉: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的大众化探索》,《传媒评论》,2017年第3期。
⑦ 张步中、李晨:《〈信·中国〉:书信题材文化类节目的叙事创新——与〈见字如面〉的对比分析》,《中国电视》,2018年第8期。
⑨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⑩ 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