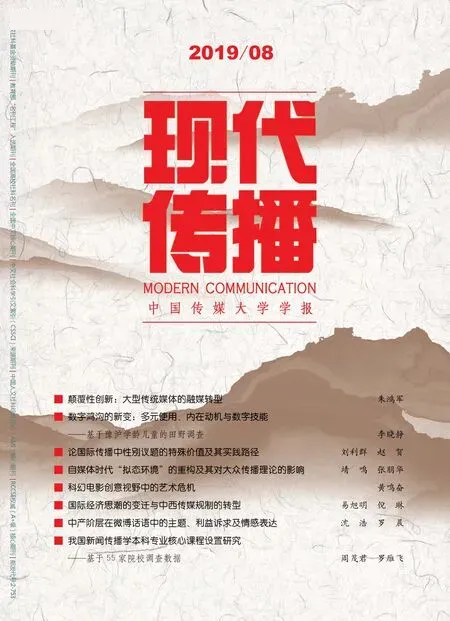融合传播时代网络舆论引导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践行*
——基于共情理论的思考
■ 郭 蓓
201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舆论的力量绝不能小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受融合传播的影响,舆论成为事实、意见、情感、行动的混合物,其中,情感中的共情心理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网络环境所发生的重大变迁以及公众心理的特征,进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健全融合传播时代舆情引导体系,提高舆情引导能力。
一、融合传播时代网络舆论的特点
传统意义上的舆论是公众意见的集合,是多数人意志的统一表达。舆论被认为是一种公意,是共同体的最高意志。①公共领域中舆论的形成是公众进行理性思考所得出的结果,其作用是促进社会的进步,促进民主的形成。②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是融合传播的产物,舆论成为事实、意见、情感、行动的混合物。个人越来越有机会将自己的观点或意见通过个人传播上升到群体传播甚至大众传播的空间。
融合传播是媒介融合的体现。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浦尔教授提出。在技术的推动下,“一种单一的媒介,无论它是电话线、电缆还是无线电波,都将承载过去需要多种媒介才能承载的服务。同时,任何一种过去只能通过单一媒介提供的服务,例如广播、报纸、电话,现在都可以由多种媒介来提供。由此,过去在媒介与它所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的一对一的关系正在被侵蚀。”③一般认为,媒介融合包括媒介技术融合、媒介业务融合和媒介所有权融合。尽管大众对于媒介融合有诸多讨论,但媒介融合的社会意义一直被忽略。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微博、微信打通了互联网和电信网,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它其实联通了个人传播网络和公共传播网络,打通了个人传播和群体传播的界限,这是以往从传统媒体到即时通讯(QQ)都没有完成的。因此,融合传播是个人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个人情绪化观点很容易裹挟事实,从而通过个人传播上升到群体传播进而进入大众传播的层面,使舆论迅速扩大。不仅如此,群体情绪容易相互感染,这将影响群体行为的认知和选择。本能的情绪特别容易感染,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毫无作用。④公众容易因为突发偶然事件的刺激以及自身的不公平感而聚集起来而形成情绪共同体。他们本身与事件没有关系,但为事情原由所吸引,为现场共同的兴奋、愤怒、仇恨等集体情绪所感染。⑤
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除了公共舆论中表现出来的集体情绪外,情感在公共舆论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情绪与情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情绪指个体或群体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反映,是一种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反映。⑥情感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中所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所持有的态度,是人类所特有的情感。情感也用来描述具有稳定而深刻社会含义的内心体验,具有社会性、历史性。⑦与心理学中将情感作为私人的心理感觉不同,情感社会学将它看作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从而专注于社会的共同情感和其形成的深层动力机制。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指出情感对于社会事件以及公共舆论的影响。杨国斌揭示了情感在网络事件中的作用,认为相对于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而言,网络事件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媒介的情感动员过程。⑧Scheufele认为,公共舆论的内容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探讨: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和情感维度(Affective Dimension)。⑨张志安与晏齐宏指出在探讨新媒体与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时,情感分析是一项重要的因素。⑩进而在之后的研究中,分析了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从个人情绪、社会情感及集体意志三个维度进行了探讨。袁光锋以公共舆论中的“同情”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同情是如何嵌入到媒体报道和公共舆论中的。已有的研究尽管丰富,但忽视了作为形成情感共同体的共情在公共舆论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共情不仅仅是个体的私人体验和心理过程,它也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建构起来的产物。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又重构了人们的情感表达形态与情感关系。在网络空间中,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边界是交叠、模糊和动态的。社交媒体不仅实现了技术上的融合,更使得个人传播与群体传播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公众的情感几乎无障碍地进入到公共空间,网民更容易基于共同的情感而聚集。这种情感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有效的情感共振,使得个体事件成为公共事件,引发公共舆论的产生并影响其走向。
二、作为公共情感的共情及其对公共舆论的影响
共情(empathy)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最近几年逐渐受到许多其他领域的关注,比如共情在服务设计(service design)中的体现,共情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共情简单来讲就是同理心,我们传统中所说的“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以及儒家思想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共情的表现。具体而言,“共情”首先指一种我们直接在情感上去感受他人的心理状态的能力,是一种微妙的、普遍存在的、促使人理解他人的情绪和心理。
很长时间以来共情与同情在英语当中是一样的,都用sympathy。直到1950年左右,人们才逐渐把共情作为一个单独的词语使用。最先提出“共情”一词的是德国心理学家李普斯。德语中有个词,意思是“感受进去”,使人联想到一个动词involved(卷入)。后来英美心理学家将德语“感受进去”这个词借用过来,变成了empathy,即共情或者移情。需要指出的是,共情(empathy)在许多时候与怜悯(pity)、同情(sympathy)以及悲情(compassion)交替使用。尽管相似,但这些词语之间又有一些微妙的区别。Sympathy和compassion非常相似,都表示同情,但sympathy没有compassion表达的感情强烈,后者更强调对人类苦难所表达的深深的同情。如果说当代词语表达中sympathy和compassion有任何不同的话,那么这个不同就在于后者无论对遭遇苦难的人还是同情苦难的人而言,感情更强烈。比较而言,怜悯(pity)则指对于弱势群体所遭受的苦难表达的自上而下的略带优越感的同情,它与共情以及同情的差异比较大。
这些词中共情与同情(sympathy)的差别最小。共情是一种“想象的对他人经历不作任何评价的重构活动”,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自然而然的感知、理解与共享,是能够充分体会、感知其他人心理的一种自觉反应,是一种in-feeling状态。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能与他人做到感同身受的心理,而同情是作为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他人的心理。当我们与他人产生共情时,我们就触及最根本的人性以及与他人共同享有的品质(common qualities)。共情更多地体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比如东亚文化中。
共情让人类成为整体,将个体的痛苦转化为群体的痛苦,人与人之间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共情能力让“我”变成了“我们”。尽管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共情心的触发其实也是有条件的。那些与我们关系越亲密的人,越是受到我们认同的人,就越容易引发我们的共情心。当看到他人遭受痛苦时,我们会潸然泪下。在灾难和异族面前,我们相濡以沫,可以形成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的能力。共情不仅在个体社会化及人际交往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基石。进化生物学家们通常通过生物性的角度评判社会问题而避免考虑到参与者的心理状态。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行为往往基于自私的属性。但不能否认的是,人类天性中同时有另一些特质,将人与人紧紧聚在一起,在基于功利计算的理性之外,调整彼此的步伐,关怀弱者、帮助他人。
共情对当下的公共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社会公共舆论的形成有明显的身份叙事倾向。公共议题的讨论很容易从事件本身转向当事人的社会身份与处境,从而使普通的新闻事件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舆论是情绪、事实、观点的混合物,体现出我国社会舆论生态的复杂特点。以下将从几个方面具体阐述共情在公共舆论中的具体体现:
首先,共情是对人类自然身份的唤醒。无论是轰动社会的“山东辱母事件”,还是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为母复仇杀人事件”,事件之所以从对普通刑事案件的讨论进入到公共舆论讨论的范畴,原因在于公众将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叙事融入到集体叙事的框架中来。两起案件都将人类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母亲”身份唤醒从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共情让人与人之间多时间内产生共鸣,从而聚结成一个整体,通过内部的沟通交流和外界的刺激进一步加强共情,将个体所受的痛苦转化为群体的痛苦。共情让“我”变成了“我们”。那些与我们关系越亲密的人,越和我们有共性的人,就越容易引发我们的共情心。
其次,共情除了能够唤醒公众的自然身份,也能唤醒人们的社会身份。社会认同是个体对社会身份的一种主观性确认,一方面,是个体对自我特性的认可;另一方面,个体通过归类将自己或他人归于某一群体,并将群体的特征赋予自己或他人,内化其价值观并且接受其行为规范。公众通过社会认知、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将自身或与自身身份相似的他人进行一定的群体分类,进而获得社会认可。决定社会身份认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阶层,这在近些年来许多舆情事件中都有反映。身份是对个体所扮演的角色认定,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的阶层结构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形成。近年来,“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等词的出现,反映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的不断加剧,阶层之间垂直流动性减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及更上阶层的流动的难度增加,因此出现了“仇富”“仇官”现象,社会矛盾突出。这种对社会身份的影响从最初的“我爸是李刚”,到“‘钱多后台硬’女司机社会关系”的事件,都反映了公共舆论中公众对社会身份的唤醒。
再次,相比于以上两种共情对身份唤醒的事件,共情还能使得公众对不确定风险产生共同的担忧以及对社会处境产生共鸣。现代社会,尽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人们对收入、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担忧,使得社会与人类的生活模式不可阻挡地将以风险为核心被重新组织与安排,人们普遍感到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这种全民性的状态体现在人们对周遭所处的生活、生命以及财产的不安全感。
最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共情还表现在公众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这种关注偏颇的背后是社会舆论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及对城管阶层的痛恨带进了案件评价。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使得人们对强权厌恶、对弱势同情。换句话说,这是公众是对自身处境的同情和对不公现象的对抗的反映。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践行的基本路径
与传统媒体时代自上而下式的垂直传播不同,融合传播时代的最大特征是去中心化和赋权化。个人经验、群体情感都成为认识和判断事实的重要依据。在对事件进行讨论时,各种话语相互交织,事实陈述和真相还原不再是新闻媒体的专业行为,而成为一种开放的社会动员机制。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新闻与舆论的界限日益模糊,新闻可以引发舆论,舆论也可以成为新闻。另外,新闻与舆论在时间上相伴而生,不分先后。”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党在开展舆论宣传工作中的重要指导理论,我们应该主动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获取启示,从而提升党对融合传播时代舆论的引导能力。
首先,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了解民众所想。互动性是Web 2.0时代最大的特征,提升舆论引导能力,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这一特征,及时了解民众所想、民众所需,充分了解民众的情感,这样才能在舆论引导过程中有的放矢,把握公众的情感走向,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单一事件能否成为舆情事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情感因素,这种情感因素是一些偶然或者个别事件发酵成公共事件从而引发公共舆论的温床或者动力机制。人们对于周遭发生的不幸或危及生存的事件有一种天然的共情和代入感,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新媒体平台的推波助澜下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 “4·19 讲话”中指出:“老百姓在哪儿,民意就在哪儿。我国有 7 亿网民,传统方式和网络渠道共同构成了现在反映民意、了解民意、沟通民意的新途径。”网络平台是卓有成效的意见获取渠道。因此,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移动终端等渠道,及时广泛地收集民意,因势利导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基础下,舆论引导不能脱离民众的情感,尤其是一些事件中可能出现的共情心理。要充分认识到民众之所想、所忧,进而精准引导舆论。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在网络舆论引导中重视人民性原则。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做出的新的贡献。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就是要在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中“实现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 “2·19 讲话”中,针对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48字工作方针中,突出强调了要“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要重视共情在融合传播中的作用,重视民众的认同感、参与感在舆情事件中的作用。在信息传播格局发生巨变的今天,舆论由单一变为多元,因此,传播必须要把握规律,将负面影响转向正面的引导。换句话说,传播必须要符合网络传播的特征及必须遵守认识论的规律。此外,传播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满足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真正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为民服务的情怀,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新闻报道的主体和服务对象。在充分肯定民众的共情心理在舆情事件中的作用基础上,寻找有效的切入点进行议程设置,开展有针对性的舆论引导。
再次,充分利用和发挥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将舆论热点与融合传播结合起来。这既是为了适应媒介技术发展所引起的传播格局变化,也是为了适应舆论的传播,能更好地将公众的共情心理纳入到媒介的主流议程中来,更好地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2014年 8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到中国新闻奖在 2018 年首次设立了 “媒体融合”奖项,融合传播已是大势所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充分重视新媒体、新技术在传播中的影响。早前由人民日报客户端策划出品并主导开发,腾讯天天P图提供图像处理支持的H5产品“军装照”,是公众共情心理和融合传播共振的一个成功案例。在传播传播时代,需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和共情心理有效结合,在数据新闻、算法新闻、大数据等新媒体技术先行的同时,要实现媒介议程和公众情感的有效共鸣。
最后,政府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要端正立场和态度,不仅要以理服人,还要以情动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提供的事实有限,而且为追求流量等目标,会更注重内容中的对立性、对抗性和戏剧性,从而对事实造成更大的影响。在信息如此多元化的今天,敷衍式地应对已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反而会给网民创造无限的想象空间,导致谣言的传播从而影响舆论引导。在情绪、观点、事实混合的复杂舆情事件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民众的情感走向,端正引导态度,站稳立场。由于公众的情感代入,对公共事务的判断容易情感先行,这会影响到理性的判断甚至被别有用心之人所操纵,因此,在充分重视公众情感的前提下,还需要警惕私力救济给事件本身的非正常性搭上正当的外衣。面对新媒体环境中出现的舆情危机,要有全局性、系统性的整体认识,进一步发挥舆论引导工作中凝聚力量“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功能。
注释:
①②⑩ 张志安、晏齐宏:《网络舆论的概念认知、分析层次与引导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
③ Henry Jenkins.ConvergenceCulture.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p.10.
④⑥ 张志安、晏齐宏:《个体情绪 社会情感 集体意志——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及其因素研究》,《新闻记者》,2016年第11期。
⑤ 彭广林:《从“事件”到“身份”:社会冲突事件报道的叙事倾向探析》,《编辑之友》,2015年第9期。
⑦ 张浩:《论情绪和情感及其在认识中的功能——主体认识结构中的非理性要素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6 期。
⑧ 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9年总第9期。
⑨ 杨击、叶柳:《情感结构: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遗产》,《新闻大学》,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