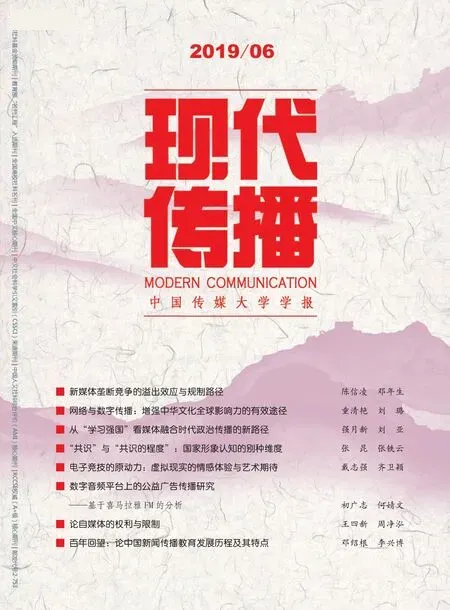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电影的影院本体论
■ 潘 桦 李 亚
在互联网时代,以美国Netflix(奈飞)为首的流媒体公司实行新的“day and date”(全球同步上映)策略,即跳过传统的院线,将自制影片在流媒体平台上针对订阅用户进行首发。2017年4月,Netflix的影片《玉子》(Okja,2017)和《迈耶罗维茨的故事》(The Meyerowitz Stories,2017)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在入围名单公布后的第二天,法国院线联盟即向组委会提出抗议,原因是两部影片没有达到在法国院线公映的要求。电影节刚一开幕,评委会主席阿尔莫多瓦便声称:“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金棕榈颁给一部在大银幕上看不到的电影。”70周岁的戛纳电影节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难题。它在各方间斡旋,虽然最后保留了两部影片的竞赛资格,却制定了新规:今后所有的竞赛片都必须在法国的院线进行公映。Netflix并不买账。由此,2018年,戛纳电影节拒绝了它的5部影片,其中包括《罗马》(Roma,2018)和奥逊·威尔斯的遗作《风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2018)。2019年3月份,《罗马》在第91届奥斯卡上斩获了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等3项大奖,再次引发了学院导演分部主管斯皮尔伯格的强烈不满。他早就对Netflix参与奥斯卡奖角逐的资质提出过质疑,认为它出品的电影最多算是电视片,应该去竞争的是艾美奖。
在阿尔莫多瓦和斯皮尔伯格看来,一部不经影院上映的电影便不可以称之为电影。这种立场反应了他们的电影本体观,即对“什么是电影”“电影与其他艺术的区别”等根本问题的回答。在传统观念中,我们认为电影是一种影院艺术品,即在影院中放映或者以影院放映为最终目的的影像产品。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本体属性却遭遇了以Netflix为代表的流媒体公司的发行和放映模式的冲击。戛纳与奈飞之争,正处于电影的又一次本体危机之中,这其中既有商业利益的考量,也有相关人士对电影边界消融的忧思。
一、电影的影院本体
哲学上的本体(ontology)是对事物的存在基础或本原的思考,对其进行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根基,是“第一哲学”:“有一门学术,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者’,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①“是者之所以为是者”的思考就使亚里士多德与其他哲学家区分开来:“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是什么’,而在于‘何以是’,即,追问是者之所以然。‘本体’应该是对‘何以是’即原因的回答,而不是对‘是什么’的回答。”②
在思考电影的本体时,我们同样需要如亚里士多德那般追问:不是去追问“电影是什么”,而是追问“什么使电影成为电影”。这里的“什么”,也就是电影的本体规定。如果我们认为电影的本体是其影院性,那么便可以换一种说法: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因为它是一种影院艺术品。影院性就成为了电影的基本规定,成为了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的首要条件。亚里士多德将本体研究作为“第一哲学”,认为“第一”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事物之称为第一(原始)者有数义——一于定义为始,二于认识之次序为始,三于时间为始。——本体于此三者皆为始。”③以此考察电影的影院本体,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影院性之所以成为电影的本体属性,是因为三点:影院性是关于电影的最早定义;影院放映是我们对电影的最早认识;影院也是电影最早的放映媒介。
一般而言,电影的本体研究有两种思路:其一是针对电影的元素、形式和形态的研究,在文艺研究中一般称之为“内部理论”;另外一种是关于电影的功能和价值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文艺研究的“外部理论”。同样的,电影的影院本体也包括内部和外部两种表现,其内部表现是指影院决定了电影的艺术形态,外部表现则牵涉到影院的观影环境、心理机制和观影的文化意义以及院线在整个电影产业中的位置。
首先,电影院决定了电影的艺术形态。影院本体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诞生的初期,电影不过是现代科技创造的新奇玩意,“在节日市场上和X光、无线电报、有胡子的美女、飞艇模型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供人们前来欣赏”④。嘈杂的市场或流动放映棚自然不是欣赏严肃艺术的地方。要成为艺术,电影就必须改进放映方式和放映环境。之后,电影转向以戏剧的形式讲述故事和电影院的普及方式几乎同步进行着。在这个过程中,后者的技术要素转化为了前者的艺术标准,推动着这门新兴艺术走向成熟。
电影院的基建尤其是观众厅的设计规定了银幕的大小和性能,从而决定了电影的视觉表现。一般而言,放映35毫米影片的标准银幕宽度为1/4、1/5或者1/6有效厅长,而宽银幕影片的银幕宽度则为0.4—0.45倍有效厅长。无论何种比例,镜头所拍摄的原始物体都会在银幕上放大数倍,从而对电影的视觉特性提出了极为严苛的技术和艺术要求。同理,电影院高品质的声音系统也对电影的听觉特性划定了同样严格的标准。在电影发展的早期阶段,电影院对电影艺术的视听形态的成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推动其发展出了无与伦比的视听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将这门曾被轻视的街头杂耍提升为了一种杰出的艺术。2019年2月份,法国艺术院线联盟发出了致阿方索·卡隆和科恩兄弟的公开信,以艺术的名义指责他们放弃了影院:“你们放弃了在大银幕上以技术层面作为最佳的展现方式为你们的电影赋予价值,用电影院中的声音系统传达作品的诸多细节与微妙之处。”⑤这种观点无可指摘,因为电影艺术的最高魅力也只有在电影院中才能真正实现。
其次,电影院奠定了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的基本产业模式。在漫长的电影发展史中,电影院曾是电影的唯一放映渠道,是整个产业回收资金,保障再生产的基础。在好莱坞黄金时代,94%的资金都被投放到了带有固定资产性质的电影院上,能够有效地经营的电影放映业成为了行业经济的稳定器。和很多人认为的不同,大制片厂所建立的垂直垄断体系中最关键的环节并不是其制片活动,而是庞大的发行和影院体系。当时,五家大公司拥有的大城市的首轮豪华影院,每年会以首轮放映的高票价卷走当年票房总收入的70%。
随着科技进步,信息传输和存储成本大大降低,电影的放映窗口也在不断增加。从电视到录像带再到目前的互联网,影院早已不再是电影唯一的放映渠道,其收入在电影整体收入中的份额也在不断下降,目前只占到了很小一部分。但是,影院依然是电影的发行网络中最重要的一环。由于影院的票房决定着影片在其后窗口甚至衍生品销售中的表现,因此被称为电影发行的“推进器”或“发动机”。“影片在影院的上映是决定性的:既关系到直接得失,还关系到影片的声誉及其未来增值的可能性。所以,影院日益被用作影片的发射平台和商品增值的展览窗口,而增值主要还是在其他地方产生。”⑥通俗点讲,影院票房高,DVD才能卖得好。
第三,影院观影满足了电影的“公共观看属性”,从而成为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公共观看属性”即指电影一次放映供多人同时欣赏的属性。公共观看属性与电影相伴而生,卢米埃尔兄弟进行的世界上第一次电影放映便是一次公开放映。1895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一群观众聚集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集体观看了十部电影短片。这次公开放映使卢米埃尔兄弟成为了电影的发明人,在与爱迪生的竞争中获得了胜利,关键原因便在于他们解决了集体观影的问题,而爱迪生始终固执地在一次仅能供一位观众欣赏的“电影视镜”上放映影片。电影院是满足电影的公共观看属性的最佳装置,甚至可以说,电影院天然地为电影而生。自诞生以来,电影院便成为了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电影院是公共场所。电影院在20世纪成为人们自由穿越的空间之一,就像相聚的场所一样,电影院成为卓越的大众空间。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既神秘又平常,既独特又具有共性的世界。”⑦对观众而言,观影活动中与同伴之间的互动和对银幕上人物形象的认同同样重要。我们的观影习惯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也可以在影院的观影行为中找到。通过对虚构叙事的共同消费,我们与其他观众分享了相似的社会经验,塑造或者重塑了自己的社会认同,并最终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部分。
第四,影院观影实现了电影艺术的潜意识魅力。电影院的观影环境非常关键:封闭、单一,座椅舒适,声音从四周传来,除去银幕上的光影,一切都隐藏在黑暗之中。对影院观影环境的这种描绘在将电影与梦境进行对比时十分常见,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精神分析理论进入电影研究,电影与梦在机制上的相似更加得到确认。理查德·麦特白直言电影院是一个提供“公共梦幻”的场所:“为梦工厂出售梦幻的巨大而黑暗的影院,允许它的观众在一个公共空间里拥有高度的私密性。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心灵,有时候是我们的双手,能够自由舒展,我们或许能进入那些遭到禁止的空间,探讨自我、他者以及差异问题。我们知道——或许我们想起——那个巨大的黑暗空间是爱欲之所:是青春期性启蒙的日常文化场所,但它也是提供公共梦幻的地方,为我们的观念和行为提供集体表达形式,而这些观念和行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受到压抑的。”⑧让-路易·博德里甚至将影院空间提升到了比影片本身更为重要的地位,他断言:“电影院中产生幻觉的力量不在影片的内容,而在制作电影和展播电影的机器和体制。”⑨他还将这种体验与文化原型中的某些内容进行了类比,认为影院的环境与精神分析中的子宫和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类似。子宫和柏拉图的洞穴分别象征着人类在生命和历史早期阶段的幻觉体验。让-路易·博德里认为,长期以来人类都在寻找着能够产生同样梦幻经验的物质环境,而电影的诞生终于为这个耽搁长久的梦幻提供了一个等值体。经历了长时间的等待后,人类终于在影院里的黑暗中得到了心灵的满足。
二、危机:互联网时代的影院本体
互联网科技发展之下,像奈飞这样的流媒体企业不再满足于仅作为一个放映窗口参与电影事业,而开始将重金投放到原创内容的制作中,依托自身的视频平台进行在线发行和播放。这个新的产业模式完全取消了影院在电影产业中的作用,也悄然改变着人们的观影方式,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电影本体的忧思:一部从未在影院进行过放映,也根本不以影院放映作为制作和发行目标的电影可以称之为电影吗?流媒体网站的发展会逐渐取代传统影院吗?在线观影会取代影院观影吗?电影的形态会最终被改变吗?
1.网络小屏中的电影艺术
电影的小屏播放开始于电视时代。在播放时,为了适应电视机的屏幕尺寸,电影画面的边缘会被部分剪裁。宽银幕电影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从原始的1.85∶1或者2.35∶1的宽画幅变为了电视的4∶3比例,很多画面不得不被切除,甚至有些双人镜头会被分割成两个单人镜头。好莱坞导演彼得·博格丹诺维奇曾说过:“直到在大银幕上重看《西北偏北》,我才确实了解银幕尺寸带来的巨大差别……也许这就是年轻人很难欣赏老电影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只在电视上看过这些电影,而这会减少电影的奥秘与神秘震撼性。”⑩
不过,电视小屏播放的电影即便品质有所减损,却依然是院线电影,电视不过是电影众多放映方式中的一个,而网络小屏却完全不同。网络电影不以影院作为发行和放映目标,也不必严守影院的技术和艺术标准。如果像斯皮尔伯格所言,奈飞将自制影片作为和电视电影相似的作品去角逐艾美奖,或许不会引发如此的争议和担忧。但《罗马》《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The Ballad of Buster Scruggs,2018)这样的网络电影,却同传统的院线电影一起角逐奖项并大获成功。在威尼斯电影节将金狮奖颁给《罗马》之后,奥斯卡奖又将最佳外语片奖颁给了它。可以说在艺术上,这两个主流电影奖项完全认可了这部网络电影的艺术身份。斯皮尔伯格对《罗马》的不满也并非因其艺术水准,而只是担忧电影艺术所坚守的影院本体就这样被轻易地攻陷,从而造成本体,边界的消融和艺术形态的混乱。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如果任何叙事性的视听产品都可以成为“电影”,不管它们是否进入过影院,那么“电影”这个概念的外延便会无限地扩张。影院本体之所以是电影的“第一哲学”,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与电影相伴而生,无论从“定义”“认识次序”还是“时间”上,它都决定了电影的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体是事物独立的、客观的存在,因此并不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电视普及后,出现了专门为电视台制作的一类“电影”,一个新的概念适时出现来适应这种新的视听形态,即“电视电影”,而电影依然坚守着影院本体。在互联网时代,小屏幕的类型激增,电影的形态也更为多样化。戛纳和奥斯卡曾向奈飞的示好,正反映了影院本体所遭受的又一次威胁。和电视电影一样,不以影院放映为目标,网络电影就不必严格遵守影院的技术和艺术的规定,从而在本体形态上与电影区分了开来。很少有人把电视电影与院线电影相提并论,我们都明白前者是一种电视产品,但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泾渭分明的本体界限却被网络电影打破了。网络屏幕和电视屏幕都是可以播放电影的一种小屏,为网络小屏而制作的网络电影与为电视而制作电视电影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产品。但和电视电影不同,网络电影却被传统电影节、影展、媒体以及部分观众接纳为了传统电影,这不仅推翻了电影的最初定义,颠覆了我们对电影的传统认知,也否定了电影从新生的“杂耍”成长为严肃艺术那个历史阶段里影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个媒介环境急速变革的时代,保持电影艺术的纯度,就必须坚守电影的影院本体。阿尔莫多瓦、斯皮尔伯格等影人的坚持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保守”,戛纳颁布新规限制奈飞也引发了部分非议,但在我们看来,这至少是一种艺术上的正当。
2.网络发行引发的院线危机
在一般的发行模式中,网络发行只是电影的配套市场中的一个窗口。为了保障每个窗口的收益最大化,电影的窗口期会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操作:一般以电影院为首,以网络播放为末尾。网络窗口的发展不但开拓了电影的销售市场,提高了整体利润,还为众多独立制片商的作品提供了放映渠道,使那些没有办法进入电影院的小成本影片能够在视频网站上与观众见面。但近年来,很多流媒体公司开始涉足内容制作。这些新兴的公司资金雄厚,有大量的观众基础和独立的播放平台,依靠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将原本处于窗口期末尾的视频网站提升至了发行顺序的第一位,从而完全将院线放弃了。“一个市场的成长,往往或多或少意味着另外一个市场的损失。总体而言,配套市场的现金流量之间存在强烈的互相替代性。”也就是说,在网站上看电影的观众增加,必然会导致进入影院的观众减少。电影史上,类似的现象在电视和录像带普及之后都曾出现过。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电视为主导的新兴娱乐产业的发展,也曾将电影院逼至绝境。
因此,不仅在艺术上,网络放映也在产业上开始威胁电影的影院本体。电影院会不会消失的话题在近年来被频繁提及。在国内,爱奇艺的创始人龚宇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实体影院终将消失,代表了很多人的立场。电影院面临的这次危机和历史上有所不同。以往的商业模式中,电视、录像带等发行窗口都依赖院线的带动作用,即便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但院线发行始终是电影的发行网络中最重要的一环。但现在,互联网平台却可以完全取代电影院的作用。很多传统事物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消失了,电影院可能会是下一个。从最直观的影院票房上看,尽管近两年北美年度票房总量还略有增加,但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总体票房趋势和人均观影次数都在不断下降,而网络观影正是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目前,更多的发行商倾向于缩短影院的窗口周期,以尽快将产品投放到网络上。院线和网络的同步发行也越来越受欢迎,很多以院线为目标的电影甚至放弃了影院,将赌注完全押在了视频平台上。2018年,美国的在线点播业务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影院,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拉大,使华尔街的金融业对影院的未来愈加担忧。
3.在线观影与电影的公共属性
观影方式的多样化为观众提供了选择的自由,这也是奈飞的主张。在2019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之后,处于舆论旋涡中心的奈飞曾在官方推特账号上进行回应:“我们热爱电影。不过下面是一些我们也同样热爱的事情:为那些去不起影院,或住在没有影院的小镇的人们提供渠道,让每个人,在任何地方,在同一时间享受电影,以及给电影制作者更多的方式来分享艺术。这些事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并不否认网络观影的便捷和低成本,但同样不可被否认的是,奈飞所主张的商业模式一定意义上却是对自由观影的剥夺。奈飞坚信,流媒体网站吸引观众的主要手段就是独享内容。因此,观众在影院中看不到《罗马》,在亚马逊、hulu上也看不到。想要欣赏这部影片,就必须注册成为奈飞的付费会员。法国艺术院线联盟因此指责道:“至于Netflix加入后,不是你去适应观众,而是恰恰相反:观众们必须要适应你做出的决定——将你最新的作品独家、长期委托给一个特定的平台。这样,观众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订阅Netflix在小屏幕上观看你的电影,要么就根本不看。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起码对你的粉丝来说是这样的。这种义务还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存在的,是没有明说的陷阱。这是对艺术品的私有化。”
奈飞的商业模式几乎使观众重新回到了爱迪生的电影视镜时代。当时,爱迪生将电影视为会生金蛋的母鸡,因此拒绝在银幕上进行公开放映。和爱迪生一样,奈飞也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拒绝公开放映影片——也许唯一的不同是,爱迪生时代的观众排着队,弯着腰,透过一个一次仅可供一人观看的小窗口欣赏他的影片,而奈飞的观众则是在各种私人小屏幕——手机、个人电脑上进行观看。如果爱迪生的发明不能算是电影,那么奈飞的算是吗?
奈飞认为影院观影过程繁琐、成本过高,将观影改造为一个任意的、日常的,甚至隐秘的个人活动确实给观众带来了便捷,但却丧失了影院观影的视觉、心理和文化的体验。看电影不再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集体活动。博德里早就对电视观众放弃影院表达过不解:“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渴望在漆黑的电影院里让心灵得到满足之后,当电视来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随意选择的视觉之时(应该注意,这种经验通常是在灯火通明、充满各种声音和活动的房间里实现的),如此众多的工业化社会的成员却随意放弃,不再去实现看电影那种完美的心灵需求,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一事实呢?”博德里应该会对现在的情况更加绝望。在电视时代,观众至少还可以在影院和电视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他们连这种基本的选择权也被剥夺了。
三、影院本体的未来
历史是一个循环。当下影院正在经历的一切,也都曾在历史上发生过,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电视普及后,电影观众大幅下降,好莱坞惶恐了一段时间便发现了其中的商机,或者出售播放版权给电视台,或者干脆拍摄专供电视播放的电视电影。电视从而成为了电影产业链的一个新成员。当前,面对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挑战,电影产业的各方,包括电影节、院线、制作和发行企业等,都在尝试各种应对措施,努力使危机成为新的机遇,也捍卫着电影的影院本体。
1.电影的影院规定性
面对影院本体的危机,传统电影节最直接的应对方式是通过增加或者修改规则,强硬地捍卫电影必须经过影院放映这一传统。戛纳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筛选参赛影片的资质。2017年,由于《玉子》和《迈耶罗维茨的故事》两部主竞赛影片引发的风波,戛纳电影节颁布了新规,规定所有的参赛影片都必须在影院中进行公映。奥斯卡奖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参奖影片必须在院线中上映过一个周。不过奈飞钻了这条规则的空子。为了参加2019年3月的奥斯卡奖评选,《罗马》曾于去年12月份在美国几家影院中象征性地上映过一周时间,之后便进入了奈飞的流媒体平台,甚至连这一周的票房收入都没有公布。
在媒体和观众眼中,是否在影院中上映过以及上映的时长并不影响一部作品成为“电影”。有一些电影因各种原因没有机会进入影院,却并不妨碍它们获得电影的身份。尽管奥逊·威尔斯尘封40年的遗作《风的另一边》的放映平台是流媒体网站,尽管戛纳拒绝了它的参赛,但在媒体和观众的话语中,它和《罗马》一样都是毫无置疑的电影。在很多影迷杂志的年度盘点中,这两部影片也都名列2018年的十佳。长期以来,观众已经习惯了通过各种小屏欣赏电影。对他们来说,一部电影是否经过院线上映并不重要。当然,但这并非是说观众对电影的影院本体没有任何要求,《罗马》之所以被接受为电影并在奥斯卡上斩获大奖,根本原因还是它具备电影的影院规定性,能够满足观众对电影艺术品质的要求。
影院性能保障电影艺术的品质。影院帮助电影成为艺术,也在捍卫电影的艺术身份,能够承受大银幕的考验是对一部作品的艺术品质的基本认可,无论是电视电影还是网络电影,都以能够进入院线作为一项成就。在美国,制作和发行公司都乐于将最优质的电视电影送入影院进行放映。在近年的中国,网络电影经历了火山爆发式的增长后又迅速进入到了一个回落期,总量从2016年的2463部下降至2018年的1030部,原因之一便是其饱受诟病的品质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网络电影的精品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很多精耕品质的网络电影也开始试水院线发行,实行院网同步,这其中既有回收的考虑,也又一次印证了影院与电影艺术的本体关系。在这门艺术的王国里,影院是最崇高的殿堂。任何声称自己为“电影”的视听产品,都需要在这里进行加冕。
可以确定的是,电影技术还在不断进步,电影艺术也会继续朝向更高层次演进,也唯有在电影院中,我们才可以充分享有这门艺术进步的成果。回顾电影史,即便电影的放映平台在不断增加,电影院在产业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但它始终代表了电影艺术的最高成就。电影在艺术上的任何进步,声音、色彩的出现,宽银幕、3D技术、环绕声、4K、120帧等,都在影院中以技术的名义得到响应。早在上世纪50年代好莱坞用“重磅炸弹”(blockbuster)对抗电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无论小屏如何便捷和低成本,也永远无法取代影院的大银幕所带给观众的震撼。在个人化小屏设备中,观众遭遇了多重损失——影像尺寸、画面质量、声音质量,对观影体验有更高要求的观众真的能忍受这种损失吗?无论小屏如何变大,私人设备的质量如何提高,小屏也永远无法传达电影艺术所能到达的极致。我们完全相信,电影院将和电影艺术同生永存。
2.永恒的院线发行
从商业角度看,电影院的危机也许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严重。尽管网络发行降低了电影信息传输、存储和放映的成本,但仅靠单位成本的降低能否从长远地增加电影产业的整体收入依然存疑。在奈飞的电影版图突飞猛涨的这些年,北美电影的票房总额不降反升,关键原因便在于一些“热门大片”(hit)——比如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的持续吸引力。对很多观众而言,这是一类“不看不可”(must-see)的电影,并且只能在影院中观看。这类电影早在默片时期便已出现,在此后电影院的数次危机中都被用来力挽狂澜。它们的存在显示了电影在大众性上所能到达的高度,也是电影院不会被取代的证明。
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网络放映也是院线放映的有益补充。在线观影的增加,事实上也在培养电影的爱好者,增加了电影的观众基础。“配套市场的发展事实上还拓宽了观影人口,吸引了许多从来不上电影院的人在看电影。此外,数据显示,无论在家看电影的成本有多低,会上电影院的人依然喜欢上电影院。”中国放映业在上世纪90年代跌落至低谷,观众热衷于电视观影和录像带,无数影院卷入了关门风潮。那个时候,电影院的消失不仅仅是一个忧虑,而已经成为了赤裸裸的现实。但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的改革和多厅影院的兴建又将观众拉回了影院。通过观看影碟成长起来的那批观众,现在已经成为了电影院的常客。历史将证明,网络观影的这批观众,也将成为未来影院的潜在顾客。
电影院将会消失的论调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尤其是新的技术和媒介出现的时候——在电视,录像带出现的时候,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影院收入长期停滞的时候,自然还有当下。但回顾电影院的发展历史,从最初的镍币影院到豪华的电影宫殿,再到现在嵌入商业地产的多厅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顽强而不断变革,适应新的媒介环境,与电影艺术同生共进的事物。不必过度焦虑,电影院衰落的趋势尚未真正显现,在和法国院线联盟的对抗中,奈飞已经输掉了。而激进如奈飞,也并未完全放弃影院。将影片在院线和网络中进行双线发行,显然比单一的发行更利于获益。在可见的未来,影院依然是能在短时间内回收制作成本的主要手段,依然会是大部分电影的首选。
3.影院观影会被取代吗
作为电影院的直接竞争对手,家庭影院一直以接近影院标准作为发展目标:更大的尺寸、更好的视听效果。影院中最为先进的放映技术,4K、3D、IMAX也被引入到了家庭影院中。“在家庭数字影院中,放映质量是关键,需要研制专用的放映终端设备,它既能够保证影片的放映质量,让消费者感受到影院级别的观影感受……”不过,家庭影院在技术上完全匹配影院只能是一种奢望。高品质的家庭影院不仅需要昂贵的设备,还对房间面积、高度、混响时间、背景噪声、空气声隔声量和房间比例等提出了严格要求,也注定只有很少一部分家庭才能拥有这种奢侈的享受。
从文化原型的视角看,影院观影也同样不可取代。柏拉图在洞穴隐喻中描述了这样一幅意象:一群生活在洞穴中的囚徒身后燃烧着熊熊火焰。火焰前有人来回走动,人形和各种器物被投射到了墙壁上。囚徒们不能回头,只能看着眼前的影子,从而将它们当作了唯一的真实。洞穴与电影院的构造何其相似:观众心甘情愿地走进影院,注视着从身后投向银幕的幻影,实践着柏拉图的思想实验,置身于欺骗之中,暂时逃离现实。
影院观影的文化原型的最初描述或许比柏拉图的洞穴隐喻还要更早,甚至可以追溯至人类生命的早期。可以想象一下在原始社会的夜晚,饭饱之后,临睡之前,我们的祖先们聚集在篝火四周,听着见多识广的猎手们讲述自己的冒险。四周一片安静,唯有篝火的光亮照在他们的脸上。在今后数万年,人类一直在追寻能够实现同样体验的装置,直到电影院的出现。我们在影院的幻影中向祖先致敬。
电影院也是一种生命的返祖装置。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的进化有两个方向:向前发展理性、认知和爱;向后返回黑暗、土地、祖先、血脉,以及子宫。艺术将返祖的冲动形象化了:“思想的全能观念在现代文明里所仅仅剩下的就只有艺术了。只有在艺术的范畴里,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做出或画出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在这个严苛的世界中,焦虑不安的人类总有重返母亲的怀抱,甚至重返子宫的本能冲动。电影院满足了这种欲求:封闭、安静、黑暗,舒适的体姿,充足的供给,无忧无虑,全知全能。电影院的传统也在苦心经营这种环境:不允许吃带有响声、发出气味的食物;不允许交头接耳;不允许接听电话。所有胎儿的大忌,也同时是影院中的大忌。
在目前的文化中,电影院依然是最接近于生命起源体验的装置,人类并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切。那些津津乐道于网络小屏的观众,那些欢欣地期盼影院灭亡的观众,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灵魂中与生俱来的秘密。潜意识中的返祖冲动在文化中演变成了各种仪式:“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当人们感觉他们团结了起来,他们就会集合在一起,并逐渐意识到了他们的道德统一体,这种团结部分是因为血缘纽带,但更主要是因为他们结成了利益和传统的共同体。”无论互联网如何发展,但人类之间的血缘纽带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将我们带入影院,与他人——自己熟悉的人、陌生的人共享同一体验。这个仪式过程被影院观影的强制性规定所确认——固定放映时间、放映地点、放映时长,还有至关重要的,这个过程是连续的,不会像小屏观影那样可能随时中断。和宗教仪式相似,电影的信徒也从四周聚集而来,同赴圣殿,宛如巫术,宛如梦境,甚至如弗洛伊德所言的“强迫性神经症”。
注释:
①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125-126页。
②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
④ [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徐昭、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⑤ [法]法国艺术院线联盟:《法国艺术院线联盟致阿方索·卡隆和科恩兄弟的公开信》,深焦,shttp://www.sohu.com/a/297000172_758090,发表时间:2019年2月23日,访问时间:2019年4月4日。
⑥⑦ [法]洛朗·克勒通:《电影经济学》,刘云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63、1页。
⑧ [美]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吴菁、何建平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⑩ [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