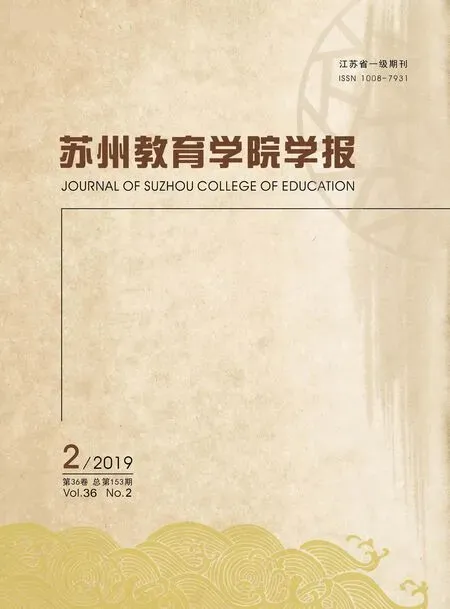寻找绝望中的希望
——《童眸》中的死亡书写
石 英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部,江苏 苏州 215131)
“生活如此绝望,每个人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黄蓓佳在《童眸》的后记中引用奈保尔的话来概括这本书。借助朵儿的童眸,我们看到了仁字巷的白毛、二丫头、细妹、马小五在荒凉又贫瘠的时代,如何把日子活出了动静。绝望的极致是死亡,《童眸》是黄蓓佳借助回忆加工而成的作品,作为对童年经验书写的现实主义小说,《童眸》并没有回避“死亡”这一话题。“现实主义小说中,作为线性的发展,死亡是一个高潮,可以承载很多东西。”[1]33那么,作为现实主义的儿童小说,其中关于死亡的书写可以承载的,会有哪些与一般现实主义小说相同或不同的意义呢?探索以《童眸》为代表的黄蓓佳儿童小说文本,可以让我们思考在儿童文学中死亡书写可以和可能承载的意义。
儿童文学并不回避书写死亡。在《不老泉》①纳塔莉·巴比特著、吕明译:《不老泉》,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②凯瑟琳·佩特森著、陈静抒译:《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新蕾出版社2014年版。《我亲爱的甜橙树》③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著、蔚玲译:《我亲爱的甜橙树》,天天出版社2010年版。等作品中都写到了死亡,这些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对死亡本身的形而上的思考,有对死亡带来的伤痛的疗愈,有追寻在死亡事件中成长的意义。黄蓓佳的很多儿童小说都写到死亡事件。在早期的《小船,小船》中,刘老师的死亡给成长中的芦芦带来了哀伤。在之后的小说中,关于至亲死亡的角色有:《亲亲我的妈妈》中的爸爸、《你是我的宝贝》中的奶奶、《鬼眼男孩》中的爸爸;关于写到同伴死亡的角色有:《我飞了》中的杜小亚、《鬼眼男孩》中的孟小伟、《草镯子》中的秀秀。这些小说中虽有“杜小亚变为天使”“余宝有预知危险的鬼眼”这样有幻想色彩的设置,但幻想只是点缀,并没有推动小说的发展,其创作依然以现实主义色彩为主。在这些事件中,有时,死亡只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转折,如《亲亲我的妈妈》和《你是我的宝贝》,小主人公都是因为至亲的去世,生命轨迹发生改变,从而被抛入到了一段新的生活中,死亡在这里具有引出下一个场景的功能,但小说对死亡本身以及死亡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影响并没有过多书写。有时,死亡作为成长中的一种伤痛出现,如《鬼眼男孩》中父亲的死亡,以及其他小说中同伴的死亡,这些事件打破了生活原有的平静,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哀伤,让他们了解了生命的无常。从这种书写方式中可以看出,死亡并没有像《不老泉》或《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那样成为小说探讨的主题,它只是作为一个人生不可回避的话题出现在小说中。《童眸》延续了这种书写方式,同时又有所改变。
在《童眸》中,作为绝望的死亡更多地不是以事件的方式出现,而是作为故事发生的一个语境。《童眸》一开场并没有着力介绍仁字巷的物理环境,而是把物理环境放到了第二节。第一节开场描写的是:兴高采烈地生活着的人们,在傍晚巷弄里最为热闹的时候,他们倒掉热腾腾的洗澡水,他们摆出餐桌趁着天还亮吃晚餐,他们逗弄孩子哈哈大笑,而就在这个时候,白毛一家出现了,他们像是很久以前遭了水灾出门逃难的人,蓬头垢面,风尘仆仆,筋疲力尽。白毛一家在巷子最为热闹的时候出现,十分具有戏剧化,他们的安静和疲惫发出了比巷弄的热闹更为强烈的声音,因为安静和疲惫里有死亡的味道。巷弄里的孩子们“个个活得粗粝,活得饥渴,活得丢三落四顾头不顾脚,可是他们的生命无比健旺,旭阳高照”[2]8,唯有生了病的白毛不是,白毛生下来就是个白毛怪,眼睛半闭半眯缝着睁不开。一面是旭阳高照的生存高歌,一面是掩门哭泣的死亡之音,两相交织,生存就有了份挣扎的味道。不先写物理环境,是因为作者在写另一种更重要“环境”——在绝望中生存的生死场,这才是故事发生的真正的“环境”。书写绝望中生存的生死场,在作者之前的儿童小说中已初见端倪,《鬼眼男孩》中“鬼眼”的设置,让余宝处在了对死亡的观察之中:被水淹的天使街、雨中倒塌的颓墙、即将关闭的学校、需要肾透析的邻居、贫病的亲戚,这让兴高采烈的天使街居民多多少少也有些绝望的味道;《我要做好孩子》中金铃妈妈时时处在焦虑之中,带着孩子到脑科医院检查、让孩子减肥,如同左冲右突的困兽,升学考试成为了孩子和家庭的生死之劫。不管是在追忆型还是在反应当下的作品中,都展示了人特别是儿童的生存的艰难。不过,相较于《我要做好孩子》《鬼眼男孩》这类描写当下儿童生活的作品,追忆型的作品——《童眸》中的儿童形象更加丰富有层次感。金铃、余宝都是相对扁平的人物形象,而白毛、二丫、细妹则处于更极端的环境下,现实生活中的冲突能激发他们表现出人性中原本就有的善恶美丑。白毛在同伴的排斥和死亡的阴影之下寻找着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二丫头诅咒大丫头,带着大丫头跳水,最后自己却在保护大丫头时死亡;细妹在父亲死后,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在无嗣的闻家,过继的闻庆来要么在一个新的家庭和新的学校以新的身份新生,要么只能回到乡下过原来贫困的生活。他们都生活在绝望中并与之抗争。“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他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该有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猥琐退缩,他们身上也有。”[2]283二丫头自私、刻薄、桀骜不驯,但在大丫头受到婆家虐待时,二丫头卖掉自己喜欢的衣服,放弃了改善家境的机会,甚至不要命地想要保护和解救大丫头。二丫头不仅被“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更被“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3]卡尔维诺认为,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云朵一样的轻;另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4]《童眸》的绝望的死亡书写,直面了生活的艰难,呈现了人性的复杂。
一方面,死亡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增加了现实的沉重感,张扬了生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儿童文学的范畴内,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必须有儿童性的一面,在儿童小说中,它还有另一重意义,即对于成长的意义。“现实主义少年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即试图去促进目标读者的‘社会化’”。[5]“社会化”是指:儿童不仅需要从家庭走向更大、更多样化的社群,还要在经历外在和内在的考验之后,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在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这就是儿童的成长,儿童的成长是一种新生,而新生与死亡相关。在原始社会和现在的一些原始部落,成人仪式就包含了象征性的死亡,考验是“成人礼”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文化内容,只有通过“成人礼”考验的人才能被所在民族、部落或氏族接纳为正式成员。在“成人礼”的“死亡—再生”过程中,死亡是手段,再生是目的,再生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新生。儿童穿越过危险黑暗的死亡之路,进入新的世界,作为成人而诞生。这一原型在神话中也可以看到:英雄从日常世界勇敢地进入到超自然的神奇世界,获得了神奇的力量,并带其回到人间。[6]离开日常世界进入迷宫、森林、地府,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死亡,经历死亡然后重生。要经历成长,穿越象征性的死亡,儿童需要成长的内在驱力,因而儿童小说不仅要介入社会历史,还需深入儿童内心,寻找到儿童成长的内在驱力。
《童眸》中的孩子们需要面对各自不同的“死亡”。白毛有些“独”,他的“独”一开始是因为被同伴群体排斥拒绝,他识相的主动避开众人,走路都贴着墙角跟。身体上的缺陷让白毛处在卑微之中,卑微到甚至朵儿都不知道他的名字。然而,白毛了解自己的病情后,在死亡的威胁之下,突然于绝望中生出了力量,他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面对世界,仿佛要拿回世界亏欠自己的东西。如何面对同伴的排斥,如何面对死亡,是白毛的成长课题。二丫头试图承担超越其年龄的责任,但她还没有掌握成人世界的规则,她不了解大丫头出嫁可能受的苦,她不了解仅靠还回彩礼是无法换回大丫头的,哪怕她是带着居委会主任一起去解救姐姐大丫头。二丫头的挣扎是孩子气的,是与成人社会规则相悖的,她拖着大丫头一起跳水,试图摆脱大丫头;她“偷”走了大丫头,躲在野外,试图解救大丫头。这注定了她的反抗在成人社会的无效,缺少成人力量的牵引,找不到内心可以引导成长的驱力,二丫头没有在成人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她退回到了更年幼的时代,她“有点儿丢魂了,好像”[2]125,她幻想“绿大仙”可以保护她。
无论是白毛还是二丫头,死亡都真实地存在于他们周围,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周围成人的引导,也看不到他们内心的光,他们无法穿越死亡,完成成长。细妹、马小五、闻庆来看起来有更强韧的生命力,他们对施诸身上的绝望一一反击,但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和为了成长而进行的努力是有所区别的。在《米格尔街》①奈保尔著、张琪译:《米格尔街》,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的绝望荒诞的环境中,有流浪诗人布莱克·沃兹沃斯询问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在《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②安东尼·多尔著、高环宇译:《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中,法国少女玛丽洛尔的大脑虽然被禁锢在一片黑暗中,但内心的世界却充满光明,涌动着色彩和变化;《城南旧事》③林海音:《城南旧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里的英子,向往着看海去,思考着哪个是疯子哪个是贼……这些探寻、向往、追问是内心成长的驱力,是看待生活的一种方式,让生活经验变成某种有意义的东西,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联结。
作为拥有“童眸”的见证者,朵儿见证了白毛和二丫头的挣扎,但死亡并没有激起朵儿内心的震荡。《童眸》的四个故事独自成篇,串连了四个故事的朵儿并没有将白毛和二丫头带到其他故事里,他们孤独的生孤独的死,其他人继续自己的生存挣扎。《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中,杰西面对一系列的成长课题:与贫穷的家境、校园霸凌的抗争,对绘画的喜爱,对音乐老师的暗恋等。在莱斯莉的帮助下,杰西开始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生活,探寻自己的位置。在莱斯莉过世后,杰西有过迷失,但他带着莱斯莉给予的力量,穿越了黑暗之路,完成了自我探寻,并将力量带给周围的人。而朵儿,似乎没有自身需要成长的课题,也无需从周围汲取成长的力量。与《城南旧事》的英子的追问不同,朵儿似乎只是同情白毛,只是被二丫头的刻薄、精明和古怪吸引,只是接受,而缺乏好奇、探寻、向往。因而二丫头、白毛会让她产生震惊、同情,却没有激活她自己内心成长的驱力。透过童眸,我们只看到童年的经验,却没有发现童年生命内在的力量,朵儿、白毛、二丫头被经验世界挟裹而行,没有主体性,死亡变成了一场伤逝,一场无法完成的成长课题。
李利安在《欢欣岁月》里评价马克·吐温时说:“回顾密西西比河的少年时代的马克·吐温的作品,他所反映的并不是一个时代,而是普遍的,永恒的,不变的少年心。它虽然紧密地结合在密西西比河,不过却是世界的一部分。”[7]虽然不同时代的儿童经验千差万别,但其差异性中一定具有趋同性,普遍的、永恒的少年心,儿童心灵深处的奥秘,能获得超越时空的生命力等,这些都是穿越绝望的力量。小说的使命之一是探索人存在的可能性,“(文字)它可以有着自身的力量,这个力量不是依附于历史的意义,而是文字本身进入到精神层面所产生出来的力”[1]156。
在黄蓓佳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将笔触伸向儿童外在经验世界的力度,但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她对儿童内心世界的忽略。对于现实主义儿童小说而言,只有从绝望中看到希望,才能发现儿童穿越死亡并完成重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