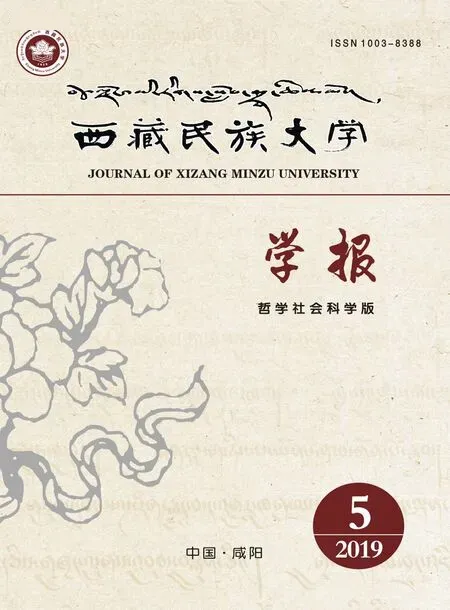“何以为家”的伦理迷思
——藏族作家王小忠小说创作心路历程蠡测
魏春春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陈忠实以为“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做的准确而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个‘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1](P177)在陈忠实看来,“自己的句子”是作家个性的彰显和作品风格的生成,亦是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理应是所有作家毕其文学生涯而追求的文学荣誉。“寻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自己”不间断的发现,而“句子”则是作家深度认识自己所得的精粹,蕴含着作家的生活体验、人生感悟和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由此而言“寻找自己的句子”就是不断突破已有的“自己”而塑造新的“自己”的过程,具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P204)的品格。
“寻找自己的句子”亦展现出作家们苦心经营自我文学世界的努力。以藏族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例,拉萨的次仁罗布二十多年来游走在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天空下寻找、发掘当代西藏民众的生活琐细,康定的尹向东编织着翁贡玛贡玛草场的世事纠葛、梳弄着康定城的心灵激荡,而甘南青年作家王小忠近年来也在尝试着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甘南。王小忠在《有关兄弟的话》中传递出他的创作起点: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农牧业结合地带,隶属于历史上的安多藏区。就在这片高海拔地区,我的祖祖辈辈们艰难的生活着,他们谈论着人生无常,叙述着命运多舛。这块贫瘠的土地养育着成千上万的民众,可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大家拼命挣扎的同时,也渐而迷失了方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加之外来人口的迁移和融合,以及旅游大力开发的今天,使这片土地原有的游牧文化在不断丧失的同时,渐而多出了形同城市的文明,以及文明掩盖下的难以说清的复杂与颓败。[3]
祖先留下的生活方式遭遇了“形同城市的文明”侵袭的危机,在王小忠的眼中,甘南呈现出“难以说清的复杂与颓败”,他的甘南“兄弟们都处在‘被绑缚’与‘想挣脱’的精神状态之中”,他试图以“撕开‘兄弟’一词中被天然‘温暖’包裹着的现实‘寒冰’的决绝与勇气”为突破口,展现甘南人生活的变化、精神的挣扎、灵魂的漂泊。
王小忠在创作小说之前,着力于诗歌和散文的写作,先后出版了诗集《小镇上》和散文集《静静守望太阳神》,他在提纯诗情、萃取画意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甘南乡土精神世界的裂隙,可能基于此,他放下了迷幻的抒情之笔,而抓起了沉重的现实之笔,勾勒出现实甘南的文学景观。王小忠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算得上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这一代人未曾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直面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生长在乡村,曾经历过乡村淳朴温馨而又相对缓慢的生活节奏;就学于城市,也感受过城市文明的迅捷凌厉,恣肆激扬过青春;这两种生活经验的对撞,使得他们成为乡村的身体与现代的心灵扭结在一起的社会个体。他们某一天猝然发现他们的乡土家园改变了容颜,不复旧时的光景,他们惶惑无措,但愈加萧索的现实迫使他们追索、探求自己的文化根脉,进而以文学的方式表达现代的强行闯入与传统的黯然无力,他们怀恋传统的温情但又畅享现代物质生活,他们的创作呈现出身心矛盾、自我分裂的特点,或许这就是这一代乡土底色的作家们文学伦理的基本形态。另外,王小忠曾有八年的基层教师经历,他感同身受偏远农牧区基层教师的付出和渴求,也看到了挣扎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教师们的辛酸与无奈。因此,当王小忠借助小说表达他的乡土之恋和乡土之思,势必要以他的生活经历、情感遭际等个体的心路历程为基础。检视王小忠的小说,以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学生时代的青涩记忆、教师生涯的理想坚守、乡土记忆的明日黄花、家庭危机的阴云笼罩及传统生活的现实破败等方面,亦暗合王小忠的成长历程。基于此,王小忠的小说中渗透出浓郁的乡土伦理书写的意味。
一
《黑色文胸》[4]是王小忠青春记忆书写的起点。情感炽热而又敏感的青年学生徐羽飞热恋着年轻女教师沙丽,不同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往,师生之间囿于世俗伦理的藩篱,只能以讲义、苹果作为他们之间交往的信物,由此,讲义成为师生间精神交流的媒介,苹果成为师生间物质来往的工具。而对于青年学生徐羽飞而言,讲义抑或苹果都是情感隔膜的象征,并不是体达灵肉交融的表现,尤其是沙丽与徐羽飞在仅有的一次亲密接触后,两人陷入了深深的自责,都选择了离开学校以平息情欲之火,分别之际,徐羽飞窃取了沙丽老师的黑色文胸,他的情欲表达以文胸的象征而达到了极致,文胸是展现女性身体性属的重要标志,是沙丽女性魅力的表征,是性的张扬与表达;但文胸又是保护女性身体的重要物件,是隔绝师生间热恋的最后屏障,徐羽飞携带着具有双重意味的文胸仓皇而走。沙丽并未因为文胸丢失而怪怨徐羽飞,反而避而不见以留言的形式表达内心的不舍与现实的无奈。师生间的恋情戛然而止,如同“盘子里的苹果”,即便“居住在同一个盘子里”,却注定无法相拥,只能彼此张望,而留下美好的记忆。《黑色文胸》以隐晦的方式展现出青春情欲的滚烫而不得。师范生徐羽飞带着如是的青春记忆而奔赴了新的人生旅程,“一个秋天的傍晚,我拎着那个黑色的皮包回到家乡,院子里菊花怒放”,那么等待徐羽飞们的又将是怎样的人生路途呢?王小忠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铺陈,一个方面是走向草原教师生涯的徐羽飞,一个方面是陷入情欲世界而无法自拔的徐羽飞,或者可以说一个是带着日神精神气质的徜徉在理想与现实境遇的徐羽飞,一个是在酒神精神的牵引下走向人生迷醉、迷惘的徐羽飞。
离开学校,开启教师生涯的徐羽飞们奋战在基层教育的最前沿,他们满怀着教书育人的职业情怀,但冰冷的现实让他们迅速陷入生活和理想的困惑泥潭,于是王小忠接续创作了《遥远的雪花》、《愿望》、《遥远的秀玛》、《最后的评语》①等作品,这几篇作品中的年轻教师们从师范院校毕业后满怀着激情走向散布在草原上的中小学,他们热爱教育事业,尽其所能地向学生传递知识,但教育考核的数量化、学生学习状态的懒散化、学校教学秩序的功利化等等情态使得他们的激情消泯,再加上教师生活的清贫化又使得他们的家庭陷入了一种缺乏温情的困境,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促迫着他们艰难选择,或者逃离现有的生活环境而走向更为遥远的“秀玛草原”去实现自我的教师职业价值,或者铤而走险背离职业操守以实现自我的生活价值,于是《遥远的秀玛》[5]中的乔高申请去草原更深处的学校去支教,期望实现教育理想,《遥远的雪花》[6]中的孙军去银行行窃而被刺身亡,在这两篇以“遥远的”命名的作品中,王小忠为人们展现出走出校门的徐羽飞们面对严酷的生活伦理,胸中的理想逐渐破灭的历程。
而如果离开学校的徐羽飞们没有选择教师生涯,王小忠在《再前进一步》②中呈现了“书读了,学上了,文凭也拿到了,可是混不到一口饭”[7]的徐羽飞的另一种人生情态,或者说是“黑色文胸”的情欲充斥在内心深处的徐羽飞的人生境况。《再前进一步》中,表妹琪琪洋溢着青春激情的身体开启了“我”的情欲之旅,如同“黑色文胸”的诱惑功能一般,让“我”在情欲之路上纵横驰骋,但表妹的伦理身份又让“我”望而却步,于是琪琪的朋友紫蝴蝶就承担起情欲表达的功能,若让“我”在情欲之路上一往无前又当如何,王小忠对此没有把握,为了阻隔情欲恣肆地突破伦理藩篱,《再前进一步》中设置了小玲儿的角色。小玲儿是寡妇,自食其力生活,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我”的期望。“我”游移在表妹琪琪家的铁门前、小玲儿的家门前以及茶楼紫蝴蝶的房门前,琪琪已经转变为茶楼的老板,不再回家,那青涩的青春回忆已成为过往云烟;小玲儿恬适闲淡,生活依旧波澜不兴,家里院外彰显着生命的坚韧;茶楼里的紫蝴蝶游走在各色男人之间,期望实现龙门跃就此改变生活处境。就此而言,“黑色文胸”的诱惑与保护功能共同发挥作用,几经周折,“我”最终选择了“黑色文胸”的诱惑,弃绝了小玲儿的痴情与期待,撕碎了象征知识的“许多证件”,“然后放开脚步,向省城的方向走去。眼前是茫茫黑夜,身后是茫茫黑夜”,从“黑色文胸”走向“茫茫黑夜”,意味着“我”选择走向更为浓郁的人生情欲之路。
至此,王小忠彻底完成了师范生徐羽飞的“黑色文胸”之情欲表达,表现出出生草原的乡野青年即便拥有现代文化知识依然无法摆脱黑色命运的人生羁绊,或走向遥远,或走向暗夜。由此,我们也能看到乡土知识分子王小忠青春记忆的黯淡与茫然,那么他将如何救赎日渐消沉的灵魂,换句话说,他如何破解何以为家的伦理迷思呢?这是王小忠们必须面对的伦理困境,不仅是人生路径的选择,也是文学伦理的择取,他们势必要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二
为了破解伦理迷思的僵局,王小忠选择回归原乡,力图以淳朴、蛮霸的生命原力来拯溺“黑色文胸”的人生迷境,在祖辈繁衍、生长的甘南大地上寻找精神的慰藉和灵魂的归属,于是,他先后创作了反映草原生活记忆的《我的故事本》和乡土生活回顾的《堡子记》③,这可能与王小忠的临潭人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临潭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农区与牧区、藏区与汉地的结合部,是多民族文化生活融合的所在,因此,王小忠从小耳濡目染,既熟悉藏民的游牧生活,也知晓农区的耕读生活,这两种生活方式毫无隔碍地融汇在王小忠的乡土记忆中,或可说,王小忠的乡土记忆更为驳杂、粗粝,也为深度开掘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我的故事本》[8]追述的是父辈的故事,次第描述了索南丹柱的传奇故事,草原的游牧、森林的砍伐和山野的狩猎,这都是个人与自然的抗争,彰显的是个人的伟力和自然的凌然不可侵犯,尽管海明威所谓的“人生来并不是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展现的是虽败犹荣的抗争精神,但在实际的抗争中索南丹柱一次次地走向失败。若探究索南丹柱失败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自然的无与伦比的强大,人在自然面前渺小无力,即便是暂时的胜利也无法改变最终的失利结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索南丹柱内心的挣扎,他既遵循祖先的教诲,又渴望改变生活现状,两相对抗,陷入焦灼。索南丹柱的每一次冒险都有确定的目标,为了保护牧场牲畜,索南丹柱与群狼斗争;为了改善住宿条件,索南丹柱进林砍伐椽子;为了补贴日常家用,索南丹柱上山打猎,而一旦既定目标无法实现,索南丹柱即刻抽身而退,再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也说明索南丹柱这一代人并没有延续祖先的生活方式,拘执于某种生产行为,而是以一种变通的生活智慧应对生活。而索南丹柱最后一次的抗争依然是“心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占有的欲望也使他变得粗野而残暴”,表现为“开始做起屠宰生意”,但是妻子的病又使得他一次次走向破产的边缘,索南丹柱最终要对抗的竟然是命运。索南丹柱一生为了生活奔波,人生经历波澜起伏,他最大的希望是儿子道吉才让能远离父辈的冒险生活,定居下来,好好念书;而道吉才让自小生活在康多峡牧村,基本远离父亲索南丹柱的生活方式,他的希望是儿子丹珠“好好念书,将来住比这更漂亮的房子”。王小忠的《我的故事本》本来要找寻祖辈的荣光,最后却发现父辈认为他们最大的荣光竟然是孩子们远离自己的生活,显然王小忠并未在游牧生活的先辈中找寻到答案。
《堡子记》[9]不再演绎父辈的故事,而是父辈追寻更早的父辈的故事,故事的时间向记忆的更深处延伸,已突破了《我的故事本》中母亲所讲的故事的范围。“故事”是传奇,是掌故,是过去的记忆,也是过去的荣耀,但同时“故事”又是农耕时代、游牧时代人们围炉夜话,聆听长辈讲述的农夫的耕种经验和水手的航海传奇,一旦生活、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人们眼中的世界发生变化,“故事”的生活指导意义渐次失去其价值,那就势必会产生新的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故事”。《堡子记》所追述的则是人称锉墩子的何三斤讲述的堡子的历史,追述者又是曾聆听过何三斤讲故事的老者,因此,就出现了一位老者在讲述另一位老人所讲述的故事,在时光顺序中,过去的影像在清晰的描述中渐趋模糊,成为历史记忆,诸如堡子的夯筑、堡子面临的匪患、堡子里的好汉、堡子里的风流韵事、堡子间的争斗等等,这一切都随着堡子为新村所替代而成为过眼云烟,“堡子只是一个遗留下来的名字,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亮亮堂堂的全新的村子。奇怪的是村子里人也少了许多,村道上空空荡荡,田野里更是空空荡荡”,土地荒芜,“满山遍野都长出了蒿草,不见一棵庄稼”,这就是新的堡子传奇的开端。王小忠在农耕记忆中依然没有找寻到他所需要的精神宽慰,反而更加重了他的忧伤。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王小忠回溯到故土的“青草更青处”,希望“满载一船星辉”以破解何以为家的伦理迷思,但在事实上无论是父辈的艰辛卓越的抗争,还是何三斤渐行渐远的乡土感怀,都昭示出传统生活智慧与当下生活现实之间的隔膜,祖先的智慧并不能解决当下的生活伦理困惑,王小忠的“寻找自己的句子”注定要回到甘南大地的现实,直面生活本身。
三
既然乡老们的乡土记忆无法荡涤内在的伦理困惑,无法安置精神家园的安适,王小忠开始从破裂处入手寻找无以为家的伦理现状,为此王小忠立足于生活中的某些不正常的现象展开他的寻找之旅。在寻找的过程中,王小忠采取了非常讨巧的方式,他采取故事嵌套的叙述模式,借助他人之口引发的自我感怀来描述生活现状。而在当下的生活中,能充分地接触到甘南民众生活情态,熟知甘南的地方性经验的当属基层干部,为此,王小忠首先将目光投向基层干部的经纬人生体验,多层次多角度地勾勒某些社会乱象,《朵朵》系列小说即其探索的开端。
《朵朵》[10]由若干篇作品构成,每一篇皆立足一个话题,在故事的展开中表现出王小忠对现存某些现象的伦理批评。朵朵是一名基层公务员,因工作便利容易接触到各种类型的人和事,此种以朵朵为中心的游移的写作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展现王小忠的观察视野的宽泛和深入。《传染病》描摹了离家出走的村妇五月赴深圳打工而后染病,接受民政局救助,并以为要挟民政局每月按时为其发放救助金,展现出某些人不以为耻的行为反而成为其明目张胆行为的合法性依据;《失踪的猫咪》描写的是农村重男轻女的生育现状,结果老人去世时陪在身边竟然是一只猫;《相信轮回》描写的是女性情感世界的空虚,展现出男权秩序对女性尊严的践踏;《日光温室》呈现的是地方政府套取补贴的堂而皇之的行为;《要人命的项链》则是旅游市场的乱象,看似便宜的项链其实暗藏杀机,伤害人们的身体,引发旅游市场信任危机;《医嘱》展现的是医院的潜规则,引发患者的医疗信任危机;《大字报》表达的是职场女性的窘境,即不但承受着和男性一样的工作压力,还存在着道德指责的隐患。王小忠通过朵朵的叙述将众多的社会现象以伦理的形态加以展现,表达出期望改变当下社会伦理的文学努力和社会担当。尽管目前刊发的《朵朵》系列只由七篇小小说所结构,但有理由相信王小忠类似于《米格尔大街》的素材积累方式和文学表达方式,或会成为他关照甘南现实、表达甘南伦理情态的重要依仗。
《朵朵》的书写为王小忠深入了解社会现实开启了一种探索模式,在悉心涵咏之后,他把《朵朵》中的伦理情态在作品中细致地呈现,由此而言,《朵朵》在王小忠的创作序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孵化作用④,如关于女性沉沦,王小忠在《秘密城堡》⑤中接续《传染病》中五月赴深圳的叙述方式,展现了农村女青年张彩乐的城市沦落过程,填充了《传染病》中叙述的缺失;关于女性情感世界的空虚,《血色的月亮》⑥接续了《相信轮回》中朵朵和小马豢养宠物排遣情感缺失的书写,呈现出结婚后丈夫外出,妻子为男人们侮辱的伦理丑行;关于老年人生存问题,《出逃》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失踪的猫咪》的续写,展现九月被媳妇撵出家门被迫打工的故事。由此来看,《朵朵》具有与《黑色文胸》同样的文学延伸和探索价值,是王小忠拓展文学路径和实践文学多样性的阶段性基点,当他把《朵朵》中的若干单一伦理问题整合起来,在更为宏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这些现象的时候,也就生成了王小忠关注现实问题及表达生活伦理关怀写作个性,他的“寻找自己的句子”的旅途就向前迈出一大步。
《朵朵》的结尾是饱经世事磨砺的朵朵希望与她的忠实听者“我”一同步入婚姻殿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王小忠的写作重点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辐射性的社会问题书写。依据是2012年王小忠发表了小说《暖流》[11],这在王小忠的整个小说创作中是非常温暖的一篇作品。何香、徐细舟夫妇生活不宽裕,但家庭中充满了活力和希冀,即便是女儿雪儿的手指被炸伤,夫妻俩依然坚定生活的信念,凭借自己的努力一定能改变生活的面相,在结尾处伴随着“春天就来了。春天来了多好”的期待中,“细舟猛地搂住何香和雪儿,他感到一股暖流如电般传遍他全身”。但《西藏文学》2016年5期刊发的《他们的苦衷中》,王小忠在《暖流》的结尾处增加了新的故事情节,着重展现徐细舟外出打工期间妻子何香与村委会主任马利之间的暧昧情节,这说明王小忠意图突破家庭温情叙事的限制,以家庭为窗口展现社会伦理的复杂与多样。而在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中情感的背叛是最突出的伦理问题,为此,王小忠先后发表了《隐形婚姻》、《流窜客》、《九月》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婚内出轨的乱象。《隐形婚姻》[12]书写的是常出公差的丈夫剑外出期间的出轨行为,以及妻子对丈夫行径的无望而引发的出轨报复,表达出夫妻之间既渴望婚姻的稳定,又渴望能够寻求情感的刺激;在表面平和的家庭假象的掩盖下,夫妻的内心中却激荡着情欲的洪流,表达出当代婚姻关系扭结的松散。《流窜客》[13]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隐形婚姻》初次出轨遭遇的补充,女性以身体换的金钱近似卖淫的行为,却被程刚们以扶贫救济的说辞所掩盖,或者说人们往往为自己的不轨行为寻求合法性的依据,以躲避自我道德法庭的审讯。而《九月》[14]中王燕的丈夫辛刚不但出轨小保姆,甚至与妻妹合谋欺骗妻子,王燕能够原谅辛刚出轨小保姆,但无法容忍辛刚与王茜出轨的伦理丑态,也就是说人们难以忍受姻亲与血亲的不伦行为,王燕最终在神思恍惚中遭遇车祸,这说明情感背叛已成为家庭生活的痼疾,而传统的伦理秩序在当下生活中几乎完全失去效能。家庭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以血亲和姻亲连缀在一起的家庭则是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石,若家庭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那么社会如何保持其相对稳定呢?这是王小忠社会伦理观念中无以为家的又一深重思考。
四
21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申报、保护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各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层出不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如何在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取得融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王小忠将目光投向甘南草原深处的传统技艺,试图探究在现代化语境下,传统技艺如何传承的问题,以及由传统技艺的传承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2013年王小忠发表《小镇上的银匠》[15],该作以老银匠择取徒弟为线索串联情节。老银匠嘉木措手艺高超讲诚信,他最在意的是银饰手艺的传承和女儿拉姆草的婚嫁,认为这两件事是合二为一的,手艺是他一生心血的象征,女儿是他血脉的传承,这两者之间须臾不可分割。南木卡觊觎的是嘉木措的手艺,且心术不正,故无法成为银匠手艺的继承人;道智在意的是拉姆草的美貌,对银匠手艺同样不感兴趣,故亦无法成为嘉木措的继承人。而外地来的小银匠折服于嘉木措的手艺,甘心放弃机器铸造银饰的生意,而专心学习手工打造银饰的手艺。最终小银匠继承了银匠手艺,与拉姆草成婚。《小镇上的银匠》故事情节简单,主要侧重老银匠嘉木措的塑造,展现老银匠技艺高超,且见识不凡,关于银匠手艺,老银匠认为“打做佛像才是一个匠人真正的手艺,它不但饱含着虔敬,而且还有善良和慈爱。当你真正成为一个手艺人之后,面对那些无论慈祥或狰狞的佛像的时候,你都会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在说世界上最善良的话”,这也就是说只有心地善良、充满虔敬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银匠,在光彩夺目的银饰里潜藏着人们的慈爱与谦卑。在小说最后,小银匠穿着老银匠“那件满是窟窿眼睛的羊皮围裙”,意味着他不仅学到了银匠手艺,也继承了银匠精神。王小忠在《小镇上的银匠》中以理想的方式使得传统技艺得到传承,传统工艺的精神得以彰显,暂时解决了何以为家的伦理困境,即继承传统、着眼当下、保持内心的谦卑与平和。但在事实上,王小忠亦在《小镇上的银匠》中表达出他的担忧,“小镇上游人络绎不绝,外地人纷纷扬扬云集到这里,街道变得宽阔了许多。大部分牧民也搬了过来,不去放牧,专门做生意。隆达、经幡、首饰、藏刀、狼牙……应有尽有”,小镇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小镇人的精神世界随之也相应地发生或迅疾或缓慢的变化,现代化的冲击无处不在,如何葆有本心和初心就成为草原上的匠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就引发了相应的伦理迷思,这成为王小忠深入探索的新的起点。
接续《小镇上的银匠》的是王小忠2015年发表的《羊皮围裙》[16]。在《羊皮围裙》的结构格局中,《小镇上的银匠》相对完整地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而故事的裂隙就从小银匠继承手艺、打造佛像之后呈现的。小银匠不安分于匠人的生活,渴望获得更多的现实利益,游走于商场与官场之间,当他“连羊皮围裙都装了起来”时,意味着小银匠要放弃银匠手艺与银匠精神,而回转为小商人的面相;拉姆草依然徜徉在牧场与羊群之间,在天地间舒展个性和心灵,因此,小银匠和拉姆草的隔阂开始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两种生活伦理观念开始发生碰撞。及至小银匠远走美仁草原,开启新的生活模式,或者说完全恢复了商人的本性,不仅有家不回、移情别恋,甚至要以法律诉讼的方式瓜分拉姆草父女的房屋,最终小银匠败诉远遁,在两种生活伦理的交锋中,看似小银匠失败了,其实真正失败的是拉姆草父女所秉持的草原生活伦理,于是,拉姆草陷入无法自拔的情感泥潭中,在悔恨、自责中艰难度日,甚至产生了远离红尘遁入空门的念头;老银匠嘉木措不愿再从事银匠工作,更不愿意收徒授业,而将羊皮围裙“放在柜子里”。至此,“羊皮围裙”所代表的善良、虔敬、忠实、诚信的匠人信条在老银匠的三个徒弟的连番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草原技艺、草原伦理似乎已被人们弃之若敝履。但王小忠似乎并未放弃对于草原伦理的追索,他执拗地以为随着旅游业的兴起,现代商业化的伦理与传统草原伦理必能尽弃前嫌,而生发出新的适应生活现实的全新的伦理新形态,因此,当小镇又一次焕发生机,当老主顾们先后光临,当小镇的游客日渐增加且对手工制品的需求愈益强烈,当得知政府“要给老手艺人特别的待遇,不能让手艺失传”,这一切新的变化激发了老银匠端木错的匠人情怀,他找到了“羊皮围裙”并且“那件羊皮围裙周身的小窟窿都被他认真地缝补了起来”,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羊皮围裙所象征的技艺和伦理将绽放出新的光彩。
但若是草原技艺伦理与现代生产伦理发生龃龉,又会发生怎样的情态呢?王小忠在《小镇上的银匠》中以小银匠看到老银匠的手工饰品而震撼的情节描写,表现出传统技艺完胜现代机器制品的观念;在《羊皮围裙》中,王小忠描述了小银匠将手工银饰品与机器银饰品摆放在一起出售的场景,传达出两者所象征的伦理争斗并未落幕。及至《缸里的羊皮》[17],王小忠极力渲染手工技艺与机器制作之间的冲突及对人心的伦理冲击。楞木代擅长手工羊皮袄的缝制,班玛次力在服刑期间学会了机器缝纫技能,两人合作生产羊皮袄后,楞木代提供的是炮制、鞣制后的羊皮材料,班玛次力进行的是最后的机器成品加工,看起来两人的合作是草原传统技艺与现代机器工艺的合作,但实际上,机器成品加工截断了传统缝纫技艺的成品阶段,也就是说传统的草原缝纫技艺遭遇了挑战,不再是完整的缝纫流程。由于劳动分工的不同,人们看到的是班玛次力的成品加工,而逐渐忽视了楞木代前期准备羊皮材料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能,证据就是班玛次力逐渐取代楞木代而获得了牧场上最好的缝制羊皮袄匠人的声誉。楞木代的“心里憋满了气”,以为他所做的“泡皮子、揉皮子、铲皮子”的工作“明明是学徒干的活”,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手工技艺完败于机器工艺;而班玛次力明显看不起楞木代的前期加工,不仅没有帮忙,反而冷嘲热讽,并且拒绝传授给楞木代的机器缝纫技能,于是裂隙又一次产生了,两种伦理的对抗拉开了帷幕。随后,班玛次力放弃了缝纫工作,远走他乡寻找新的生意。楞木代无法按时完成主顾的业务,声誉更是一落千丈,又随着羊皮被贩卖到工厂而批量生产的皮袄流行在草原上,楞木代的手工缝纫技能彻底为人们所遗忘。在人们的漠视中、生意的凋敝中,楞木代将这一切的结果归罪于班玛次力,认为“破坏市场,让皮匠在草原上彻底消失的凶手就是劳改犯班玛次力”。楞木代与班玛次力的合作意味着两种生产伦理的交融能创造出超越手工制作的生产利润;而羊皮被送进工作后的批量生产,又意味着机器化大生产取代分工协助的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传统技艺在机器化的打击下逐渐走向没落,也表征着传统手工生产伦理的凋敝引发草原固有社会伦理的渐趋消泯。至此,王小忠不得不面对草原手工业为机器工艺取代的现实,无奈地眼见草原传统生产伦理的远去。如果说“羊皮围裙”还在表明王小忠对草原伦理复苏的期待,那么泡在“缸里的羊皮”则意味着草原手工生产方式及其伦理形态的黯然退场,王小忠对“羊皮”的两种态度显然隐喻草原伦理在现代化生产、生活中的尴尬景象。但是,如果班玛次力们掌握了现代机器工业生产技能,草原伦理会呈现出怎么样的面貌,对此,王小忠没有深入探究,或者说他正处在探究之中。
此外,王小忠涉及的非物质文化还有中医药。在《锦旗上的眼睛》和《虚劳》中,王小忠以中医药为镜子影射人心的复杂与多样,展现现代社会伦理的多种面相。《锦旗上的眼睛》[18]中鳏夫大夫魏红精通针灸之术,在治疗杨艳产后乳痈的过程中,内心的情欲渐渐复苏,及至最后一次治疗时,魏红与杨艳相拥在一起,这一幕为学徒银秀所见,魏红担心自己多年的清誉付之流水而陷入深深的焦虑状态,他开始逃避银秀,逃避熟悉的人群,“渐渐喜欢上独自去村口的那天小路埋在那条小路上,他可以想想自己的心事,可以给自己说说不愿意让别人听见的话。魏红喜欢上了孤独,也喜欢上了想象和猜测”,而在治疗银秀的高烧时,魏红使用了针灸之术使银秀陷入安宁,却也耽误银秀的及时治疗致使银秀“脑子被烧坏了”。为此,魏红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最终得出“作为大夫,良心和职业操守才是值得终身相守的”结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治好银秀的疯癫。在《锦旗上的眼睛》中,魏红徘徊于医生的职业伦理与个人的道德清誉之间,内在世界天人交织,承受着情欲的煎熬和职业道德的纠结,意味着王小忠试图从职业操守与社会身份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个体的伦理归属。而《虚劳》[19]中,王小忠展现的是本为清修之地的天伦寺在市场经济中变为名利场的故事。僧人不枯钻研中医药学,本为疗治母亲的病痛,却在无意间治疗了张老板等人的疾患,为寺庙带来了可观的布施,为此,不枯在寺庙的地位直线上升。这就成为一个悖论,弘法之所竟以创造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个体价值的标准。而虔诚的母亲依然要求不枯将苦心积攒的钱财交给智慧长老作为功德;智慧长老将不枯作为摇钱树,要求他答应众位老板的请求进城作法、治病;最终不枯以虚劳为由拒绝智慧长老的要求而还俗。不枯罹患的“虚劳”是因“烦劳过度,加之饮食不节,实为精气有损”,通过药物治疗和自我调理即可恢复身体健康,但是天伦寺的“虚劳”又该如何诊治呢?又能开出怎样的药方呢?王小忠似乎为我们的生活诊断出“虚劳”的伦理病灶,而至于如何疗治,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由此而言,《锦旗上的眼睛》与《虚劳》都是以药石隐喻社会生活的病灶,而解决此种社会病患只能从净化人心、涤荡风气入手,方能建构新兴的适应当代人生活方式的伦理秩序,才能安置人们“虚劳”的身心。
总体上看,王小忠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始终关注现实,审视人心,立足甘南一隅而辐射广泛,他在何以为家的伦理迷思中挣扎、跋涉,显示出文学即人学的人文情怀;王小忠还不断地求变,从不同层面展现社会生活的面相,尽管他所呈现的生活区域狭小,或是草原定居点,或是草原边缘的某个小镇,但他善于捕捉生活世相的点点滴滴以昭示社会伦理的嬗变。尽管王小忠渴望突破“兄弟”一词的束缚与羁绊,渴望能在更为宽广的境地展现他的文学甘南,但不可否认的是,离开“兄弟”,王小忠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他的何以为家的伦理迷思生发的基点还是甘南吗?因此,对于王小忠而言,既脚踏甘南大地,又能与甘南保持适当的距离,方能呈现出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伦理甘南的面相。
[注 释]
①《愿望》与《遥远的秀玛》内容完全相同,故作一篇计。
②《再前进一步》与《茫茫黑夜》内容基本相同,但其中人物的名字发生了变化,为便于叙述,故只选择最早发表的《再前进一步》。
③2011年5期《凉山文学》刊发的《枪王阿米》、《赌王刘拐子》及2013年10期《黄河文学》刊发王小忠《堡子的故事》,与2018年7期《青海湖》刊发的《堡子记》有明显的承嗣关系,但在内容上《堡子记》更为丰富些,故择取《堡子记》为对象。
④尽管《朵朵》发表于2014年,但是《朵朵》中的《传染病》发表于2011年,这意味着王小忠的《朵朵》系列的写作或者说是思考最晚已在2011年已初见端倪。
⑤此作还曾以《我们的秘密》为题刊发于2015年7期的《朔方》。
⑥2015年,以《血色的月亮》为基础,经过修改的《你不知道的心愿》刊发于《滇池》第5期。
⑦2016年,以《出逃》为底本的《九月》刊发于《贡嘎山》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