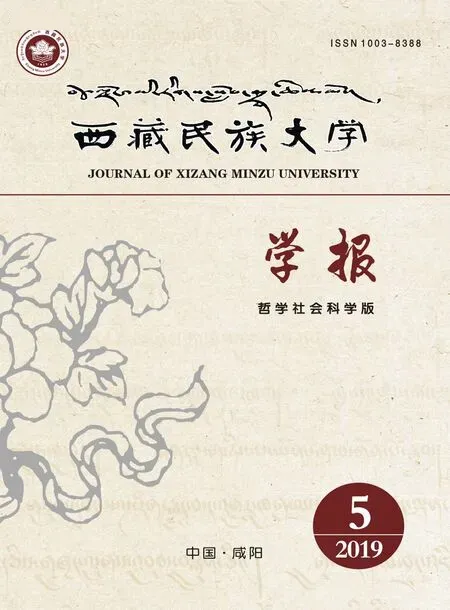清朝前期方志与史料中的藏北防线
马天祥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需要申明的是,准噶尔部属清代中国漠西蒙古一支。因此,平定准噶尔部战争,属独立主权国家内部事务。清朝初年,准噶尔部的扩张对王朝北部和西部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乌兰布通之役爆发,其为乱之意已显露无遗。仅就其对西藏地区的大规模袭扰来看,准噶尔部就曾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入藏为乱,其后又于雍正五年(1727)欲借藏地内乱之际入藏“煎茶设供”未果,以及乾隆十二年(1747)准噶尔又借“进藏熬茶”之名伺机为乱等若干次袭扰行径。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被彻底平定,才使王朝西部边疆重归安宁。
清朝初年为应对准噶尔部的袭扰,藏地北境曾经建立起一条绵延数千里的庞大防御体系,然而伴随着准噶尔部的平定,这条庞大的防线渐渐湮没在了文献与史料之中。①准噶尔部属漠西蒙古,其主要势力位于藏地西北,因此,位于藏地西北方向的阿里及后藏北部连绵的高山荒原就都有遭到准噶尔部袭扰的可能。
成书于雍正年间的《西藏志考》“兵防甲胄”条中详细载录了全藏兵员及配属情况:“西藏设额马步兵六万四千余名,拉撒马兵三千名,②后藏马兵二千名,阿里马兵五千名。”③可见在雍正一朝,西藏地区的防御重点为阿里、后藏与拉萨。随后,成书于乾隆初年的《西藏志》“边防条”亦载:
西藏接壤外藩,界连蒙古,雍正八年,准噶尔侵犯西北两路军营。颇罗鼐奏准,夏初冰雪全消,青草萌时,派驻藏大臣一员,绿旗官兵一千五百名;其次子台吉朱米那木查尔带拉萨兵一千名,前赴打木腾格那尔地方驻防;派长子辅国公朱尔吗特策登夏初带蒙古番兵二千名,赴门里、噶尔、波鲁多克三处驻防;④每年派其弟诺彦和硕气赴哈拉乌素训练该地兵马二千余名,即统领驻防;约至九月,雪封山径撤回。⑤
引文中“打木腾格那尔”即清代文献中多次出现的“达木腾格里淖尔”(纳木错);⑥门里、噶尔、波鲁多克三地实为清初藏地西境阿里之防卫重镇;而“哈拉乌素”亦即清代方志与文献中之“喀喇乌苏”(那曲)乃清初藏地东北由青海方向进出西藏之要冲。可见至乾隆初年,在关涉西藏的方志文献中,藏地防御重点似乎是以距拉萨较近的腾格里淖尔(纳木错)为纽带,勾连起了东北方向的喀喇乌苏(那曲)与西北方向的阿里。考诸有清一代各类西藏方志,唯有以上雍正、乾隆初方志言及此三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清中乾隆末年以后的西藏方志则将更多的关注视线和笔墨集中在了藏地南境上。⑦
清代西藏方志的编纂多为“资政”之用,故多从简、从要。因此,清初藏地西北的防御问题绝非方志文献中的寥寥数笔可以概言。换言之,喀喇乌苏(那曲)、腾格里淖尔(纳木错)、阿里三地确系清初藏地防御重点但绝非全貌。当然,清初藏地针对准噶尔部的最初防御确系依托这三点来建立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袭扰西藏,更为确切地说应该是偷袭。意大利学者伯戴克指出“和田是他的根据地,他企图从那里行经西藏西北部进抵那曲卡,向在避暑毫无防备的拉藏汗进行突然袭击。”[1](P52)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准噶尔军突然出现在了那仓(纳仓)。据伯戴克L.Petech注解可知“那仓这个地方是腾格里诺尔湖西部和西北部湖区。”⑧据此,中外研究者们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准噶尔部的袭扰是以和田为跳板,穿越昆仑山脉进入阿里的。⑨作为地理上抵挡西北准噶尔部的第一道屏障,阿里的重要战略地位不言自明。
然而,西藏地理条件有别于中原,高山大川、茫茫荒原,中原地区的传统战法并不适用,康熙五十七年(1718)朝廷平乱大军的全军覆没就足以印证这个道理。“(康熙五十七年)西安将军额伦特率西宁、松潘、打箭炉、噶斯丹,会同青海诸台吉及土司属下赴援,至喀喇河,遇伏,败殁。”[2](卷五二五)考诸《清史稿·额伦特传》亦对此惨败有详细载录:
(五十七年)六月,额伦特与色楞分道进兵,额伦特出库库赛尔岭。七月,至齐诺郭勒,策凌敦多布遣兵夜来侵,击之退。次日复至,额伦特亲督兵缘山接战,贼溃遁,追击十余里,多所斩获。疏入,上深嘉其勇。俄,策凌敦多布遣兵潜出喀喇乌苏,额伦特率所部疾趋渡河,扼狼拉岭,据险御敌。比至喀喇乌苏,色楞以兵来会,合力击贼。贼数万环攻,额伦特督兵与战,被重创,战益力。相持者数月。九月,复厉兵进战,射杀贼甚众。矢尽,持刀麾兵斫贼,贼益兵合围,额伦特中伤,犹力战,遂没于阵。[2](卷二八一)从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额伦特与色楞进兵时采取“分道进兵”不可谓不审慎;退守时采取“据险御敌”不可谓不周全;并且在战斗中“被重创,战益力”不可谓不勇猛;但最终仍不免于覆没。也许《清史稿·圣祖本纪》五十七年条“屡败贼,贼愈进,师无后继,矢竭力战,殁于阵。”中的“师无后继”这四个字道尽了个中的无奈与心酸。随后,康熙五十九年(1720)纵然清廷平定了在藏地为乱的准噶尔部势力,但这亦得益于外有青海蒙古诸部策应,内有岳钟琪奇谋建功:
(康熙五十九年)钟琪次察木多,选军中通西藏语者三十人,更衣间行至洛隆宗,斩准噶尔使人,番众惊,请降。噶尔弼至军,用钟琪策,招西藏公布,以二千人出降。钟琪遂督兵渡江,直薄拉萨,大破西藏兵,禽喇嘛为内应者四百余人。策凌敦多布败走,西藏平。[2](卷二九六)可见,这次平定藏地准噶尔部势力实借奇谋而非力战。质而论之,并未彻底肃清准噶尔部的影响,只治标而未治本。翻检史料不难看出,此后准噶尔部时而请和、时而为乱便是有力证明。雍正初年清廷在彻底平定青海地区叛乱后,在西部边疆开始推行稳扎稳打的战略。考诸史料,雍正八年(1730)清廷已开始在藏地实施稳步推进的战略,已于川藏要道的打箭炉(康定)、泰宁、三渡(三渡口)、吹音堡等(雅江)处设立塘站五十五座。⑩作为该阶段的策应,前藏、卫藏、阿里等地亦就准噶尔来犯之路做重点防御:
(雍正八年1730)盖通准夷之路有三:其极西由叶尔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远易备;其东路之喀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中路之腾格里海逼近卫地,故防守犹要。并以颇罗鼐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统阿里诸路兵。[2](卷五二五)
可见,雍正八年(1730)的防御思想是针对三条来犯要道做重点防御,这三条要道就是前文西藏方志中言及的阿里、腾格里淖尔(纳木错)、喀喇乌苏(那曲),不过此时的防御属于重点把守,难成体系。那么究竟从何时开始由单纯的重点防御转变为防线,以及后来严密防御体系的呢?考诸清代史料,《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条中已有关于藏地新增阿哈雅克卡座的记载。此外《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十二年(1747)又见对藏东北-青海一线卡座“每卡添兵三十名”的记载。且对准噶尔至藏的五条路径“每处安设卡座,每卡派兵一百名,头目一名。”《清史稿·治大雄传》亦有:
疏言:“西藏喀拉乌苏诸地与准噶尔连界,盗窃纷扰,是其故习。今藏北鄙即我边地,防边自可弭盗。请驻藏大臣仍设重兵,循大道置台站,以资防守。”上嘉其留心。[2](卷三一二)
这则乾隆十三年(1748)治大雄的进言说明了,乾隆初年清廷已经确立起了藏北防线的概念,并已付诸行动派遣重兵,另又设置供应粮饷的台站。至乾隆十五年(1750)藏北防线已然初具规模:
自喀喇乌苏至库车增台八,设兵。准噶尔通藏,凡阿里、那克桑、腾格里淖尔、阿哈雅克四路,各于隘口设卡伦。又有勒底雅路,为准噶尔犯藏时间道,亦驻兵防守。迭疏陈请,皆如议行。[7]
驻藏办事大臣集福等奏:卫藏北沿边一带,西自阿哩起,东至喀喇乌苏,安设十三台站。乾隆二十三年,将军伯伍弥泰奏裁,经军机大臣等议,以现值进兵叶尔羌、喀什噶尔,防逆匪窜越,令照旧设,俟应彻时再奏。今大功告蒇,外夷宁谧,实与内地无异,复据噶隆公班第达等呈称,准噶尔、叶尔羌等,俱蒙圣化,安享太平,卫藏台站,可无庸设。[3](册九,315)
可以肯定的是,逐渐完善的藏北防线与喀喇乌苏(那曲)-库车防线,为日后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清廷又在此基础上,对藏北防线渐次加以完善,至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
谕军机大臣等,据班第奏公班弟达告称:“有拉达克汗书来称,近日准噶尔人,从叶尔羌城至伊处贸易,询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安否,并及广兴黄教之事等语。”……今观准噶尔常差人赴拉达克贸易,则彼处自有通藏之路。朕虽不准其进藏,而伊倘由叶尔羌城差人进藏,则所关甚要。
……由叶尔羌城至阿里克地方,中隔大山,水草甚少,难少行走。每年贸易人赴拉达克皆有定数,若大众前来,拉达克汗亦不许过。即使前至阿里克地方,自阿里克至藏尚有两月路程,亦不难备御。又叶尔羌城有路可通鲁都克地方,亦须经戈壁行走月余。现在鲁都克地方常设卡座,至冬不彻,各处卡座严密连络。自咱拉山以外至拉卜赛那穆,自阿哈雅克以外至顺图古尔等处亦通准噶尔,今请将卡座再行展放严加防范,仍派谙练扎萨克台吉,前往巡查报闻。[3](册六,26)
较之此前部署,乾隆十六年(1751)亦有颇多增益之处。首先,将藏北防线向西延伸,将阿里以西的拉达克部纳入防线之中。纵然拉达克部尚未完全隶属于该防线之下,但在报送军情、设卡布控方面已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次,在原有藏北防线基础上大力拓宽防御纵深、广布卡座,完善防御体系,对准噶尔部有可能进犯的多条通道实施全面布控,在对叶尔羌(莎车)通往鲁都克要道设立卡座的同时,更对拉卜塞那穆至咱拉山与顺图古尔至阿哈雅克两条要道广设卡座以为联络策应。至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乾隆皇帝更是责令藏地官员标明阿哈雅克在内的所有防御准噶尔部袭扰的险关要冲:
西藏北边有阿哈雅克地方,距藏甚近,由此直赴噶斯乃通准噶尔便路等语。朕观藏图,并无阿哈雅克地名,或当日遗漏未画,抑所画未全。著将此图寄与班第,查明阿哈雅克地方与此图所载何处相近,并除阿哈雅克之外,曾否尚有遗漏未画要隘,查明添入,另画全图,于奏事之便,一并呈览。[3]
足见此时的藏北防线已成体系,清廷在努力进行着补充完善的工作,力求在藏北地区对准噶尔部做到最为周全的布控与防御。至乾隆十七年(1752),经过不断补充完善的藏北防线已然成型:
至准噶尔通藏之路有四:惟那克桑一路稍近,现已放卡,倘有贼踪,即速报信,一面派兵抵截,一面移徙游牧,不致使贼得利;又拉达克至阿里之路亦近,但拉达克与准噶尔往来贸易,人数无多,大兵恐不能入境;如不由拉达克地方,从叶尔羌城,亦可通阿里,但中有大山障隔;自阿里克至藏,尚有两月路程一得贼信,可以备御;惟腾格里诺尔、阿哈雅克两路较为广阔,今俱放卡,昼夜瞭望,不致疎懈。[3](册六,339)
综上所述,与雍正八年(1730)实施重点防御相比,乾隆十七年(1752)的藏北防御部署已然形成了一个东西呼应,联络通畅,应对灵活的有机整体。从根本上扭转了此前单纯重点防御的局面,为后来全面平定准噶尔部打下了坚实基础。翻检此后史料,亦不见准噶尔大规模袭扰藏地的记录。
至此,以清朝前期西藏方志为“索引”,综合大量清初史料,方可比较全面地一窥清初藏北防线全貌,该防线并非方志中阿里、腾格里淖尔(纳木错)、喀喇乌苏(那曲)这几个孤立地名所能概言。这条藏北防线实际上是以阿里、那克桑、腾格里淖尔(纳木错)、阿哈雅克、喀喇乌苏(那曲)五处为纵深支撑,以十三台站为坚实纽带,以和田-勒底雅、叶尔羌(莎车)-鲁都克、拉卜塞那穆-咱拉山、顺图古尔-阿哈雅克四条要道广布卡座为前哨,所构建起的一条绵延藏北的有机防御体系。当然,这条带状防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乃至功成身退,亦是经历了前后近三十年的漫长过程。由于藏北地区独特的地理特征,清朝前期从被迫推行重点防御到渐成体系,业已耗费二十余年光景,而平定准噶尔部的四年之后,该条防线方功成身退,彻底尘封在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之中。
[注释]
①仅就清朝西藏方志文献而言,清初西藏方志仅载阿里、那克桑、腾格里淖尔、喀喇乌苏等要冲,清中期以后的西藏文献则完全将视线集中于应对廓尔喀侵略,而清末西藏方志则将焦点集中于应对英军侵略,因此,清代西藏方志类文献中并无对这条藏北防线的详细记录。
②“拉撒”即“拉萨”。
③《西藏志考》成书早于《西藏志》、《西藏考》,关于该问题可参看赵心愚《<西藏考>与<西藏志>、<西藏志考>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2012年3月,第52-61页。
④“门里”似为“阿里”传抄之误,“波鲁多克”似为噶尔附近之“鲁多克”。
⑤此外,该书“边防条”中还言及的防御地点包括玉树、纳克产、奔卡立马尔、生根物角及拉萨附近的浪宕、帕尔离藏两处关卡,以上各处驻兵多者二十人,少者十余人,可见只是单纯的防御节点而非重点。
⑥“达木腾格里淖尔”具体指今纳木错至当雄一线。“腾格里淖尔”即纳木错;“达木”即纳木错以东、拉萨以北的当雄。
⑦值得一提的是,清中期以后的诸西藏方志中唯有松筠在其《西招纪程》中历数藏地边关要隘时,亦言明清初阿里的重要战略地位:“阿里乃卫藏西北极边,驻有营官二员,边外西北与拉达克汗部落交界,由拉达克北行月余可抵回疆叶尔羌地方。康熙年间,准噶尔策凌敦多布曾由回疆经阿里至藏滋扰,是阿里地方从前为西招要隘。”可见纵《西招纪程》篇幅简省,但在编纂裁量史料时已露渐能兼顾古今之意。
⑧“那仓”即“纳仓”。
⑨关于1717年准噶尔部入侵西藏的具体路线问题,另有内蒙古大学宝因特古斯以满文档案为依据,认为准噶尔军队实际上是从和田出发“由克里野路穿越昆仑山而悄无声息地抵达藏北纳克产地方的。”见2015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召开的“多语言史料背景下的西北研究”会议报告。实际上该文对准噶尔穿越昆仑山进犯之路的论断,在清代汉文文献亦有载录:“又有勒底雅路,为准噶尔犯藏时间道,亦驻兵防守。”见《清史稿·纳穆札尔传》卷三一二。此外伯戴克L.Pe⁃tech还在其著述中言及Sven·Hedin《A Conquest of Tibet》一书中亦对准噶尔部侵袭路线作了详细说明。
⑩“吹音堡”《清实录·宪宗实录》卷八十二载:“噶达之西吹音堡,亦系雅笼江渡口。”故推断此处当系雅江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