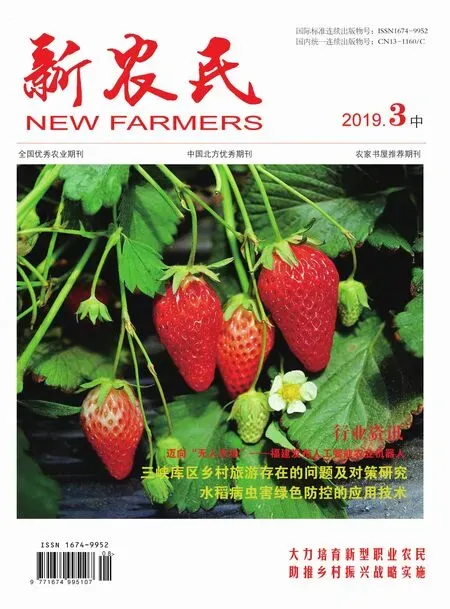农业大田作物有害生物种群规模与危害形式的变动趋势概述
张敬君
(临泉县城东街道农业综合服务站,安徽 阜阳 236000)
(1)害虫和较大有害生物种群中,低等或小型的动物更易成为成为主流害虫:在生物学分类中,越是高等动物,其种群会变得更弱,在同类动物中,越是体型大的生物越易被淘汰,而体型更小的生物则变得更繁盛,比如,在农业生产中,哺乳动物野免、田鼠、刺猬基本灭绝,爬行动物的蛇类数量急剧下降,这是因为在多种动物类有害生物的防治措施中,化学药剂防治占绝对主体地位,其中胃毒剂又占主体,在农田有害动物中,体型越大的生物,其生物体结构越复杂,胃吸收能力越强,而越复杂的生物体,其被药剂毒害,发生病变或死亡的机率越高,而发生变异、适应恶劣化学环境的能力越差,这就是兔子,田鼠最先消亡的原因。在同一大类种群中,也表现这种趋势:比如,在昆虫纲内部:体积较大的昆虫如蝗虫种群最先减弱,而体积较小的蚜虫上升为主要害虫。另外,机械化作业、土地规模流转、也是造成较大动物难以生存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对微型动物如昆虫纲、蜘蛛纲生物的影响是微乎其微。
(2)有益生物比有害生物更易于灭绝。好像越保护越易消亡,越打击越易繁盛:比如胡蜂,蝼蜂,螵虫是有益生物,现在种群很弱,螳螂、蝎子、蛐蛐、蝈蝈这些本没有重大危害的害虫基本灭绝,原本危害较重,被重点防治的蝶蛾类害虫变得更加猖獗,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针对性的药剂防治刺激了有害生物的变异与适应速度,在这个过程中,生存能力弱的品种面临灭绝,其中的强势品种发生适应性变异,产生了适应品种,这种新品种一旦摆脱农药的控制,便会疯狂增殖,呈现暴发式危害,而有益生物缺乏这种刺激,便会保持原来的状态,在生存竞争中失去优势,被有害生物控制住其规模,也可能是有有害生物被农药毒死后,农药残留体中,而其天敌食用了这些害虫,体内农药发生富集,最终导致其死亡,而以害虫为食物的有益生物,其规模会比害虫明显少得多,这种处于食物链上端的生物灭绝的机率会明显增高。
(3)微生物的重点危害转入地下:微生物病原菌危害分布基本不变:真菌类病害仍占病害的主体,细菌性病害次之,病毒性病害再次之,但线虫类病害明显减少,在危害形式上发生较大变化,病原菌危害作物的地上部分得到控制,而土传病害变得更加难以控制。近些年,保护地的重茬种植导致土壤带菌严重,秸秆禁烧与秸秆还田,导致土壤中菌类规模加大,而化学药剂对土壤内的病原菌杀灭效果很差,因为土壤对农药具有极强的降解能力,这样,土壤中的病原菌就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土传病害成为作物病害防治的重点。
(4)同翅目昆虫的重点危害变成携毒传染:昆虫纲动物是农业害虫的最大和种群,这个没有改变,但同翅目昆虫危害更重,因为同翅目昆虫体型总体偏小,群体规模大,都能吸食作物汁液危害,更重要的是,像蚜虫、飞虱能传播病毒,引起病毒病的暴发,近5年的玉米粗缩病的大发生就是其中一个重大表现,这种带毒传染危害的方式远比本身吸食作物汁液的危害要大得多,蚜虫作为孤雌卵胎生昆虫,其繁殖能力堪比病毒,是近年害虫防治的重中之重,而其严重发生的原因是:在临泉持续实行玉米、小麦轮作模式,而这两种作物都是蚜虫的生存宿主,而油菜、花生、甘薯、芝麻都不是,玉米小麦连作导致蚜虫持续存在危害宿主。在药剂防治上,持续使用同一种药物,交替施药执行不力,近二十年一直是吡虫啉的天下,虽然也有其他药物进入市场,但吡虫啉以其价格低,防效好而独占鳌头,我们当谨慎对待这种特效药的持续使用,当及时跟进研制新型药物,与吡虫啉交替应用,防止出现蚜虫对吡虫啉抗性品种。
(5)鳞翅目昆虫成为影响农产品安全的重要隐患:鳞翅目昆虫是昆虫纲害中群体最多的一个类群,其危害程度较大,在农业生产中,对鳞翅目昆虫的防治最易影响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因为其中的蛾蝶类昆虫,其幼虫对作物进行危害时的主要形式是进行卷叶危害、蛀茎危害、蛀食危害、直接食叶危害,直接施药时,防效甚差,因为药物无法进入害虫体内,内能采用内吸式的杀虫剂,而内吸剂的应用会导致农产品内的农药积累难以控制,在这方面,国家当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加大生物农药的应用,加大虫情监测力度,抓住对其卵与成虫的杀灭机会,避免幼虫进入作物内部危害。
(6)田间杂草品种减少,个别品种成长为“霸王”害草:在田间杂草分布上,根据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新编植物保护实用手册》登记,小麦田的杂草种类为:小藜、卷茎蓼、播娘蒿、看麦娘、猪毛菜、地肤、马齿苋、牛繁缕、荠、离子草、独行菜、遏菜、野燕麦,雀麦和蓟等15种,而现在实地调查发现,当前在小麦田实际达到防治需要的仅有猪殃殃和野燕麦,需要控制的有马唐和牛筋草,其他杂草无法对生产生成实质性的影响;在玉米地也是,上书登记的杂草品种有马唐、狗尾草、萹蓄、凹头苋、牛筋草、藜、葎草、苣荬菜、田旋花等9种,而现在田间调查,能达到防治指标的虽然也很多,包括:马唐、牛筋草、莎草和稗,但危害品种也明显减少,并且危害杂草的生物学分类中更趋向单科别。单子叶的禾本科杂草表现明显的竞争优势。
(7)在非侵染性病害中,自然因素造成的病害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病害变多:作物干旱、营养缺乏、冻害、渍害越来越少,因为生产力的进步,人们有足够的技术与设施来解决这些困扰,比如通过使用配方肥减少营养缺乏症,完善抗旱排涝设施减少旱害和渍害、使用用抗寒品种可以解决冻害;但人为因素的增多,会产生新的非侵染性病害,比如:化学农药施用不当会产生药害,特别是除草剂的应用,成为当前作物药害的重要表现形式;邻近化工厂的地方,时有发生污染空气、粉尘对作物造成伤害;生产生活垃圾进入土壤,造成土壤有害化学元素超标,产生病害;污染水灌溉农田,发生病害,这些成为非侵染性病害的主流,需要密切关注。
(8)农业有害生物种群规模与危害形式变动的普遍原因:环境污染加重,农业防治措施的缺失,化学防治一家独大,化学药剂对有害生物的刺激使之发生快速变异、对新环境快速适应。特别农业有害生物的防治违背了我国植保工作中“预防为主,综合防治”这个根本原则,甚至是完全颠倒的,比如,本来农业优良的农业轮作制度就是很好的农业有害生物防治措施:但在实际种植中,仅在蔬菜、中药材这些敏感性作物得到较好的实施,比如,西瓜实行五年以上轮作以减少枯萎病的发生;穿心莲实行三年以上轮作,以减少立枯病的发生,但在大宗粮食作物的种植上,还没有更好的轮作制度,比如,在临泉,持续近二十年都是小麦玉米轮作模式占绝对主体地位,这种固定模式使得某些病虫草害的繁殖得以维持更充足的繁殖源,而其他的病虫草害可能面临灭绝,这就造成物种的单一化,生态系统的线性化。个别有害生物的更容易异常暴发,变异速度加快,防治难度加大,大量施用化学农药又会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陷入恶心性循环。
(9)多措并举应对农业有害生物变动危害:在对抗农业有害生物的技术应用中,当更充分地应用农业技术措施,虽然其成本相对较高,但这是可持续的,是环保的,从长远来看还是可以推广的;在生物防治中,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有益生物,使之种群达到相应规模,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在农药的研发中,当更多地进行新型农药的研发,特别是研制生物农药制剂,比如:细菌杀虫剂、农用抗生素制剂、细菌治病剂、真菌杀虫剂、病毒杀虫剂以及昆虫病原线虫、微孢子虫杀虫剂、植物弱毒疫苗等;在提高作物抗性中,大力开展研制生产转基因抗病虫作物品种,通过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减少农药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度,
(10)结语:农业田间有害生物种群规模与危害形式的变化趋势是:大型动物变得更少、微型生物变得更多;高等动物变得更少,低等动物变得更多;有益生物比有害生物更易失去生存优势;微生物和部分害虫的危害形式从地上危害转向地下危害,从作物外部危害转向作物内部危害;杂草危害中,更接近于作物近缘的杂草更易成为重危害杂草,其余杂草则失去危害能力;微生物危害中,病原菌的变异成为种群产生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非侵性病害中,自然环境造成的因素不再重要,而人为主动因素占据主体。我们当充分重视变化趋势,利用其变化带来的利益,避免更严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