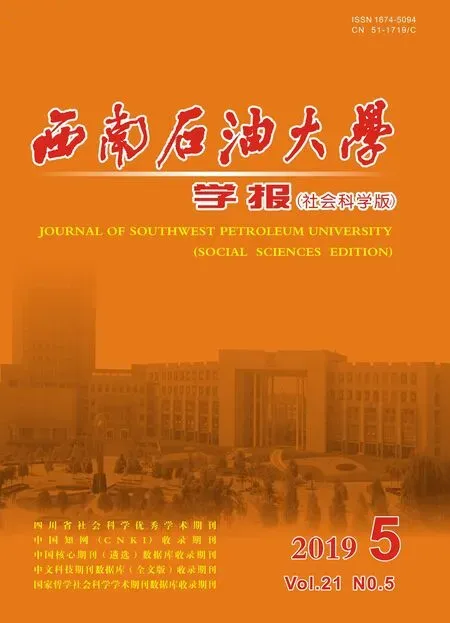回译的类型与意义探究
聂家伟
云南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引言
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有两个译本:一个是冯友兰的学生涂又光翻译的(以下简称“涂译本”),初版于1985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个是赵复三翻译的(以下简称“赵译本”),初版于2004 年①有意思的是,涂又光翻译的《中国哲学简史》,除了收录在《三松堂全集》中进行出版之外,单行本还翻印了好几次,但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而赵复三的译本则先后有新世界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江苏文艺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双语版)、中华书局、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新星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岳麓书社、文化发展出版社等多个版本。。由于两个译本各有千秋,读者在版本选择上遇到了难题,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哪个版本更好?哪个版本更忠实原作呢?许多读者认为涂译本得到冯友兰的亲自指正,并认为赵译本掺杂了许多个人的理解,故涂译本要更好一些。但是,对照英文原著,即可发现:就对中文典籍英文版的翻译处理来看,赵译本更忠实于原作。而“对中文典籍英文版的翻译”,即涉及回译。
1 回译的内涵与对象
回译不仅与语言的翻译直接相关,更涉及语言背后的文化,对其研究看似无足轻重,实际却是大有可观。
1.1 “回译”的概念界定
所谓“回译”,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将已经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文本再翻译成原语言文本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将把A 语言翻译成B 语言的过程视为通常意义上的翻译(即顺译)的话,那么,回译就是再将B 语言翻译成A 语言的过程。这种文本语言的复归,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但两者均属于回译。狭义的回译就是将已译成的B 文本再译回原原本本的A 文本的过程,亦即许多学者所称的“原文复现”或“有本回译”。广义的回译除了“原文复现”或“有本回译”之外,还指将已译成的B 语言的文化再译回A 语言文化的过程。如果说狭义的回译是“(A文本—)B 文本—A 文本”的过程,那么,广义的回译则指“(A 文化—)B 文化—A 文化”的过程。可见,狭义的回译有原语(A 文本)作参照,在翻译处理过程中,可以还原为中文原文本。而广义的回译没有原语作参照,在语言的处理上,不存在有中文原文本作为翻译的依据,只有源语(A 文化)作参照,亦即许多学者所称的“无本回译”;此外,将对原文本做出解释、描述或改写的部分再译回源语的行为也应属于广义回译范畴。鉴于本研究主要讨论中英互译,为叙述方便,笔者将中文顺译成英文的文本称为“英译文”,将英译文回译成中文的文本称为“回译文”。
无论怎样,只要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个“回”的过程,无论这个“回”指的是具体的文本(狭义的回译、原文复现、有本回译),还是抽象的文化(广义的回译、无本回译),应该都属于回译范畴。
许多人认为,译回原文本(或原文化)的回译是定向的,即回译文是在回译之前(甚至是在顺译之前)就客观存在的,是不以译者的主观因素而改变的,故许多人认为回译是轻而易举之事,回译只是落实转换、照抄中文原文(或回归原文化)而已,并称其无多大学术研究价值与意义。不过,回译绝非轻松的事,试看一下译例:
孟子(原文)——Mencius(英译文)——门修斯(回译文)
蒋介石——Chiang Kai-shek——常凯申
新月派——Crescent Moon School——月牙儿学校
亚洲四小龙——Four Asian Tigers——亚洲四小虎
例中,回译者将“孟子”“蒋介石”这种名人的姓名回译错误,看似小问题,实则显示出回译者的不专业和不负责任。而将“Crescent Moon School”(新月派)回译成“月牙儿学校”,还说徐志摩等人都是从月牙儿学校毕业的,这简直就成了天大的笑话。而“亚洲四小龙”的英译文因为并不是对应的“Four Asian Dragons”而是“Four Asian Tigers”②关于“亚洲四小龙”的翻译问题,笔者联想到师存勋《论“龙”之西译与“dragon”之汉译策略》(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17 年第1 期)一文。该文论到:“龙”虽然在中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文化寓意,但是在西方,“龙”的形象多是负面的。这很可能就是“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而不是“Four Asian Dragons”的原因。,也使回译容易出错。
由例可见,要回译到原文本(或原文化),其回译过程需要花一番苦功夫:回译时,首先需要对英译文进行直译,并尽量传达英译文的字面意义,然后对直译进行必要的修辞上的校改、调整,使其符合回译语(本文即指中文)的文化,最后再通过对该翻译进行检索,找到原文本或符合原文化的表述。
1.2 回译的对象与分类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不断增强,国外的汉学研究日渐火热,中国元素也逐渐走向世界,中国古代典籍中丰富的思想逐渐为各国学者(汉学家)所熟悉,并在他们的著作(汉学著作)中得以体现。在文化的交流、传播过程中,翻译这批学者的著作也就提上了日程,而这类翻译往往就面临中文典籍的回译问题。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有许多回译研究将对海外华人著述的翻译与对汉学著作的翻译混为一谈,将其全部纳入回译的范畴,这是不对的。也就是说,若华人所写与中国文化无关,则对其翻译不属于回译;若与中国文化有关,则相关部分的翻译就属于回译,在广义上亦可视为汉学回译。
除此之外,对于本国作者的非母语写作的翻译,也涉及回译。不过,并非用非本国语言写作的著作都值得翻译并纳入回译范畴。比如,各大高校英语专业学生所使用的《英美文学教程》,是我国专家学者用英语写作的,但对其研究就只是通常意义的翻译(或顺译)研究而已,而不能纳入回译研究之列。可见,如果用异语创作的与本国文化无关的著作,就不存在回译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语原文化写作”[1]一说,即用非本国语言写作的与本国文化有关的著作。这一概念与汉学著作截然分开了,再也不会产生歧义,并且都可以纳入到回译范畴。由此可见,回译的对象有汉学著作与异语原文化写作两类。这种划分,“以人为本”,将本国作者与外国作者都纳入其中,但又以(中国)本国文化为本位。
在处理有本回译过程中,回译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还原为中文原文本,要么难以还原为原文本;还原为原文本的回译称为“至译”,未还原为原文本的回译称为“未至译”[2]25。而无本回译则不存在至译与否的问题。
根据有本与无本之别、至译与未至译之别,无论是汉学著作还是异语原文化写作,其回译均可分为三类:有本可至译,即可以回译成原语(原文本),属于有本回译的一类;无本无至译,即“无本回译”,无原语作参照,只可回译成源语(原文化);有本难至译,即本可以回译成原语,但未能找出对应原文本,故暂且回译成源语,属于有本回译的另一类。但在具体的回译处理上,三类回译所反映出的策略却是不同的。
2 有本可至译
本是有本回译,但由于回译者的不同处理,有本可至译的回译结果通常出现三种形态:
类型一。在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引述了《庄子·齐物论》中的一段话:
“‘Since all things are one,what room is there for speech?But since I have already spoken of the one,is this not already speech?One plus speech make two.Two plus one make three.Going on from this,even the most reckoner will not be able to reach the end,and how much less able to do so are ordinary people!If proceeding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we can reach three,how much further shall we reach,if we proceed from something to something!Let us not proceed.Let us stop here.’”[3]113
涂译本的回译为:“‘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4]137-138
类型二。英译文同出于类型一,但赵译本的回译却是:“‘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这是说,既然万物都通为一,具有同一性,那还需要说什么呢?但是,既已说了一,这不是已经有言了吗?‘一’加上‘言’,便成了‘二’,‘二’再加上一,便成了三。即便有一个最善于计数的人,也无法把数目数算到尽头,何况凡人呢?由无到有,已经出现了三,如果从有到有,还能数到尽头吗?不必再数,就此停住吧。”[5]99
类型三。在《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中,刘若愚将曹丕《典论·论文》作了相应的英译,而其学生杜国清在回译成中文时,却作了这样一种处理: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In literature,the main thing is ch’i.The purity[or lightness,ch’ing]or impurity[or heaviness,cho]of this ch’i has substance,and cannot be achieved by strenuous efforts.To draw an analogy with music:though the tune may be the same and the rhythm regulated the same way,when it comes to the drawing of breath[ch’i],which will be different[from person to person],or the skillfulness or clumsiness,which depends on natural endowment,even a father cannot pass it to on his son,or an older brother to a younger brother.”[6]
类型一中,回译文直接照抄中文典籍原文本;类型二中,回译文不只是照抄了典籍原文本,而且还将英译文回译成现代汉语;类型三中,回译文照抄了典籍原文本和英译文。类型一是一种通行的回译处理手段,只不过这种回译无法显示英译者对于典籍原文的理解。对此伍晓明认为:“在这样的汉语翻译中,西方译者(冯友兰虽然不是西方译者,但道理相通——引者注)的前言、导论、简介、评述、译注、后记、附录等等皆被一一翻译,而唯一不被翻译的就是被翻译为西方语言的汉语经典本身,”这是“译而不译”,不算翻译[7]553。类型三是一种聪明的处理方法,它以“排印汉语原文和西方语言翻译的形式”[7]553作出某种补救,但这也不是翻译;此外,英译文的出现不仅有碍读者的阅读,而且对于读者来说,英译文本身并不能直接显示出英译者对于典籍原文的理解;而读者要想了解英译者对于典籍原文的理解,就必须自己亲自翻译,这就加大了读者的工作量。因此,类型三“只能为能穿梭于不同语言的学者提供某种便利”[7]553:它将典籍原文中的某些术语或概念的英译展现出来,有助于学者们更加详细地与典籍原文进行对比,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典籍原文。而类型二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处理方式,它不仅抄录典籍原文本,而且还对英译文进行了翻译,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英译者的意思。
下面这段英译文与类型一、二中冯友兰的英译文同出《庄子·齐物论》的同一段话:
“Since all things are one,how can there be anything to talk about?But since I have already said that all things are one,how can there be nothing to talk about?One and speech makes two,two and one makes three.Continuing on in this fashion,even the cleverest mathematician couldn’t keep up,how much less an ordinary person!Therefore,if in proceeding from nonbeing to being we arrive at three,how much farther we shall reach when proceeding from being to being.We need not proceed at all if we understand the mutual dependence of‘this’and‘that.’”[8]
这段话直译即为:“既然都通为一,那有待讨论的又是怎么存在的呢?但是,既已说万物都通为一,那有待讨论的无又是怎么存在的呢?‘一’和‘言’一起便成了‘二’,‘二’和‘一’一起便成了‘三’。继续用这种方式,即便是一个最聪明的数学家,也不能保持下去,何况更不如的凡人呢?因此,从无到有,能得到三,那么,当从有到有会到达什么尽头呢?如果理解‘彼’与‘此’相互依存,就不必再数下去了。”①这里的回译文,为了尽量减小与赵译本(类型二)可能存在的差异,在英文原文句子基本相同的情况下,笔者照抄了赵复三的译文。
冯友兰和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两段英文一样吗?通过对比可知,对于“巧历”的英译,两个英译文有所区别:“巧历”在这里是一个中性词且不无一定贬义色彩,梅维恒翻译的“the cleverest mathematician”有褒义色彩,而冯友兰翻译的“the most reckoner”较之梅维恒的译文更符合原文;而对于重要概念“无”“有”(“自无适有”)的英译,梅维恒的“nonbeing”和“being”则比冯友兰的“nothing”和“something”更具抽象意义,也更符合《庄子》原意。但饶是回译成现代汉语,两个回译文本却无法体现出两个英译者对于“有”“无”理解上的差别;而若将两者所有的英译文仅仅按照类型一、三那样回译成中文典籍原文,那两位学者对于中文典籍原文作何理解、理解是否有偏差也就更无从体现了。
经对比,可以看出,类型二的回译处理要比类型一、三的回译处理好。结合以上例子,在处理有本可至译的回译上,笔者建议使用类型二这种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的好处是:不仅忠实地回译了英译文,而且也将英译文的优点和缺点展现出来,更有利于让读者理解英译者的意思。正如吴万伟所言:“既列出汉语原文又能够直接译出英文的翻译,两厢对照,文化的理解和误读才可以得到彰显,由此呈现给读者一个不偏不倚的思考平台。”[9]
3 无本无至译
如果说有本回译更多涉及中文原典的翻译的话,那么无本回译则涉及中国文化的翻译。无本回译看似只是一种单向的顺译活动,并不需要至译(还原为原文本或原文化),但是其单向翻译过程却隐含着回译的活动。这里的回译是由英译文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有无、多寡所决定的。也即是说:英译文本只要与中国文化有关,其相关翻译即为无本回译。
根据无本回译的界定,可知无本回译应分为两类:一类指虽无完全对应原文本,但英译文为中文原文的解释、描述或改写;另一类则完全是文化上的回译。
类型四。在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并且无引号:
“each family should plant mulberry trees around its five-acre homestead in its own field so that its aged members may be clothed with silk.Each family should also raise fowls and pigs,so that its aged members may be nourished with meat.”[3]75
涂译本为:“各家在其私田中五亩宅基的周围,要种上桑树,这样,老年人就可以穿上丝稠了。各家还要养鸡养猪,这样,老年人就有肉吃了。”[4]91
赵译本为:“每户人家以五亩土地作为居住的房屋,房屋周围种植桑树,桑叶可以养蚕,这样,每户人家的老人可以穿上丝绸的锦衣,每户人家还要饲养生猪、家禽,这样,老人可以有肉吃。”[5]67
而叶绍丹则认为应该翻译(回译)成《孟子》的原文[10]:“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
叶绍丹的译文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孟子》原文可知,“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必要条件除了畜养“鸡豚狗彘之畜”,还得“无失其时”——这是孟子仁政思想中“使民以时”中很重要的一点;冯友兰的英译文并没有引号,可见不是直接引用,况且英译文也没有译出“无失其时”。显然,冯友兰的英译文只是转述而已,不能与《孟子》原文完全划等号。不过,涂译本、赵译本虽然并未还原为中文典籍原文,但却在文后指出了原文出处。
类型五。林语堂的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苏东坡传》),可以视为国外学者了解苏东坡的一部学术读物。目前国内至少有两个译本:一个是张振玉翻译的(以下称为“张译本”),另一个是宋碧云翻译的(以下称为“宋译本”)。虽然张振玉是翻译大家,并且翻译过林语堂众多英文书,但是,张译本和宋译本各有千秋,在回译上也都有缺点。比如该书第一章《文忠公》(Literary Patriotic Duke)中,原文有这样一句话:
“I think Li Po reached a greater height of sublimity and Tu Fu reached a greater stature in his total impressions as a poet great by all the standards of greatness of poetry—freshness,naturalness,technical skill,and compassion.”[11]3
张译本为:“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12]4而宋译本则是这样的:“以诗词伟大的标准——清新、自然、技巧和同情心——来说,我认为李白已达到更卓越的成就,杜甫更能给人大诗圣的完整印象。”[13]28初看两文,似乎张译本更文雅,其“工巧、悲天悯人”要比“技巧和同情心”译得更符合文化语境——一般文学史上,认为杜甫诗歌的特殊风格即是“沉郁顿挫”,而“沉郁”“顿挫”正对应地涵盖了原文中所说的“悲天悯人”“工巧”。但是,张译本的译文由于语序的问题而犯了文学常识的错误(这不是林语堂本人的错误):他将本属于李白诗“清新、自然”的风格特点也归之于杜甫,则与史不符。后文有一句话:“At the time of Su Tangpo’s youth there was a brilliant galaxy of scholars gathered at the court of the Chinese emperor.”[11]6张译本为:“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12]7而宋译本则是:“苏东坡年青的时候,有一大群卓越的学者围在皇帝朝中”[13]34。一比较,这句话的翻译,两者高下立判:“学者”是一个西方词汇,放在这里是不符合当时文化语境的,而“淳儒贤臣”则显得文雅多了。抛开其他因素,两相比较,张译本更符合中文的文化语境。
总之,此类回译文在回译过程中,应尽力将原本属于回译文本所属文化的英译文回译成符合回译文所属的文化语境。类型四、五的回译均无本可依,不能达到至译,也不需要至译。不过类型四的回译,需要考虑中文原文本的文本语境,而类型五的回译,则要考虑文化语境。换句话说,“无本回译的基本特征要求翻译实践中,即原著在返回汉语时应朝向中国文化文本前进,最大限度的再现该文本”[14]。
综上所言,对于无本无至译的回译,回译文可以直接翻译英译文,但在翻译过程中要切合被转述或解释的中文典籍原文或要考虑回译语的文化语境。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加上备注或注释,指出转述或解释中文典籍原文的出处,正如涂译本、赵译本所作的那样。
4 有本难至译
有本难至译的现象往往出现在汉学著作的翻译中,由于中文原文(尤其是中文典籍)的翻译并非出自作者本人之手,往往是转述(或转引)他人翻译文本,而在注释中并未作相关说明,故回译难考其究。更有甚者,其所转述(转引)的英译文已经作了某些个人的理解或阐释,则更增加了回译的难度,更难以做到至译。不过,这种类型的译文并非以一种类型出现。
类型六。张宁在《古籍回译的理念和方法》一文中,针对有本回译难以找到典籍原文的现象,提出一种“整旧如旧”的翻译策略,即:在翻译中文典籍的英译文时,尽量考量典籍当时的语气,模仿当时的语气或行文风格进行回译。“这就要求译者在遣词造句上尽量要古雅一点,要整旧如旧。这样才能保存原作的风貌,让读者领略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和风味。”[15]他在翻译下面这段文字时,即采用了上述策略:
“China’s most serious problem is that only the scholars are educated.The soldiers,farmers,workers,and merchants have all been kept on the margins of the system of education.——“Lun Puji Jiaoyu”Shibao,Jan 26,1906”
根据英文可知,这段文字引述的是1906 年1 月26 日《时报》上的《论普及教育》,但由于张宁没能检索到原文,即将其“整旧如旧”译为:“中国之痼疾,在于唯士人为受过一定教育之阶层,而农、工、商、军士均无缘于教育也。”[15]这类回译是在没有找到典籍原文的基础上,以模仿当时文章的语气翻译而成的。
笔者根据张宁的翻译以及上文的文章出处,最后在1906 年2 月19 日的《时报》上查找到原话:“中国之患,莫大于唯士有学,而兵农工商均屏诸学界之外。”[16]原来,英译作者在引述过程中,将阴历的正月二十六日(实为阳历2 月19 日)写成阳历“1 月26 日”,这样就增加了检索的难度,使回译文难以达到至译。
类型七。中文版《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 世纪》①除了下文提到的两处外,该书的第56 页、97-98 页、150-151 页、151 页、159 页等多处也属于“无本无至译”类型。中,有这样一段译文:“既然你们已经臣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产品中获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50 盎司的白银、8 万匹丝绸和40 万担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17]261从文章注释和译文可知,这段文字大概是出自某部古代典籍。由于译者并未找到英译文对应的典籍原文,所以直接将英译文翻译过来。不过笔者通过关键词检索,发现这段文字应该出自《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原文如下:
“‘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因奏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
此类回译文是在没有找到对应中文典籍原文的情况下直接将英译文回译成现代汉语。而该书后文中所说的“‘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对诗人来说已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17]264,经多次检索显示,这位明朝学者是薛瑄,他的原话出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一》:“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虽然上述几个例子均检索到了中文典籍原文,但却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检索的过程中,无法检索到中文典籍原文时,那回译文该如何处理呢?
1993 年,欧阳昱曾将当时《亚洲华文作家》杂志主编林焕彰的一首小诗翻译为英文。小诗原题叫“《人生》:‘这世界,不是我的/我能争什么?/这世界,是我的/我又何必去争?’”欧阳昱的英译文的题目叫“Life:‘“This world is not mine/what do I fight for?/this world is mine/why would I fight’”但欧阳昱翻译完后,只保留了自己的英译文。时隔多年之后,当有编辑要出版他的集子,看中他的这首译作时,欧阳昱试图通过英译文来找作者林焕彰要原诗时,林焕彰已经不记得发表过这首诗。直到欧阳昱将他的英译文再回译成中文时,林焕彰才记起来,并将原诗发给欧阳昱。欧阳昱将其回译为“《生活》‘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的/我何必要争什么?/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我的/我干嘛要争什么?’”尽管欧阳昱感叹,林焕彰原诗“更干脆有力,简明扼要,而我的英文则似乎有点小啰嗦了”,但毕竟林焕彰是靠欧阳昱的回译文才回想起自己的原诗(原文本)的[18]。但若只懂一门语言,其回译过程该是何等艰难啊!
当然,有本回译最理想的结果是至译,但是,有时候因为主客观原因,不能做到至译。那么,权宜之计即是将英译文直接译成现代汉语,但需在回译文后作相应注释说明,以便于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找到中文典籍原文。
5 回译的意义再思考
在我国,回译行为自古有之,最早可追溯至唐玄奘回译印度佛教哲理著作《大乘起信论》。但是,我国对于回译的研究却很晚,国内有关回译的真正研究要晚至21 世纪初。而对其意义的研究,绝大多数则聚焦于两点:(1)将回译作为检验译文和翻译教学的一种手段,如张春柏的《还原翻译练习——一种行之有效的翻译练习方法》(1997 年),管雪兰、李思龙的《论回译性与翻译》(2002 年),肖水来的《回译的误区》(2004 年),段冬升的《回译的理性分析》(2016 年)等文;(2)将回译作为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的辅助工具,如王宏印的《〈红楼梦〉回目辞趣两种英译的比较研究》(2002 年)一文,未提“回译”一词,作者也未意识到其研究正是利用回译来比较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夫妇与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在翻译《红楼梦》回目上的一些不同处理。而有的学者更是认为回译研究的意义在于“便于读者理解和检索原文,方便他们借鉴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对研究工作有所裨益”[19],仅仅把回译当作一种工具而已,还是低估了回译的意义。而国内以“回译”为名的三部著作,辜鸿铭著写、王京涛译注的《西播〈论语〉回译:辜鸿铭英译〈论语〉详释》(2013 年)、江慧敏的《京华旧事,译坛烟云——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 无本回译研究》(2016 年)及其博士论文均未谈及回译的意义,而王正良的《回译研究》(2007 年,其博士论文)虽然认为回译有“检验文化传播的效果”和“激活淡忘的文化成果”等文化传播的意义[2]125-131,但其论述略显单薄、缺乏力度。不过,有的学者提出的“回译经过长途跋涉、一路颠簸,经受了异域文化的排斥与接纳、冲突与融合、传播与洗礼,依然能在什么方面还原多少比例的中国本土文化”[20]的疑问,却引起了大家的思考。
同时,对于汉学著作的翻译(回译),许多研究者认为回译的结果既然是还原,亦即许多学者口中的“原文再现”,那么,回译“返璞归真最是信”,否则“中文译者再用现代汉语译回来,转译之间,原文的韵味和情感色彩无形中几乎丧失殆尽”[21]。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在回译过程中,为了力求译文的流畅、简洁、清晰、直接,符合译入语的习惯,应该要化解歧义、消除啰嗦的废话、纠正错误[22]。
其实,无论是顺译,还是回译,都应被视为一种文化馈赠。也就是说,在翻译中文典籍时,汉学家(西方文化)在接受中国文化的馈赠,但在回译这些汉学著作时,中国文化又反过来接受西方文化所给予的馈赠。如此往复,馈赠者与接受者身份不断互换,在接受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馈赠的同时,也从外来文化眼中看到本土文化,从而审视本土文化,丰富和扩展我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进而发现本土文化的价值[7]552-553。
翻译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比较原语与译语两个国家语言上的差别,而更多的是比较文化上的差别,以及两个国家在(文化)沟通交流之间的隔阂与默契。就顺译而言,对于译入国来讲,也就是要通过译入文本来吸收译出国的文化,通过“引进来”(“拿来主义”)而发展本国文化,壮大本国实力。反之,回译的目的则是通过回译文,了解本国文化在国外怎么传播,以及在传播的过程中,哪些文化元素被“激活”、哪些文化元素被“遮蔽”,从而在“回望”本国文化的同时,使本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如果仅仅“原文再现”或“返璞归真”,西方翻译中的独到之处固然消失了,但作者的风格也模糊了,甚至连英译文本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可能消失殆尽了。如此回译,貌似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实则又回到了留恋老祖宗与故步自封的地步,而西方文化给予中国文化的馈赠也就荡然无存了。
但是,我们又发现:当我们翻译(或回译)汉学著作,接受来自西方文化的馈赠、“拿来”并吸收时,似乎缺少了本土文化给予西方文化馈赠这样一个文化“走出去”的环节。要知道,汉学家固然是用外语写作汉学著作,他们在进行写作或翻译时,似乎在接受中国文化的馈赠,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汉学家在著述时,他们是在以他们本土文化(或西方文化)的视角审视着中国文化,我们在将这些汉学著作翻译过来时,我们仅仅接受了他们对于我们的馈赠,而并没有给予馈赠。那么,中国文化想“走出去”,取得文化自信,给予西方文化馈赠,就应该提倡异语原文化写作。不同于汉学著作的“汉语—西方语言—汉语”的馈赠模式,异语原文化写作可以直接是西方语言的写作,也可以是对于中国本土经典著作的西译(“汉语—西方语言”)。因为只有本土作家的异语原文化写作(包括翻译),才能将本土文化的精髓传达到西方国家。唯有如此,西方文化才能接触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从而在他们的扬弃中,接受中国文化的馈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务之急就是国家相关文化部门鼓励异语原文化写作。当然,这里已经包括了对于本土经典著作的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