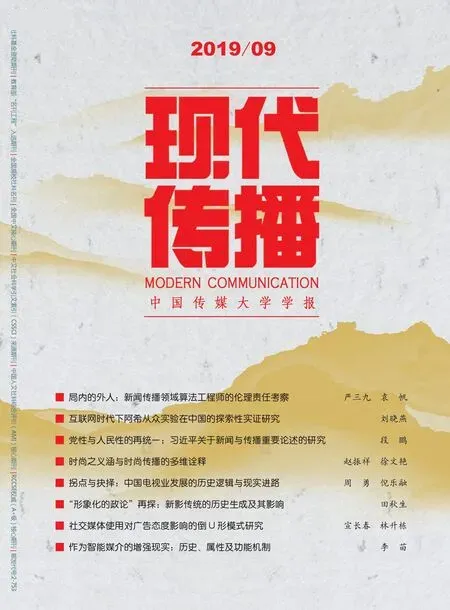海洋传播刍议
■ 马克秀
海洋孕育了人类的文明。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探索海洋的民族之一,中国也是世界航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伴随着海洋大科学的迅速发展,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对海洋的研究都在逐步深入,而基于传播学视角关注海洋议题的学术研究和传播实践都相对滞后。理解人类文明的进程、建立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关系,都需要人类对海洋有一定的认知。但是,由于大多数人难以与海洋进行亲密接触,从而限制了人们对海洋的认知,而突破该限制的方式之一则是加强海洋信息的媒介化传播。
当前,声呐技术、深海摄像技术、AR/VR、海洋Argo计划浮标观测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物理层面上保障了“透明海洋”的实现。同时,在新媒介域中,海洋传播在载体形式、扩散方式及制度等方面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在此背景下,传播研究如何从根据自身学科特性,进行海洋传播实践探索,并思考海洋传播的理论模式,改变人们对海洋的信息接触、思维方式、信仰理念及行为方式,以反哺海洋社会的发展,成为传播研究的新任务之一。
一、追根溯源:海洋传播研究的本体论
我国海洋传播实践自古就有且源远流长,但从理论角度上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国内学者对海洋传播探讨多集中于现代海洋媒介传播体系的构建、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的战略定位、区域海洋文化体系的建构、大众传媒与国民海洋观教育、中国历史上海洋知识的传播等方面。目前研究主题较为分散,学术共同体还未形成。这归因于我们对海洋传播研究的本体论还未进行自觉反思,而深层次的、重要的理论问题都根源于对本体的认识之中。①因此,海洋传播研究如何从实践与理论方面强调其自身特性,从而与海洋社会学、海洋经济学、海洋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相区别,是海洋传播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概念范畴
进行海洋传播研究,首先要厘清“海洋”的概念。“海洋”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的语汇。在不同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中,海洋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从空间上来说,海洋是相对于陆地的一个概念范畴;从功能上来说,海洋不只是陆地之间的间隔,它本身是经济与文化的活力之源与联系纽带;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生命起源于海洋,海洋生命与陆地生命有着紧密关联;而在文明价值的层面上,人类文明的诞生及其发展也依赖于海洋。
在对海洋传播的界定上,静恩英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海洋传播的概念,她从场域理论出发,指出“场域视野下的海洋传播涵盖海洋场域及海洋场域与其他场域间的信息传递活动。”②她还强调“海洋传播的提出并非以地理空间区隔传播学研究,而是传播研究在应用领域的拓展,是对一个被忽略的领域的明确关照。”③毕研韬、卢瑄、焦昆指出“海洋传播涵盖海洋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的传播等,其主要功能有四:互鉴文明、塑造共识、协调政策与行动、减少敌意与阻力,核心目标是提升我方公信度与合法性。”④郑保卫、程佳琳、莫茜等学者探讨的都是“海洋文化传播”的概念。另外,李思屈从构建现代海洋媒介传播体系的视角出发,指出我国当前“海洋传播意识薄弱、海洋传播思维缺乏、海洋传播专业性不强、海洋传播理论研究不够”。陆小华从新闻报道的实践出发,指出:一个大国的传媒,不管其是“大”传媒,还是“小”传媒,都需要以其远见卓识去帮助人们从战略层面认识海洋、认识海权,以提供足够的信息帮助人们了解与理解为什么及如何去经略海洋、利用海洋,以其远见卓识所形成的舆论影响力去推动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并对世界海洋事业做出贡献。⑤
海洋传播是海洋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从上述学者们对“海洋传播”的界定来看,不同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试图解释:海洋传播是什么?海洋传播包含哪些内容?尽管还没形成统一的、相对成熟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从海洋文明、国家海洋战略及公众日常生活层面,媒体报道都需要关涉到海洋议题的信息。
鉴于此,我认为海洋传播指的是将海洋相关的元素或议题通过媒介传递给公众,建构公众对海洋的全面认知,以反哺海洋社会的发展,促进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关系。针对该领域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海洋传播研究,它是一个多维的复杂体系,是以传播学和海洋大科学为基础的交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体来说,海洋传播研究是以海洋议题的媒体呈现为研究对象,关注领域包括海洋战略传播、海洋科普传播、海洋生态文明传播、海洋文化传播如区域海洋文化、海洋名城建设、岛屿旅游文化、渔村社会文化、海洋美食文化、妈祖文化、海军文化、海产品经济文化、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播等方向,涉及到的媒体载体包含图书、报纸、电视、广播、纪录片、动漫以及微博、微信、客户端App等新媒体形式。
(二)研究前提
传播指人类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目的是通过中介化的信息传递与他人共享信息。人类需要参与和共享海洋议题的信息是海洋传播研究的前提条件。
首先,维护好人类与海洋的关系,需要海洋信息传播实践的介入。海洋作为“蓝色国土”,⑥是人类生存发展新的地域空间。人类与海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由于大多数人不能直接接触海洋,对海洋的了解依赖媒体的海洋信息传播。借助于媒介,海洋信息可以实现传播范围更广、传播内容多元、传播过程的可持续等效果。
其次,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促进了“透明海洋”的实现,这不仅让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就能深度认知海洋,也让海洋信息报道有了可靠的信源。2004年国家“863”计划海洋资源技术开发主题中的深海数字摄像技术获重大突破并通过验收,⑦该技术让我国在2005年实现了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的数字化传输,也为海洋类电视剧、纪录片等的拍摄奠定了技术基础。海洋科学技术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让海洋议题的媒体呈现更为生动、准确和有效。
最后,人类与海洋互动产生的社会性问题需要传播的介入。伴随着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对海洋开发深入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以海洋环境问题、海洋权益问题等为例,它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大国际问题。尤其是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保护方面,传播的介入可以让更多公众了解并参与其中。
(三)研究视角
海洋传播研究属于应用传播的范畴,但其发展仍需要从理论建设出发,通过形成稳定成熟的概念体系,确定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从而确保该研究领域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1.全球化发展的视角
海洋不仅是重要的全球文明交流通道,更是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中,首次提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能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实际上是安危与共。”作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海洋传播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始终具备全球发展的意识。
2.区域共同体的视角
因水域资源、气候特点、沿海社会文化习俗及海洋发展的相关制度等各有异同,海洋传播又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点。对于沿海区域来说,探讨海洋传播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是海洋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海洋文化本身具有“重商性”“开放性”“外向性”等特点,其中关于海洋旅游、美食等议题的传播如何开展,是海洋传播研究需要关涉到的亚文化传播内容。
3.战略传播的需求
在国际传播层面,“海洋国土”的概念对海洋传播研究提出了战略传播的要求。“谁更早意识到新世纪海洋作为人类发展新空间的重要性,谁就能抢得海洋经济发展的先机和国家强大的优势地位。”⑧在国内传播层面,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强国、海洋强省建设等战略的推进也需要媒体承担宣传的义务,坚持政治正确和技术正确。因此,依托媒体资源和传播新业态向国内外受众“讲好海洋故事”是海洋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
(四)研究的学科贡献
1.海洋传播研究拓展了传播学研究领域的边界
传播学在海洋议题上的探索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近现代媒介的发源地为沿海城市,它是大航海时代市场开拓、商品贸易催生的产物,但是人类的陆地生存发展史,让媒体传播深深烙下陆地思维的印记。即使是沿海城市的大众媒介,也常常忽略了海洋这一特定地理区域定位,没有充分利用海洋资源体现海洋特色。⑨因此,海洋传播研究的贡献之一是拓宽传播学学科的研究视野,增强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者及实践者对海洋议题的重视,进而构建社会公众对海洋的深度认知。
2.海洋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非陆地中心主义的视角
林肯·佩恩在《海洋与文明》中写道“航海事业如何扩大共享了某种知识的贸易区域,语言、宗教和法律的跨海传播如何便利了区域间的联系……”⑩海洋一直处在人类传播活动发展的进程中,从为了跨越海洋的阻隔而产生的短波通讯,到各国海底光缆建设工程的推进;从殖民与大规模远距离的海上航行带来的文化移植与全球贸易,到集装箱引发的全球海上贸易,都是直接聚焦于海洋元素的传播行为,“我们只是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地球图景称之为陆地图景,而忘记了我们还可以把它叫做海洋图景”。海洋传播研究打破了陆地中心主义的窠臼,为传播学提供了一个非陆地中心主义的视角。
3.海洋传播研究在方法上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海洋传播研究重视历史研究法,要求研究者以“宏大视角”和“全球思维”思考文明史以及传播和文明史的关系。同时,海洋传播研究经常用“采风”的方式,用人类学的方法去收集、观察和分析区域海洋文化传播。最后,海洋传播研究还需要遵循科学传播的规律,要求研究者与海洋科学家保持紧密关系,采用包括日记法、实验室观察法等进行研究。
二、历史回顾:国内外海洋传播研究的历史演进
(一)国外海洋传播研究历程回顾
国外的海洋传播研究主要分布在海洋科普、海洋公共关系以及海洋教育的框架体系中。在海洋教育领域,很多国家除了课堂的正规教育外,由媒介参与的海洋传播也是海洋教育体系中非正规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海洋科普报道、海洋科学家的媒介报道、海洋科学的电视节目等。海洋科学知识的公众传播被称作海洋科学传播(Mar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强调的是如何通过媒体传播提升公众海洋素养(Ocean Literacy)。同时,与海洋传播关系紧密、涉及范围更广的一个概念是蓝色传播(Blue Communication),后者包含气候传播主题。
1.国外海洋传播研究的孕育期(1948—1979年)
从1948年美国科学促进会成立开始到1980年,国外学者对海洋科学传播的关注处于孕育期。其中成立于1948年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对公众理解科学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推进。“通过媒体中科学技术覆盖率的提高来增强对科学的理解”是该促进会的目标之一,实际上该项目通常被研究生们当作试探改行到科学新闻界工作的机会。1972年由博格斯(Elisabeth Mann Borgese)教授倡导的非政府、非盈利性国际组织国际海洋学院(International Ocean Institute)在马耳他成立,致力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教育和培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海洋能力建设,开创了海洋综合管理国际培训的先河。这一阶段海洋传播研究逐渐成为科学传播研究的内容之一,学者们提出来的命题集中在“公众如何理解海洋”“海洋教育如何展开”等方面。
2.国外海洋传播研究的萌芽期(1980-2005年)
在萌芽期,除了国际海洋学院在不同国家展开海洋培训外,1984年澳大利亚成立了海洋教育学会,同年美国政府制定了面向公众科学教育的“2061计划”,美国媒体面向公众层面进行科学传播的程度逐步加深、范围也逐步扩大。该计划要求公众科学教育中媒体传播活动占据39%的比例,通过科技新闻、网络游戏、虚拟现实、动画、漫画、科幻、故事、音频和视频节目等进行传播。与此同时,科研机构、院校和实验室经常向社会开放,共同推动海洋议题的公众普及。自2000年起,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海洋科学新闻工作坊(The WHOI Ocean Science Journalism Fellowship)项目开始设立科学新闻奖学金,向科学记者介绍广泛意义上的海洋学和海洋工程。该项目通过研讨会、实验室访问和简短的实地考察,让海洋科学新闻研究员获悉最新海洋研究成果,增强了媒体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2005年美国海洋教育者协会制定“海洋素养”框架和内涵,指出“Ocean literacy i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ocean’s influence on you—and your influence on the ocean”。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如何通过媒体进行战略传播以提升公众海洋素养的海洋传播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媒体如何与海洋科研院所、高校、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成为媒介组织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3.国外海洋传播研究的发展期(2006-至今)
这一阶段有影响力的海洋主题作品以海洋主题纪录片为主,例如雅克·贝汉的《海洋Océans》(2009)、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向深海出发》(2009)及《蓝色星球II》(2017)等作品,其影响范围广、涉猎议题宽泛,并且符合受众的信息获取习惯,对公众的海洋认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一阶段国外海洋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涉海传播的议题多元化,例如讨论如何进行蓝色海洋传播、海洋公民意识提升、海洋灾害报道、海洋素养和海洋社会科学等;其次是海洋传播研究的组织机构逐渐增多。2002年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科学中心的劳伦斯科学馆(The Lawrence Hall of Science)开始创设海洋传播课程(Communicating Ocean Science Course),包括汉普敦大学佛尼亚水族馆、俄勒冈州立大学哈特菲尔德海洋科学中心、罗格斯大学自由科学中心、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南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等七个合作方。该课程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由科学家和一名正式教育工作者合作教授,旨在向未来的科学教育家介绍如何向普通公众传授海洋科学知识,并为学生们提供海洋科学传播的实践机会,以及如何与公众交流他们的科学知识。具有代表性的机构还有葡萄牙欧洲海洋传播委员会(European Marine Board Communications Panel)组建的海洋传播(Commocean)机构,该机构从2014年起每两年组织一次海洋科学传播会议(Mar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来自世界各国从事海洋科学传播的人员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有效地进行海洋传播。2016年该机构推出了海洋科学传播工作坊(Ocean Science Communication Tools Workshop)的课程;最后是基于新媒体的海洋传播实践逐渐增多,随之进行的学术探讨也逐渐增多,例如2009年日本举办的海洋社会学会议探讨了海洋科学的传播问题,提出使用博客、社交网络以及面对面讨论等多种海洋科学传播方式,并指出新媒体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海洋科学问题。
(二)国内海洋传播研究历程回顾
以学术研究机构及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为标志,我国海洋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孕育期(1958-1997年)、萌芽期(1998-2012年)、发展期(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1997年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追溯到1958年海洋综合调查办公室的创办,属于海洋传播研究的孕育阶段。此后,萌芽期的海洋传播研究主要表现在学术论文、论著及学术研讨会的陆续出现。2012年后,随着海洋强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部署与推进,各高校海洋文化研究机构以及学术团体不断设立,将海洋传播研究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1.我国海洋传播研究的孕育期(1958—1997年)
孕育期的海洋传播实践与海洋信息领域的发展紧密相关。海洋信息情报研究经历了海洋综合调查办公室创办(1958年)、海洋文献馆建立(1964年)、《海洋信息》期刊创办(1986年)、《海洋预报》电视节目播出(1986年)、《中国海洋报》创刊(1989年)、首家气象广播台舟山海洋气象广播台开播(1995年)等一系列重要发展历程,这种基于电报、书籍、报纸、广播和早期电视栏目的海洋传播实践促进了海洋信息情报研究,也逐渐孕育了我国海洋传播的研究。
处在孕育期的海洋传播研究在内容上有两个侧重点。首先是注重宣传研究,主要涉及如何进行海洋法律、海洋保护等信息的宣传,例如《继续努力挖掘、整理、宣传中国的海洋文化》等文章发表在期刊和报纸上;其次是关注海洋文学作品、渔歌等海洋文化载体的影响力,代表作是叶林在《音乐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渔歌:广东民歌海洋里的瑰宝》。此外,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团队1996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开设“海洋文化研究”专栏,1997年正式成立海洋文化研究所。该研究所在海洋文化传播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可以说,海洋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海洋传播研究从孕育期走向萌芽期。
2.我国海洋传播研究的萌芽期(1998-2012年)
这一阶段海洋传播实践的重点是海洋信息的宣传。1998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委员会规约的“国际海洋年”,这一年海洋宣传的文章数量较往年大幅度增多,2011年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的成立直接推进了海洋传播实践活动的开展。因此,如何通过各种媒介形式进行有效的海洋宣传也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海洋传播研究的关注重点。
一方面是我国高校开始逐渐建立海洋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包括福建省东海海洋研究院(2005年)、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中心(2010年)等。依托海洋研究机构,2007年福建省举办了首届海洋文化研讨会,发表了一系列海洋文化研究的论文,如《夏曼·蓝波安与海洋文化传播》《福建海洋文化与佛教的传播》等,促进了海洋文化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另一方面是海洋传播研究的研究主题开始逐渐丰富。除了区域海洋文化建设外,海洋新闻、海洋科普教育的媒介化发展等议题也逐渐被学者们重视。在海洋新闻研究主题上,《中国记者》2007年第6期开设了海洋新闻研究的专栏,刊发了《一块亟待“开发”的报道领域:海洋新闻现状、特点及热点领域解析》《海洋新闻的任务、问题与对策》《海洋新闻报道的理念及原则》《欧美海洋新闻的语境和特点》《利用海洋新闻打造特色媒体》《海洋石油报道的三个意识》等论文,此外还有《海洋环境新闻传播模式及关联问题探究:基于拉斯韦尔传播过程模式的分析》等文章关注了海洋环境新闻的报道问题。在海洋科普教育的媒介化发展主题上,出现了《大众传媒的传播盲点:国民海洋观教育》《国际海洋科普模式演进及其传播方法比较》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出现促进了人们思考海洋社会与传媒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海洋科学传播的必要性。
3.我国海洋传播研究的发展期(2013-至今)
2012年以后,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海洋传播的实践活动愈发丰富。这一阶段我国少数电视台开始设立海洋频道,并在海洋纪录片、主题电视剧上也产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同时结合新媒体技术如VR直播、抖音短视频等的海洋新媒体实践丰富了海洋传播的传播内容,也为海洋传播实践开辟了新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模式。
在理论进展方面,首先是高校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等综合性和专题性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不断创建,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专题的海洋文化论坛与研讨会频繁举办,涉及海洋文化传播的学术探讨越来越多。2013年浙江大学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成立,2014年由该中心承办的“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产业”国际学术会议,围绕“海洋文化传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洋文化产业与海洋经济发展、数字媒体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论题展开讨论。2018年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与青岛新闻网联合筹建海洋大数据与新媒体研究中心,在海洋类热点事件、海洋大数据舆情、海洋新媒体指数以及一带一路舆情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传播研究领域重视并提倡发展海洋传播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郑保卫、李杰、张君昌、静恩英等。他们提出了海洋传播研究的几个重要主题。首先是海洋战略传播,代表性文章郑保卫教授的《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的战略定位与策略思考》《大众传媒在海洋维权中的使命与责任》等;其次是海洋媒介体系构建研究,代表性文章有浙江大学李杰的《论现代海洋媒介传播体系的构建:以提升浙江媒介海洋传播力为例》、张君昌《加快面向“海洋世纪”的新闻传播研究》、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静恩英的《海洋传播建构的必要性及其研究视域》、郑宇博士论文《中国海洋意识建构的大众传播策略研究》等文章;再次是地方海洋文化的研究,例如《福建海洋文化与佛教的传播》《闽台海洋文化的建构与传播》等文章;最后是探讨媒体如何讲好海洋故事,如《海洋强国梦愿景下我国地方媒体传播策略研究:以“湛江日报”为例》《从陆地传媒到海洋传媒:多重视角看危机事件报道的基本原则与思路拓展》等文章。
“媒介技术重新结构了社会力量的组合方式,决定这个时代的主流媒体的外形和配置”,媒介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海洋传播的实践,传播学者开始将研究视域介入到海洋议题上,并针对如何建立海洋传播媒介体系、海洋争端的新闻报道以及海洋电视传播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传播学学科中海洋传播研究也开始逐渐建构了自己的研究空间。但相较于成熟的研究领域及学科发展而言,当前海洋传播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是海洋传播研究在传播学科领域中的受重视程度仍然不够,还需要大量的学者关注该领域,并从学术活动组织、学术成果发表、学术共同体建设等方面积极促进海洋传播研究的发展;其次,海洋传播的研究属于交叉研究领域,研究者需要结合海洋自然科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生物学、海洋人类学以及海洋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采用定量与定性、人文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最后,海洋传播研究的议题丰富程度还需要加强。尤其是自媒体时代新闻形态与宣传方式已经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例如青岛电视台“蓝睛看海洋”利用全媒体手段通过网络向公众进行海洋传播、塞舌尔总统海底124米开直播呼吁公众保护海洋、美国蒙特利湾水族馆的VR海洋直播等,将海洋议题置于新媒体的媒介域中实现了有效传播。这些新媒体实践将引发业界和学界共同思考海洋传播的模式及内容生产机制等问题。
三、未来展望:海洋传播研究的主体性分析
在建构中国海洋传播研究的主体性上,笔者认为,首先,海洋传播研究必须体现传播学的学科特性。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需要源自社会的认同,并为社会实践提供更多的指导、帮助和服务,才能持续彰显它的社会价值。海洋传播研究作为传播研究的应用领域,其意义在于与日常海洋传播实践展开对话;其次,海洋传播是海洋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海洋战略传播、海洋文化传播、海洋意识与生态传播等基础概念是围绕这一核心概念构建起来的,其中海洋传播的研究对象应是人们对海洋的传播实践行为;最后,围绕人类进行的海洋传播实践,海洋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海洋议题的传播实践及理论探讨。因此,起步阶段的海洋传播研究要以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对人类的海洋传播实践活动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以拉斯韦尔5W模式为框架,再结合“社会情境”和“传播史”这两个重要变量,笔者尝试勾勒海洋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一)海洋传播的传者、受者研究
海洋传播研究的重要性首先是如何建构人们其关于海洋的认知,具体而言,是谁来建构、谁来接收的问题。传受双方是海洋传播研究的主体,也是理解海洋传播问题的基本起点。所以,海洋传播研究首先要对传播主体和受众进行分析。
在海洋传播传者研究层面,当前涉海信息的传播主体以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及海洋科学家为主,海洋科学新闻记者较少,我们需要考证是否需要制度化地培养海洋传播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形成何种制度的问题。同时,从事海洋新闻报道的媒体主要有《中国海洋报》《海洋世界》及中国海洋新闻网等,其中综合媒体机构涉海新闻报道较少,是否应该增加综合媒体的海洋传播内容?媒体如何与涉海的海洋科普基地、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等公共文化资源,以及向社会开放的海洋实验室、科技馆、样品馆和科考船等平台进行连接,共同传播海洋信息?
在海洋传播的受众研究层面,除了面向海洋科学家、海军、渔民、海洋旅游服务者、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受众的传播外,海洋传播对内需要面向普通公众传播海洋知识以提升海洋素养,对外需要面向其他国家受众,正确进行对外的海洋权益表达,承担海洋维权中的使命与责任。
(二)海洋传播内容研究
海洋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涉及哪几大领域?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媒体技术的更新,海洋传播的内容及其载体将发生哪些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海洋传播研究在内容及其载体上存在哪些差异?以行业领域作为划分标准,我国海洋传播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部分,形成海洋政治及军事新闻报道、海洋经济新闻报道、海洋文化新闻报道、海洋环境新闻报道、海洋新闻中“人”的报道等五大部分。以目标群体作为划分标准,我国海洋传播的内容可包含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个层面是媒体需要建构面向全民的海洋传播内容,营造全社会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氛围。这其中包括建构我国海洋素养水平的指标体系,对人们需要认知的基础海洋知识做出说明,在此基础上对海军文化、海洋生态文明、海洋安全知识、海洋美食文化、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洋妈祖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海洋文化产业等进行传播。此外,还要考虑媒体应以何种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普通受众进行海洋传播。
第二个层面是面向青少年及涉海人群的传播内容。这一层面的海洋传播内容包括专业的海洋科学知识,及其他丰富的海洋文化。例如海洋物质文化是指人们开拓、利用、维护海洋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海洋实物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如渔网、渔船等。涉海制度研究是指开拓和维护海洋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协调人与海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各种制度,如《海洋环境保护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涉海行为研究是指人们在海洋开发、利用、保护过程中所贡献的、有价值的且能够促进海洋文明、文化以及未来海洋发展的经验及创造性活动,如海洋捕捞与养殖、海洋资源开采等。在实际传播实践中,传播主体如果可以实现从专业化传播到科学普及传播,则意义更为重大。
第三个层面是面向国际受众的海洋传播。研究海洋主权的对外传播无疑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已有研究中,国内学者发表《领土争端报道的对外传播要点:以“钓鱼岛事件”为例》《钓鱼岛争端中社会舆论传播研究》等文章。当然,这要求传播主体对国外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进行深入分析,需要遵循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接收规律,进行海权信息传播、海洋跨文化传播,与受众共同重构、记忆和应用信息。
(三)海洋传播的媒介与效果研究
媒介与效果研究有海洋传播媒介研究与海洋传播效果研究两个组成部分,具体包括:哪些媒体在海洋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各自的角色和功能是什么?不同媒介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的策略是什么?
在媒介分析上,我们需要关注报纸、电视、期刊、广播以及互联网新媒体(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等)等不同媒介对海洋信息的传播,关注媒介域的转换对海洋信息传播带来的影响。例如针对报纸的分析方面,需要关注专业性报纸《中国海洋报》、地方媒体如《湛江日报》以及综合媒体如《人民日报》的海洋传播策略。在期刊杂志方面,我们需要关注中小学订阅的海洋类专业杂志,其内容策划与传播形式如何。涉及海洋文学作品的创作,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海洋题材作品,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被重新提炼和传播。同时,正如美国的海洋文学被当成一个产业来发展,国内文学领域是否也应该对海洋体裁的文学作品进行更多的关注,这同样需要媒体的引导和国家制度的扶持。在电视节目分析方面,也有一些案例值得研究,例如2018年7月份青岛市国家海洋重点实验室举办的夏令营节目,同时与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共同主办了《我是海洋科学演说家》节目,吸引全国中小学的教师、学生及家长参与到海洋知识的传播中。
关于海洋的视觉传播上,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海洋主题纪录片影响很大。视觉传播还可以采用海洋主题摄影展、海洋文化艺术展、海洋虚拟博物馆等方式进行。例如海洋虚拟博物馆可以结合VR、AR等虚拟技术实现辅助的视觉沉浸式体验,同时结合海洋动漫、海洋主题电子游戏,在媒介的选择上创新,可以很好地满足新媒介环境中受众的需求。在新媒体环境中可以进行海洋信息的创意传播,例如中国海洋大学吴立新院士具有“专业网红”的特点,在海洋传播方面属于意见领袖,可以打造海洋传播领域的IP。
(四)海洋传播理论研究
上述三个部分涉及的经验分析,最终要形成理论,才能更好地分析人类与海洋互动的普遍性关系,从而建构起一个解释人类海洋传播实践的变迁模型。因此,海洋传播理论研究是海洋传播研究的重点内容。从宏观上来说,海洋传播理论的研究需要建立在不同学科知识、不同经验模型的基础之上,并且海洋传播理论一定与陆地上的人类传播理论存在着差异,其中如何阐释清楚海洋传播理论的独有之处,是海洋传播研究人员的使命和责任。从中观层面上看,区域海洋文化传播模式是什么?媒介对海洋信息的建构模式有几种?模式是否发生变迁?海洋新闻人才培育的制度是什么?从微观层面上看,海洋在中国媒体中的符号建构是什么?从心理学方面分析,人们对待海洋环保、海洋宗教文化的态度是什么?这些方面都可以进行理论的探索。
(五)海洋传播史研究
中国自古就是海洋大国。从先民发轫,及至秦朝、东吴、唐代、宋元明清,中国海洋文化也伴随中国人走向“蔚蓝”的步伐,而逐步形成与完善。例如宋代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开启了航海活动和海洋知识积累的新时代。海洋知识通过口耳相传、航海使节和僧侣、礼宾机构及沿边官员的记录等方式传播,使宋人构建出动态、险恶、奇异而充满财富和商机的海洋意象。那么从古至今,不同媒介是如何对海洋信息进行传播的?不同时期海洋传播的重点是什么?如何建构了人们对海洋的认知?这些都是海洋传播史的研究内容。
此外,构建中国海洋传播研究的主体性,还要看海洋传播研究是否已经形成学术共同体,研究者是否在关键问题、知识生产上形成共识。国外的海洋传播研究有相对成熟的学术共同体,有专业的研究人员、代表作、教育机构、学术机构等,学术共同体内部交流比较活跃,专业上的看法比较一致。通过共同的语言,他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学术领域、分享资源,进行交流沟通。
相比之下,近年来我国传播研究领域缺少关注海洋传播的学者。有少数的学者开始涉及关注海洋传播研究,但并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学者们大都是根据自己的研究背景和研究兴趣进行问题的探索和理论阐释,未对海洋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学理发展做出分析,这意味着该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并未就核心问题达成共识,相互之间的对话、互动和共鸣也很少,学者们在知识谱系中的相互勾连还需要加强。
综上,凝聚中国海洋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以提升共同体的学术创新能力、话语权和归属感为核心使命,形成广泛认同的学术理念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强化主体性认同,是促进海洋传播研究繁荣、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路径。
注释:
① 刘远传:《关于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问题研讨综述》,《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②③ 静恩英、杨励轩:《海洋传播建构的必要性及其研究视域》,《传播与版权》,2018年第11期。
④ 毕研韬、卢瑄、焦昆:《我国海洋传播策略及海南机遇》,《新东方》,2016年第2期。
⑤ 陆小华:《从陆地传媒到海洋传媒——多重视角看海洋危机事件报道的基本原则与思路拓展》,《新闻记者》,2011年第10期。
⑥ 《联合国海洋公约法》,http://www.xinhuanet.com//ziliao/2005-04/04/content_2784208.htm,2005年4月4日。
⑦ 《我国深海数字摄像技术获重大突破并通过验收》,http://www.zgny.com.cn/ifm/consultation/2004-01-09/54424.shtml,2004年1月9日。
⑧ 张君昌:《加快面向“海洋世纪”的新闻传播研究》,《现代传播》,2013年第6期。
⑨ 李思屈、郑宇:《论现代海洋媒介传播体系的构建:以提升浙江媒介海洋传播力为例》,《现代传播》,2013年第10期。
⑩ [美]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陈建军、罗燚英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