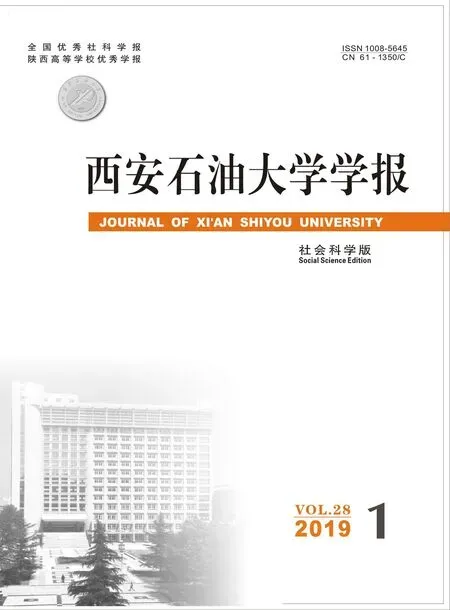法律保障视野下的反贫困现状探究
——以青海省农牧区为例
闻其通
(青海民族大学 法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0 引 言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反贫困工作作为首要任务,通过不断努力使将近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如此空前壮举,在全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由于多种原因,截至2017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3 046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为2 572.49亿元,除港澳台之外,在全国的排名是第29位,在西北五省中排名第三。特别是青海省农牧区,由于贫困人口基数大,经济尚不发达,一直是我国反贫困的主战场之一。我国关于反贫困理论研究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反贫困工作推进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关于反贫困问题,专家和学者往往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探究,而忽视了法律在反贫困中的作用。笔者试从法律视角寻找解决贫困问题的突破口,进而为反贫困战略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
1 青海省农牧区的贫困状况及致贫原因
1.1 青海省农牧区的贫困状况
从1994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2020年)》,青海省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4年2 942元提高到2016年43 71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4年的869.34元提高到2016年的8 664.4元。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 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的提高,使更多低收入者被纳入到扶贫的范围内。根据该标准,青海省有15个县成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占全省总县数44.1%。通过2016年中国和青海省年鉴的数据可知,2015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 421.7元,同年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 605元。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相比,存在明显差距。2015年中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1%,同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7.8%。青海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虽不是很低,但是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反映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实情。青海省反贫困的任务任道重远。
1.2 青海省农牧区的致贫原因
(1)先天自然环境的劣势。青海省位于我国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全省均属高原地区,平均海拔在3 000米以上。青海省属于高原大陆性气候,以高寒干旱为主要特征。低温和干旱少雨是限制青海农牧业最主要的原因,低温造成该地区农作物生长周期普遍较短,同时也造成能够利用的草场有限,因此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干旱少雨导致农作物不能及时播种,农作物发育不良,牧草推迟返青,牛羊膘情下降,导致农牧业减产。除此之外,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使其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2)劳动力素质低,自我发展能力弱。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青海省乡村15岁及以上文盲比重是18.32%,除港澳台之外,在全国的排名仅次于西藏,位列第2位,是全国平均比重的2.5倍多。农牧区人口文化水平偏低导致劳动力素质水平偏低,因此只能从事一些传统的、科技含量低的农牧业生产劳动。舒尔茨曾说:“经济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在于农业的落后,而农业的落后关键不是缺少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不足。而增加教育投资又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1]153如果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得不到提高,接受新鲜事物和应用新技能的能力水平也不会得到提高,将导致农牧业科技难以在农牧区推广,农牧业产量也得不到增长。这样一来,贫困人口的“等、靠、要”思想依然存在,同时也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对更加需要帮助的贫困人群造成新的“不公平”。
(3)产业结构单一,农牧业缺乏产业化。2016年青海省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比(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为45.8:2.44:48.9:0.97,农牧业占青海省第一产业总产值的97.14。在现实中,农牧业生产劳作往往是在青海省农牧区进行。青海省农牧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一些地区因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大部分生活资料靠自给,从而造成了农牧区经济结构单一,耕作方式粗放,谋生手段较为简单,缺乏自主增收致富能力,收入渠道狭窄和收入水平低而不稳。[2]54与此同时,农牧区依然保持着传统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农牧民由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只能出售初级农畜产品并且高价购买各类生产原材料,导致农牧民利益受到双重损失。牧区农民对于现代的生产经营模式缺少认知,不能有效地把农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低下。
2 青海省农牧区反贫困现状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3]24青海省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同时结合本省特色,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提高牧区当地特有的农畜产品深加工扶持力度;为从生态脆弱地区搬迁的群众提供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帮助,根据家庭情况和劳动力的不同进行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省内直属单位与深度贫困家庭进行“一对一”帮助,不仅在物资上给予扶持,在技能培训、求职推荐、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大力度地给予支持;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具备条件的贫困农牧户设置生态公益性管护工作等使当地的贫困率逐渐降低。但青海省农牧区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反贫现象,与此同时,青海省农牧区贫困人口多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多为文盲半文盲等,这使青海省的反贫困任务仍十分艰巨。
3 法律保障视角下青海省农牧区反贫困面临的困境
3.1 反贫困法律法规缺失
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关于反贫困的法律法规还是一项空白,中央主要是凭借已经颁布的“扶贫计划”“扶贫规划”“扶贫开发纲要”等作为反贫困的依据来源。这些文件主要针对当前或者将来某一阶段所做的决策提出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指标、方针与途径、开发优惠政策等。虽具有政策指引作用,但并不是国家层面的法律,其约束性和效力性不强。在国家层面反贫困法尚未出台前,部分省份为加快反贫困进程,在与宪法、有关法律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出台了地方性反贫困法规。1995年11月14日,我国第一部地方性反贫困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条例》出台。截至目前,一共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本地区的扶贫开发条例。2015年,青海省制定《青海省农村牧区扶贫开发条例》,共有7章55条。但从这些已经颁布的扶贫开发条例来看,行政化色彩过于浓重,政策性强;章节结构、内容与政策性文件如出一辙;类似于“政府应当……”的描述在条例中普遍存在。条例没有把法律责任明确化,为一些违法行为逃避责任提供了可乘之机;在监督上,只是通过行政手段监督,没有构建多元化的监督模式,达不到良好的监督效果。
3.2 扶贫过程中存在贪污腐化现象
扶贫资金既是贫困地区人民的“保命钱”,也是精准扶贫的“助推剂”。但是,一些干部利用党和人民赋予其的职权为自己谋私,凡是涉及群众的钱财,总要想方设法地揩“油水”。也有一些基层干部自认为“天高皇帝远”,缺少了外部监督和自我约束,从轻微违纪走上最终的犯罪道路上。例如,2013年,西宁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向湟源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下达在波航乡纳隆村实施连片养殖业扶贫项目资金160万元。后经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研究决定,又从其它项目中调剂51万元给纳隆村,2014年两笔资金转入乡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账户,但该项目一直未启动实施。2015年,为应付中央和省级审计部门检查,经乡政府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协调,将两笔资金分别转入纳隆村党支部书记杨文全和 “新增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增财个人账户。两笔资金先后被杨文全和李增财挪用。2016年10月,湟源县纪委研究决定,给予杨文全开除党籍处分,两人涉嫌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挪用资金已全部追缴。[4]从这一案例不难发现,扶贫资金的分配发放环节是国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重“灾区”,涉案人员多是采取弄虚作假或隐瞒政策的方式,挪用、冒领、截留、侵吞扶贫资金,最终导致扶贫资金不能实现其价值。
3.3 监管缺失使反贫困资金难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财政扶贫资金上,不断增加扶贫资金种类;逐步提高扶贫资金额度;加大扶贫资金累积。可见,国家对反贫困问题一直是给予高度重视的。国家把财政扶贫资金划拨给地方,资金如何使用、用于何处最后决定权在地方。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往往会出现财政扶贫资金挤占挪用、资金投放不合理、“关系户”享受扶贫资金等现象。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曝光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看,挤占扶贫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原因是贫困地区在进行反贫困的同时还要进行新农村等其它项目的建设,上级财政对于下级日常办公经费不能及时划拨,贫困地区为了完成某些硬性的达标验收,不得不从财政扶贫资金上进行挤占、挪用。很多领导干部把财政扶贫资金比喻成 “唐僧肉”,究其原因一是容易挪用;二是惩处力度不够。财政扶贫资金之所以被“妖魔鬼怪”惦记,主要是因为监管困难。从横向上看,扶贫资金来源过多,其管理的部门也多,造成难以相互监管的问题。从纵向看,中央政府赋予县级政府对扶贫项目资金享有审批权限,防止审批权限滥用,责令省市级政府对此审批权进行监督。现实中经常会出现上下级官员同流合污侵占扶贫资金现象,使监管变得名存实亡。
4 推动青海省农牧区建立有效反贫困法律保障机制的建议
4.1 完善反贫困法律法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党和国家一直致力于反贫困斗争,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种佳绩的取得使一部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实惠。如何才能将这种实惠不因一些外部原因而丧失呢?正在接受国家扶贫帮助的贫困人民,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呢?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将其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通过法律对其引导、规范、监管,才能使反贫困工作得到根本上的保障。从地方层面来看,已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本地区的扶贫开发条例,但是法律条文行政色彩浓厚,责任承担上规定得不够明确,操作性不强。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出台统一的反贫困基本法,为保障反贫困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反贫困基本法中应该包括以下内容:扶贫对象,可根据不同地区城乡最低生活标准确定。扶贫主体,应把各级政府作为扶贫主体,同时也可把其他经济组织纳入扶贫主体当中,使政府扶贫与市场主体扶贫相结合,进而提高扶贫力度,使更多贫困人口脱贫。扶贫应坚持国家责任为主原则、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相结合原则、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原则以及扶贫资源有效利用原则等。[5]19贫困救济制度,即确定受救助人员范围、救助金额标准、资助方式等内容。法律责任,即对资助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员相关法律责任的相关认定。在国家层面的反贫困基本法出台后,各级政府应以基本法为依据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修改、完善地方反贫困法规、规章。
4.2 完善反贫困法配套机制
4.2.1 建立廉洁的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发展先进生产力,实现科学发展,建成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6]328在反贫困工作中如何才能让政府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俗地说,只有让贫困百姓不失望的政府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基层干部只有自身廉洁,自然而然就能增加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真正的好政府。在具体的反贫困工作中,能够有效地贯彻反贫困法律法规的首当其冲的还是政府及其基层干部,他们的作为决定了反贫困法律法规实施效果的好与坏。在现实中,有很多基层干部由于民主法制意识淡薄,在处理问题时靠“拍脑门”决定事情,进而忽视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问题。因此可以说,基层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是建立廉洁法治政府的前提。只有基层领导干部的意识真正“变”了,才会主动地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才能用所学的法律知识解决问题,而不是一遇到事情就只会运用行政手段处理。
4.2.2 实行反贫困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制度是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的一座沟通桥梁。自从中央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国家不仅在精准扶贫资金的额度上不断加大,而且在扶贫资金类型上也逐渐增加,因此,对于扶贫资金的使用、扶贫对象等信息有必要进行公开。通过反贫困信息公开,可以提高扶贫主体工作的透明度,防止权力腐败,进而营造一个和谐的反贫困工作环境。
4.2.3 开展反贫困普法宣传
制定得再好的法律若是不能有效地实施,就是一纸空文。各级政府部门要把宣传反贫困相关法律法规作为反贫困工作的重中之中。通过普法宣传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贫困相关法律法规有充分认知。由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偏低,民众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各级政府应通过不同形式广泛开展反贫困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如采用传统板报的形式宣传,将法律法规编成易于记忆、容易相传的“顺口溜”“三字歌”等,还可以借助微信、QQ等新媒体平台等将反贫困法律法规精神传达给老百姓。
4.3 加强财政专用扶贫资金监管
财政扶贫资金是指国家为改善贫困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而设立的财政专项资金。[7]3可以说,财政扶贫资金是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和减少贫困人口的“救命稻草”,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绝不允许任何人对财政扶贫资金动歪脑筋。特别是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面对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变大,加强资金监管非常必要。在此,不妨把企业产品质量管理当中的“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事后监管”的质量监理体系应用到反贫困资金监管中去,进而使财政专用扶贫资金得到有效监管。首先,加强事前监管,防患于未然。很多领导干部在做某些决定时,总是凭着个人经验去“拍板”做决定,结果因为缺乏事前有针对性的调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财政扶贫资金是贫困老百姓的“命根子”,因此必须做好事前监管工作,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资金使用率,同时也可以有效纠正资金的不合理使用。建议青海省在扶贫项目上做重大决策时,可以组织有关单位、联系有关专家学者对重大决策进行调研、论证,促进科学决策、提升管理水平。其次,加强事中监管。国家划拨给地方的财政扶贫资金只有有效地运用到反贫困工作中,才能真正体现它的价值。财政扶贫资金事中监管应把扶贫资金申请、分配、拨付、管理、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虚报冒领、贪污侵占、挤占挪用、资金闲置、优亲厚友、使用效益不高、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作为监管对象。建议青海省在财政扶贫资金事中监管环节中,建立各级扶贫绩效考核机制,对各阶段的扶贫成果、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等做量化考核,逐步建立以考核结果为导向的激励和问责制。最后,突出事后监管。事后监管主要是扶贫项目资金投入后,且扶贫项目已经实施完成的后续运行监管。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下,扶贫机构既承担项目的实施,又管理项目验收工作,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不仅体制内缺乏相互监管,更缺乏第三方的参与,扶贫项目的验收评估缺乏透明度。[8]55建议青海省在对项目验收时,打破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份,积极引入体制外的第三方监管,对于第三方要的反馈意见应给予高度重视,对于出现的问题能及时纠正,不置若罔闻,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