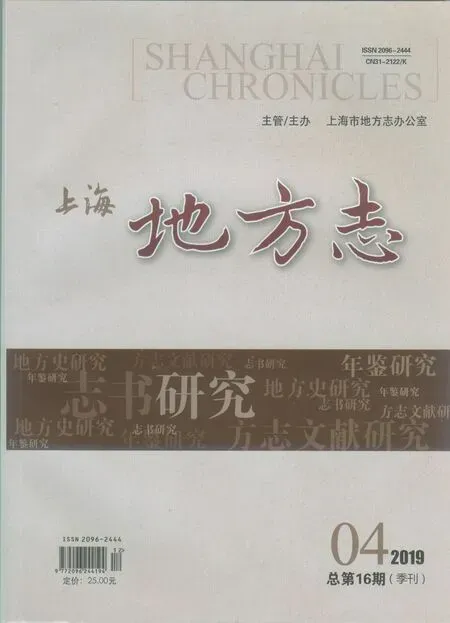从《警世》看《民抄董宦》真相
董玉兴
明人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尤以书画闻名于世,《明史》对他的为官品德和艺术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然而,多年以来,一些人士依据译本尚待考证的《民抄董宦》(以下简称《民抄》)将董其昌沦为一位毁誉不一、贬褒互有的历史争议人物。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法制理念认识的加深,在做事和论事上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尤其是在文化界,已扬弃过去那种政治偏见,开始注重以现实和法理来评议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好多年被排斥在中国书画展览之外的董其昌的书画,近年来也开始陆续展览。2016年1月,上海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馆联动,两地共展董其昌的书画后,2019年1月20日,在上海召开由上海博物馆主办的国际董其昌学术交流会。董其昌的故地松江建起董其昌博物馆。国内媒体于2016年6月,赴上海市松江区、闵行区马桥镇、江苏省苏州等地摄制董其昌专题篇,这些举动唤起人们对董其昌的重新认识。然而,要还原董其昌的真实历史面貌,就得弄清《民抄》披露的所谓“真相”是否属实。《警世録》在这种形势下恰逢面世,其中抄录的三十篇文稿正是处理“焚抢董宅”的原始公文、书信、檄文等,它將对已尘封四百余年的该案是不是“民抄”提供确实有力的证据。
《警世録》是董其昌原籍马桥一位董氏后人珍藏于家中的一本祖传明代手抄本,书中原文抄录的三十篇文稿,正是处理发生在四百年前松江那起焚抢董宅案的原始公文以及有关该案的书信、檄文,公揭等,现已由马桥和松江史志办邀请有关专家鉴定确系明末抄本。其中内容翔实,属不可多得的官方第一手可靠资料。有关《警世録》的文章已登载于《松江史志·2016·第一期》,三十篇文稿的目录为:《华亭偾事纪略》《三月初八日吴玄水闻董其昌赴抚、学二院告將状与书》《冯氏合族刊刻冤揭》《五学檄》《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实》《府示》《又示》《又示》《县示十七日示贴坐化庵》《府申各院道公文》《十七日董求吴玄水书》《府学申复理刑厅公文》《府学申复学院公文》《署府理刑吴初审申文》《学院驳批道申》《兵道驳批》《学院奏疏》《学院提考牌》《合郡乡士大夫公书》《合郡孝廉公揭》《学院回书》《吴理刑回书》《又请教各仕夫书》《道尊回书》《抚台回书》《抚台示》《本府复审申文》《批申》《苏常镇三府会审断词》《松江府辩冤生员翁元升张复本姚瑞征沈国光张扬誉冯大辰陆石麟姚麟祚丁宣马或李澹陆兆芳》。
二、从《警世》分析“焚抢董宅”一案之真实性
1.发生“焚抢董宅”一案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董其昌的处境
“焚抢董宅”一案发生在明末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史书称万历朝的后期是执政帝神宗的醉梦之朝,沉溺酒色,怠理朝政,“不郊不庙三十年,与外廷隔绝”,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社会风气日益愈下,道德衰微,乱象纷生。从《警世録》中就可看到,在该案发生前不久,江南地区就已发生了浙省民变和江苏昆山民抄乡宦周玄晖二件重大事件,可见当时是个乱世年代。
据史记,董其昌在任皇子讲官时曾对神宗的私生活进言节制(《陈言时政疏》),又力劝皇子朱常洛不要沉溺于修道炼丹,遭神宗嫌弃,坐失执政意。任湖广提学副使时,因拒收贿赂,整饬学政,被同行排挤、遭儒生的围攻。一个无党无派的董其昌,要想行清官之道,在那个党争酷烈的年代,结果只会是四处碰壁,辞官是必然的。辞官,意味着脱离官场,失去朝廷的庇护,自然也失去权势。所以,《民抄》说董其昌父子倚仗权势作恶乡里是不太符合逻辑的。董其昌是1604年辞去湖广提学副使,至1620年才应光宗帝的起召,1616年是董辞官回乡的第12个年头。从一本《明人尺牍》董其昌致友人的书札中就可看出,其实董其昌辞官回乡后生活并不如意,尤其在发生焚抢第宅的前五年,频遭一位仇家的造谣中伤。“闻吾乡此人,至今下石不已。”“僻居五年,炎凉万状,也有小人当事。”“七、八月间,吾乡有一人属山阴令中伤我家。”“弟自入籍以来,不买小民一亩田,不受旧家投身之仆,与里人绝不交涉,故得无可攻耳。”上文中说及的“小人、山阴令”是衙门的一位官员、说明“焚抢董宅”的前兆可能并非是董其昌父子敛冤乡邻,而可能是仇家对董挑事设局。
2.“焚抢董宅”始末的真实性
《民抄》说,“民抄”董宦的衅始是董其昌的次子祖常强抢陆家使女,并作这样的描述:“绿英係陆生家人之女,承继与董宦家人,绿英因本生母有病,望探未回,祖常疑有他故,辄肆扛抢。”从一个“疑”字看出,绿英是祖常的恋人,望探未回并非感情生变,而是祖常多疑,那么祖常去陆家便知,怎会发生强抢一事?可见《民抄》的描述存在矛盾和质疑之处。
然从《警世録》对此事的记载:“从公备细查得,因陆兆芳家使女继养宦仆之家,此女探母未回,董仆陈明纠众打毁陆家家资,將女抢去”可证明有三,一、绿英早已脱离陆家成为董仆陈明的继女,《民抄》对绿英的身份有混淆的故意;二、抢回绿英的不是祖常,而是继父陈明,《民抄》有对祖常栽赃的故意;三、陆兆芳曾把陈明告府,从陈没被判罪可证明陈没有过错。然为何又会发生陆与祖常相争女婢一事?“昨岁生员陆兆芳与董宦家因一女婢竞口。”因为绿英事后与祖常相恋,陆知道后醋意大发,诬称祖常是陈明抢回绿英的主使,并把祖常也告上府衙。从“陆兆芳先蒙号革”证明,陆的诬告被董的仇家乘机搅局,引发了大案,后陆被三府会审判定是该案的衅始,革去秀才名号。可见祖常根本没有强抢使女一事。
《民抄》说,“民抄”董宦的续衅是董其昌诬指并逼死范昶,并描述说:“有苏州人说书钱二者,在街唱说,觅钱廷芝(范昶)从旁窃听,为董仆所见,密报其主,遂擒钱二锁打,而坐廷芝以主使之罪逼跪于廷,廷芝不胜愤懑而死。”
然从《警世録》对此事的记载:“致有流言黑白小传,并丑詈曲本,董宦告官严缉,并无主名。捕得说书钱二,口称生员范昶。”可证明有四,一、因为陆的诬告,确被董的仇家乘机揑编诬董《黑白小传》,并唆使艺人改编成曲本四处宣传;二、董其昌没有让仆人四处搜拿造谣者,而是告官严缉,并告知没有怀疑的对象;三、说书钱二是被捕官缉拿归案的;四、说范昶是《黑白小传》的揑编者又是钱二的主使者,都是钱二当堂招供揭发的。从“无怪董仆陈明之根究耳”证实,因为松江府擅放钱、范二嫌犯,才被陈明拦下,要他们去董家三头对案。因为钱二仍坚称范昶是作传和唆使者,为表清白,范去庙面神咒誓。从“昶归遂不胜愤懑而死”证实,范不是死在董家,而是数天后郁死在家中。后此案被三府会审判定:“范昶以钱二妄指作传,遂誓神愤懑以死,此莫致之命,与董何尤。”
对于董仆“辱殴范妇”一说是存有较大质疑的。一、从范、冯(范母的娘家)二家联合炮制的揭文:“揭为殴姐异案,寒宗受辱,恳激公愤”看到,当事人范家起先说的是董仆殴打范妇,根本没有辱殴一词;二、从《警世録》中看到,从府衙到乡绅以及董的仇家,对“辱殴”一说的描绘都各不相同。三、不管从《警世録》还是《民抄》,都没有记载松江府曾以“辱殴”一事立过案,说明范家事先没有以“辱殴”一说告董于松江府。没有诉告,就没有立案,那么何来“辱殴”一说的真相,可见“辱殴”一说是有揑编之嫌的。
既然董祖常没有强抢使女,董其昌没有诬指、逼死范昶,董仆辱殴范妇存有重大质疑,说董其昌父子敛冤三县军民没有凭据,那么又怎会发生“焚抢董宅”一案?
从“揭为殴姐异案,寒宗受辱,恳激公愤,……今日之公评,期共严于斧钺……丗奉先规,素甘株守……各持清议,誓剪元恶。”看到,因为范家不敢诉告诬指者钱二,怕钱二死咬住范昶作传不放,然又唯恐范昶真被认定有作传一事,为表范昶的清白,才以三头对案一事为由,把要想弄清事情真相的董其昌作为发泄怨气的替罪羊,范家依仗在松江有人脉基础,原先的意图只想鼓动乡绅和五学生员准备对董其昌展开一场舆论鞑伐。然从判文中:“诸生一时过信啟宋之词,愤激成仇,扬袂而起,率众鸣学,持檄禀府,挟持控告,同投冤单。”及“畴昔金阊凌宦,只因一士之仇……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看到,啟宋为何又成了这起造乱的鼓动者、发起者?这对一名知晓律法的秀才胆敢发动造乱似乎不合情理。原来范家的意图被董的仇家利用,通过怂恿,并与范啟宋合谋,以效仿昆山的民抄周玄晖事件为方式,鼓动百姓去焚抢董宅。从“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单投揭布满街衢。”“王皮、曹辰诸人遂乘此为烧抢之资也,周麾而呼,先骋而倡,一条龙係胡龙,地扁蛇係朱观,嗜抢如饴,走险如鹜……海邦之民,轻剽易利,刹那之顷,聚者万馀。”看到,通过鼓动,平日里那些早就对董家虎视眈眈的嫉才仇富的好事之徒、市井刁民、凶徒恶少,纷纷跳出来附和响应乘机搅局,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掠夺董家的财物。然从“范啟宋十四日告诉姑苏、十六日告状江阴,”“二姓越数百里赴臣投状,而事外之人辄从中鼓煽,构此奇变。”看到,范啟宋没有公开亮相领导由他一手发动起来的这场造乱,原因是当时(即初九日)董去苏州会友,范误以为董是去学院告他,为防应诉时因有涉造乱而被扣押,故才不公开亮相。然当范得知董去苏州不是告状而是会友,并即将回松的消息后,为防造乱因董其昌的回松而被夭折,在合谋人的唆使下,范以揑编的“辱殴”一说为诉告理由,赶紧奔赴苏州去学院告董,企图以告董的方式,把董其昌牢牢缠住在苏州与他訐讼。唯恐单只诉告学院纠缠不住董,范又于十六日赶赴江阴的抚台投状。在他们的精心谋划下,范啟宋终于成功制造了这起轰动东南半壁的恶性案件。
那么,作为担负一方平安的松江府在这起造乱中是否立于公心恪尽了职守?从一份《学院奏疏》中就可看出他的真面目:“是变也,白昼大都,焚抢无忌,非直一方之变,所关风俗纪纲甚大……据实奏闻,至若变起之日勅手敛足,全不为地方担当,变定之后,半吞半吐,只知为青衿卸脱,畏旁掣甚于畏法纪,迁延至今,该地方有司实不能逃其责者。”
从“钦差提督御史王以宁,一本士宦因事忿争,棍徒乘机煽祸,先据实上闻,恭候勅旨……谨会同巡抚王应麟先將查报情略。”看到,该案当时是由学院、抚台受理。
从《署府理刑吴初审申文》《抚台示》《本府复审申文》《批申》《苏常镇三府会审断词》这些公文看到,本案的审理严格遵守司法程序。先由松江府初审,学院核审,又抚台御史王应麟亲临松江察访案情,再把案犯发回松江府复审,最后才有苏常镇三府会审判定结案。
从《学院驳批道申》:“据详,行凶恶少不过为打抢财耳,岂可即指为民抄?此事衅孽,原起学校。”《兵道驳批》:“看得董宦被祸之烈,其所不甘者民抄两字,即谓士抄,亦应坐以据,今据刑官之审已得其详,乃此一变也。”证实,二院否定了松江府擅定的“民抄”一说。
通过三府会审,对涉案罪犯都作出公正的判决:“陆兆芳先行号革。首事郁伯绅翁元升张复本姚瑞征沈国光并应杖革;李澹张扬誉陆石麟冯大辰姚麟祚并应杖降;马或丁宣方小一并应杖惩。王昇董元已登鬼録;金留曹辰皆首恶,骈斩不枉;胡龙与唱书钱二階厉,徒各允宜;范啟宋父死非命,门庭受辱,与被告家人情俱可原,董祖常屋被焚抢,故免深求,陈明召祸累主,身亦受殃,故杖之。所抢家资,法应追给。”
因为“辱殴范妇”一说被有涉案嫌疑的松江府坚称有之,二院无奈认可。范因没有公开参与造乱,故也没被判罪。而被诬称有涉“辱殴”一说的董祖常和陈明自然也被判有过错。
通过三府会审也还董其昌一身清白:“夫董宦夙擅文望,名满寰中。今以使女之故,被造黑白传奇玷其闺阃,此即贤者难堪。范昶以钱二妄指作传,遂誓神忿懑以死,此莫致之命,于董何尤。至其母妻籍内亲之情,登门诉骂,随从婢女三、四人,概被剥打虐辱,昶之母妻羞窘逃回,则奴辈之不法,而或董宦未之知也。”
《三府会审》对最后作出的裁判是这样表述的:“祸虽因士胚胎,士实未尝与乱同事。民虽乘机肆横,罪自不得与士同科。即挽风者防其流,杜乱萌者穷其源。而定公案者,期于得情无枉,则何敢得私情为低昂,借公法为报怨也。”虽然是为了平息“士抄”还是“民抄”以及“士人”与“罪民”判决不同的争议,但以此仍能证明“焚抢董宅”一案的源头与本质。
综上所证,焚抢董宅一案在四百余年前由官方判定为“士抄”,不是“民抄”,它是嫉才仇富的地方排外势力以及民间“凶徒、恶少”共同推动酿成的一桩冤案。
虽然《明史》没有该案的记载,但是史书《明实录》有此案的记载,虽寥寥数言却能印证该案的真相:“六月已末,巡抚应天都察院右副督御史王应麟奏称,(董其昌)三月间,忽与生员范啟宋并至苏州互相告訐,方行批发,而其昌华亭之居业于此时化为灰烬矣……海上之民,易动难静,难发于士子,而乱成于奸民。董其昌起家词林,素负时望……”其后万历皇帝下旨“董其昌事,严查首从”。王应麟与学院御史王以宁是一起处理此案的当事人,他的奏章虽不及王以宁的奏章详尽,然也简言说明了发案的过程和造成此案的缘由。
3.“焚抢董宅”一案是有主谋者的
那么,怂恿并与范啟宋合谋作乱的人究竟是谁呢?从《松江府辩冤生员……》中:“至欲与周玄晖之事同类而共观之,岂不冤哉?夫昆庠之公呈有据,而松士之风闻不实,况彼亦一公举,此亦一公举,彼无一士之号革,此乃十人之株连,宽严既已悬殊,权衡宁无倒置……何以服升等。”看到,原来一直在背后为范坐阵的人叫“升”,“升”才是这起焚抢案的主谋者。他对筹划这起造乱被二院判定为“士抄”,而且参与生员都被判罪,心里是极不平衡。“升”是何人?他就是被杖革的翁元升。翁胆敢领衔具名以松江府的名义作此辩文,证实其是在松江府做事的,从他被府学开报给二院一事看出,他不是在册官员,而是一名聘用官员。按明朝政府聘用官员的规定,推定翁是一名书官。故此范啟宋敢蓄谋作乱,原来有松江府的官员在背后撑腰。凭翁胆敢作此辩文向二院叫板,足证其是一个胆大妄为之人,对辞官回乡的董其昌的确不会放在眼里。追溯焚抢案的始终,翁先是对董其昌造谣、中伤,怂恿范啟宋作乱,直至公开参与倡议、鼓煽。翁之所以敢利用手中的刀笔胡作非为,从案后知府黄朝鼎、理刑吴玄水、教官胡公胄挂冠走人一事可看出,为了陷害董其昌,他们之间是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的。从《五学檄》:“董其昌称小有才,非大受器,……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词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倖,以滥大名。”《松江府辩冤生员……》:“吾松豪宦董其昌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丹青薄技,辄思垄断利津,点画微长,每谓雄视当路。”看出,翁元升与董其昌为仇完全是出于嫉才的原因。翁能成功策划这起焚抢案,除了乱世年代这个客观历史原因外,其还摸准抓住了董其昌的五个所谓“短处”。一、董是从上海县入籍松江的,故在松江没有深厚的人脉基础;二、松江本是书家云集之地,名人辈出,同行间竞争也异常激烈。董靠字画在松江成名致富,必然会招致一些人的嫉才仇富,同行间还会结有冤家。三、从史记:“其昌善待平民,和易近人,不为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至前。”“达官贵人以重金请乞者,不是严词不予,就是给其家属仿作的代笔书画。”看出,董这种亲贫疏富的脾性,也必会激起权贵势家对他的忌恨;四、董为官时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回家省亲从不惊动地方官员,他这种清正廉洁自然会遭致那些庸官俗吏的不满;五、松江辖有五学,秀才芸芸,常有众多秀才去南京参加三年一次的科举和乡试。董曾任过南京的主考官,其不徇私情、坚守原则的处事作风,可能招怨于部分素质低下、动机不良的考生。这些所谓董的“短处”,在焚抢一案中都一一得以证实。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乘了董的辞官之机。从1620年董答应光宗帝的起召,就平息翁发起的这场已闹得沸沸扬扬的翻案风可证明,假如1620年之前,董其昌还身居高官之位,松江也就可能不会发生焚抢董宅一案。
三、《民抄》一书可能是仇家翁元升所编
有何依据说《民抄》一书可能是仇家翁元升所编?依据如下;在《警世録》中有四份整篇内容都是陷害董其昌的文稿,即《华亭偾事纪略》《五学檄》《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实》《松江府辩冤生员……》,从这些文稿中可能贬损、丑化董其昌的内容相同;从这些文稿中透露出的官腔味;这些文稿把官员在现场办事的言行细节描绘得细腻活现;作者敢以五学的名义炮制檄文以及敢以松江府的名义炮制辩文,可以推定,这些文稿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其人可能是董其昌的仇家,而且这位仇家还是位官员,在《松江府辩冤生员》一文中也亮了相,他可能就是被杖革的书官翁元升。原版的《民抄》本是由《华亭偾事纪略》《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实》二篇文组成,那么,翁元升可能就是《民抄》一书的作者。翁之所以不敢署名。可能是担心世人识破真相。他编这本《民抄》的意图可能就是想隐瞒焚抢一案的真相。
该本《民抄》面世以来,就有学者对它提出过质疑。松江档案馆藏有一本原始版《民抄》的转抄本,抄录人于前言曰:“华亭偾事纪略一篇,不知何人所作,仲鱼孝广,从吴中抄得,予读之,不禁戒欢,盖文敏一代人物,即有过,当应不郅是,良由后嗣之不贤,致累乃公之清德,可不惜哉。此记纵或为怨华亭者甚言之,要么必尽出于子虚,读者更详之。”可见这位抄录者已怀疑《民抄》是仇家所为。而学者陈家洛对“民抄”一事是这样认为的:“而《明史》则言,所谓民抄董宦乃因董氏不徇私情得罪特权,仇家煽动乡人暴动之果。”美籍学者何惠鉴、何晓嘉对这本《民抄》考证后,也指出这是董其昌的仇家所编,并对社会上那些罔顾历史、肆意批董的风气表示不满:“根据董氏政敌的一面之词及某些野史笔记及现代传纪的一家之见,从而把一个明末典型士大夫的董其昌描绘成最违反儒家的传统,以书画为谋求名利的手段,是一个毫无德行、自私自利的无耻政客,而对其大肆口诛笔伐。董的画在好多年被排斥在中国书画展览之外,这是董氏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剧。”
由于各类史册缺失对这起焚抢案的收载,故《民抄》影响甚大,长期以来,董其昌一直被一些人误认为有“民抄”所称的失德行为,蒙受不公正的评说,
——松江二中(集团)初级中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