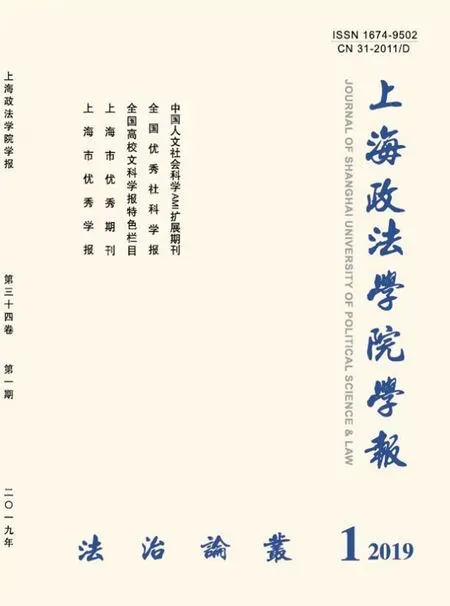法律逻辑的拓展研究
——以新兴交叉学科为背景
吕玉赞 焦宝乾
法律逻辑一直被默认为是经典逻辑即形式演绎逻辑在法律领域的一种应用,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用学、修辞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论辩理论、实验心理学、话语和会话分析、谬误理论和法庭科学(forensic science)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揭露了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非单调性和合情理性,指出法律推理作为一种实践推理的基本特性与经典逻辑存在冲突,从而推动了法律逻辑的“实践转向”(practical turn)。这些新兴交叉学科不仅拓展了法律逻辑的研究进路、研究领域以及理论体系,同时也为法律逻辑在法律获取、法律解释、价值判断、利益衡量以及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中的拓展应用提供了可能性。
一、借力新兴交叉学科拓宽法律逻辑研究进路
迄今为止,法律逻辑研究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逻辑研究阶段,采取的是“传统逻辑原理+法律领域例子”的研究进路;第二阶段是现代逻辑研究阶段,试图参照现代逻辑的模式建构法律逻辑体系;第三阶段是法理学研究阶段,运用法律方法论刻画了一种特殊的法律逻辑;第四阶段是非形式逻辑研究阶段,主张运用当代西方非形式逻辑和论证理论来研究法律逻辑。尽管如此,法律逻辑研究依然未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仍徘徊于运用“传统逻辑”“现代逻辑”或“非形式逻辑”对法律推理进行形式刻画。然而,现代法律以及法律实践、法律适用早已放弃了声名狼藉的“法律形式主义”。①陈锐:《法律与逻辑——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一种全面解读》,《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现代法律乃是以法律语言为媒介,充斥着诸多利益和价值,由多主体参与和博弈的法律言语行为或法律交往行为。法律适用压根就不是封闭体系之内的形式演绎推理,法官要么需要考虑社会中的各种“活法”和“自由法”,要么需要考虑法律背后的真实利益冲突和价值考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语用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和论辩理论等一系列新兴学科,不但推动了法律逻辑的“实践转向”,而且也拓展了法律逻辑的研究视野。
例如,在语用学的影响下,法律逻辑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法律语用推理。如果说传统逻辑与经典逻辑研究的只是语形推理或语义推理的话,那么语用推理则开始关注自然语言推理。英国哲学家、语用学家P.F斯特劳森(P.F. Strawson)认为,研究语言的逻辑运作过程,不能单单考虑简单的演绎关系,必须让思维超越蕴含着矛盾的这些概念,运用形式逻辑之外的许多其他的分析工具。①参见蒋严:《论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形式语用学初探》,《外国语》2002年第3期。语用推理虽不具备形式逻辑所具有的系统性,但可以考察动态的语言思维过程,弥补演绎逻辑单调性的不足,将言说符号的语形、语义和语用连贯起来。在丰富多彩的论辩研究中,语用哲学家爱默伦因着力探讨了论证的语用性而倍受关注,是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转向”在论证领域的主要代表。爱默伦把论辩视为一个基于具体背景的批判性讨论的过程与结果的结合体,在经典逻辑的论证分析与评价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语用的论辩模型。②参见金立:《逻辑视域中的论辩》,《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语用学不仅可以将法律推理作为语用行为的性质运用于实践论辩效果的证成之中,建构一种对话实践的动态逻辑,并且还能够剖析论辩言说的不同部分、单元、阶段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其中涉及的语用效果之间的递进或转换,从而拓展了法律逻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③参见徐梦醒、张斌峰:《法律论证的语用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5期。
“言语行为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后,引起了逻辑学界的广泛关注。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区分了“描述句”(performative)和“施为句”(constative)两类话语。前者指陈述状态、描写事物等且本身具有真假值的话语;后者指具有一定的会话功能但没有真假值的话语。在第二个阶段,奥斯汀放弃了原先的两分说,转而将言语行为划分为3类:以言指事(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act)。后来,塞尔在奥斯汀研究的基础上对言语行为理论做了一定的改进。他将言语行为重新划分为4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行事行为和成事行为,并基于说话者的意图和目的划分出了5类以言行事行为:断言类(assertive)、指令类(directive)、承诺类(commissive)、表达类(expressive)和宣告类(declaration)。此外,塞尔还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的概念。所谓“间接言语行为”是指说话者通过他和听话者共有的语言,或者非语言的背景知识和信息,以及听话者合理的推理,向听话者传达比他实际说出的话更多的信息。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推翻了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一传统观点,从而脱离了一味研究抽象命题及真值的传统逻辑框架。言语行为理论弥补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不足,即仅从语言本身的意义、逻辑结构和使用规则等方面研究语言的意义,提出了言语行为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④参见宋平锋、邓志勇:《言语行为理论的西方修辞学透视》,《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为了理解语言的意义,必须探究言语交际的全部过程,从言语环境诸要素中寻找其真实用意。爱默伦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论证研究的语用辩证分析法,认为法律推理是一个针对接受或批评某一观点而试图克服质疑的复合言语行为。语用辩证分析法,一方面,从言语行为的属性出发,探讨基础言语行为、复合言语行为、批评性讨论中的言语行为、含蓄言语行为以及间接言语行为,揭示论辩这一言语行为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从言语行为的整个过程出发,将批判性讨论具体化为“冲突、开始、论辩和结论”4个阶段,建立了一套消除意见分歧的批判性讨论的评价方法和语用模型,从而使得论辩的理论分析更适应论辩的实践要求。⑤参见[荷]弗朗斯·凡·埃默伦、罗布·荷罗顿道斯特施:《论辩交际谬误》,施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感知和思维信息处理过程的科学,具体包括心理模型小概念和归纳、问题解决和认知技艺、符号结构与认知、心智结构和联结主义、模型论语义学、脑与认知记忆等。认知科学在原来6个支撑学科的内部产生了6个新的发展方向,即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人类学、人工智能和认知神经学。认知心理学把人脑看作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强调人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结构对人类当前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强调认知过程的整体性。认知心理学以及认知神经学提出了认知的双重加工理论,即人类拥有两种信息处理机制:一种是“理性—分析”的信息加工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人能理智地对待问题、运行概念、识别规则,能有意识地解决问题,并能清楚地觉察和表达自己如何处理问题;另一种是“经验—直觉”的信息加工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以非连续的整体方式处理,不受制于意识的参与,所以只需占用较少心理资源,表现出加工自动化、速度快捷等特点。①参见李安:《司法过程的直觉及其偏差控制》,《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学的这一发现,不仅直接证实了“发现”与“证立”这种传统的法律推理模型,而且有助于调和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回溯推理等推理图式之间的冲突。认知心理学可以解释归纳推理中的心理现象和演绎推理中的行为偏差,将归纳逻辑、演绎逻辑以及心理学中的推理还原为一种概率方法。②参见潘文全:《认知心理学视野中的逻辑》,《科学经济社会》2017年第2期。法律适用过程的认知活动是“经验—直觉”机制与“理性—分析”机制的统一。吸收认知科学新近研究,刻画直觉与推理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证成脉络的缺陷与发现脉络的不足,以协作的视角搭建理想的法律逻辑模式。
人工智能是一门研究使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诸如学习、推理、思考等)的新兴学科。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是21世纪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面貌。③参见陈波:《从人工智能看当代逻辑学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逻辑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人工智能关注的领域与逻辑关注的领域大量重叠,人工智能的出现为逻辑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出口。不少人工智能学者已经自己着手提出新的逻辑系统,其中成果最为集中也较有影响的是不精确推理和非单调逻辑(相对于传统的精确推理和单调逻辑)方面的发展。④参见黄志鑫:《逻辑与人工智能》,《哲学动态》2005年第4期。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模拟法官所进行的必然性推理,而且还能够刻画司法实践中的非单调推理、缺省推理和概称推论。人们通过概括所得到的一般命题,并不是一个全称量化的条件句,而是忍受真实否定实例(允许例外)的概称主张。真实生活中的法律推理行为不可能符合经典逻辑模型。法律推理多是法官能动性、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可废止性,这严重动摇了经典逻辑规范性的权威。基于人工智能的形式论证理论研究人工主体间的抽象论证活动,它在吸收非形式逻辑特性的基础上重构了非形式逻辑的诸多理论。人工智能使得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得到了更好的推广和应用,而且一些重要概念和研究对象在人工语言的形式表达下得到了更准确的刻画。⑤参见魏斌:《人工智能视域下的非形式逻辑》,《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0期。
在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认知科学、人工智能、新修辞学、论辩理论、法庭科学等交叉学科的帮助下,加上法律逻辑既有的研究进路,当代法律逻辑学将形成如下6种研究进路,同时也将生成6种法律逻辑形态:
1.法律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命题逻辑、谓词逻辑、模态逻辑、道义逻辑和规范逻辑,虽然在刻画法律推理上存在诸多分歧,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追求法律的形式化或系统化。因此,它们将为法律逻辑提供一种广义的形式化研究进路,从而形成广义的法律形式逻辑。
2.法律语用逻辑: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语言范畴理论、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均是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它们使法律逻辑从语形和语义推理转向了语用推理,并共同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法律语用逻辑。
3.法律价值逻辑:法律逻辑不仅仅指形式逻辑,而主要是价值判断。价值逻辑认为哲学和逻辑命题不是表示对象之间的相互归属关系,而是表示主体对于对象的态度和评价。修辞学和话语理论两者研究的也是价值判断的逻辑,即如何通过理性的辩论、交流、沟通,达成法律上的共识。这三门学科均主张从价值论的观点审视法律逻辑的对象和任务,把握法律规范和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
4.法律论证逻辑:运用非形式逻辑、博弈论、博弈逻辑、商谈理论的概念与方法系统地阐释法律论证型式的本质、构建、分类与功能,揭示各类主要论证型式所蕴涵的推论规则,并运用论证型式对实践中的法律论证展开剖析、评价和理性重构。
5.法律认知逻辑: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司法科学有助于刻画法律适用背后的认知机制,尤其是结合多主体认知逻辑、公开宣告逻辑和信念修正的动态逻辑等理论,对个案推理进行认知逻辑建模,由此拓展了多主体认知逻辑模式在法律论证中的应用,从而使建构的法律论证模型更符合法官的认知。
6.法律智能逻辑:法律人工智能的研究主题已经从最初的抽象论证语义扩展到对话理论、论证语义的复杂性、论证理论的应用(如法律论证的人工智能模型)等。人工智能能够模拟法律推理,深化人们对法律推理性质、要素和过程的认识,同时,还能够表达和刻画法律论证中的非形式逻辑,对法律证成、法律检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等法律适用活动进行逻辑分析,从而为掌握法律推理的过程和规律,提供逻辑模型和实验手段。
二、塑造新型法律逻辑扩展法律逻辑研究领域
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法律逻辑的研究视野,促使法律逻辑从单纯的对法律推理的形式化转向了法律规范结构分析、法律推理图式刻画、法律知识体系建构、法律论证形式建模等多样化的议题,同时还为我们塑造了一种新型法律逻辑。这种新型法律逻辑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作为思维活动的新型法律逻辑,另一种是作为思维规则的新型法律逻辑。在前一种意义上,法律逻辑的“创新”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确信存在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律逻辑,其由形式、语用、价值、论证、认知和智能6种不同的要素组合而成;二是基于法律推理对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的不同需求,以协作的视角恰当安排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等逻辑工具在法律逻辑体系中的位置;三是从法律逻辑的适用对象或研究领域出发,建构法律逻辑分层化的理论体系,再由分层之连接和过渡拓展形成自洽而融贯的法律逻辑理论体系。
在后一种意义上,法律逻辑的“创新”同样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强化与法律思维的关联,将法律逻辑定位为“一门关于法律思维规律、规则与方法的学问”①王洪:《法律逻辑研究的主要趋向》,《哲学动态》2009年第3期。;二是增强法律逻辑规则的可理解性,基于自然语言形式的法律思维规则(法律发现规则、法律解释规则、法律推理规则、法律论证规则),塑造面向法律人的法律思维逻辑规则;三是提升法律逻辑规则的抽象性和系统性,建构面向计算机专家系统的抽象法律论证规则。②参见魏斌:《法律逻辑的再思考——基于“论证逻辑”的研究视角》,《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因此,这两种意义上的新型法律逻辑构成了动态思维和静态思维的统一。一方面,由于法律逻辑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工具和方法,所以,它必须探究法律运作过程中特有的逻辑现象和逻辑问题。法官在法律适用的各个阶段, 如确认案件事实、寻找法律、解释法律、作出裁判等,都要结合各个阶段的具体要求和目的,运用逻辑方法分析、解决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从而使逻辑方法成为行之有效的、符合审判工作需要的思维工具。另一方面,法律人正确进行法律思维活动,不但要遵守制度性的法律规则,而且还要遵守思维性的法律逻辑规则,使法律概念明确,法律判断恰当,法律推理有逻辑性,法律论证有说明力。①参见郝建设:《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特征与功能》,《政法论丛》2005年第5期。
那么,新型法律逻辑的适用对象与基本体系是什么呢?对此,我国学者的观点可以划分为3种:一是将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司法裁判,法律逻辑的体系建构多围绕法律推理、法律思维展开,以至于法律逻辑被等同于司法逻辑;二是将立法和司法同时作为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立法负责解决法律概念和体系的建构问题;司法负责事实发现、法律发现或法律获取、诉讼主张或判决结论的证成问题②参见王洪:《法律逻辑研究的主要趋向》,《哲学动态》2009年第3期。;三是将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扩展为立法、司法和法教义学,但认为法律适用是法律逻辑的典型适用领域。③参见雷磊:《法律逻辑研究什么?》,《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笔者认为,新型法律逻辑贯穿于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法律逻辑的适用对象不应固守于法律适用,而应拓展到科学立法、司法裁判和法教义学等各个领域。
科学立法是一国法律体系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准之一。作为科学立法原则的核心标准,合逻辑性在立法中扮演着“理性监督者”的角色。科学立法应遵守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 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例如,同一律要求,立法及其后对相关法律概念和术语的法律解释要力求确定同一,前后一致、新旧相通,从而使立法在形式结构上形成用语规范严谨的统一整体。充足理由律要求,立法者应当对立法理由和立法规划进行充分的论证调研,对法律文本的内容、措辞、内容关联性、重复性,以及冲突可能性等进行严格逻辑考量,从而确保立法的可行性、必要性。④参见冯玉军、王柏荣:《科学立法的科学性标准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因此,科学立法首先是逻辑立法,逻辑立法必须做到法律词项的明晰性、法律命题的恰当性以及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完备性和可判定性。同时,立法还是一项实践理性事业,其理性不是笛卡尔所说的演绎性的,也不全是休谟所说的归纳性的,而是佩雷尔曼所言的论证(argument)理性。立法的科学性并不在于对普遍性规律的把握,而是在过程中所实现的 “理性地立法”,它尤其体现为立法者要展现其在立法过程中是如何理性地行动,立法的理性结构就在于立法者如何实现对其论证义务的承担。⑤参见洪冲:《科学立法的法理探微:基于理性概念嬗变的分析》,《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2期。因此,“逻辑立法”之“逻辑”,并不必然是指形式逻辑,它还可以是非形式逻辑或论证理论。⑥参见熊明辉、杜文静:《科学立法的逻辑》,《法学论坛》2017年第1期。
立法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法律规范命题适用于真实个案并解决实际法律纠纷。法律逻辑在立法领域的提前介入,不仅可以确定科学立法的逻辑准则和基本方法,揭示逻辑在立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还可以为立法和司法提供一种“沟通之维”,建立面向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的立法逻辑,预防可能出现的司法逻辑问题。在逻辑学术史上,命题逻辑、谓词逻辑、类逻辑、组合学、模态逻辑、量子逻辑、道义逻辑、关系逻辑以及模糊逻辑都曾作为法律规范的适用条件、立法概念、法律规范(体系性)结构与性质以及法律关系等问题之“形式分析”的逻辑手段,不过,道义逻辑迄今仍被认为是最常用、最有效的研究工具。运用道义逻辑,不仅可以建构一种特殊的规范逻辑和立法逻辑,而且还可以探索法律概念的逻辑分类,揭示法律规范命题的可废止性,分析法律规则之间的文本关系或句法关系。①See Giovanni Sartor, Legal Reasoning: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Law,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p.208.
司法裁判是学界公认的法律逻辑的适用对象,也是法律逻辑研究的“基本原型”。不过,既有的以司法裁判为参照的法律逻辑研究存在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以克鲁格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法律逻辑是形式逻辑规则应用于裁判领域的理论,是推理形式的一些集合,企图将法律推理的形式结构与内容要素分割开来②参见 [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而以恩吉施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认为,法律逻辑必须从法律思维独特的实质性结构开始生长,法律逻辑主要是一种非形式的逻辑,并且将法律逻辑的非形式部分描述为一种方法论与认识论。当代法律逻辑的发展早已证实,实质性—逻辑性的考察与形式逻辑立场紧密的联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③参见[以]约瑟夫·霍尔维茨:《法律与逻辑:法律论证的批判性说明》,陈锐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在新兴交叉学科的影响下所兴起的多元法律逻辑形态,为我们协调形式方法和非形式方法之间的隔离和对立提供了有效的操作方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塑造一种既兼顾语义、语形维度,而又强调语用维度,并整合逻辑、修辞、论辩三要素的司法逻辑系统。
此种司法逻辑主要研究两种推理类型:事实推理和法律推理。事实推理,是围绕事实争点和证据争点所展开的推理,旨在确认证据事实,并基于证据事实确认案件事实,以此作为裁判小前提,从而为司法判决准备事实上的根据和理由。对于如何理解事实推理以及其中的相关性概念,沃尔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事实推理作为一种动态的、受规则约束的、目的取向型会话,并增添了对于回溯法和似真推论的分析,从而为我们理解事实推理各步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洞见。④参见 [美]道格拉斯·沃尔顿:《法律论证与证据》,梁庆寅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引论8-13页。法律推理,是围绕法律争点所展开的推理,其又包括两类不同的推理:一类是“有关法律的推理”,即确定什么是可适用的法律前提的推理;另一类是“根据法律的推理”,即根据寻找到的法律前提推导裁判结论的推理。前一种推理又称为法律获取推理,它不是为了产生逻辑上精确的判断,而是为了得出合理的判断。因此,这种推理主要是一种“探索型”推理,具有非形式逻辑或论题逻辑的特点,它的推理图式主要包括“类比推理”“反对推理”“正面推理”“归谬论证”等“准逻辑论证”。后一种推理又称为法律适用推理,其主要任务是将确认的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转换为法律论据,并运用不同论证型式推导、证成法律适用结论。因此,它主要是一种“论证型”的推理。
在法律论证理论视域中,人们把法律适用推理进一步区分为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在此背景下,人们对法律适用推理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对确定性结论的探求,转变为对更为精致的推理结构和过程的关注。法律适用中的演绎推理一般是在内部证成的环节进行的。内部证成的复杂模式显示出,涵摄的过程往往不是简单的三段论形式,而是含有多个前提的推论。外部证成是法律适用推理的焦点,也是法律适用推理的核心主题。外部证成的中心问题是:按照法教义学的标准,在内部证成中所运用的论据是否可以接受?外部证成的出现显示出,当代法学家开始超越传统的逻辑形式与逻辑推演,而将个案法律前提之价值判断及论证问题,纳入研究的视域。因此,命题逻辑、谓词逻辑、现代符号逻辑公式、真值函项运算等形式逻辑的适用场域主要是“内部证成”,用于法律适用推理的形式化或系统化,而修辞学、语用学、辩证法、论题学、言语行为理论、商谈理论等非形式逻辑的适用场域主要是“外部证成,负责法律适用推理的合理化。
除此之外,严格执法、法庭论辩、裁判文书说理、刑事侦查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法律逻辑现象,这些法律活动在实质上也属于法律逻辑的研究领域。法律逻辑不仅仅是面向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实践逻辑,同时,还是面向法教义学的应用逻辑。不过,“逻辑的哪些作用,能出现在及理性地出现在法学的领域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方面,应明了存在着明显的怀疑,即它不仅对法律逻辑学的效用能力评价甚低,而且也指出法律和法学‘逻辑化’之可能的风险。”①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页。法教义学与司法进行的是同类型的思维运算,法教义学同样应该纳入新型法律逻辑的研究范围。法教义学是一门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而不加怀疑的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体系化与解释工作的规范科学,而体系方法本身就是一种逻辑的运用:它决定了某一系统语形与语义的特点,并且,人们要在这一框架之内描述论证的合理性程度。②参见[以]约瑟夫·霍尔维茨:《法律与逻辑:法律论证的批判性说明》,陈锐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在任何逻辑系统中,都能够发现这3种要素:一是要有一个形式上特定的语言;二是要有关于这种语言的解释,即它的形式语义,其中每个合式公式都指定了它为真的含义;三是要有一个超越该语言而定义的推理装置,一般而言,这个装置打算只用来证成哪些根据语义有效的推论。③参见[荷]亨利·帕肯:《建模法律论证的逻辑工具:法律可废止性推理研究》,熊明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伴随着不同逻辑观念的影响,法教义学本身的思维形式和作业方式一直在进行调整或变化。为了尽可能满足形式逻辑的要求,概念法学试图以“法学实证主义观”为基础,纯粹从体系、概念和定理中推导出法条及其适用,而不容许考虑任何法外要素。由于这种法教义学完全将重心放在概念建构和体系化上,人们仅需将案件涵摄于普遍的教义学定理之下,就可以通过逻辑运算获得正确裁判。然而,法教义学并非单单立基于形式逻辑之上。④参见雷磊:《法教义学与法治:法教义学的治理意义》,《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在语义学、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诠释学、商谈理论、认知科学、修辞学、非形式逻辑等的不断冲击下,自由法学、利益法学、自由法学主张抛弃传统法教义学及其逻辑技术,并在道义逻辑、非单调推理、关系逻辑等新逻辑工具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新法教义学。⑤参见雷磊:《什么是法教义学?——基于 19 世纪以后德国学说史的简要考察》,《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4期。此种法教义学在吸纳其他学科知识和评价的基础之上,主要进行如下3种法律逻辑操作:一是将法律概念作为“具体概念”“类型概念”或“原型范畴”进行分析,运用道义逻辑、关系逻辑、人工智能、非单调推理等新逻辑工具,刻画法律概念的“开放结构”和可废止性,从而建立可修正的法律概念体系/法律规则体系;二是借助价值逻辑、语用逻辑、论证逻辑等挖掘法律规范背后蕴含的利益、价值、道德等实质性要素,从而建构与“概念—命题体系”相对应的“价值—原则”体系;三是运用关系逻辑、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逻辑工具,建构“为了描述内部体系、满足概观和运用上的需要通过秩序概念的编排建构由秩序概念、分类以及讨论的先后顺序等所形成的学术性体系”⑥参见吴从周:《概念法学、利益法学和价值法学: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即犯罪论体系、请求权体系等具有检索功能的法教义学知识体系。
在交叉学科的影响之下,新型法律逻辑已经突破了法律推理的研究范围,开拓了一种多元分层的研究对象,法律逻辑体系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拓展。法律逻辑对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法教义学等都发挥着根本作用,虽然它们进行的未必是相同的逻辑操作,但是它们却共享着一种广义的法律逻辑概念。法律逻辑对自己适用领域的扩张并不会导致逻辑的泛方法论,而只是将法律逻辑这把“锋利的剃刀”①美国法学家莱曼·艾伦认为,法律逻辑是法律思维的“一把锋利的剃刀”,See Layman E.Allen, Symbolic Logic: A Razor-Bdged Tool for Drafting and Interpreting Legal Documents, Yale Law Journal 66 (1956-1957).施展到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广阔领域。法律逻辑研究领域的这种结构,同时也平衡了法律逻辑的实践面向和理论面向。法学逻辑、立法逻辑和司法逻辑尽管在刻画对象上存在一定的重合,但它们探讨的是不同面向的逻辑问题,建构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法律逻辑分支。
三、融入法律方法提升法律思维合理性
法律逻辑是一种真正的哲学逻辑,其探讨的不是自我封闭的逻辑体系对于法律的可适用性问题,而是由法学自身提出来的逻辑问题与任务。②参见雷磊:《什么是法律逻辑——乌尔里希·克卢格〈法律逻辑〉介评》,《政法论丛》2016年第1期。法律逻辑可以突破形式逻辑公理和基本概念的研究,延伸到法律方法论领域。法律方法既是一种实践性的司法裁判操作,也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活动,倡导什么样的法律逻辑思维,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方法。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法律方法都与逻辑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利益衡量等具体法律方法都是为法律推理做准备的思维活动。虽然法律方法不完全是逻辑,但都离不开法律逻辑的形式约束。③参见陈金钊:《探究法治实现的理论——法律方法论的学科群建构》,《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法律逻辑本身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不仅规定了法律思维的必要条件和过程,而且还从根本上塑造了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范式。同时,当面对法官、律师等法律人时,抽象的法律逻辑规则只有通过法律方法论的“媒介”,转换为语用形式的法律思维规则,才能作用于他们实践性的法律判断和推理。因此,法律方法论不仅要充分地考虑法律逻辑的帮助和借鉴,同时法律逻辑也需要法律方法论的引导。④参见张斌峰:《法律逻辑研究对象新论》,《政法论丛》2008年第5期。在新兴学科的帮助下,法律逻辑几乎已经拓展到法律获取、法律检索、法律解释、法律修辞、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所有的法律方法领域。
法律发现是指在一定的法源体系内,发现或建构与具体案件相关的裁判规范的一种方法,即所谓的“找法”“法律获取”和“法律检索”。法律发现并非完全是理性的逻辑推论的过程,在本质上有别于“单纯的”法律适用,但是,法律发现中的非理性要素需要借助逻辑工具坦率地进行理性分析。⑤参见 [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获取的程序——一种理性的分析》,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6页。首先,法律发现需要在一种体系性思维的指引下进行,法律决定要尽可能从一个由实证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组成的体系当中通过逻辑的手段,而无需法官自己的评价被推导出来。“如果通过对程序条件、请求权基础、抗辩等材料的体系化使法学能够为法官更彻底和清晰地掌握,则法发现过程可以更迅速和可靠地进行。”⑥[德] 莱茵荷德·齐佩利乌斯:《法哲学》,金振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法律渊源的分类体系以及优先规则,基于法律逻辑的系统化功能,可以为法律发现搭建一种高效的检索程序。法律发现过程中一旦出现逻辑性的冲突,则需要借助“上位法先于下位法”“程序法优于实体法”“规则先于原则”“特别法先于一般法”等融贯性论述⑦参见[荷] 伊芙琳·T.菲特丽斯:《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判之证立理论概述》,张其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3页。,以及法律规则之间的“一般—例外”的逻辑关系⑧See Giovanni Sartor, Legal Reasoning: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Law,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p.208.才能获得解决。
其次,当制定法出现“违反计划的不完满性”,法官需以造法的方式进行法律发现时,仍然需要类比推理、正面推理、反面推理、设证法、回溯推理这些“准逻辑推论”来担保法律体系的统一性或融贯性。
最后,法律获取即使出现了必需运用论题学、直觉和法律感等问题性思维的情形,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过程。论题学作为一种寻找前提的思考方式,只有经由逻辑学的处理转换为一种形式论题学,才能够更有效和更清晰地提出和组织论据。而在找法过程中,“直觉通过获取法条、形成初始结论为法律推理提供前提,逻辑自动化型直觉还可以省略认知过程、快捷获得结论。”⑨李安:《司法过程的直觉及其偏差控制》,《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同时,法律逻辑还有助于司法大数据的结构化处理,消除司法数据之间的冲突或冗余,建构可检索的法律知识体系,从而建立智能化的法律检索程序。
法律解释是通过它彻底的理性本质与那些直觉的解释形式加以区别的,它不是神秘的或者不可思议的解释,也不是深层意义的体现,而是逻辑的解释。⑩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由于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在不解释情况下要形式化法律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律逻辑对不同的法律解释总是开放的。[11]参见[荷]亨利·帕肯:《建模法律论证的逻辑工具:法律可废止性推理研究》,熊明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逻辑连同语法、历史和体系构成了经典法律解释的4种基本要素。逻辑存在于从法律形成的视角对其内容进行理解的过程中,更加关注立法者制定的文本所具有的逻辑自足性,其意在强调反映于制定法文本中的立法者思维的划分及其地位、思维与思维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以及前后一致性。[12]参见姜福东、陶卫东:《论法律解释的逻辑要素》,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页。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守“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基本逻辑原则,实现法律解释的后果的“逻辑上的一致性”,同时还要满足融贯性要求,即实现(1)逻辑上无矛盾;(2)拥有高度的无矛盾可能性;(3)解释论点之间拥有相当数量相互强烈逻辑蕴涵的关系;(4)只有少数无法说明的异常状况;(5)提供某种对于法律相对稳定的理解方式,且此种理解方式能维持融贯性。[13]Leonor Moral Soriano, A Modest Notion of Coherence in Legal Reasoning: A Model for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Ratio Juris 16, 2003.
同时,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所内隐的矛盾性也需要在法律逻辑的框架之下进行解决。“法学方法论之于法律解释方法位阶问题的主流观点内隐着矛盾性,即一方面认为各类法律解释方法之间不存在典型的并列关系,另一方面又否认它们之间可以被固定的位阶谱系所表述。”[14]王夏昊、吴国邦:《论法律解释方法抽象位阶的作用及其逻辑结构》,《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其实,在法律论证的理论视域下,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抽象位阶可以根据可废止性逻辑重构为一种非单调的优先关系,也就是说,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只能获得一种初步的推定(prima facie presumption),一旦存在更强的实质性理由,这种优先性关系便可以被推翻。不仅如此,法律逻辑还在法律解释规则的构造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诸如“明示其一、排除其他”(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 Alterius)、“严格解释规则”“同类规则”(Ejusdem Generis)、“反面解释规则”(argumentum e contrario)、“常义规则”“黄金规则”(Golden Rule)、“语法和句法规则”“禁止冗余规则”“一般/特殊规则”“有限例外规则”“不得创设例外规则”等法律解释规则主要是在借鉴道义逻辑、规范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15]See Scott Jacob, Codified Canons and the Common Law of Interpretation,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98, Issue 2 (January 2010).
除此之外,随着法律逻辑的“实践转向”,法律逻辑与法律方法的内在交融与互动,法律解释研究也随之发生了“论证转向”。在论证逻辑看来,所有的法律解释都应该以论辩的方式展开,解释本身就具有商谈(Diskurs)的特点。[16]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整个法律解释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法律论证,无论法律解释中运用何种方法,都要将解释的根据、理由、所运用的方法等阐释出来。尤其当大量涉及立法目的、宗旨、历史资料的考证等时,更需要通过论证来证明解释者的观点。①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2页。在法律论证逻辑的框架下,所有的法律解释方法都转换成了法律解释论据,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也转换成了不同法律论据的选择问题。法律解释不再意味着“对已完成之物的回溯性探寻”,而应该以对正当化理由的寻找为引导。法律解释逐渐摆脱了纯粹的规范取向,越来越注重法律解释的说理性和可接受性。同时,广义非形式逻辑框架下的法律逻辑还为“独断性”的法律解释建构了一套多主体、可废止的论辩模型,法律解释规则由此也重构成了法律解释的论证型式和法律论证规则。从现代逻辑、非形式逻辑、法律人工智能汲取的洞见被用来阐述或建构法律解释之正确性标准的规则。法律论证大有取代法律解释而独大的趋势,这首先体现对传统司法三段论的批判,用逻辑或修辞的说服力来论证法律解释过程的合理性,可以说,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展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和融合性。②参见陈金钊:《法律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0页。为了更深入地挖掘法律解释背后的认知规律、语用特点、价值判断等,我们还可以对法律解释进行语用逻辑、价值逻辑、认知逻辑和智能逻辑等方面的理性分析。
逻辑与修辞尽管在表达形式与表现方式上有很大差异,但它们往往都旨在通过推理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都是被用于论证的一种形式。在当代法学理论中,修辞作为论辩的一种,它和逻辑范式之间的对立关系已得到很大缓和。③参见焦宝乾:《逻辑与修辞:一对法学范式的区分与关联》,《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在法律推理过程中,需要通过修辞将开放的前提集合论证为可接受的封闭性前提集合,也需要通过逻辑根据封闭的前提得出必然的结论④参见张传新:《法律修辞与逻辑》,《求是学刊》2012年第3期。,法律修辞与法律逻辑呈现出了相互影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的趋势。“布局”(Dispositio)、定义、三段论、矛盾律、命题演算法、类比推论、反面推论以及正面推论等逻辑工具,经常被法律修辞作为“基本设备”(rhetorische Grundausstattung)使用⑤Vgl. 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 C. F. Müller, Juristischer Verlag, 2006, S.238-410.,同时,法律逻辑还有助于识别诸如“前提短缺”“前提间的自相矛盾”“语义性错误”“语用性错误”等法律修辞中比较容易出现的本体论谬误(Die ontologischen Fehlschlüsse)⑥Vgl. Fritjof Haft, Juristische Rhetorik, Alber, 1995, S.130-152.,从而帮助提升法律修辞的理性说服与论证的功能。除此之外,为了迎合法律修辞的可争辩性和对话特点,司法三段论等传统的逻辑图式还可以改造成各种修辞罗各斯,例如,司法三段论的涵摄可以改造为这样的法律修辞构造:(1)修辞者;(2)听众;(3)被涵摄的小前提(das zu subsumierende Besondere);(4)接受的大前提(das aufnehmende Allgemeine);(5)涵摄过程(den Vorgang des Subsumierens);(6)修辞语境(rhetorischen Situation)。⑦Wolfgang Gast, Juristische Rhetorik: Auslegung, Begründung, Subsumtion, Zweite,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 l age, R. v.Decker Verlag, 1992, S.16.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逻辑是最具说服力的一种修辞;修辞也是在无法直接进行演绎推理时所备选的逻辑。⑧参见张传新:《法律修辞与逻辑》,《求是学刊》2012年第3期。
不管是在实践的领域,还是在理论的领域,法学涉及的主要是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⑨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1页。因此,法律逻辑不仅仅指形式逻辑,而主要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理性化也需要借助法律逻辑来实现。法官的价值判断必须在司法三段论的框架内进行,必须确定大前提,并在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连接过程中进行价值判断。①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1页。价值判断必须通过特定的程序和论证过程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虽然我们无法用经典逻辑的方法证成价值判断的合理性,但可以通过论证的方式来实现。价值判断拥有一种不同于形式逻辑的逻辑基础,即非形式逻辑的基础。在新修辞学、非形式逻辑、商谈理论的加持下,法律逻辑发展出了一套主要用于价值判断的论证逻辑。在非形式逻辑的意义上,价值判断方法即是以价值权衡的方式进行说理和论证,它始终伴随着裁判者的论证义务,价值判断的妥当性也需要通过论证来证成。作为方法论的价值判断,“惟有以实体性的论证规则为前提,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方可达致相互理解,也才有可能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就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形成价值共识”②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6期。。同时,价值判断的条件、价值判断的边界、价值体系的分类、价值位阶的判定以及价值衡量的标准诸如此类的操作程序的探讨也需要法律逻辑的介入和协助。
与价值判断一样,法律逻辑也应该增强对利益衡量方法的渗透和参与。利益衡量本身无法取代三段论的操作,法官只能在三段论的框架之内进行利益衡量,必须针对特定的文本进行利益衡量,而不能脱离文本进行所谓的“法外利益衡量”。为了解决“异质利益衡量的公度性难题”,伴随着法律逻辑的“论证转向”,利益衡量方法经过重构变成了“后果导向的论证”。“后果导向的论证”也是以特定的体系和逻辑为导向的,并且也是按照教义学的结构进行相应的构筑,它仍在立法性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限度内运作,法律裁判的连续性和融贯性(Konstanz und Kohärenz der Rechtsprechung)仍会被实现。③Klaus Mathis, Folgenorientierung im Recht, in: Michael Anderheiden, Stephan Kirste (Hrsg.), Interdisziplinarität in den Rechtswissenschaften: Innen-und Aussenperspektiven, Mohr Siebeck, 2012, S.6-7.在非形式逻辑中,存在着大量的与“后果导向的论证”相近的论辩型式,例如“根据后果的论证”“目的—手段论证”“工具论辩”“因果论证”“实效论证型式”等。④参见武宏志、周建武、唐坚:《非形式逻辑导论》,人们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549页。
逻辑与论证的关联性,不仅在法律理论领域,也在一般逻辑理论和科学领域被强调。法律论证至少在其核心范围显示了或必然显示为三段论的结构,以至于逻辑推论和法律论证很大程度上被等同。逻辑规则尽管替代不了实质的论证,但却可以给法律论证设置界限,因此,逻辑规则对法律论证具有当然的约束性,违反逻辑准则的法律论证,在法律上也是错误的。⑤参见 [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律论证学》,张青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8-19页。法律论证研究中,最为悠久的方法就是逻辑方法。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某一法律论证之可接受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支持该论证的论据必须是逻辑有效的论据,另一个条件是,支持某一证立的理由依据法律标准是可以接受的。只有当某一论据在逻辑上有效时,才能从法律规则和事实前提当中得出裁判结论。在许多学者看来,形式逻辑对法律论证具有基础性的和实践上的重要性。形式逻辑不仅限定了由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条件,促成了基于证立的论述的重构,以及论证中隐含要素的明晰化,而且它还提供了一种分析和评价法律论证形式向度的批判性工具。但是,形式逻辑并不能提供用以评价法律论证实质向度和程序向度的规范,逻辑有效性只是论证的合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⑥参见[荷]伊芙琳·T. 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6-37页。,要全面评价法律论证,还需要引入语用逻辑、价值逻辑、论证逻辑、认知逻辑等建构法律论证的实质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从而争取法律论证合理性的最大化实现。
法律逻辑不仅可以将法律论证嵌入一种实践认知,进而将法律论证的不同方面整合进一个广阔的图景,而且在各种逻辑分析技术的合力下,提供一个关于法律论证图式的更精确的说明。新型法律逻辑不再将逻辑局限于单调的形式逻辑,而是转向更广阔的法律论证,考察合理性论证所蕴涵的逻辑内涵与推理规则。新逻辑观视野下的法律论证研究,一方面可以理清法律论证中隐含的推理论证进路,探讨其中合理信念的产生与迁移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将法律论证纳入实践理性的分析框架,对法律论证进行更深入和细致的逻辑刻画。除此之外,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法律逻辑还能够从论证框架和论证语义两个层面探讨法律论证的形式模型,从而拉近抽象论证模型与自然论证的距离①参见梁庆寅、魏斌:《法律论证适用的人工智能模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为法律推理和论证建立一种广义模态框架,更为理性地掌握法律获取、法律解释、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法律证成等法律推理活动。
当前,法律逻辑和法律方法已经呈现出了交叉融合的趋势。不管是“遵循规则”的法律方法,还是“超越法律”的法律方法,法律逻辑都可以找到参与的空间。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法律方法论的理论面貌,在法律逻辑的推动下法律方法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而获得了更多的逻辑有效性和合理性,同时,法律方法也对新型法律逻辑的发展起着催化剂的作用,法律逻辑获得了从法律思维的实质性结构开始生长的机会,使得其研究内容愈加贴近法律人的自然论证实践。可以预见,在非形式逻辑和形式论证理论交叉融合的背景下,“论证逻辑”将更加理解和适应法律思维的理性特质,其理论的革新和深入也必将引领和启发法律方法新的研究方向。②参见魏斌:《法律逻辑的再思考——基于“论证逻辑”的研究视角》,《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四、结 语
法律逻辑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新兴的、正在快速成长的交叉学科。法律逻辑的拓展不仅跨越逻辑学、法理学和法律方法论,而且涉及语用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不同的学科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用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为法律逻辑学开辟了“形式”“语用”“价值”“论证”“认知”和“智能”等彼此竞争的研究进路,从而相应地生成了多元法律逻辑形态,并在整合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等逻辑工具的基础上,塑造了一种新型法律逻辑系统。这种法律逻辑具有两种平行的意义,一是作为思维活动的新型法律逻辑,另一种是作为思维规则的新型法律逻辑。在每一种意义上,新型法律逻辑都对传统法律逻辑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新型法律逻辑的适用对象不再局限为法律推理,而是延伸到了立法活动、司法裁判和法教义学等诸多不同的领域。法律逻辑的研究领域和理论体系由此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拓展。同时,为了提升法律思维的逻辑合理性,在新兴学科的帮助下,法律逻辑作为典型的工具性学科,还需要拓展到所有的法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