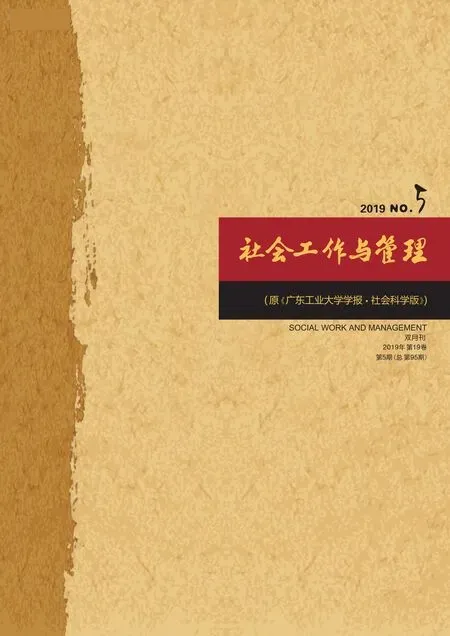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一项社会工作历史视角的知识观考察
童 敏,辛峻青,骆成俊
(1.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2. 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广东 深圳,518000)
一、问题提出
任何职业都有它的专业关系要求,以便指导和规范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社会工作也不例外,作为一种职业在服务中也需要建立专业关系。不同的是,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的职业,目的是增进个人的福祉和社会的公正,专业关系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服务的开展和服务的成效,因而专业关系一直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关注,称为社会工作的“灵魂”[1]。有学者甚至把人际关系作为社会工作的核心,强调社会工作需要重新回归社会关系这一幸福感产生的本源。[2]180但是,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环境中开展专业服务的职业,时刻都能够察觉到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双重关系”成为无法回避的伦理难题[3],尤其在一些需要长期陪伴的服务中,情况更是如此。[4]到目前为止,如何处理“双重关系”仍是众说纷纭。
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社会工作进入了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的关键期,如何保持良好的专业关系已成为需要面对的难题[5-7],它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社会工作的进程[8],而且也直接关乎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发展路径和方向的选择[9]。因此,本文将围绕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这一“双重关系”进行探索,从历史视角出发考察西方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双重关系”的演变历程以及处理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西方社会工作的知识观进行讨论和分析,以便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路径和方向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
虽然有关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双重关系”的讨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是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专门针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开始探究。由于当时西方社会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20年代之后,社会工作开始转向人际关系的处理,关系在专业服务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最早提及服务中人际关系的是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W. Odum),她在1926年提出,社会工作是帮助人们“在迷失的人际关系中寻找、恢复和发展的过程”[10]。而另一位学者弗兰克•布鲁诺(Frank Bruno)则更明确地指出,“修复那些遭受破裂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工作唯一的治疗手段”[11]。这样,“社会工作处理的就不是社会环境或者人的性格,而是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它的目标也不是改变社会结构或者个人的人格,而是随着服务的推进,让人们能够发现、维持和使用建设性的人际关系”。[12]
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深入和专业知识的积累,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工作的专业化逐渐成型。[13]专业关系作为专业成熟的标志之一,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例如,普尔曼(Helen Harris Perlman)在1957年出版的《个案社会工作:解决问题的过程》一书中专门列出一章就个案工作的专业关系开展讨论,认为良好的专业关系具有多种治疗的功能,是服务对象成长改变不可缺少的条件。[14]有的学者甚至直接指出,正是因为专业关系在社会工作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与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动态关联,使得社会工作有别于其他职业,良好的专业关系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不仅是有益的,而且还是必需的。[1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有关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个案工作领域,通常认为良好的个案工作关系可以促使服务对象在服务中感受到温暖、体验和建立新的建设性的关系、承担个人的责任、认同周围他人、接纳相互之间的差异、促进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化。[16]就个案工作专业关系的要素而言,尽管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有的认为是6个,即服务对象自决、态度友善、非评判、适当的情绪介入、促进服务对象的成长和保密[17];有的则强调是7个,即个别化、有目的的情感表达、适当的情感介入、接纳、非评判的态度、服务对象自决和保密。[15]23-120但是他们都认同,良好的个案工作关系至少表现为3个方面:服务对象的自决;社会工作者的接纳、不批判态度和适当的情感介入;保密。
显然,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有其自己的独特要求,“不同于自由自在互相享受的朋友关系,为了提高服务对象的生活福祉,社会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主动将专业关系当作服务的桥梁”[18]。因此,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职业关系,比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关系更具有控制性和目的性”[19]。除了控制性和目的性之外,有学者指出,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还需要“将服务对象的需求和福祉考虑在内”。[17]16这样,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也就具有了助人的特点。实际上,这种助人的专业关系不仅能够更好地“帮助服务对象调整自己与周围他人的关系”[15]12,而且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工作者的自我反思以及对专业关系的警觉”,避免专业关系中的权力失衡和歧视现象的存在[20]。
仔细分析个案工作中的这种专业关系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理性把控关系的能力;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注重情感交流的朋友关系正好相反,要求社会工作者时刻警觉自己与服务对象的交流,保持适当的交往距离;既能够采取不批判的态度,接纳服务对象,也能够遵守保密的原则,促进服务对象的自决。至于适当的情感介入,也只是为了让服务对象信任社会工作者。由此可见,在个案工作看来,专业关系与日常生活的朋友关系根本不同,社会工作者需要从日常生活中的朋友关系中抽离出来,与服务对象保持可以理性把握的清晰的交往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个案工作中的这种专业关系之所以能够存在,与社会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机构服务的方式是分不开的。[21]30正是在这种机构服务方式中,服务对象才能够从日常生活中走出来主动来到服务机构寻求帮助,与社会工作者形成一对一的专业关系,而此时社会工作者也只关注服务对象在机构场景中提出的服务需求。[22]
三、“双重关系”中的专业关系
20世纪60年代之后,社区工作开始受到社会工作者的青睐。一方面因受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影响,人们逐渐相信,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21]39另一方面在西方政府的倡导下,社区工作逐渐推广开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府开始大幅度消减福利服务的经费开支,这迫使社会工作者走向社区,学习挖掘社区的资源。[2]83-87社区工作不仅涉及的利益群体比较多样,而且服务形式也更加丰富。如何加强社区弱势人群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社区的资源以及如何协助社区弱势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做好早期预防,就成为社会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难题。[23-25]此时的社会工作者已经从关注个人和家庭转向社区,必然需要面对社区弱势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复杂的人际张力,而要在此时保持像个案工作中那样的清晰明确的专业关系界限,显然是很难做到的。正是因为如此,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有关专业关系界定中的矛盾困惑的讨论,专业服务中的“双重关系”成为社会工作者讨论的焦点。
所谓“双重关系”是指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象保持专业关系的同时,还与服务对象建立了商业伙伴、雇佣、朋友或者性伴侣等专业之外的关系。[26-27]这种“双重关系”会破坏服务对象的自决权,削弱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地位,[28-30]甚至还可能出现借助专业关系谋取个人私利的不当行为。[31]因此,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的“双重关系”通常被认为是有害的,需要加以制止。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在2018年制定的“道德守则”标准中就对如何处理“双重关系”做了明确规定:“由于存在对服务对象进行剥削和其他潜在危害的风险,社会工作者不应与服务对象或者之前的服务对象建立双重或者多重关系。在双重或者多重关系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服务对象,并且需要负责设定清晰、适当和具有文化敏感的交往界限。”[32]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专业服务中涉及与性有关联的双重关系已经得到共识,认为是不合适的,[26,33-34]但是就其他的“双重关系”而言,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的相信这是不道德的,需要避免;[26,35-36]有的却强调这种“双重关系”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一味地禁止,只会适得其反;[37-39]甚至有的声称这种“双重关系”是社会工作所特有的,反映的恰恰是社会工作的“人在情境中”的基本服务原则。[40-42]
显然,在社区工作中,要划清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的界限并不容易,因为社会工作者需要走到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特别是在农村或者偏远的社区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时,情况更是如此,社会工作者根本无法从熟人的关系中抽离出来。[36,41]实际上,农村社区的社会工作者经常需要参与社区的各种其他社会活动,加入社区中的其他社会组织。[29,43]同样,在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社区环境中社会工作者也始终需要与服务对象保持“双重关系”,甚至有些时候,对于专业服务的推进而言,朋友关系比专业关系还要重要。[26,44]
随着专业关系讨论的深入,有些学者逐渐发现,划清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的界限实际上并不一定有利于专业服务的开展,在社区工作场景中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根本无法撇开朋友关系来开展。[43,45]因此,过分强调专业关系的清晰界限,只会增加社会工作的难度,给社会工作者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使社会工作者在成功借助朋友关系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之后,仍会感到来自专业服务方面的压力、担心和内疚。[46-48]此外,也有些学者直接从实务层面寻找更灵活有效的应对方法,他们关注社会工作者如何与服务对象家庭成员交往、如何呈现自己的会心微笑和手势以及如何参加社区的婚丧嫁娶等。[49-50]有的学者则强调,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遵守一种潜在的互惠原则。[51]
西方社会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遭遇的“双重关系”的冲突,反映了专业服务从机构走向社区时面临的困境: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需要走进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与服务对象建立起信任的朋友关系,在了解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需求基础上开展专业服务;另一方面又需要与服务对象保持一定的交往距离,维护专业服务所需要的专业关系。由于西方社会工作是从机构延伸到社区的,因此,专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就成了专业服务的主线,而朋友关系只是专业关系实现的辅助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社区中开展专业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不仅具有专业身份,而且同时也拥有相对完备的专业服务系统作为专业服务开展的支撑。
四、朋友式的专业关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开始推崇多元福利服务制度,走多方参与的“第三条道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也因此出现了综合的趋势,除了机构服务走向社区之外,社区服务也不断被引入到机构中,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出现了双向流动,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更有弹性。[2]83-87一项有关2003年至2008年英国社会工作伦理投诉的调查显示,40%的行为纠纷涉及到社会工作者的“不恰当关系”。[52]显然,原有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界限迫切需要修正,因为任何有效的关系往往都需要具有友谊的品质,绝不是“非黑即白”。[48,53]
这种“非黑即白”的专业关系不仅受到社会工作实践者的质疑,同时也面临来自社会工作理论界的批评,那些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工作学者把服务对象视为服务对象自己生活的“专家”,强调服务对象的主动参与是服务对象创造自身成长改变不可缺少的环节。[54-55]这样,服务对象在整个服务过程中的自主性、参与度和尊严水平等,就成为促进个人成长改变的必要条件,专业关系变得更加人性化,常常与朋友关系融合在一起,无法截然分隔开来。[56-57]有的学者称这种新型的专业关系为“平等的”职业化。[52]
徐明心等人提出,社会工作不同于其他助人的专业,社会交往能力是其核心的技能,通过这项技能的使用社会工作者才能与服务对象建立起必要的信任关系,开展专业的服务。他们强调,这种信任的关系包含许多友善、亲密等类似朋友式的友谊特质,而这些特质是成功干预的基础。因此,他们提倡社会工作者使用一种具有参与性、包容性和反思性的方式来创造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的边界;同时,社会工作者始终需要保持对专业角色的警觉意识以及对个人行为的适当限制,在专业服务过程中巧妙呈现“专业距离”。[58]当然,在以关系为导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中,专业关系的边界就更为复杂和模糊,社会工作者除了需要与服务对象建立这种复杂的专业关系外,同时还需要与服务对象的亲属以及服务的社区建立这样的复杂的专业关系。[59]
显然,运用单一、标准的方法应对这样复杂的专业关系是很难做到的。有学者直接放弃“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原则,将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比作是“有弹性的橡皮圈”,强调社会工作者需要在专业服务中根据具体的情况调整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的界限,而无法预先给定一个明确的标准。这个“有弹性的橡皮圈”一头是“客观的专家”,另一头是“有用的朋友”,而大多数的专业关系则处于两者之间。[56]因此,有学者呼吁在社区的场景服务中把朋友式的友谊直接作为专业关系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当作专业关系的另一面。[60]也就是说,在社区的场景服务中社会工作者需要一种朋友式的专业关系,而这种专业关系往往通过与服务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长期互动来实现。[61]正是借助这种朋友式的专业关系,不仅服务对象能够获得成长的空间[62],而且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也能够取得最大化的服务成效[4]。
尽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社会工作“双重关系”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不仅专业关系影响着朋友关系,朋友关系也在影响着专业关系。那种“非黑即白”的专业关系界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人们越来越转向弹性的处理方式,让社会工作者能够结合具体场景的要求,将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融合在一起,避免因过分关注专业关系而导致损害服务对象的利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一阶段的“双重关系”是一种朋友式的专业关系,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但是实际上专业关系仍然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交往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整个服务的目标也是借助专业关系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面临的问题。
五、中西“双重关系”内涵的比较
从历史发展的简要回顾中可以发现,西方社会工作的“双重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明确清晰的个案工作的专业关系发展出社区服务中的含混不清的“双重关系”,再从这种含混不清的“双重关系”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的弹性处理的朋友式的专业关系。显然,西方专业关系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从机构服务到社区服务再到综合服务的路径,这样的发展路径使得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出一种以机构服务为基础、能够同时覆盖机构服务和社区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
尽管从形式上看,目前中国本土社会工作遭遇的含混不清的“双重关系”与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工作在社区开展专业服务的遭遇相似,但是实际上两者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是在社区自然场景中开始专业服务的试点和探索的,这也意味着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将从社区服务中延伸出机构服务,然后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综合服务,让服务能够同时覆盖社区服务和机构服务。由此可见,目前中国本土社会工作遭遇的“双重关系”是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并由此发展出机构服务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它不仅与社区场景服务相关联,而且也与之后需要发展的机构服务相联系。因此,如何在社区场景服务的“双重关系”中发展出专业服务就成了社会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仔细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之间已经建立起专业化的个案工作,其中包括标准化的专业关系。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西方社会工作者不仅具有稳定的专业身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且也初步拥有了专业化的服务系统,形成不同类型的服务系列。因此,西方社会工作者在进入社区开展专业服务时的状况与中国社会工作者是不同的,两者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社会工作者既没有明确的专业身份,社会的知晓度很低,也没有相对完善的服务系统,很难实现服务的转介。对西方社会工作者而言,他们在社区服务中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将专业服务延伸到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而对中国社会工作者而言,他们在社区服务中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生长出专业服务。
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工作的“双重关系”与中国社会工作的“双重关系”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对于西方社会工作来说,专业关系是主导,朋友关系是辅助,服务的目的是借助朋友关系维持专业关系,从而实现专业服务。中国社会工作就不同了,朋友关系是主导,专业关系是辅助,服务的目的是通过专业关系融入朋友关系,从而帮助服务对象有效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显然,西方社会工作是以专业关系为主轴来定位朋友关系的,专业关系是专业服务开展的基础。而中国社会工作正好相反,它是以朋友关系为主轴来定位专业关系的,专业关系依赖实际服务成效的实现。
总之,中西方“双重关系”的内涵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与中西方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差别也意味着中西方社会工作的路径选择和方向选择也将有所不同,它们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知识观作为选择的支撑。
六、中西专业关系的知识观分析
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要求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保持适度的“专业距离”,它明显受到医学模式的影响,追求一种科学实证理性,强调专业权威[58]。尽管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工作开始关注朋友关系的重要性,甚至称专业关系是一种朋友式的专业关系,但是它仍旧认为,专业关系注重客观性和技术性,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朋友关系。一旦两者混淆,就可能妨碍服务对象的成长改变。[49]这种专业关系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相信人们的行为可以被客观地观察、分析和研究,从而能够从中概括出客观的行为规律,不受个人的主观爱好和偏见的影响,而专业关系也就因此拥有了保持价值中立的“专业距离”的要求。[56]
显然,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是以实证理性为基础的。它推崇的是一种抽离具体场景和时间的普遍化、规律化的知识,假设现象背后存在事物的本质,通过对事物本质的了解,就能够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这是一种专业知识,不同于生活经验,存在于日常生活经验之外,依赖这一领域专家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积累。[63]33而这种专业知识只有借助专业的关系,才能将社会工作者拥有的专业知识输入给服务对象,协助服务对象解决面临的问题。[55]41这样,专业身份和专业服务系统就成了这种专业关系能否建立和维持的基础。一旦社会工作者失去了专业身份和专业服务系统的依托,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与服务对象建立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专业关系,专业服务也就根本无法实现。[64]
实际上,这种追求普遍化、规律化的实证理性的知识,本身就遭受很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65]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社会工作领域也开始反思实证理性知识存在的困境。[66]对于社会工作来说,这种知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经验的忽视。一旦社会工作者追求抽离生活场景的普遍化知识,就会忽视服务对象自身拥有的日常生活经验的知识,看不到这些知识对于服务对象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重要性。[67]第二,对专业关系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的忽视。尽管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很多种办法让服务对象参与服务过程,与自己进行平等的对话,将朋友关系与专业关系融合在一起,但是实际上,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就是存在权力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社会服务机制的结构决定的。如果看不到专业关系背后的社会结构,就会陷入表面平等的“公平陷阱”中。[68]第三,对服务对象自决能力的忽视。这种实证理性的知识只注重专家的经验,要求服务对象按照“科学”的专业标准采取行动,忽视服务对象对自己生活的自决能力,根本无法实现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的目标。[55]55有学者声称,这种实证理性知识的根本假设,是认为任何事物背后都存在本质。[69]
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有学者开始认识到事物背后未必存在本质,知识是人们建构的过程,要求建立一种以日常生活为本的知识。[70]这种知识注重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且以此为基础探究社会结构的影响,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改变紧密结合起来。[63]29这种知识也注重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通过对话交流让服务对象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处境,认识到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当然,这样的认识是需要借助服务对象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能力才能实现的。因为只有当服务对象投入到自己的生活场景中,通过对自己日常生活经验的反思以及相关联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分析,才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生活提出的挑战。[63]41显然,这种知识与实证理性根本不同,是融入具体场景的特定时间和场域中体验和把握生活变化规律的知识,是一种场景实践的知识。[63]40
仔细观察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服务就会发现,目前我国本土的社会工作者在专业服务中既缺乏专业身份,也缺乏完善的专业服务系统作为支持,很容易把这样的处境理解成类似于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初期,也就自然按照西方社会工作所要求的标准处理专业服务中的“双重关系”。实际上,西方专业关系的处理依据的是实证理性的知识观,需要以专业身份和专业服务系统为基础,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使社会工作者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依照西方社会工作的实证理性的专业标准做不出来;另一方面依照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经验开展的服务又看不到专业性。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需要选择另一种知识观,即场景实践的知识,深入到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以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经验为核心来处理专业服务中的“双重关系”,借助日常生活中专业关系的建立,在日常生活场景的实践中带动服务对象应对日常生活挑战能力的提升。
七、总结
通过对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发展历程的历史回顾可以发现,专业关系从西方社会工作产生之初就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主题。尽管在开始阶段专业关系主要表现为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它与人们的日常朋友关系有着清晰的分界线,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社会工作者走进服务对象生活的社区开展专业服务时,朋友关系就成为专业关系建立不可缺少的条件。特别是在一些关系比较紧密的农村社区或者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熟人社区,情况尤其如此,使得专业服务中的“双重关系”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成为社会工作无法回避的难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多元福利服务的推进和综合服务的实施,“双重关系”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非此即彼”的专业关系的二分原则已经无法适应专业服务的要求,将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融合在一起,采取朋友式的专业关系方式弹性处理具体场景中的专业服务要求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的基本共识。
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机构的个案服务到社区服务再到综合服务的历程。尽管他们在社区服务中面临的“双重关系”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相似,但是两种的内涵却有本质的差别。西方社会工作的“双重关系”的处理是以社会工作者的明确专业身份和完善的专业服务系统为前提的,依据的是抽离日常生活经验的实证理性的“专家”的知识观。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就不同了,社会工作者既没有明确的专业身份,也缺乏完善的专业服务系统作为支持。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需要选择场景实践的知识观来处理专业服务中的“双重关系”,借助日常生活中专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围绕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经验,推动服务对象应对日常生活挑战能力的提升,走一种从社区场景的服务到机构服务再到综合服务的自己的专业化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