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有个迟子建
卢美慧
先声夺人
起先,她非常干脆地拒绝了当面采访的请求。发邮件可以,有问必答,这是多年以来迟子建对待大多数媒体采访的习惯,邮件省事,你也省得跑一趟,而且像钱锺书先生说的:“干吗非要看看下蛋鸡呢?”
后来答应见面是记者无意中说了大学时学的是物理,迟子建好奇心上来了。见面地点在哈尔滨一家东北菜馆,不知是不是永远保持好奇心的缘故,隔着一屋子的喧嚣和热菜上桌时飘散开来的水汽,迟子建的眼睛放着亮亮的光,“物理?我就一下子很好奇,一个关心文学的姑娘,学物理,她是什么样的。”
迟子建有东北女人天然的爽利亲切,叫上几个她认为最有特点的东北菜,招呼服务员上了两瓶啤酒,“你来哈尔滨,一定要尝尝这儿的啤酒。”菜陆续上桌,每一道她都能说出门道,声音也亮,直冲冲的干脆,又很爱笑,作家阿来形容迟子建的笑声,一群作家扎在一起,“她给我的印象总是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听见她在某一处和人交谈,但你总是会先于其他人的声音而听到她的。更多的时候,人还没有出现,就听见她爽朗的笑声,预告她的出现。”
迟子建自己说,如果不当作家,她大概会是个好的农妇。写了三十几年,文坛热闹过也冷清过,迟子建倒还真像个守着时令的农妇,春种秋收,不疾不徐地维持自己的节奏。
许多年前,苏童写他眼中的迟子建,“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
2018年5月,迟子建出版新书《候鸟的勇敢》,这个伴着松花江上的黄昏写成的故事,讲述了在东北一座小城栖息停留的候鸟和保护它们、扑杀它们的人类之间的种种纠葛,一如既往的迟子建。2018年迟子建还收获了三个语种的翻译书,分别是瑞典语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英文版的《晚安玫瑰》,还有泰文版的与莫言的一个合集。
对于“收成”,迟子建很淡然。新书《候鸟的勇敢》除了参加了首发式,其余推广活动都推掉了,海外译本也是,出版商希望她能参加一些活动,都谢绝了。
对外界的热闹,迟子建有本能的抗拒。饭桌上一口菜一口啤酒的间隙,迟子建说:“海外翻译这一块,我觉得作家应该还是把它看得淡一点更好,别觉得多了几个语种,好像自己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作家,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变成一种烟花,绚丽一时,立刻就寂然无声。对吧?吃菜吃菜,这个鱼要多吃。这个豆豉鸭也很好吃。”
不在潮流之中

30多年的写作,迟子建用超过600万字的体量建立起一个美丽与苍凉并存的文学王国。我们在她的笔下总能看到,北国满世界的大雪,冰冻或奔涌的河流,自由自在的鱼,生生不息的树,飞鸟与野兽,鲜花或云朵,风的声音,星空的低语,清凛的月色,虽然人在烟火和红尘之中,但迟子建的笔下,“自然”一直作为永恒的背景承载着一切,注视着一切,当然也抚慰着一切。
作家梁鸿非常喜欢迟子建的作品,她认为迟子建最了不起的是,“她的作品具有独有的‘风景,这个风景要打引号。”梁鸿解释,“风景”指的是一个内部景观,是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她并不是说只是为了写异域的风景而写风景,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迟子建的书写解决了客观风景和人的生存场景之间的关系,风景要和人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形成一体化的存在,风景也是人,人也是风景,对吧,它们俩互为存在,互相彰显对方。”
出生于同样辽阔壮美的四川阿坝藏地,阿来珍视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我喜欢迟子建的小說,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小说里面有自然,中国不少小说里只有人跟人的关系,看不到自然界。”
2015年,迟子建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驻校作家。后来,莫言和苏童主持了一场迟子建作品研讨会。
迟子建不怎么喜欢研讨会的形式,“一开始我拒绝,我不喜欢研讨会,但我无法取消,因为它是规定动作,每一个驻校作家,苏童、余华、贾平凹、格非,他们都有一场研讨会在北师大,我去我也要必须(参加)。”于是这个研讨会,成为了迟子建步入文坛30年后,第一个作品研讨会。
研讨会上,苏童说起迟子建作品的与众不同,“大多数中国文学的作品在看待现实时采取批判、尖锐、狠毒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这种作品容易引起注意和阐述。迟子建最不容易的是一直用美好的、温情的眼光看待人、事、物、世界。”
作家李洱和诗人欧阳江河都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在处理恶、反讽和批判的问题,实质上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不满。欧阳江河说迟子建正是从这一层面努力超越,尝试从更大层面对现代文明做出评价。“美可以跟很多东西构成复义关系”,欧阳江河强调,迟子建的美跟一般的美不一样,“她把美推到极善的程度,把人性缩小,从而得以从终极意义来考虑问题。”
几年后,在哈尔滨的饭桌上,迟子建说外界的声音其实很难影响到她,当记者向她复述其中的某些观点,迟子建忽闪着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有吗?是不是我当时溜号儿,我怎么不记得了?”说完把筷子探向她爱吃的鱼,很是专注地享用她的晚餐。
残酷之后呢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力是迟子建长期的读者和研究者,她认为一路写下来,迟子建的写作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北中国的冰雪给予她的韧性和开阔,“在这个高寒的纬度之上,有作家对于生命的独特的体验,就是说雪国这样的一个,就是北方的洁白的这样一个雪乡,使她瞬间在这个天地间的广阔,这种洁净,广阔的这种美,使她笔下的景物是独特的,不仅带有生命的这种悲悯,同时也带着北方的那种生命的韧性。”
郭力觉得,温情的标签是对迟子建的误解和不公平。迟子建一直试图回答“残酷之后”的命题
郭力覺得,温情的标签是对迟子建的误解和不公平。她认为,迟子建一直试图回答“残酷之后”的命题,残酷之处比比皆是。她写《额尔古纳河右岸》,写被现代文明挤迫和围堵的鄂温克民族,写他们风雨雷电之下百年民族悲歌,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时代风云之下人必须要承受的残酷命运,迟子建描写的死亡之密集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与此同时,“残酷之后呢?”她一定把笔触延宕出去,写他们的顽强,写他们在命运面前的坦然。
“不是说迟子建她回避残酷,她不回避,生命的悲哀这些,那种大的悲痛,人性的龃龉之处,她都没有回避。”但即便生活这个样子,人间这个样子,迟子建还是爱着脚下的土地,郭力觉得这是土地、故乡和书写者关系的迷人之处。
郭力觉得文学的价值或魅力正在于此,一方面它是虚构的,一方面它又最大限度地再造了某种真实。从这一点上,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余华之于浙江嘉兴,刘震云之于河南延津,苏童、毕飞宇之于江苏水乡,迟子建之于东北雪国,“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
迟子建对美的最初认知,当然来自她的家乡。迟子建写过太多关于故乡的片段,其中有一则是,“当我童年在故乡北极村生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那么大。当我成年以后到过了许多地方,见到了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
迟子建的父亲爱喝酒,爱写字,会拉小提琴和手风琴,是一位豁达又浪漫的小学校长,她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在1964年,大多数国人争着给孩子起名“卫红”、“卫东”、“志国”的年月,因为很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父亲给二女儿取了“子建”的名字。母亲则“坚韧又慈悲”,大兴安岭半年时间都是冰雪,雪特别大的时候,母亲在房间里看着外面的鸟儿发愁,雪把世界盖住,那鸟不都饿死了么。她就隔着窗子给鸟儿撒米吃,鸟们受够了人类的捕杀,开始不愿意落脚,后来一只两只陆陆续续过来,母亲高兴得不行。
对于荣誉和热闹,迟子建一直看得淡泊。她是中国文坛唯一一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并且获得过一次茅盾文学奖,一次冰心散文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摘下茅盾文学奖的那年,回到哈尔滨下飞机后被家乡的记者围住谈感受,迟子建脱口而出最希望的是采访赶紧结束,马上回到原来的生活。
倒是2011年在北京参加活动时一份特别的礼物,她每次都特别骄傲地跟外界分享,因为“迎灯”的乳名,她的读者们自称“灯迷”。2010年,来自不同城市的60位灯迷,给迟子建送上了一本墨绿色封面的厚书,60位读者把20万字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抄了一遍,有心的读者还在空白处画上小说中出现的驯鹿、树木和溪流。迟子建喜欢得不行,她把这部独一无二的手抄本摆在书柜上,正对写字台,写得疲惫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
自我
迟子建有自己的小顽固。她至今不用智能手机,一个磨掉烤漆的老款三星手机已经用了十几年,“能接发短信,能联系朋友,不就够了吗?”她有微博,但只在电脑上用,一直没有微信,对一个小软件营造的天涯若比邻的幻象没有兴趣,“生活够喧嚣的了,作家对于这个世界,既要倾情拥抱,又要有所保留,因为艺术是需要距离的。既要多听,又要少听,有意识地屏蔽一些东西,保持心灵的自由和独立。”
在科技越来越将人类大一统的当下,这样的自我常常制造一些小插曲。前年去西班牙参加文学论坛,在飞机上苏童笑她,“你等着吧,都智能时代了,你下了地面肯定没信号。”到了西班牙,“有信号呀。”迟子建很雀跃地描述当时的情景,可是今年到了新加坡,她的老款手机就失灵了。
前阵子迟子建去哈尔滨当地一家俄罗斯面包店买面包,一共二十几块钱,付钱的时候,俄罗斯小伙儿说,他们不收现金,只能支付宝或微信,迟子建轴劲儿上来了,跟小伙儿理论起来,“你还担心钱是假的吗?二十几块钱的面包,我至于去骗你吗?”
跟人们通常理解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作家不一样,迟子建对烟火人间爱得不行,尤其爱吃
这很像2015年的那次研讨会上莫言对迟子建的描述。1987年,迟子建和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一起进入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莫言说,“当年在北师大研究生班的时候,迟子建是我们小师妹,年龄很小、很高傲、脾气也很大,惹不好她会动手‘打人。”
聊到这一段儿,迟子建来了精神,搭配着标志性的笑声,“他那是调侃,我怎么会打人,哈哈。”她说起属于这群作家的80年代,大家凑到一起,真的会认真聊文学,那时莫言和余华一个宿舍,“嗯,他们的房间很有灵性,出了两位大作家。”
迟子建的室友是女诗人海男,她口吃,但挡不住对文学的热情,每每写完了就给迟子建朗读。
“那就是文学的青春,无论怀念还是遗忘,它不会与我们重逢了。30年代有位歌手叫白光,她有首歌叫《魂萦旧梦》,其中有句歌词‘青春一去,永不重逢,我很喜欢。”
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问迟子建她对这40年中文写作的评价,干脆利落的八个大字,“大河奔流,泥沙俱下”,除此之外,不愿多言。
过去了就过去了,她还是要写下去。大约是骨子里沉寂的风雪发生着作用,迟子建对一切突然的热闹都抱有一份怀疑,“80年代的文学热当然不可复制,留下了一些代表性作品,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泡沫,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80年代我们在文学准备上并不很充分,也就是说在80年代的文学大合唱中,歌唱票友多,而真正具备歌唱家素质的不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作家会歌声渐淡,后劲乏力。”
这很像经历了一场高烧,退烧之后,大体能检验出人们对文学的忠诚。
迟子建是忠诚的那个。“如果一开始写作,有人告诉我你会写三五十年,我会吓一跳,觉得那会是一种苦役。可是写作伴我走过30多年的时光后,我陡然发现,没有写作,我在人生的一些关隘上可能会倒下。”
“勃勃的生氣”
写作是迟子建抵御人生荒寒的武器,也给了她应对命运时必须的顽强。
王安忆也说起过迟子建的笑,“我最先是从照片上认得她,那时还没看她小说呢。看照片就觉得她很会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疯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笑,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写出好东西,然后我看到了她的小说。我不是说她小说写得如何完美,我就觉得她有生气,这真是叫勃勃的生气。”
但命运似乎瞅准了这个有着勃勃生气的东北女人,一定要伺机给她来那么致命的一下。迟子建刚过20岁就失去了深爱的父亲,至亲过早离场,让迟子建早早就意识到人生的苍凉。

迟子建在华中科技大学作题为“求经之路”的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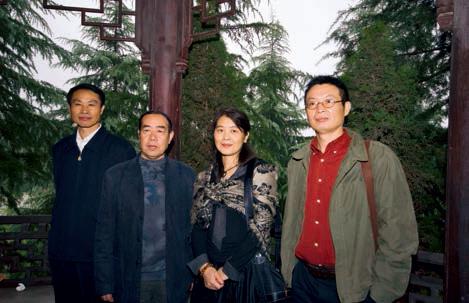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新闻发布会后,周大新、贾平凹、迟子建、麦家合影
2002年5月,迟子建结婚不满四年的丈夫又因为一场意外车祸身故。在人生中最甜美的时刻,命运一下子把迟子建推进又一场暴风雪中。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办公室副主任罗纯睿在那一年前后进入作协工作,之前,她是迟子建的读者,但并未谋面。回忆第一次见面,罗纯睿记得当时在作协一楼,迟子建穿一件墨绿色的长裙,很美,“就是眼神很忧郁的样子,但还是很美。”罗纯睿当时并不知道迟子建家中的事,几年之后,她读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当时我怀孕,我看那本书,我哭得啊,那本书我是一宿看完的。”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写于丈夫去世之后,开篇第一句,迟子建写,“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见我的哀伤。”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悲痛难抑、感觉被命运遗弃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一位魔术师,因为车祸离开人世,带着悲痛,她决定前往曾与丈夫相约一起去的三山湖。一路上,这个一度自以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见证了世间的种种苦难、悲哀和死亡,主角蒋百嫂,甚至连大声哭一哭的机会也不曾有。若是按照小说创作的定式,故事停在蒋百嫂命运的最悲哀处或是很多创作者的选择,但迟子建继续往前走,遇到一对经历不幸的父子,故事临近尾声,“我”由小男孩带着,到森林里一处最清澈的溪流放河灯,祭奠故去的亲人,矗立在溪流边,“我”拿出魔术师的剃须盒,将一直保存的残留的胡茬儿送进水流。“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
故事的最后,“我”再一次打开剃须刀盒,“一只精灵般的蓝蝴蝶飞出了剃须刀盒,落在她右手的无名指。”
罗纯睿觉得迟子建身上就是有这种乐观和生命力,“换我们一般人,一个事给你打击得,你就狼狈得不行了。她从不狼狈。”罗纯睿说起陪央视做迟子建节目,到过她家里,家被她收拾得特别清爽干净,很多书,但不杂乱,居室挂着她随意画的小画,画里是她钟爱的山川树木。
迟子建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罗纯睿曾看着迟子建在家中忙忙碌碌,打点一切,“后来她说我这一辈子,其实我能做一个非常好的贤妻良母,我什么都会,但人生没能给我这样的机会。”罗纯睿至今记得迟子建当时的表情,不是凄凄然那种,很平静,很淡然。
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司兆国原是省委机关的干部,到作协工作之前,他心里想,“这个著名的女作家,会不会不好打交道?”但共事后,司兆国在迟子建身上也发现了那种勃勃生机,作协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要负责全省的文学工作,常年写作让迟子建的颈椎腰椎都落下了毛病,但“她从没有说太累了,或我要写书了,就推托什么,她能平衡得很好”。司兆国和迟子建住同一小区,有时候碰到了,她买个花儿什么的回来,都很高兴,“她是真的会生活,爱这个生活。”
阿来写过跟迟子建转机时的见闻,“在机场等待下一个航班,用了9个小时,说了多少回话,喝了多少回咖啡和茶,又逛了多少遍候机楼里的免税店。每逛一遍,这个有点购物狂的迟子建,都要买一两样什么,好像她对守着冷清店面的店员都深怀同情。”
“阿来把我写得,买东西啊还有那个笑,写得跟王熙凤似的,其实哪有那么夸张。”迟子建笑着为自己辩白,但很快顺口就说出来,在阿根廷机场看到一个玉质的小鹿摆件,“很好看啊,下次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就买吧。”又一次,看到一件墨西哥的小花毛衣,还是“很好看啊,下次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就买吧”。
她还爱电影。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在哈尔滨排片很少,迟子建一查,离自己住的地方好远,溜达着坐地铁去,影院所在的地铁站离医院很近,她观察了一路那些被生活摧折的面孔,想说不定他们中的某个人会成为之后小说人物,最后在一家藏在装饰材料城内的有点老旧的影院看了《小偷家族》,“很不错。没白跑一趟。”
跟人们通常理解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作家不一样,迟子建对烟火人间爱得不行,寻常日子里的迟子建爱吃,这是打小儿的习惯,小时候的她会去偷腐乳,把小指头伸进去抠出来吃。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因为食堂伙食不好,她从外面买那种很多刺儿的鲢鱼,用电热杯煮着吃。
采访中的文学问题,迟子建兴致一般,好像没什么特别可说,但说到吃,她像分享武功秘籍似的说起自己新近发明一道菜:新鲜的柚子拦腰切成两半儿,把果肉挖出来,把柚子壳儿当容器,放进糯米和叉烧鸭,再切上一点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去蒸,时间一到,柚子的香气,叉烧鸭的香气,全部都沁到糯米里,“哎呀,那个味道真是太棒了。”
总的说来,迟子建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唯一不满意的是,今年哈尔滨只下了一场小雪,也没那么冷,“这还叫东北吗?”
不管是在文学世界还是现实世界,迟子建一直笃信万物有灵,不知道是不是听见了她的抱怨,采访结束次日,迟子建发来信息,“哈尔滨下雪了,还不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