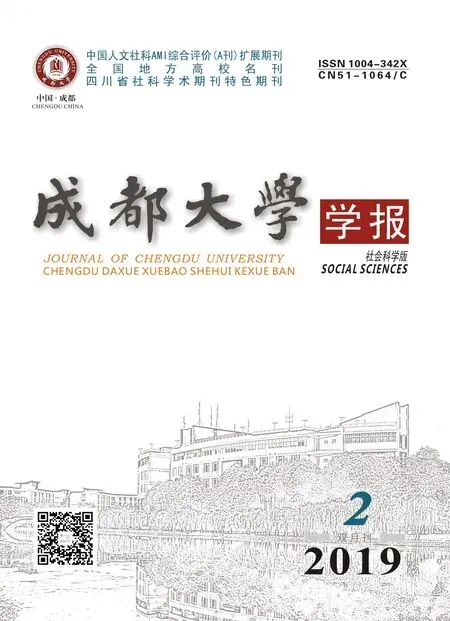穆时英小说电影化视角下的人物*
高雅迪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武汉 050024)
穆时英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在日本新感觉派中找到源头,其作品也受到电影艺术的影响。当时穆时英所在的上海拥有全国最出色的电影产业。穆时英是忠实的电影爱好者,也是最成熟的电影评论家之一,他善于从艺术的角度分析电影,他本人的小说中也能寻到电影手法的蛛丝马迹。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塑造人物,穆时英塑造人物的方法也受到了电影艺术的影响,笔下的人物有较强的电影化色彩。
一、电影化的人物出场方式——“行为出场”
在小说中,人物出场方式一般可粗略分为“自出式”和“引出式”。
“自出式”出场,就是让人物直接出场,让人物以自己独特的外形、语言和动作等做“自我表演”。如赵七爷在鲁迅《风波》里的出场,是从七斤嫂的眼中引出来的,细致描写了赵七爷的身形、衣着颜色;再如王熙凤在《红楼梦》中的出场,就是先有笑声,后有语言。
“引出式”出场,指本该正面描写某一人物,但作者故意作侧面描写,使此人物处于呼之欲出的情势后才“应境而出”。如贾宝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出场,是冷子兴与贾雨村闲谈引出的,黛玉来到荣国府,也是先让王夫人向黛玉介绍宝玉,又提到黛玉的母亲对宝玉的评价,这才让宝玉千呼万唤始出来。
而在影视作品中,人物出场通过具体画面呈现,不管有没有台词,都要人物做出行动,去说明自己。影视人物出场一般有两类:一是行为出场。在电影中常见,主要是让人物去实现一件事,并在此过程中有目的有方向地向观众呈现人物的特色、性格、来历等等。观众形成的是直观印象,比小说借助评语似的介绍更有冲击力。二是台词出场。这种出场方式在电影中少见,多见于电视剧和舞台剧、戏曲等。尤其是戏曲中,人物出场会“自报家门”,直接让人物自己用语言介绍自己。
以小说的标准来看, 穆时英笔下人物的出场也大体属于“自出式”的出场方式。但在上文所举的赵七爷和祥林嫂的例子中,“自出式”的出场方式是可以包括肖像描写、语言描写的,虽然人物是直接出场,但并不是用动作去表现。有时会通过其他人物的眼睛去表现,这就让读者和这个出场人物隔了一双眼睛,没有直观的冲击力。穆时英的作品中,人物出场的行动是最重要的,不少人物的出场几乎没有进行肖像描写和语言描写。他也不会对人物进行提前的介绍,而是把人物一下推到读者眼前。他笔下的人物一出来就处于一个场景中,在行动着,具有很强的画面感。更主要的是,他的作品常常省略叙述人,他自己是一个导演,读者就像观众,镜头呈现的就是观众看到的,这种直接的看到不是经过叙述人或者是别的人物的眼光,这一切仿佛就在观众眼前发生。虽然穆时英在写作时已经把表现出来的画面进行了主观化处理,并将他的感情融在里面,但人物的直接出场,而且是行为出场,不经过叙述人的眼光,读者会身临其境,直接体会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获得一种类似于看电影的体验。
如《空闲少佐》,少佐在第一段就已经出场:“一点儿不含糊的,就在空闲少佐的后边儿,手榴弹猛地炸了起来……神经纤维组织那儿像一万只蚱蚂在爬着那么的难受。一阵冷,觉得血顺着脊梁盖儿往下淌。”[1]又如《圣处女的感情》:“低下了头,跟在姆姆的后边眼皮给大风琴染上了宗教感,溅在滤过了五色玻璃洒到地上来的静穆的阳光上面,是安详地走进了教堂的陶茜和玛丽。”[2]再如《上海的季节梦》中刘有德的出场,也是这种出场方式:“徐祖霖仓皇地跨进金城银行总经理室的时候,刘有德先生还坐在华东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室里边,红蓝铅笔,报告书,账目,统计表,损益表,请客单横七竖八地堆在桌子上面。”[3]刘有德的名字在这之前从未出现,也没有任何人物提到过他,他的外形、语言也未进行展示。他一出场,就处于一个总经理室的环境,徐祖霖到刘有德的转变仿佛镜头的切换,刘有德被推到观众眼前,让观众直接去审视它。作者用环境表明他的身份,用桌面上乱糟糟的文件代表他的心乱如麻以及野心勃勃。人物出现得虽略显突然,但他的行动和场景一并在表现着他的心理,而且人物一出来,镜头就对准了这个人物,故事也就开始了,不像鲁迅《祝福》中祥林嫂出现时她的故事还未开始。所以,“行为出场”除了能给读者直观的电影式的体验,这种快捷的、直入主题的方式也有电影的艺术特色。
穆时英在《南北极》的集子中也有反例,如《黑旋风》:“汪国勋!这姓名多漂亮,多响!他是我们的老大哥……他孝极了他的母亲……”[4]。汪国勋的出场明显属于小说中的“引出式”。作者借叙述人之口介绍汪国勋的品行,人物没有直接出场,是一种类似于评价式的介绍,没有描绘出画面,直白的叙述性语言不能对读者形成直观的冲击力。这本文集是他最初没有受到电影化影响的作品,这也证明,电影艺术对穆时英小说创作的影响。
所以,穆时英受电影艺术特征影响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可以属于小说中人物的“自出式”的出场方式,但“自出式”的概念范围很大,它可以是行为出场,也可以是肖像出场、语言出场,不能完全解释穆时英独特的人物出场方式,而用电影中的“行为出场”解释则较为贴切,它伴随着叙述人的消失,并在同时具有电影化的出场方式直观、直入主题的优点。
二、电影化的色彩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诉诸于人的视觉。穆时英的小说中也常出现各种色彩,给人极强的视觉体验。其中与人物有关的色彩常起到塑造人物性格、心理的作用,是对人物的一种暗喻,并且带有主观化倾向。如《红色的女猎神》《墨绿衫的小姐》,人物衣服的颜色直接出现在题目中,证明不是可有可无的。“女猎神”的红色衣衫和Senorita的墨绿衫、墨绿鞋一直在诱惑着男主,也刺激着读者的视觉。浓烈的颜色充满着诱惑性,这种诱惑性既是这些女性赋予这件衣服的,也是这浓烈的颜色带给这些女性的。这种深色调的女性还有《白金的女体塑像》中的女病人也穿了一件暗绿色旗袍、《黑牡丹》中的舞女穿着黑色衣服。穿这种深色衣服的女性一般不会是未涉世事的小女孩,而是一个成熟、神秘的女人,它代表着一种性的诱惑。除了颜色本身独有的含义,如红色代表“女猎神”的野蛮等,这些深色调的颜色还有共同的特点:魅惑、神秘。
除了深色系,浅色系的运用也不在少数。如《圣处女的感情》中陶茜和玛丽穿着白纱的睡衣,床也是白色的;《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男主人公眼中不谙世事的女性穿着白绸的衬衫和嫩黄的裙;《五月》中最开始不会玩弄男人的蔡佩佩有粉红的丝带、白的裙子、绿的绸衫。浅嫩的颜色象征这些女性的天真、纯洁,她们的感情简单又隐秘,但是神秘度较之深色系的女性就少得多。
作者把自己对人物的想象外化成与人物有关的带有主观性的颜色,让观众得到视觉的体验而不是需要从文字上进行分析。电影中人物的服装十分重要,不仅是款式,颜色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色彩在电影中不只发挥写实功能,还具有造型功能和表意功能。不少导演会独具匠心地夸大某种颜色,起到塑造人物的作用。比如电影《山楂树之恋》,若把女主角的白衬衫换成其他颜色的衣服,就很难表现人物的清纯。穆时英精心设计了重要女性的代表色,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色系,人物所穿衣服颜色的多次出现,给读者留下强烈的直观印象,在视觉上首先让读者获得一种对人物内心的辨别,这也正是电影所擅长的。
除了这些可见的、具有实在颜色的衣服等,穆时英还经常把主观化的颜色赋予有固定颜色的事物,或者是心脏等不能外化的器官。在《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女主人公吐出的烟是莲紫色的;《PIERROT》中的女主人公有蔚蓝的眼珠子和蔚蓝的心脏;《圣处女的感情》中陶茜和玛丽有白色的心脏。这些颜色与写实的颜色一样可以表现人物的内在。如果说烟雾和眼睛的颜色还可以在电影镜头中表现,但心脏则不能外化成视觉体验。虽然这种描写是小说中的技法,但这种将主观感情外化的技巧却受到了电影视觉化特点的影响。这是穆时英写作时,将电影手法与小说手法结合的结果。
在电影中,镜头中的颜色要互相配合,或是进行对比。强烈的对比给观众的印象极深,可以突出人物特点,引导观众的注意。而且镜头常是移动的,所以颜色的表现也多变。穆时英在运用色彩时也常使用对比、变化的颜色。
对比可以是上面提到的深色系和浅色系的对比,暗喻不同的女性形象。同时这种颜色对比也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物身上。穆时英笔下的都市女性多画浓妆,《白金的女体塑像》中女病人“嘴唇有着一种焦红色,眼皮黑得发紫,脸是一朵惨淡的白莲”[5];《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的女人有黑眼珠子、红腻嘴唇,还穿了白色衬衫。这种白脸、黑眼皮、红嘴唇的浓妆强化了女性魅惑、神秘的特点。穆时英把女性的特征放大,完完整整地“画”出一张吸引人的脸。颜色的对比也可以暗喻一个人不同的个性或者前后变化。《上海的季节梦》中的玛莎“在秋天,她是紫色的,感伤的;在冬天,她是黑色的,缄默的;在春天,她是嫩黄色的,温柔的;在夏天,她是白色的,纯洁的,热情的,而且爱着我的。”[6]作者用诸多具有对比性的颜色刻画了一个捉摸不定,引男子追求的女性形象,而且这些颜色同时具有了变化的特点。在更细微处,作者喜欢描写人物眼睛的颜色,而且随着人物心境的变化,眼睛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红色的女猎神》中的女性“有着大胆的,褐色的眸子,笑的时候有着诡秘的,黑色的眸子”[7];《上海的季节梦》里的李玲仙“在太阳底下有着明朗的褐色的眸子,在和男子讲话的时候有着诡秘的黑色的眸子”[8];《Graven“A”》中的余慧娴“有两种眼珠子:抽着Graven“A”的时候,那眼珠子是浅灰色的维也勒绒似的……照着手提袋上的镜子搽粉的时候,舞着的时候,笑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她有一对狡黠的,耗子似的深黑眼珠子”[9]。由上可知,这些女性在高兴时、和男子交流时都是黑色眸子,黑色充满不可知性,有诱惑力和神秘感,宛如一口深井。而像余慧娴抽烟时的浅灰色眸子,则有一种忧郁感。穆时英在《电影的散步》中将风格演员分为两类:一类是神秘的,让人捉摸不定;另一类是性感的,开门见山式的。一般学者常将余慧娴归于第二类。如果按男性眼光来看,她的确是一个“旅行箱”式的女子,但在文中的“我”并没有把她完全当成一个旅行箱似的女子,反而是对她比较关心,而且余慧娴也对别的男人把她当做廉价品感到不忿。她的浅灰色的忧郁的眸子正说明了她的内心,她有着自己的痛苦,并不完全是一个“旅行箱”,而且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让人随开随关。这也说明穆时英并不是完全按照两类女性形象去塑造女性的,他笔下的人物更复杂,更偏向神秘,而且在《电影的散步》中他也更倾向于赞美第一类神秘主义的女性。
眼睛颜色的变化描绘了人物复杂的性格,突出了她们面对男性时的特点,和自己内心隐秘的感情,塑造了女性身上不同的个性。同样,这种诉诸视觉的表达方法,变化着的具有对比性的颜色,也像电影镜头似的把人物放映在读者眼前,让读者的感受更直观、真切。这样的颜色也像电影镜头一样,极易抓住观众的注意,引领观众由颜色变化探知主人公心理变化。
三、特写镜头和重复镜头
电影镜头有不同的景别和多样的拍摄方式。穆时英的小说中常用特写和重复镜头的手法表现人物,引导读者的注意。
电影镜头擅长表现生活的细节,从细处把握整体。按景别来说,电影镜头可以给出人物的特写,通常以人体肩部以上的头像为取景参照,突出强调人体的某个局部,或相应的物件细节;突出头像的局部,或身体、物体的某一细部,如眉毛、眼睛等,称为大特写,又称“细部特写”。在塑造人物时,穆时英常把“注意力”放在人物的脸部,突出眉眼和人物身上的装饰,用精细的语言定格一个特写或大特写镜头。如《五月》中蔡佩佩的“速写像”:“嘴角的那颗大黑痣和那眼梢那儿的五颗梅斑是他不会忽略了的东西”[10];如《骆驼·尼采主义者和女人》中让男主人公情不自已的女人“绘着嘉宝型的眉,有着天鹅绒那么温柔的黑眼珠子,和红腻的嘴唇”[11];再如《街景》中老乞丐的脸部特写“脸是褐色的,嘴唇是褐色的,眉毛也是褐色的——没有眼白的一张单纯色调的脸,脸上的皱纹全打了疙瘩,东一堆西一堆的”[12]。穆时英用特写细致地表现人物的面貌、神态,从细节处看到整个人,让读者近距离地感知人物的特点或者魅力。他一笔一划“画”出人物的五官,正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样清晰。而且在上文中,他专注于并且多次描写女性眼睛颜色,也是一个大特写。
除了人物的脸部特写,穆时英也不放过其他能表现人物的地方。他经常给出的特写还有人的鞋和脚。如《墨绿衫的小姐》中“在墨绿色的鞋上露了脆弱的脚踝”[13];《Graven“A”》中也多次提到余慧娴的脚是“两只黑嘴的白海鸥”[14]。人物的脚和她们的脸在文中男性看来,都是可以诱惑人的东西。此外,人物身上装饰品的特写也同样起着强调人物特点的作用,《黑牡丹》中的舞女头上“白色的康纳馨”一共被提到了五次,突出了人物的舞女身份,强调了她的迷人,同时纯洁又忧伤的白色康纳馨也是人物的象征。《白金的女体塑像》中的女病人“一副静默的,黑宝石的长耳坠子,一只静默的,黑宝石的戒指,一只白金手表”[15],这些首饰都被重点提及,不通过近距离的特写镜头是难以描绘得如此清晰的。黑白两色给人冷冰冰之感,让人物显得更加神秘,让文中的“医生”有心而不敢妄为。所以,特写在穆时英的文章中,不仅可以清晰地表现人物细节特征,发挥镜头似的引导性作用,还具有深刻的含义。
特写镜头在小说中的表现就是细节,其他的小说家也有类似于特写的描写,但如穆时英这般运用特写数量如此之多、如此密集的还是少见。他不把特写镜头单纯地当成一种表现,而是用它去塑造人物的内心。
穆时英还经常运用重复的镜头,表现人物心境,具有一闪而过的镜头无法拥有的特殊作用。《街景》中“站长手里的红旗,烂苹果似地落在地上”[16],这个“红旗”的特写在文中出现了两次。红旗落下,是火车开动的信号。第一次出现时,是主人公背井离乡,泪别亲人;第二次出现时,是他心灰意冷、对生活已经绝望,跃身于车轨之下时。烂苹果似的红旗暗示着这个无法使人谋生的世界的荒唐和肮脏,它的起落象征着主人公的命运波折。就像电影《看不见的客人》中多次出现的钢笔和表,具有象征性。再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季洁拗火柴的镜头出现了两次,而且第一次是着重描绘的。重复的镜头有力地表现了人物内心的挣扎迷惘,这种神经质的举动也反映了人物神经质的内心。唯其是重复的,才能让读者印象深刻,也才能取得深刻的含义。如果《看不见的客人》中的钢笔和表没有重复出现,就很难让人记住,也很难说这些道具具有象征意义。
穆时英的描写具有画面感,运用多样的镜头化手法,让人物立体起来,把画面真真切切展现在读者眼前。
四、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两性关系
穆时英代表的新感觉派在全盛期时,电影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穆时英等人的创作也受到了当时热映的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好莱坞电影具有娱乐化的特点,擅长表现都市男女在灯红酒绿的酒吧、舞厅等场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且多爱情题材。穆时英小说中的人物也多处于都市中,多有着孤独空虚的心理,是高度物化的人群,在面对异性时也显示出了放纵的情欲,放纵中又有着难以言表的愁闷。像《墨绿衫的小姐》《骆驼·尼采主义者和女人》《红色的女猎神》等众多小说都从或只从都市中的两性关系入手,去表现男女主人公,只有少数如《街景》这样的小说只有男主人公。穆时英的价值观也由男女两性关系中得以窥见一二。
虽然穆时英小说中的男男女女都患有孤独放纵的都市病,但男女的病因却不尽相同。男性各有各的痛苦,如《夜总会中的五个人》中胡均益为金钱而愁,郑萍为爱情而愁,季洁为哲学问题而愁,缪宗旦为职业而愁;再如《上海的季节梦》中李铁侯、徐祖霖、刘有德等人为事业、金钱、地位而焦头烂额或野心勃勃。女性的都市病因却多集中于爱情或和爱情有关的方面,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黄黛茜所愁之事就是自己的年龄和容貌,这是她获得爱情或放纵生活的资本;再如《墨绿衫的小姐》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为了爱情而喝醉,又倒在另一个陌生男子怀中;更有《Graven“A”》中的余慧娴、《黑牡丹》中的舞女更是不得不在爱情交际场中周旋,难以摆脱,也难以寻觅真爱。
这不同的病因与穆时英如何看待男女两性的关系有关。好莱坞电影中女性多作为展览的对象,女性的肉体美、行为美都在镜头的展示下一览无遗,而不管是影片中的男性还是观众席中的男性都被他们的美吸引着,同时评价着她们。穆时英的小说初看是女性作为主导,她们选择、玩弄着男性,《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的题目看上去男性似乎就处于劣势,《红色的女猎神》《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中的女性也把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中,有的还拥有众多的秘密情人。小说中也有很多表述女性身体美、以情色诱惑男性的片段。但小说的叙述角度却是从男性视角出发,小说中的“我”,也就是叙述者,多是男性,女性的身体美、魅惑,都是在男性眼中看到的,而女性所诱惑的对象也是男性,她们为男性而美、为获得男性的爱情而愁。
另外,小说中女性的心理描写极少,她们似乎只是一具具美丽而没有灵魂的肉体,如《白金的女体塑像》:“一个没有羞惭,没有道德观念,也没有人类欲望似的,无机的人体塑像”;再如《Graven“A”》中开头将余慧娴的身体详尽地展示为一幅地图。女性众多的外貌、神态和动作描写也正说明了在男性叙述者的眼中,她们也只是一些“人体塑像”“石膏模型”,是没有内涵的,尽管她们的内心会像余慧娴、“黑牡丹”一样,不满于自己被当成一个廉价品、洋娃娃,但并没有男性会去关注她们的内心。相比来讲,男性的心理描写更多。如《红色的女猎神》中时刻都在展示“我”遇到红衣女人的欣喜和欲望,其他涉及到两性关系的作品中,男性也一直在心里品评、思考着对面的女性,众多的心理描写也证明了女性在实质上处于被选择、被看的地位,男性才是真正的评委,掌握着女性晋级与淘汰的权利。好莱坞的电影把女性置于被观赏的地位,穆时英小说中也因其影响形成了表面上女性开放自主,实质上一切为男性服务的两性关系。
穆时英不仅是电影艺术的研究者,还把多样的电影技巧和电影中的价值观带入了自己的作品中,使自己的小说具有了电影化的创作手法。在电影艺术兴起的时代,穆时英抓住了时代特点,用新颖的手法使自己笔下的人物有了独特的“行为出场”的方式,有了属于自己的色彩,又用特写和重复镜头细致地描摹都市人的苦乐和病态,这样才有了他笔下不可替代的、立体的、视觉化的人物形象,也因此他才得以吸引众多读者,成为一代“鬼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