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与性别立场
郭冰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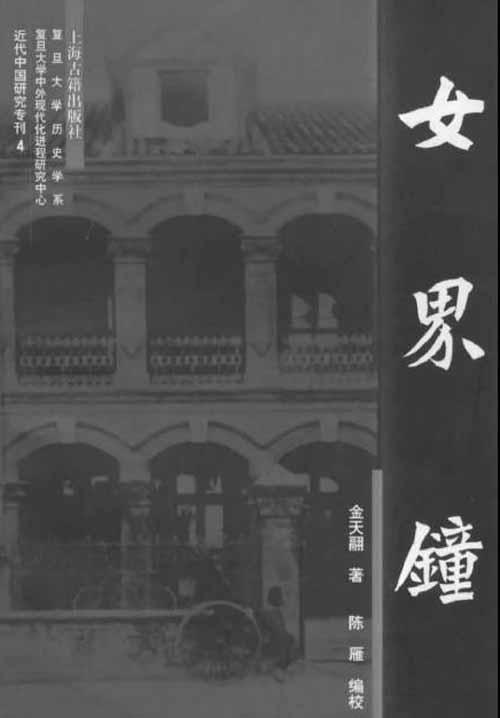
女性问题在中国或许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在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时,都应当正视其历史文化语境的复杂性,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性别立场对女性写作的影响以及相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因此,在以女性主义为理论支点,选择性别立场去观照历史、审视现实时,我们首先应该对晚清尤其是五四以来的历史语境清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如何论述中国女性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现成的结论是男尊女卑,女性不仅处于弱势的位置,而且没有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性别主体。我对这个概述性的结论并无异议,但是当我们以性别群体的概述来代替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时,便会发现这样的结论存在不少偏差。
比如我们认为女性在历史上没有政治地位,但秦汉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特别是贵族妇女,太后干预朝政就是汉代历史的一大特色,而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女性在社会中享有的权利都是不同的。所以五四时期讨论妇女解放会牵涉阶级,陈望道总结说:“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灭‘因为伊是穷人因而承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宗旨很是差异,要求也不相同。”而说到参政问题,在清代功名最甚的乾嘉时代,有功名的人也不过占全国人口的1%,虽然女性不能考取功名,学而优则仕,但男性能参政的比例也是微乎其微的。
在经济方面,我们认为历史上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没有经济能力,对婚姻和家庭的依附性非常强,而这是女性处于受奴役地位的症结。但是在唐代的一些户籍文书、赋役文书、契约文书或其他一些账目案卷的实际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女性户主,她们或者是寡妇,或者是单身女性,承担着赋税的责任,她们独立的经济地位为地方官府和左邻右舍承认,显然这个“内”与“外”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此外,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到了18世纪的清代,很多地区女性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男性。
在文化方面,女性受奴役受压迫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比如守节问题,明代官府提倡寡妇守节,但民间女性再嫁现象依然盛行,缺乏生活来源的寡妇为生计所迫往往选择再嫁,而她们的亲族、夫族也往往要求她们再嫁。清朝满族女子守节的很多,这与八旗制度保障寡妇生计有关。当然除了经济因素,夫妻的情感因素,女性的生理因素都构成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一些个案,我当然不能,也无意凭借这些个案来抹杀历史上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弱势地位这一基本事实。相对于浩大的历史,我想说的是,这些个案带来的问题,启示我们或许应该在性别立场中加入其他一些与性别相关或者无关的参照系。也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也不难发现,现代女性写作中呈现的性别问题不仅仅关乎性别本身,而是始终与晚清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元叙事相关联的,换言之,对性别问题的讨论深刻地打上了元叙事的烙印。
晚清的大变局,让女性解放成为可能。虽然变法维新与女权运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但二者之间的联系除了社会变革可能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影响之外,还得益于晚清维新人士将对女性解放的倡导与“强国保种”的国家诉求勾连在一起,由是女性解放的话题从一开始就被植入政治体制的变革之中。1902年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明确地体现了维新党人在“国家”范围内讨论“女性解放”的思路。这篇洋洋万言的长文将罗兰夫人安置在国民之母、文明之母和革命之母的圣坛上,供后来者学习和效法。当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让女性“受命于家”而与国家、民族绝缘时,维新人士把女性与“强国保种”联系起来便为女性走出家庭,登上社会舞台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合法性。这样的勾连一方面可以推动女性的解放,但另一方面也使女性问题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问题了。
“百日维新”之后,不论是倡导女子独立还是呼吁女子自省,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金天翮在《女界钟》中将爱国与救世认定为“女子的本分”;《女学报》的主笔陈撷芬强调女子应该自谋女学和女权,以“备教育后来国民之用”。随后,出现了大量出自女性之手,鼓吹男女平权和女子独立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各有侧重,但将女性解放与国家兴衰相连接则是当时的共识。而与此同时,女界也开始反省女子自身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些反省也是指向国家兴衰的。
但是,女性为何要解放?或者說女性何以成为弱势群体?辛亥之前的女权倡导者们虽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控诉社会对女子的不公,大力倡导女子解放,却从未有人清算过这种不公的文化根源,他们甚至在新学失衡,新女界出现种种弊端之后把旧学视为最终可以坚守的底线,比如丁初我就断言“女子苟无旧道德,女子断不容有新文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才触及思想文化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正是从女子问题人手的,新文化运动借女性在家庭、婚姻、贞操、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劣势地位来批判礼教,来确立“个人”,但这个“个人”并没有具体的性别指向。叶绍钧强调的“独立健全的人格”,邓颖超呼唤“起来呦!勇敢地起来,做一个真独立的‘人吧!”以及子君那句经典对白“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适用于每一个想要冲破旧家庭桎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从礼教中解放了自己,并在与民族国家天然的同构关系中获得了自我认同;女性同样也从礼教中解放了自己,只是这个“自己”是与男子一样的“人”,她也需要和男子一样建立起与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才能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在倡导人的解放和青年人独立自主的人格时,将女性解放纳入这一话语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思想界对女性问题的特别关注,也暗示了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晚清以及民国初年一样,它只能在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中顺势跟进。
由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从属性,由于男性推手对妇女解放思潮的领导和介入,诸多关乎女性切身感受的问题无法得到深入的思考,比如从旧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女性如何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献身社会事业/革命的女性是否真的因此而改变了女性的宿命,等等。而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在五四退潮以后,特别是在革命和战争到来以后,就变得十分紧迫和复杂了。
“救亡”压倒“启蒙”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一种叙述。如果我们撇开对此的辨析和歧见,可以肯定的是,与个性解放、性别建构相关的五四思潮退场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和政党意识形态。此时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和晚清提出“强国保种”、五四倡导“个人解放”已经有了历史语境的不同,但其受制于社会政治的大格局并没有改变。在这个大的框架中,革命、政党、阶级、民族等开始成为性别建构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性别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革命和战争促成了性别越界:比如丁玲放弃了“莎菲式”的个人追求,投身了革命;比如张爱玲,借了沦陷区新文学的退场而成为耀眼的作家明星;比如萧红对革命既有所介入,又有所疏离。这些不同的选择,不仅留下了大时代的影子,也留下了至今难解的困惑。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性别建构的历史,依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复杂的历史。
新中国的建立也意味着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女性的性别建构仍需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和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相比,新中国对妇女地位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带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女性的塑造也是空前而具体的。类似于“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样的标语口号使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消隐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革命目标中。如果说,五四时期有个人的解放,却没有具体的性别指向,那么在这个时代,性别指向的目标明确了,个人却消失了。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重回五四起跑线”,但逐渐展开的现代化建设则为性别建构提供了一个斑驳陆离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代女性再一次面对婚姻、家庭、职业、爱情等关乎性别的基本问题,她们对五四前辈思想资源的继承和拓展构成了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
自五四始,女性性别建构的历史充分反映在女性写作之中,而女性写作本身也成为性别建构的一种方式。女性作者在五四时期大量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晚清不断推进的女子解放和维新派确立起来的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巨大感召力为其出现孕育了条件,而投身写作也为刚刚获得“解放”走人社会的青年(包括女青年)提供了自我实现的途径和经济独立的可能,尽管在当时,女性从事文学创作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鼓励或者限制。
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意味着女性有了自由言说的可能,性别问题也有了被表述的可能。这正是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变动过程中知识界塑造女性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化,始终是在“他者”的影响下进行的。历史首先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它总是以大势规定女性解放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位置和顺序,因此女性解放始终是这一元叙事的一部分。知识界则是另外一个“他者”,它在完成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塑造女性。这是“他者”之于女性解放的积极意义。但是,历史的规定和知识界的塑造,也使女性解放带有了宿命性的困境,她们始终想在独立的意义上构建自己,形成自己的叙事。因此,当女性能够以文字的方式介入社会、国家时,当女性参与宏大叙事的建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性别问题的思考时,女性写作之于文学史的独特意义也就显示出来。
事实上,无论是现代女性建构的历史,还是女性写作的历史都显示了历史大势的巨大影响。丁玲在1942年的检讨预示了女性话语面对民族国家话语巨大力量之后的妥协,而这种妥协绵延至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当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风靡中国大陆时,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否认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自认并非只为女性而写作,而如果将其写作限定在“女性”的范围之内,那么则局限了她们的写作意义。
如何叙述20世纪中国女性性别建构的历史,以及作为性别建构言说文本的女性写作,是文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女性主义理论是我们讨论性别问题的切人点之一。但是,当“女性主义”成为一个标签被随意张贴的时候,对文本中“性别被压抑”的过度解读,对性别意识的过度阐释以及分析论证中过度的理论膨胀常常偏离了女性写作本身,同时也使“女性主义”“女性写作”陷入困境。
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首先来自理论与历史语境的差异。在西方,“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的产物,也是女权运动的革命纲领。从对社会结构的触动来看,无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这场革命都不彻底,因为核心家庭的存在是男权制得以继续存在的保证,正如凯特·米利特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完全由家庭成员组成的社会里,女人不愿放弃在家庭里的依赖和安全,男人同样也不愿放弃传统的地位和特权,所以,尽管人们谈论性别平等,却很少有人愿意将其付诸实施。而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还有其特殊的原因。这场运动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国民族斗争、民主革命的附属物,它不仅缺乏独立的斗争纲领和明确的性别意识,甚至缺乏女性参与者的自觉。这场革命即便胜利,也只能是少数女性参与的社会革命的胜利,并不能唤起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的觉醒。而且,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女性接受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这近于坐享其成的胜利成果,但同时这种从天而降的平等也成为女性的一种强制身份。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其在嫁接西方理论时的水土不服。
其次,国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写作实践又往往陷于不断重复的循環论证中。原本,理论与实践是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女性意识的自觉产生女性写作,对女性意识的理论提升指导女性写作实践。但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往往只立足于性别立场,从女性文本中收集材料,经过分析综合之后再服务于创作实践,而忽略了对其他理论资源的开放性吸收,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的论证系统。与之相关的是,女性主义批评因此具备了某种排他性,王小波在对陈染《私人生活》进行批评时做了一个“单向闸门”的比喻,他说面对一个女性写作的文本,男性批评家如果说不好,就会被认为是男权的偏见,如果说好,那么他的批评在一大堆颂扬的文字中就显得无足轻重,“单向闸门”的作用便是颂扬的话能通过,批评的话就通不过。偏执的性别立场无形中压缩女性写作开拓与发展的空间,使女性写作在单向的文学批评中将自身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当我们把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将女性写作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工具时,为了达到既定的叙述目的,对20世纪女性文学进行归纳总结,去除枝蔓,突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表达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也是以往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所做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做法的代价便是遮蔽了女性写作自身的丰富性,也剔除了所谓“旁枝末节”改写历史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性别问题并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包括风俗习惯等相关联而非相剥离的“集合体”。重视性别立场,同时也重视比如官方宣导的意识形态与民间私人生活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不同的阶级/阶层、经济水平、地域、社区/生活圈、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造成的个体差异,等等。如此,才可能贴近丰富的、复杂的女性生活史和社会史,才有可能重新审视女性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批评视角和言说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