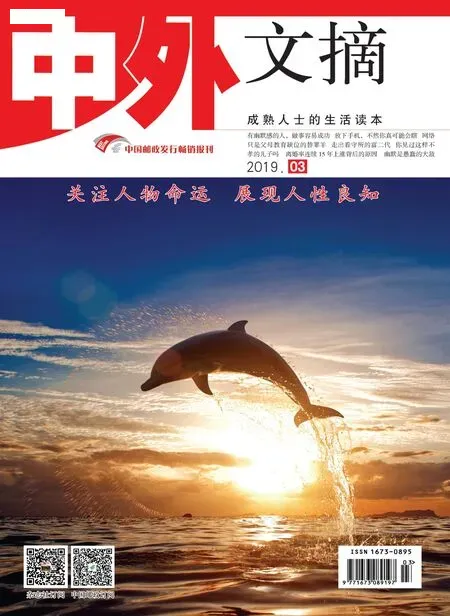走出看守所的富二代
□ 陈 洋

去年10月,因为一篇题为“被抓进看守所的町町单车创始人:我已一无所有”的媒体报道,丁伟首次闯入大众视线。
文章以口述为主,在记者着墨不多的文字里,丁伟的故事被概括为——一个喜欢折腾的富二代,靠着父亲的投资,跟风创立了共享单车品牌“町町单车”,又因为父亲生意变故,先后遭遇公司倒闭、家庭破产、女友分手。父母被带进看守所后不久,作为爸妈公司股东的他,也被押入看守所接受调查。近30天后,再度获得自由的他,却已是天上地下。
一天挣了64000的“网络乞丐”
9月底,在一栋办公楼的9层,我见到了因工作重新回到上海两个月的丁伟。
搬入不久的单人办公室略显空荡,丁伟的职位是“总监”,“管的人倒不是很多,我主要攒资源。”根据公开资料,他所在的这家公司之前主要提供车联网领域的技术和运营服务,今年7月,刚刚被上市公司并购。
加入这家公司前,丁伟的职业是主播,在直播平台虎牙上“熬”过了最难的三四个月。之所以说“熬”,是因为他从来没喜欢过这项工作,准确地说,是“很讨厌”。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主播更像是一根渡劫的稻草。
“来钱快”曾是他的惟一要求。那时,家里的车、房、地、款,所有资产都被银行冻结,用于破产清算。姐姐已经出嫁,担子大部分落到了丁伟肩上。除了要支付自己和父母数十万的律师费、父母在看守所的各种开销,最重的负担是一笔170万的银行贷款,那是他作为担保人,在2015年前后为父亲贷的。这样算下来,他一个月需要支出十万余元。“单靠工资,我养不活自己。”
最初,从没缺过钱的他,并不觉得这是件难事,虽然暂时很穷,但他自信怎么都能挣到钱。可当他揣着家人给凑的12000元钱回到熟悉的上海,却接连碰壁。很多朋友以为他爸虽然进去了,但一定给他留了钱,所以见面大多是谈项目,像往常一样,找他投资,可后来知道真实情况,便没了下文。
他决定去北京做主播,主播符合他“挣快钱”的要求。出事前,爱玩游戏的丁伟就常在虎牙直播打游戏,数年的重金加持下,他的号级别很高,这为他赢得了不少人气。虽然游戏账号早在需要钱的时候被卖掉,但直播间积累下来的万余粉丝,成了他的新起点。
11月开播的第一天,丁伟就跃上了直播榜的热门。“以前玩游戏,我花钱多,线上的朋友也都是花钱多的,他们一看我出事了,进来了就啪一下刷个两三万,然后大家一看有土豪刷礼物,都会进来看看。”那时,线上的朋友比线下的靠谱,按照三分之一的抽成比例,他当天的收入达到64000元。
媒体采访也成了直播间的人气来源。最初,丁伟只在刚从看守所出来时接受了一家南京媒体的采访,那是他主动联系的,主要为了澄清,“那时候好多人说我带着小姨子跑路了,我在看守所手机也没有,怎么接电话,只能是失联了;又有说我集资买R8,那辆R8都买三四年了……”他不希望自己以后背着这些骂名度日。
可之后,联系他的媒体越来越多,有的还会在采访时带上水果,甚至两三千元的“车马费”。于是,驱动他接受采访的东西开始变化,“那个时候很在意这个,因为没钱嘛,你得靠这个生活。”
丁伟将所谓的“直播经济”分为三种,除了信息不对称和无聊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暧昧经济——因为喜欢你,而坚持看你的直播。“像我们男主播,刚开始大家是看热闹,后期坚持给你刷礼物的,就都是女孩了。”
但这种簇拥感没能像最初预计的那样受用,比如一些女粉丝会向他咨询感情问题,这时常让他觉得尴尬又无奈,“我自己都一团糟,我前任现在还在撕我呢。”前女友在出事后不久离开了他,中间又经历颇多曲折反复。
3个月里,丁伟接触到了至少10个同性恋。最初,他们只是在刷礼物的时候,亲昵地称呼一声“弟弟”,接着就会私下加好友,拉丁伟聊天。“哪怕很不喜欢这人,哪怕这人很丑,你还得陪他聊。关键是,1个你可能就很烦了,如果是10个、20个,每天这么找你,你烦不烦?烦,你也得维系他们,因为你需要钱。”
“网络乞丐,”如今的丁伟描述起自己当时的状态不乏刻薄,“就跟跪着找别人要钱没什么区别。有钱的时候,你感觉不会做这种事;当你必须要拿出那么多钱,又没有别的办法时,你就会很极端了。”
今年过完年,手头没那么紧张了,丁伟决定不再直播。媒体的曝光,让他陆续得到了一些工作邀约。丁伟打算抓住机会。事实上,与现在的老板第一次见面时,老板直接提出让他加盟做一个汽车消费金融的项目。待遇优渥(近3万元/月的底薪加上股票),丁伟无法拒绝。
事 业
丁伟的老家泰州位于江苏省中部。丁家从丁伟的父亲丁万青这代开始经商,最初做的是粮食收购、加工和销售。后来,随着大米利润降低,丁万青开始转做年糕,同样一袋大米直接卖也就挣两三块,加工成年糕,利润能翻三四百倍。
生意越做越大,丁家工厂的加工品类又扩展到卤蛋、素肉串、素鸡等等,不仅给一些大品牌做代工,也会直接销往家乐福、沃尔玛这样的大商超。
和所有供应商一样,丁万青一度对合作方拖欠货款十分头疼,经常要主动送礼,只为让对方早点结账。一来二去,丁万青决定改变规则,牺牲些账期带来的利润,改为全款提货,手上余下的钱,就拿来作借贷。“我爸就想,与其像孙子一样找别人要钱,还不如把钱借给别人,自己做大爷。”2010年左右,丁伟上初中时,父亲开始涉足民间借贷业务。
一开始,出借资金都是自家的,泰州地方小,借款人大多知根知底,年利率在22%到24%左右。日子久了,一些生意上的朋友也开始把暂时不用的钱交给丁万青。随着资金量的增长,来丁家做资金流转的人越来越多,丁家投入的精力也越来越大。
事实上,事后将丁伟一家拖入破产漩涡的“普发创投”正是由其之前的业务衍生而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普发创投成立于2015年1月。而依据丁伟的说法,父亲最初成立普发创投,正是受到他的启发。
那时,腻味了大学玩乐生活的丁伟决定回老家找些事做。那是2014年,正值P2P创企井喷,丁伟拿着父亲给他的150万担保金,加盟了朋友创办的瑞银创投。在那个P2P的“黄金年代”,丁伟一个月能贷出去三四百万,利润接近二十万。
丁伟的生意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作为家里和公司的绝对权威,父亲的手毫无意外地伸了过来。父子矛盾的典型表现在于,丁万青会经常干涉丁伟对贷款人资质的判断。多次意见不合、争吵无解后,丁万青在2015年成立了普发创投,直接跟儿子做起了竞争对手。丁伟最终“没玩过”父亲,被“赶”到上海,接手了父亲给他盘下的一家连锁珠宝店。
一年多后,吹皱平静的是又一个资本风口——共享单车。不过这次,做共享单车是丁万青的主意。
2016年4月,成立一年多的摩拜单车首登上海,一时备受追捧。小橙车的用户里,不仅有希望省下打车费的小白领,也有常年开超跑的丁伟。丁伟在上海的公寓离珠宝店仅有800米,但因地处闹市,通常他开跑车去店里,堵车就要半小时,到了地方还得找车位,从车库到店里还要再走一段,但如果骑车,五六分钟就到了。一次,丁万青来上海办事,看到连丁伟都在骑摩拜,便对共享单车生起好奇。丁伟简单介绍后,父子俩算了笔账,“我们就觉得哪怕一天就四个人骑,一辆车一天能进账两块,一年就有七百多块。”花了一段时间把珠宝店盘出去,就开始投入了町町单车的创业中。但这次,父亲的烙印依然明显。
12月,当22岁的丁伟顶着“町町单车创始人、CEO”的头衔来到南京时,父亲已经帮他开好了头。不仅办公室、营业执照都办好了,父亲还为此裁撤了一个分公司,把员工调配过来。
和其他分公司一样,町町单车没有单独的财务,走的是公司大账。在父亲公司出事前,他从没意识到财务独立的必要性,“都是自己家,也习惯了,他(丁万青)不可能把这么多钱都放我这。之前珠宝店,也是我取了货后,他把钱直接打给对方。”“自家公司”的理念,也导致他经常为公司事务自掏腰包,且从不记账。
据丁伟介绍,在町町单车出事前,共在南京铺了约一万辆车,但几乎是一夜之间,开着保时捷跟车投放的丁伟眼前就出现了数万敌军。町町单车的首次发布会开了没到一个月,ofo、摩拜相继登陆南京。
町町措手不及。当时,父子俩之所以选择落地南京,除了当时的南京还是块“无主之地”,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丁父的人脉。“当时做的时候,政府是跟我爸说好了的,肯定不会让第二家进来,扶持本地企业,但是他们2万辆车,什么都没说,啪就进来了。”
虽然根据丁伟的说法,当地政府一度信守承诺,尝试清理;但政府一边收,他们一边铺,直到收来的六七千辆车整整堆满了江中的一个岛,政府只有转为数量约束,甚至罚款,但也没能阻挡他们的扩张。“1万辆车跟5万辆、10万辆车打,怎么打?”丁伟不得不变换思路,他希望通过资源合作把战场拉得更长,比如开发电助力车,并利用原有的市政公共自行车桩来充电;跟大型商超合作,进一步推出共享汽车;同时,积极推进对外融资。
但没等想法付诸实践,便已地覆天翻。
按照丁伟的说法,去年3月,因老家的一家P2P平台宝鼎财富被传“跑路”,一时引发投资者恐慌,丁万青的普发创投遭遇挤兑,老赖趁火打劫,丁家措手不及,百般腾挪后,最终资金链断裂,町町单车被牵连调查。
5月份,丁万青夫妇因涉嫌非法集资罪等被警方带走调查,3个月后,自杀两次未遂的丁伟也在福建朋友家中被警方带走协查,跟父母关进了同一间看守所。24天后,他率先被释放,丁万青夫妇则至今仍被羁押在看守所,等待审讯。
二 代
“一般人如果被问,‘你长大有什么愿望’,他可能会说,‘我以后要当警察’,‘要当老师’,‘当医生’,像我们就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知道长大以后干什么——就是做生意嘛。”
当然,“做生意”并不意味着“接班”,在丁伟的老家泰州,二代接班有着明显的时间节点——婚后已育,而“没结婚”的一律被视为“小孩”。但“小孩”只要毕业,在家就不能闲着,往往需要帮家里送送材料、打点打点关系,作为“自家人”看看店,也会做些朋友间的投资。
据丁伟介绍,生意出事时,丁万青的借贷业务已经遍布了江苏十几个城市。“在我们那个小城市,有个把亿现金在手,他就很飘了,就跟皇帝似的,每天被人捧着,阿谀奉承。他后面的那帮管理也没有反对他的,都是‘丁总说的对,丁总说的好’,我妈妈的意见他也不会听”。
丁伟记得有一次,贷款人的银行流水根本支撑不起还款,但父亲还是不顾他的反对,坚持要贷出去18万。当时账面上的钱太多,如果借不出去,需要垫付出借人的利息。但丁伟不以为然,“你想的是人家的利息,人家想的是你的本金。”最后,这成了笔坏账,丁万青没能瞒住,父子大吵了一架。
“五十多岁了,他脑子已经糊了。他这种,要么不出问题,出了问题,都是大问题。”
在丁伟眼中,父亲的公司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表面上顶着“互联网公司”的名号,其实办公室里大都是跟着丁万青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头”,还有一些虽然有些资源,但丝毫不懂管理的退休官员,“他们根本不会经营互联网公司。”
“我为什么不在他那公司干?说难听点,公司的人都是看着我拿枪拿炮长大的,我去公司还叫着我乳名,你让我怎么去管理他们?我一个从小到大生活在外面的人,开个会,他们满桌人操着大方言,我听也听不懂。”
那向外呢?
丁伟提起曾经属于他的一个“觉醒时刻”。那是在上海念大学的最后一年,一次宿醉后,他和四五个朋友围坐在出租公寓的沙发上,突然生发出一种无聊至死的感觉。这些21岁上下的少年已经度过了数个月浑浑噩噩的日子——玩一天,第二天宿醉,第三天接着玩,然后又是宿醉。“就觉得这样玩有点过分了,真不太好,父母都五六十了,还是找点事做吧。”
于是,众人四散,有人开起了宠物店,有人回家搞房地产,有人做了汽车改装,还有人卖起了鱼翅海产,而丁伟则接了那家珠宝店。相比兴趣,丁伟觉得他们这群人选择做什么,更多是依据手中握有的资源,“比如房地产这东西谁有兴趣,但可能刚好能批到哪块地,就可以做。”
据丁伟所知,当时那些项目坚持到现在的,也就只剩下做海产的一家,其余的几乎都没做起来。
“为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方面束缚我们,比如说……年龄。别人看我们年龄小,就会觉得我们做不了这摊事。比如去国企招标,就不可能派我们过去。在你没有创造很大价值之前,你就是个小孩,你怎么做都是个小孩。”或许,也因为终局已定。
“我的朋友当中很多年龄都比我大,现在也不会说还自己在外面闯了,基本上也都接班了。”丁伟觉得接班是惟一的选项,“你到最后肯定都得回去,父母老了,你再怎么做,也不可能跟父母做了几十年的基础相比。比如我今天一件事做了3年,每年可以挣个几十万,那你爸爸那事都做了30年了,你是放弃小盘子,还是放弃大盘子?”
现 实
至少,如今一无所有的状态,反倒让丁伟有了更多选择。
最近,他挖来了自己之前所在超跑俱乐部的一位高管,筹划替公司组建一个新的超跑俱乐部。为了打响知名度,他成功说服了超跑圈的一位知名网红领衔,还在计划把几位明星拉进来。
“有超跑的人,至少还会有一辆奔驰、宝马、奥迪来代步,也就是说一个人最少有两台豪车。如果我们俱乐部做到300个客户,就有600辆高端车,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养护中心,相比4S店,我们既能做到更低的价格,还能满足他们对人脉、资源互换的需求。下一步,还可以去做私人会所、进口车专卖。很多东西远比表面上有价值。”
丁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以前是超跑俱乐部的会员,我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我可以让大家都玩得开心。”
想象中的落差感并不明显,在他看来,从参与者到组织者,只是角色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如今的状态似乎更自如了,“即便我们公司不做活动,这些富二代们想组织活动,也会交给我们,帮大家攒局。现在是想见谁,随时都能见。”
这个圈子的凉薄,他不是没见识过。去年家里出事后,他主动退出了前俱乐部的群,但还是有人在群里骂他“败坏圈子名声”。“也有人啪啪跳出来(维护我说),‘人家好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跟人家合影、碰杯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当时因为这,吵了好多架,也看清了一些人。”
可如今,这些在他眼中也都渐渐变淡。“这个圈子最看重的是资源,最轻视的是那些为资源而混圈子的人,所以你要有资源去交换。现在我有上市公司这个平台,就可以跟我以前的朋友进行利益交换。如果我没有平台,就靠我这个人,说难听点,他们能不能答应还是个问题。讲实话,人是很现实的。”
同样被彻底扭转的,还有对钱的态度。
没缺过钱的时候,丁伟讨厌钱,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甚至找个女朋友,都不知道对方喜欢的是人还是钱。可到如今,自认为“重生”了的他反而觉得,“物质是最重要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人会对你一味付出,哪怕是我现在这个公司,我如果一直给老板挣不着钱,滚蛋!”
甚至他还会想,如果父亲进去前真的藏了钱,或许有钱好办事,一切都会容易很多。“以前,我天天有人叫着玩,生病一下,发个朋友圈,马上十个女孩送粥到我家,我一点不夸张;现在,我搬家一个人,过生日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没人养我。”
“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我死过,我不敢再死,那我要活,能怎么办?只有拼,只能靠自己。你不行,就真不行了。”这股热血不是没有反复。今年4月,母亲就再次让他失望了。“本来我妈是今年就能出来的,没她什么事,但是我妈她傻。她觉得如果我爸本身判十年,她能给我爸承担一点,两个人可以一人五年就出来。结果……”
这一度给了他很大的打击,“我本来想的是,你出来了,我也有个动力,对吧?”他的计划原本是想先保母亲,为此他在母亲身上花掉了一大笔律师费,但希望再次破灭。“你看,人活着是为自己活吗?那为自己活,太简单了,我一个月3000块钱,我也能活,是么?”
但那种“很火、很气”的感觉还是随着时间消散了,现在,他会调侃说,父亲在里面日子过得挺好的。看守所里的饭菜简单,一日三餐都是粥和白菜豆腐,但可以花钱“加餐”,一个月集中送一次。说到这里,笑容再次爬上了脸,“他也想跟别人证明他儿子很优秀。之前我给他写信,也吹点小牛逼,说我现在做得怎么怎么样,还真把我当富豪了。”他笑出了声。
今年以来,丁伟只崩溃过一次。平时,情绪的盒子被谨慎地密封起来,一切再正常不过,维系平静的方法是不让自己闲着,“白天上班,到晚上,我有时间就会去学跳舞,以后办酒会可能会用到。到11点,我就睡了。”
惟一那次,曾在出事期间给了他莫大帮助的发小来京,丁伟没控制住,喝到断片。第二天醒来时,只发现自己满身是伤,查看通话记录,他给自己、爸妈、前任各打了十几个电话。朋友告诉他,他像发疯一样,哭了整夜。那次之后,他给自己定下规矩——绝对不能断片,任何场合都要控制住自己。
但命运这种事情,或许从来就没有控制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