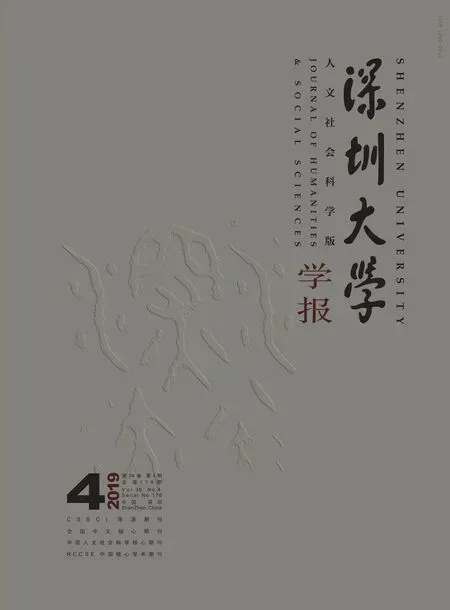宋代长江沿线的水系变迁:基于主要河道与湖泊的考察
谭静怡
(1.云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云南 昆明 650091;2.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长江自古航运发达,素有“黄金水道”之称,而湖泊广布是其标识性特征。有宋一代,我国气候较为干燥,这对长江沿线的水系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①,直接导致沿江湖泊的大面积萎缩。靖康之乱以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沿线人口剧增,大规模的围湖造田运动亦加剧了沿线湖泊的缩小。在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合力影响下,两宋时期长江沿线的水系发生了一系列变迁,但囿于年代、地域、史料等诸种原因,20世纪50年代后学界开始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探索长江沿线的水文情况,直到近年才逐渐关注水环境演变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然成果十分有限,主要反映在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沿江湖泊与长江入海口的变化上②。故而,本文从生态环境入手,探讨宋代长江沿线主要水系的变迁过程、原因及其影响,既有利于研究沿江区域古今水系的变化,又能够为我国长江经济圈的开发和水环境保护提供有益的经验。
一、宋代长江沿线主干河道与水系变迁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东雪山,沿线水系发达,水网交织,分布着众多的湖泊,流经今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注入东海。长江干流各段名称不一,其源头至当曲河口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当曲河口至青海省玉树县巴塘河口称通天河;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宾市岷江口称金沙江;宜宾市岷江口至长江入海口通称长江。本文考察的主要区域为宜宾以下至长江入海口,可细划为五大段河道:四川省宜宾市至湖北省宜昌市南津关段称川江,水急滩多;湖北省宜都市枝江至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段称荆江;湖南岳阳城陵矶至江西湖口段河道;江西湖口至江苏扬州段河道;江苏省扬州、镇江一带至长江入海口段称扬子江。
(一)川江段
川江段河道指四川省宜宾市至湖北省宜昌市一段,属于峡谷型河流,水流湍急,峡谷甚多,沿岸皆山、丘陵和小块平原,其中重庆市奉节白帝城至湖北省宜昌市南津关的三峡河段又称峡江,包括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个大峡谷,三峡段峡谷、宽谷相间,两岸群山耸立,一水中流,面窄水深,迂回曲折,因许多支流汇聚水量猛增,有“众水会涪万”之说。宋代川江段河道经戎州、泸州、渝州、涪州、万州、夔州、归州、峡州等地,水网交织,其中三峡水道是长江沿线中最艰险的一段。在泸州江安县“道中有滩,号张旗三滩。谓湍势奔急”[1](P212),至涪州排亭前“波涛大洶,濆淖如屋,不可梢船。过州,入黔江泊。……大江怒涨,水色黄浊”[1](P214),过群猪滩“既险且长。水虽大涨,乱石犹森然”[1](P215),到云安军“风作水涌”[1](P217)。入奉节“至瞿唐口,水平如席。独滟滪之顶,犹涡纹瀺灂,……水势怒急”[1](P217-218),“峡中两岸,高崖峻壁,……两山束江骤起,水势不及平”,到大溪口“水稍阔”[1](P218)。瞿塘峡两岸高耸的悬崖峭壁夹住了江流,窄窄的峡口又布有滟灏堆,使航道更加难行,然输入与输出四川的财货均需经这条航线入川与出川。所谓:“蜀江西来已无路,凿山作浍方成川。瞿唐之口狭如带,乃欲纳此江漫漫。”[2](P220)足见,这一航段的艰难险阻。而进入巫峡,则会产生一种“束江崖欲合,漱石水多滩”[2](P214)、“峡江饶暗石,水状日千变”[2](P215)的感觉,到归州“水骤退十许丈,沿岸滩石森然”[1](P221)。时人范成大在过白狗峡时,言“连滩竹节稠,洶怒奔夷陵”[2](P212),生动地描绘了此地的水况。一言蔽之,两宋时期川江段水系变化不大。
(二)荆江段
荆江段河道是 “长江在中游冲积平原上的一段河道,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矶,全长约四百公里,其中藕池口以上称上荆江,藕池口以下为下荆江”,属蜿蜒型河型,水流较缓、曲流发达、湖泊罗列、星罗棋布、江湖相通、复盘旋回、羊肠百转、江身屈曲、九曲回肠是其水系最为典型的特点,可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在众多的湖泊中,以洞庭湖最大。“从东晋江陵荆江河段北岸创筑金堤开始,长江泛滥泥沙沉积在荆南地区;宋元明时期长江北岸穴口暂堵,水沙大量涌向长江南岸,致使荆南地区地势逐渐改变成北高南低(特别是公安县境)”[3](P95),最终初步奠定了今日松滋、公安境内河流的地貌形态。宋代处于下荆江统一河床的塑造阶段,至此江汉平原的云梦泽已消失殆尽,被星罗棋布的若干小湖沼取代,其“河床形态的形成,与云梦泽的历史演变紧密相关”[3](P87)。此外,据《太平寰宇记》、《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等文献关于荆江沿岸建宁、监利等县治设置的记载,可以看出宋代荆江河段水系摆动的情况,如乾德三年置建宁县[4]、监利县,至南宋端平年间才迁至下荆江自然堤上建今址,而它们建置的时段与当时荆江河段的演变是相吻合的。
(三)城陵矶-湖口段
城陵矶至湖口段指宋代岳州城陵矶至湖口之间河道,全长480 多公里,地跨荆湖南、荆湖北、江南西等三路,虽与荆江同属长江中游,但形态迥异,属分汊河型,可细分为顺直分汊和弯曲分汊两种。顺直分汊河型河床两侧“往往有较多的矶头濒临江边,甚至成对称地锁住江道,束缚河床自由摆动”[3](P110),河道变幅较小,江岸少动,比较稳定,如城陵矶至石码头、沙帽山至武汉市、西塞山至武穴三个河段。宋代城陵矶至湖口顺直分汊河型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刘公洲和新野夹形成上,元祐八年(1093)汉阳城南江心滩出水成洲,称为刘公洲,其形成加剧了主流过水断面缩小,使鹦鹉洲向左侧江心不断推进,鹦鹉洲“在大江东,县西南二里。西过此洲,从北头七十步大江中流,与汉阳县分界”[5];乾道年间(1165-1173)陆游知夔州经蕲口镇,“过新野夹,有石濑茂林,始闻秋莺。沙际水牛至多,往往数十为群,吴中所无也。地属兴国军大冶县”[6](P193)。可知,因大冶县江中沙洲左岸发生沉降,主泓左偏导致沙洲向右岸的大冶县靠近,汊道浅淤形成新野夹。
弯曲分汊河型的“两侧的地貌有明显差异,右岸丘陵山地濒临江边,矶头颇多;左岸大多为开阔的泛滥平原,矶头较少,间距大,利于弯曲分汊河道的发展”[3](P113),这种河型在历史时期变化较大,且河道大多向左岸方向弯曲,如石码头至沙帽山、武汉市至西塞山、武穴至湖口三个河段。宋代城陵矶至湖口弯曲分汊河型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江口的出现、东城洲和桑落洲的变化及簰洲弯曲流的形成上,从乾道六年(1170)陆游知夔州所写《入蜀记》卷四、五中的记载可窥一二:“自小孤泛彭蠡口,四望无际”。说明当时桑落洲动荡不定,南支主流十分开阔,北汊支流基本已淤废,靠向北岸的趋势愈发明显。其它史料也有相关记载,舒州宿松县“桑落洲,在县西南一百九十四里。江水始自鄂陵分派为九,于此合流,谓之九江口。……按此洲与江洲浔阳县分中流为界”[7]、“湖口之东,今但见其为一江,而不见其分流”[8]。“自兰溪而西,江面尤广、山阜平远”。故而,五洲在遭受强烈冲击的时候偏向北岸,江面拓展为单一的宽河道。“西行过西塞,因右汊江流湍险难上,即抛江走左汊的散花夹”。是以,当时散花洲左汊已淤塞为夹江。八月二十日晓,离黄州,“江平无风,挽船自赤壁矶下过,多奇石,……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狭,复出大江,过三江日,极望无际,泊戚矶港”。宋代三江口的出现,表明三江口以上的长江江中已有两个较大沙洲存在,江流被分为三汊,且这两个沙洲的位置靠近北岸的举水口附近。《舆地纪胜》对此也有记载:“三江口去黄冈县三十里,在团风镇之下,有江三路而下,至此会合为一。”[9]“过青山矶,多碎石及浅滩,晚泊白杨夹口,距鄂州三十里,陆行止十余里”。可知,当时东城洲在乾道以前已基本靠岸,汊口已淤断,只能从白杨夹穿过东城洲入江绕道三十里始至鄂州。经簰洲弯附近,言九月“一日入沌,沿长河西南行,新潭遇百里荒,无挽路,至入夜才行四十五里,泊丛苇中。二日东岸苇稍薄缺,时见大江渺弥,盖巴陵路也”。足见,簰洲弯曲流最迟在乾道年间已经形成,且为大江主泓途经,顶部距长河较近,而从鄂州到巴陵却需要绕簰洲弯近百里,说明其颈部的长江旧主泓通道已淤塞不可行舟,这与长江水文泥沙量、局部地区地质构造隆起密切相关。因而,在宋代城陵矶-湖口段的弯曲分汊河型更直观反应出该区域河道、矶头和沙洲的变化。
(四)湖口-扬州段
湖口至扬州段河道地跨江西、安徽、江苏三省,河床摆动较频繁,属典型的分汊河型,宋代该段河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第一,在湖口-吉阳段,彭郎矶与小孤山夹江相对,可谓“江流经此,湍急如沸”[10],彭郎矶靠江,小孤山则峙江北岸、“半入大江”[11],在过彭郎矶和小孤山之后,江水流速骤减、变缓,泥沙沉积成洲,当时的滶背洲、峨眉洲分列于马当矶西部与东部。第二,在吉阳-大通段,河道曲折多变,长风沙向凸岸靠近发展为边滩的趋势愈发明显,其汊河道南支成为主流,北支日益淤废、狭窄称长风夹,范成大途径皖口时即走此夹,“南岸自牛磯、雁汊行几二百里,至长风沙下口”;此外,池州一带的江河形势比今靠北,“至池州池口,泊望淮亭,去城尚十余里”[1](P232),“北至大江中流二十里与舒州桐城县分界”[12]。第三,在大通-芜湖段,沙洲、江岸多变频繁,宋以前,鹊头山到荻港的江中已有大型沙洲存在称鹊洲,宋代改为丁家洲,随着大通沙洲的形成,其有明显靠岸趋势,“匏瓠放教俱上屋,渔樵相倚自成邻”,且与右岸汊道形成“从丁家洲避风从小港出荻港大江”的丁家夹[13]。此段沿流还存在三个沙洲,一是黑沙洲,在新港对岸,周必大至繁昌即泊舟于此;二是在新港与三山间;三是无名洲,在三山至鲁港间。第四,在芜湖-扬州段,可分芜湖至南京、南京至扬州两段考察。芜湖至南京,属顺直分汊河型,分布着南京梅子洲、当涂江心洲等长江沿线较大的江心洲,该段沙洲的最大特点为向右岸弯曲,河段左岸除石跋山、西梁山、骚狗山外,多为宽阔的冲积平原,岸线较为平直;右岸近丘陵山地,分布着诸多矶头,如四褐山、采石矶、马鞍山、烈山等。南京至扬州段,沙洲大量出现,河口日趋东延,导致江面逐渐狭束,据《入蜀记》、《吴船录》记载,宋代此段的马昂洲、上新洲、下新洲、长芦洲等都十分有名。易言之,宋代时此段河道虽矶头密布,但岸线相对稳定。
(五)扬子江段
扬子江段指扬州、镇江一带至长江入海口之间河道,该段水系江面开阔、水流缓慢、江海相会,可谓江天一色,且在江心形成了数十个大小不等的沙洲。两宋时期在润州、扬州间,江北瓜洲继续南扩,江面愈发狭窄,宋初时“渡江至润州七十里”[14],到乾道年间已十分窄束,在瓜洲南望“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6](P167),江面的狭缩可见一斑。扬子江河段的水上运输自六朝以后最为繁忙,太湖与江南运河相连通,水道纵横,湖荡棋布,自镇江谏壁口引长江水南流,穿越太湖水系众多的河流与湖荡,吞吐江湖,调节水量。北宋时物资在瓜步、京口间转入大运河,经扬州、楚州、宿州运至汴京;南宋时,物资从润州转至大运河,经平江府、嘉兴府运至临安府,无论北宋还是南宋,该区域都是国家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区,即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所在地。
如是,宋代长江沿线主干河道的变化主要呈现出三种趋势:其一,城陵矶至湖口段、湖口至扬州段河道,变化明显,形成了一些新的江心沙洲,如刘公洲、黑沙洲等,局部地区矶头偏多,一些岸线变动频繁;其二,荆州段、扬子江段河道,变化次之,部分地区泥沙、地质、水文发生变化,如公安县等荆南地区地势渐变为北高南低、润州与扬州间江面愈发褊狭;其三,川江段河道,相比其它河道,本段河道表现较为稳定,一定程度与其史料的丰歉程度有关,虽然两宋时期曾有较多人员因做官、贬谪、经商等原因暂时或永久居住在这里,但是有关川江段河道变迁的史料仍十分匮乏。因此,对宋代长江沿线主干河道的研究,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文献资源。
二、宋代长江沿线重要湖泊与水系变迁
湖泊变化是长江沿线水系变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宋代以前,长江沿线已呈现出河湖交织的河流港汊景象,“重湖巨泽,大者数百里,小者不啻数十里”[15]。宋代长江沿线水系发达,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它们与长江主干流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且发达的沿江水系,当时湖泊的变化主要反映在湖北宜昌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即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水域,变化较为复杂、频繁和剧烈。论文以湖泊变化为基点,探讨宋代长江沿线的水系情况,不仅有利于研究古今长江沿线湖泊的变迁状况,更有助于为今天该区域水系的开发和经济建设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
(一)太湖
太湖,古称震泽、五湖、具区、笠泽,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位于江苏省南部,湖水南部与浙江省相连,既是长江下游最大的湖泊,也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有“一湖跨三州”的说法,即东吴苏州、中吴常州、西吴湖州三个地区。历史时期,太湖“大致沿着三江→湖泊→水网化的方向发展”,下泄水道“先由吴淞江及诸港浦入海;后由浏河、吴淞江及诸港浦入海;再发展到由黄浦江、浏河及诸港浦入海”[3](P145),变化甚巨。《吴郡志》记载:“太湖,在吴县西,即古具区、震泽、五湖之处。《越绝书》云‘太湖周回三万六千顷,禹贡之震泽。’《尔雅》云‘吴越之间巨区,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带吴兴、毗陵诸县界,东南水都也。’”[16]《读史方舆纪要》亦载,太湖“在苏州府西南三十里,常州府东南八十里,浙江湖州府北二十八里。其滨湖之县曰:吴县、吴江、武进、无锡、宜兴、乌程、长兴,纵广三百八十三里,周回三万六千顷。或谓之震泽。”[17]
太湖号称“三万六千顷,周围八百里”,是一个平原水网区的大型浅水湖泊,约由180 多个大小不等的湖泊组成,水源主要来自浙江天目山的苕溪和江苏宜溧山地北麓的荆溪,对长江航运、灌溉、河湖水位调节起着重要作用。宋代太湖水系的变迁与三角洲地质发育、时人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受到泥沙淤积等因素影响,湖泊岸线的位置迅速向外扩展,为了防止海潮、发展围湖垦田,湖区修筑了海塘作为防护,导致湖区地面高差加大。郏亶言“凡冈阜之地,高于积水之处四五尺至七八尺”[18],其子郏侨也提及茜泾一带“地浸高,比之苏州及昆山县地形,不啻丈余”[19]。宋代长江入海口平面上升,太湖湖区地面差的改变,引发了江湖水流量比重的变化,致使长江下游地区河流排水不畅,原来泄太湖水的吴淞江及诸港浦反而成为江水内浸的主要通道,“向之欲东导于海者反西流,欲北导于江者反南下”[18],部分低洼区域被水淹没,沦为水泽,太湖水只有在低潮期才能泄入江海,后经治理积水有所好转,但依然有不少农田、村落被水所浸没。北宋时期,娄江、东江相继湮没、淤塞,太湖水系先后形成了多个大小零星的湖沼,呈现出了湖泊广布的景致。宋代文人对太湖的发展情况也进行了详细记载,略举几例。
景祐二年,姑苏四郊略平窊而为湖者十之二三……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虽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或一岁大水,久而未耗,来年暑雨复为沴焉。[20]
元祐六年,臣(苏轼)到吴中二年,虽为多雨,亦未至过甚,而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虽为淫雨,过常三州之水,遂合为一。太湖、松江,与海渺然无辨者,盖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积雨所能独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从来未远,不过四五十年耳,而近岁特甚。[21]
锷于熙宁八年,岁遇大旱,窃观震泽水退数里,清泉乡湖乾数里,面其地皆昔日邱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数里之间,信知昔为民田,今为太湖也,太湖即震泽也。以是推之,太湖宽广,逾于昔时。……锷又尝游下乡,窃见陂淹之间,亦多邱墓,皆为鱼鳖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则于平地陆野之间,岂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尝得唐埋铭于水穴之中,今犹存焉,信夫昔为高原,今为污泽,今之水不泄如故也。[22]
限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人类活动等因素,宋代太湖经历了由大到小的变化。据成书于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的《吴郡图经》载,在东江故道流经区域只有白蚬、谷湖、马腾、瑇瑁、锜湖、来苏、唳鹤、永兴诸湖[23],但除了白蚬、谷湖,其它湖泊并不见唐以前史料中,推知其应为被水淹而成的新湖泊。今澄湖,又名陈湖、沉湖,在北宋水利专著中未见记载,然在《宋史·河渠志》、《宋会要辑稿》中却被列为乾道年间秀州四大湖泊之一,说明其很有可能为积水所形成。此外,通过太湖湖区围垦时发现在湖底的建筑遗址、宋井、宋币以及文物③,也可推知这些湖泊应为当时陆地淹没而成。南宋末期,因为不合理的垦殖,太湖水网较为紊乱,部分水体已处于淤废状态,加之黄浦江成为太湖外泄的主要水道,太湖水系面积日趋收缩。由此,“唐宋以前,由于长江三角洲的不等量下沉和沿海地区泥沙的不断淤积,导致太湖积水不畅,面积不断扩大。宋元以来太湖平原还在继续下沉,为了排除积水,当地人民大兴水利,形成完整的水网系统,大量的土地得到开发。随着人口的增多,围湖垦田日渐发展,导致南宋以来湖泊面积不断缩小”[3](P106-108)。总体上,两宋时期太湖水网化的变化加速了本区农业进程,围湖垦田蓬勃发展,“原田腴沃,常获丰穰”[24],并使其成为当时长江沿线乃至整个宋代经济发展最为迅速、资源最为富饶的地区之一。
(二)鄱阳湖
鄱阳湖,又称彭蠡湖、扬澜湖、宫亭湖等,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九江河段南岸,既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和第二大湖,又是世界最大的鸟类保护区,上承赣、抚、信、饶、修五江之水,由湖口注入长江,“根据湖区地貌形态和历史演变情况,以老爷岭、杨家山之间的婴子口为界,可分为鄱阳北湖和鄱阳南湖。南湖又以矶山-四山一线为界,分为东鄱湖和西鄱湖两部分”[3](P124),鄱阳北湖,或称西鄱湖,湖面狭窄;南湖,或称东鄱湖,湖面宽阔,为湖区主体,整个鄱阳湖可谓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波翻浪涌、滋养生灵。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曰:“山苍苍,江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25]李纲在《彭蠡》中也言:“世传扬澜并左蠡,无风白浪如山起。”[26]余靖的《松门守风》记载则更为详细:“彭蠡古来险,汤汤贯侯卫。源长云共浮,望极天无际。传闻五月交,兹时一阴至。飓风生海隅,余力千里噎。万窍争怒号,惊涛得狂势。”[27]
鄱阳湖首次见于史籍,载于《太平寰宇记》饶州余干县条,言“康郎山,在县西北八十里鄱阳湖中”[28]。宋代鄱阳湖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主要跨洪州、江州、饶州等地,是长江沿线重要的调蓄型湖泊,具有保护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特殊生态功能。盛唐时,鄱阳湖面积最大可达6000 平方公里,宋初洪州南昌县“松门山在县北,水路一百一十五里,……北临……彭蠡湖”。足见,当时彭蠡泽已溢出婴子口过松门向东南方向的鄱阳湖平原延伸,鄱阳湖在范围上发生了扩展。之后北宋大部分时段鄱阳湖地区都处于高温多雨的状态下,水量继续大幅增加,湖泊显著延展扩张,在洪水时节表现得尤为突出。《舆地纪胜》隆兴府条载:“彭泽湖在进贤县一百二十里,接南康、饶州及本府三州之境,弥茫浩渺,与天无际。”[29]至此,鄱阳南湖地区的古鄱阳湖平原基本消失,鄱阳县被茫茫湖水所包围,大体奠定了其今天的形态,其东界在今莲荷山与波阳县间,南界在今康山以南,河网交错、波光粼粼的鄱阳景色最终形成。鄱阳湖是一个时令性湖泊,“中有鹰泊小湖,每春涨则与鄱江连接,水缩则黄茅白苇,旷如平野”[30],但即使处于丰水期,水体也不深。
(三)洞庭湖
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荆江段河道南岸,位于宋代荆湖南路北部,湖区包括荆湖南路的潭州、益阳、岳阳、湘潭和荆湖北路的松滋、公安、石首等地,以赤山-禹山一线为界分为东西两区,由岳州城陵矶泄入长江,属于一个水体较为统一的湖泊,既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泊,又是长江流域内最为重要的储水与蓄洪湖盆。唐代时,洞庭湖从东洞庭湖区向西区扩展,水域“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31],已由南朝的“五百余里”发展至“周及八百里”,水面可谓快速扩展。《元和郡县图志》也有相似记载:“洞庭湖,在县西南一里五十步。周回二百六十里。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县南七十九里。周回二百六十五里。”[32]换言之,唐代“东洞庭水面已开始向西洞庭扩展,赤沙湖有纳入洞庭湖的趋势”[3](P105)。
在唐代基础上,宋代洞庭湖将若干小湖泊并吞形成广阔无垠的湖面,“波浪连天”[1](P225),水面继续扩大;又因地表沉降,水体进一步下沉。《舆地纪胜》载有“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连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33](P2348)、“风帆满目八百里,人从岳阳楼上看”[33](P2366)、“洞庭八百里,幕阜三千寻”[33](P2368)等诗句。《方舆胜览》也载:洞庭湖“在巴陵县西。西吞赤沙,南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34]《岳阳风土记》亦载:“大抵湖上行舟虽泝流而遇顺风,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行二百里。岳阳西到华容,过大穴漠汴湖,一日程;又西到澧江口、鼎州江口,皆通大穴漠赤沙,三日程;南至沅江,过赤鼻山湖,四日程;又东至湘江,过磊石青草湖,两日程。”[35](P83)又言:“华容地皆面湖,夏秋霖潦,秋水时至,……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潭户。”[35](P90)如此,宋代洞庭湖水体继续沉降,赤沙与洞庭湖、青草湖连成一片浩渺水域,为洞庭湖吞没,洞庭湖水域进一步向西延展。与此同时,岳阳附近的洞庭湖因“荆江日漱而南、湘江日漱而东,湖面百里之内又常西南风,沿湖岸线白蚀倾颓颇为严重”[3](P106),岳阳“郡城西数百步,屡年湖水漱啮。今去城数十步即江岸。……北津旧去城角数百步,今逼近石嘴”[35](P78)。由上可知,宋代洞庭湖继续沉降,成为其历史时期水体最深的阶段,向西拓展趋势愈发明显,经历了由大到更大的演变过程。
本部分以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为视角,考察了宋代长江沿线湖泊的变迁轨迹。10世纪时,长江沿线湖泊数量创历史时期新高,深度与广度都有所变化;11世纪初,湖泊水面达到最大面积,部分湖泊急剧扩展。“洞庭湖从东洞庭湖区向西洞庭湖区扩展,范围从南朝的五百里发展到周极八百里,其附近的青草、赤沙等湖与之融为一体,连成一片汪洋水域,湖区继续沉降,湖水深度愈发增加,成为其历史时期发展至最深的阶段。鄱阳湖迅速扩展,已从西鄱阳湖扩展到东鄱阳湖,武林成为其东南涯,与族亭湖、担石湖合并,进贤北山成为其南涯,并取代了史籍上记载的彭蠡湖。太湖随着娄江、东江相继湮塞,出现了湖泊广布的局面,先后出现了澄湖、马腾湖、来苏湖、淀山湖等一系列新湖泊。”[3](P105-149)。因而,两宋时期是长江沿线湖泊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湖泊数量、水体深度、湖面广度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三、宋代长江沿线水系变迁的原因分析
作为唐宋变革的重要阶段,宋代处于我国历史上一个环境异常期,长江沿线河床、岸线、水量、矶头及湖泊水体、面积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变化致使其水系发生演变;而经济重心的南移、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靖康之变后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以及频繁的人类活动亦是诱发长江沿线水系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以,宋代长江沿线水系的变迁与沿江自然环境因素和人文社会因素息息相关。
(一)自然环境因素
宋代长江沿线的川江、荆江、城陵矶-湖口、湖口-扬州、扬子江等河段水量丰沛,其中川江最为艰险,三峡地区一水带束、峭壁林立;荆江是当时沿江水系变化最为典型的水域,河床淤积且不断升高,直接加速了洪水的发生频率;城陵矶至湖口分为顺直分汊与弯曲分汊两种河型,顺直分汊河型变化小、江岸少动,弯曲分汊河型变动较大、两侧地貌差异明显;湖口至扬州多分布矶头,沙洲亦多,岸线变动不大;扬子江江面开阔,与江南运河相通,水道纵横交错。有宋一代长江沿线湖泊发育进入了全盛时期,呈现星罗棋布之状,其变迁与入海口海面、气候变化密切相关。10 至11世纪初是中国湖泊的膨胀期,之后到1250年,我国湖泊面积逐渐萎缩缩小,进入了过去3000年来湖泊第二次大幅度的缩小时期,这种湖泊缩小的现象在两宋之际气候由暖转冷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气候转干,引起了沿江区域湖泊萎缩、汊道湮灭。1250年以后,我国湖泊面积则再次增加。整体来看,宋代长江沿线水系发育良好,湖泊众多,水量充裕,湖泊自身的发育、水体的变化、泥沙的淤泥等原因直接引发湖泊的变迁,逐渐形成了一些沿江小平原,它们对沿江区域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如是,宋代长江沿线的水系不仅是当时内河航运条件最为优越的河道,也是沿海与内陆联系的航运大动脉。
(二)人文社会因素
人口迁徙是导致宋代长江沿线水系变迁的主要原因,在湖泊变化方面尤其突出。两宋之际发生的靖康之乱引发了我国历史时期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移,靖康之变以后我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大量的北人举家南迁。吴松弟在《中国移民史》第四卷中对靖康之乱后北方人民的南迁分布做过详细考察,指出如若以移民分布的稀密状况和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来划分,在今白龙江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和长江南岸平原以北都属于移民的密集分布区,包括今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湖北、安徽与江苏二省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部分、以杭州、南京、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36]。换言之,人们由北至南迁到长江沿线本是为了避难和生存,却造成了沿江区域人地冲突加剧,各种资源严重短缺,而沿线人口激增则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农业活动。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土地,开展经济活动,时人多将沿江湖泊开垦为耕地,进行大面积围湖垦田,在沿岸筑堤修坝以御水,直接引起了沿江水系的变化。如绍兴五年,韩肖胄曾言:“江之南岸,并江之民甚少,旷土甚多,皆可指为屯田,沿江大将,各见分地而屯,军士旧尝为农者,十计五六,择其非甚精锐,可为田者,使各受地……军士所田,必不能尽遍长江之南岸,则募江北流徙之人给之。又有余,则募江南无业愿迁之人给之。”[37]表象上围湖垦田使宋代各种社会冲突得到缓解,拓展了宋人的生存空间,缓解了人口增加引发的人地矛盾,给农业生产提供了足够的土地,然实际上这种人为的行为方式是长江沿线湖泊变迁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中下游地区,它严重地加剧了湖泊的萎缩。此外,蓬勃发展的手工业活动亦推动了这一进程,由于当时造船、营建和伐木等行业较为发达,且交通运输十分便利,导致时人对木材的需求与日俱增,乱砍滥伐现象突出,林木资源的过度砍伐使长江沿线水土流失严重。为此,宋代是长江沿线湖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其不仅可以反映出沿江水系的变化,也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作用。
由是观之,在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两宋时期长江沿线水系发生了诸多改变,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以航运最为突出。伴随宋代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沿线的航运愈发重要,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景致,日益成为时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宋时,扬州、荆州、潭州、江陵等沿江城市的物资绝大多数是通过长江沿线的航道漕运至京师乃至全国各地;南宋时,朝廷通过长江攫取了巴蜀、两湖、两浙等地大批的财赋和资源,此外宋金以淮河为界,长江战略位置更加凸显出来,成为南宋的第二道防线。《景定建康志》载:江宁浦“夏秋胜三百石舟,春冬胜一百石”,秣陵浦“秋夏胜三百石舟,春冬胜一百五十石。”[38]综上,通过对宋代长江沿线水系变迁过程、原因及影响的考察,不仅有利于了解当时沿江水环境的发展状况,还有助于为该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水环境保护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注:
①本文的研究区域长江沿线主要指以长江主干流沿线及鄱阳湖、洞庭湖、太湖等三大湖区为主的长江流域地区,地跨今天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区域界线以两宋时期的府界为依据,主要参考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 册),即北宋时期,以政和元年(1111)的疆域政区为依据;南宋时期,以绍兴十二年(1142)、嘉定元年(1208)的疆域政区为依据。在行政区划的名称方面,为求写作统一,以使用时间较长的地名为准。
②参见拙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生态环境史研究述评》,《史林》2013年第4 期。
③ 参见康捷:《上海淀山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59年第6 期;青浦县文物调查工作组:《青浦县淀山湖新石器时代文物的初步调查》,《文物》1959年第4 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江苏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