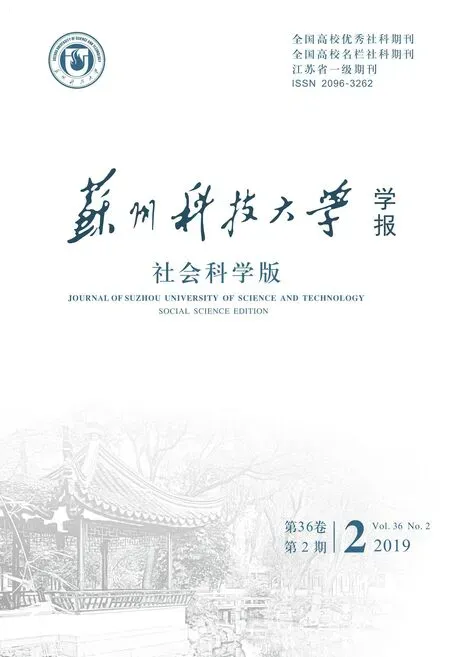武汉当局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善后处理*
郭幼茂
(陆军工程大学 军队政治工作系,江苏 南京 210014)
迄今为止,关于武汉国民政府对“八一”南昌起义善后处理问题,学界尚无专文探讨。事实上,起义发生后,武汉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查勘损失情况、判断事件的性质,在政治上极力撇清、切割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宽容态度和笼络手法坚定张发奎反共立场;在军事上调整部署,堵截追击、合力围剿南进起义部队;在对国民党其他派系关系处理上加速推进与南京、广州合流融合步伐。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使中共立足东江、进取广州的目标没能实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武汉、广州、南京三方的融合与统一。
一、极力撇清、切割与共产党的关系
众所周知,南昌暴动是共产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但打出的旗帜却是国民党的,是以国民党正统和左派面貌示人的。尽管后来的中共党内人士和中共党史研究者们对这面旗帜持诟病态度,认为“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1]96,然而,当时起义发动者领导者却坚持“国民党的旗帜还是要用的”[1]70,还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可以吸引民众和争取更多的拥护者。而在武汉当局看来,南昌暴动所持的这面旗帜容易模糊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包藏着分裂国民党武汉当局的祸心,还可能影响其政治正确及导致对南京谈判被动的可能。
为打破共产党的政治企图、维系武汉反共阵营团结统一和争取对南京谈判的主动,武汉当局采取一系列举措在政治上极力撇清、切割与共产党的关系。
一是把事变定性为共产党叛乱。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武汉当局就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电令,声称:
据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东电报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及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谋袭南昌,公然叛乱,……叶挺为共产死党,所有该党一切暴乱分子,悉萃其间。[2]
汪精卫8月5日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15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演讲都反复强调:这次事变是共产党预谋的结果,因为“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徒全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去了”[3],“共产党在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内早伏有一部分自己的党徒”[4]。8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明确指出,此次暴动就是“共产党徒,麇集南昌,煽兵构乱”[5]。此外,起义后成立的“所谓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委员半数以上不在南昌,在南昌的都有共产党党籍,七人主席团中宋庆龄、张发奎、邓演达不在南昌,掌握主席团者实际上为谭平山、恽代英,皆为共产党人,至于由主席团产生之秘书厅、参谋团、财政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工农运动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党务委员会七机关”,“其中份子十之七八皆共产党员”[6]。可见,南昌暴动纯属共产党所为。
二是发布一系列训令、通告和决议惩处暴动的领导组织者。8月2日,武汉当局以国民政府令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国民政府函的形式宣布“贺龙叶挺,着即褫夺军职,照谋叛律治罪”[2],“贺龙叶挺,应即免职拿办”[7]。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将参加暴动的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开除党籍及褫夺现职,与张国焘等一并缉拿讯办”[5]。11日,国民党中央发布通告,宣称经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开除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下令:
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委员之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开除本党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其他共产党员,列名本党执监及候补执监委员者,于树德、杨匏安、毛泽东、许甦魂、夏曦、韩麟符、董用威、邓颖超、江浩等,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8]
同日公布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议决,宣布“共产党员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一律通缉拿办,其跨有本党党籍及任职者,并即开除党籍及免职(八月十日)”[9]。17日、18日发布国民政府令,下令通缉姜济寰、肖炳章,免去刘伯承第十五军军长职并拿办。
三是通过虚构和夸大事实极力丑化、抹黑起义部队。朱培德、张发奎及其江西省当局事变后向武汉方面和对外宣传通报中诬称:“共产党在南昌杀害友军,惨杀良民”,“临走的时候,还拉夫甚多,以致人民流离满目”。
这次他们本来很可以一直到广东去,其所以要停在南昌,也有他的原故……南昌本来有朱总指挥所部两团,和程潜总指挥所部的一团,共有数千枝枪,总指挥部也有些存储,此外中央分行存着现金和纸币数十万。他们停留在南昌的目的,就是为着这些枪枝和银款……他们想出种种方法,其一是多贴标语,诋诬中央,造成一种令人迷惑的空气,其次是以奸淫劫掠,挑动人们的兽性。[4]
在起义军南进途中,他们仍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丑化诬蔑。
四是用宽容态度和笼络手段来维系内部团结统一和坚定张发奎反共立场。从表面上看,张发奎难脱南昌暴动干系,这是因为起义的贺龙、叶挺部队受其统辖,张发奎难脱失控之责。暴动前中共出于鼓动张发奎一起回广东的考虑,通过所掌握九江国民新闻等媒体,借助工会组织等,公开宣传“反对武汉政府”“欢迎张总指挥领导革命”“反对无意义的讨蒋战争”等主张;暴动后,在明知张发奎不可能与中共一起南下的情况下,出于“多玩点黄袍加身的把戏”策略考量[10],将其推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所有这些都将张发奎推到了武汉当局的对立面。武汉当局认为贺龙、叶挺虽分裂出去了,但张发奎还拥有2万多军队,仍不失为武汉方面一支重要力量;就张发奎本人政治态度和立场而言,他是反对中共土地革命政策和工农运动的。因此,武汉当局采取柔性的手段处理了与张发奎的关系。8月2日国民政府的电令和5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国民政府函都声称“张发奎初抵九江,即逢事变,应从宽免其置议”“张总指挥请免于置议”[2]等等,极力为其开脱责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8日发布的训令中,对于张发奎名列起义成立的主席团,指称是起义组织者“背签”姓名于其间,“以冀混淆视听,险恶狙诈”[5]。
为使这些处理举措能立得住脚,汪精卫披挂上阵为张发奎辩护。在8月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汪精卫声称:第一,南昌暴动是在张发奎已失去对部队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他说:
上星期本席受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两主席团委托到九江去,当时因为知道了四军、十一军、二十军的内部起了纠纷,同时张发奎总指挥请求派人去训话,庶便纠纷平息,并说内部的纠纷不解决,中央无人去,他是不敢到九江去的。[3]
以此说明由于共产党对军队的把持,张发奎对其已失去控制,故而无责。第二,共产党不可能容纳张发奎,共产党与张分裂不可避免。第三,暴动即将发生时,张发奎亲自率部向南昌进兵,竭力阻止,但由于共产党在马回岭设阻,已无法前进,故没有成功。第四,张发奎没有在其部队中彻底“清共”,是“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革命”,“又因为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已经明令保护共产党的安全”[3]。
当然,对于张发奎本人来说,也要极力地将自己与共产党进行切割,以释疑于武汉当局。为表白自己,8月6日,张发奎发表通电,极力诅咒:
叶挺贺龙,丧心病狂,甘为共党走狗,在南昌公然叛变,勾结地痞流氓,肆意妄行,实施赤化,诋毁中央诬蔑革命领袖,解散江西省政府,屠杀民众,威胁我第十师官兵附逆,围剿我友军三六九军驻南昌部队枪械,种种罪恶,罄竹难书,是党国之叛徒,总理之罪人。发奎为救国救党起见,已于本日率本方面军武装同志,声罪致讨,誓肃清凶顽,以慰总理在天之灵。[11]
9日,张发奎又致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
此次贺叶叛变中央,精神受刺激过甚,实已心灰,惟以共党阴谋,如此毒辣,为党国为人格,不能不干,屡承勉勖,自当饬率所部军队,猛进追剿,务令共党歼尽,稍赎罪过。[12]
同日张发奎又致电军事委员会和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报告第十师蔡廷锴在进贤已脱离贺叶,张下令将蔡师中的共产党员“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以泯乱源”[12],以表明自己坚定反共的立场和态度。
武汉当局在南昌暴动发生后,将暴动定性为共产党叛变国民革命,颁布一系列惩处共产党人的法令,虚构、夸大事实,丑化、抹黑起义部队,采取宽容态度和柔性手法拉拢张发奎等意在极力撇清、切割与共产党关系的诸多举措,其目的在于达成这样的结果:第一,彰显和证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7·15”事变所采取的“分共”“清共”政策的政治正确;第二,保存武汉方面军事实力,维系内部团结统一;第三,协调与广州李济深在反共方面的立场与行动,求得与南京方面融合的最大公约数。从既存史实看,这一结果基本达成,在此无须赘述。
二、调整军事部署、堵截追击、合力围剿
南昌暴动打乱了武汉当局东征讨蒋的战略部署,因应形势变化,武汉当局制定了反共压倒讨蒋的战略,调整部署、堵截追击、合力围剿起义部队。
(一)制定和实施“南堵北追”的军事部署
1927年8月2日武汉国民政府电令:
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即饬驻在赣东赣南各处驻军,严密兜截,勿任逃逸;并自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以除滋蔓,而遏乱萌。[2]
这一命令有两个方面的军事企图:一是由于得知起义部队计划南下广东的情报,通过调动朱培德部加强赣南赣东防务,从正面进行堵截;二是调动唐生智驻防湖南和湖北的军事力量,从起义部队背后进行追击。通过前堵后追,以达合力围歼之效,从而以防暴动滋生蔓延。
这一战略部署实施存在一些有利条件,“原来朱总指挥早就知道共产党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中想作乱,所以把三军、九军的两个师放在吉安”[3],即便撇开广东李济深、钱大钧所部阻截兵力不算,仅朱培德所部就在起义部队前方屯兵4万,后还有张发奎追兵2万,起义部队只有2万人(战斗兵员尚不及2万),若选此道必是两军对垒的军事决战态势。故造成“三军同九军既已有备,他们不能乘”[3],起义部队没有机会和可能实现走大路直取广州的计划。
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失败后,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和《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在分析败因的时候,都把起义部队没有走吉安、赣州和韶关直趋广州的大路看成是“严重的失着”。笔者认为这一“严重的失着”是武汉当局军事战略部署调整造成的直接后果。[13]
(二)摒弃前嫌,与广州方面合力围剿,猛进追击,务求尽歼
8月5日张发奎获悉起义部队将前往广州后,电告武汉当局请“转知广东方面的李任潮黄绍雄(竑)严密防堵”[11]。7日唐生智将张发奎提供的“叛军计划,五号由南昌开拔完毕,向抚州逃窜,限十六日到寻乌集中,向潮梅入寇,进取广州”的情报通知广东省主席李济深、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并请他们对南下起义部队“严防,无任扰窜,以靖内乱”[14]。10日李济深、黄绍竑对武汉当局的协助请求给予积极回应:
贺叶变报,为我党及政府重新结合之最好机会,武汉若能认真清党,诚意合作,我方似宜推诚相见,若仍错过,万一共党另占一地,伺隙而动,党国前途可为忧虑。[15]
这一电报所透露的信息表明,此前,广东与武汉双方的立场和关系并非一致和协调。其实,武汉当局本与广东李济深关系渊源深厚。北伐时,李济深任总参谋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四军辖有三个师及一个独立团: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独立团团长叶挺。李济深派第十师、第十二师及独立团随军北伐,亲率第十一师担任广东后方防务。但后来李济深跟着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要求第四军留守广东部队政工人员中的共产党员限期离职。李济深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为笼络部属,扩充实力以消灭起义军,对所属将领大肆加官晋爵,李济深遂升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仍兼第四军军长。武汉当局讨蒋时,也反对广州的李济深。当起义部队南进时,在反共这一问题上,双方终于取得了共识。其实,稍早之前,李济深就在韶关成立了以讨共为目的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派钱大钧4个师、黄绍竑2个师从粤北分两路入赣南堵截。在此过程中,广东与武汉方面进行了较好协调,比如8月15日李济深致电朱培德:
敝军在赣南部队,业向闽粤边境追击叶贺逆军,赣南防地,本应请贵部接防。惟因各部后方留机关尚多仍在原地,现正从事结束准备前进,一俟赶办就绪,当即通电贵部前来驻防,惟在敝军后方机关未完全结束以前,请勿派兵前来,以免发生误会。[16]
25日钱大钧部在瑞金壬田与起义南下部队激战,30日双方又于会昌再战。虽然起义南下部队取得了胜利,但由于伤员和辎重需经水路运输,乃决定不由寻乌入东江,而改由汀州经上杭取梅县。在此过程中,李济深一方面欢迎张发奎率部返广东,一方面根据战场态势进行部署。9月11日,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达作战命令,决定组成以钱大钧为右翼、以范石生为左翼、以黄绍竑为中路和以陈铭枢为东路的四路大军,要求于25日前,“集结于松口、梅县、畲坑之线,乘敌深入一举而歼灭之”[1]520。25日根据南下起义军沿韩江下潮汕欲与海陆丰农民汇合企图,李济深调整部署,命令所部向丰顺、汤坑前进,向潮安攻击。27日再令中央、东路两军向揭阳进攻,右翼军攻击三河坝。10月初,在多路敌军包围攻击下,起义部队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了失败。
起义部队不走吉安、赣州、韶关直取广州的大道而取赣东南下的小道,不走寻乌入粤的直路而改上杭、汀州入粤的弯路,不走先取梅县攻取惠州急进的捷径而采先占潮汕再取五华、揭阳等地迂缓的曲径,多次改变行动路线,是应对武汉当局采取堵截追击军事战略部署和联合广东李济深合力围剿的无奈选择。尽管学界在起义部队南进失败是由南下行动路线选择及其变动所导致,还是由中共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应该负责和负何等责任方面有争论,但如果说起义部队的失败与南下路线选择一点干系没有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也就不能不说,武汉当局的军事部署与合力围剿确实发挥了作用。
三、扩大反共共识,加速推进宁汉合流
南昌暴动之后,汪精卫借机扩大与南京方面的反共共识,求得谅解,以谋合流。众所周知,在“7·15”政变以前,南京反共,武汉方面则采取联共反蒋政策。但武汉当局领袖汪精卫本质上并非真正联共,因为他“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对工农有戒心”[17]166。汪精卫本与蒋介石存在复杂的历史纠葛,此时反蒋只是因为蒋介石主张“分共”,他“担心蒋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介石独揽”[18]86,他离开蒋介石跑到武汉,实际是带有极大的政治投机成分。周恩来说:
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由俄国回来,并没有想反蒋。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找他开会,这时陈独秀找他写了个“汪陈宣言”,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汪精卫又想不发表,而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第二天汪精卫又去开会,吴稚晖在会上大骂,汪精卫一怒,拔腿就跑到武汉去了。就这样他成了左派领袖,大叫革命的向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17]166
汪精卫到武汉后同掌握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军权的唐生智结合在一起,开始限制工农运动,力图控制武汉局势,观望风向,随时可能从动摇到背叛。1927年6月20日,经过北伐军浴血奋战而得以东出潼关的冯玉祥在徐州同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事态的发展,大大加快了汪精卫反共的步伐。“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18]94-95,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虽然武汉已公开反共,但在如何缓和与南京关系问题上,汪精卫利用了处理南昌暴动的契机以求转圜。8月5日他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上说:
共产党已经明目张胆的做了,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开战,再有谁说优容,谁就是叛徒。我们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请处分,因为我们对于容共政策,太不知变通了。[3]
汪精卫这段话意蕴很深,一方面利用暴动划线,宣布与中共彻底决裂,声称再采取“优共”“容共”政策就是叛徒,表明自己坚定的反共立场;另一方面通过自我批评的方式,暗示南京“清共”“反共”政策是正确的,而武汉“优共”“容共”是“不知变通”,以委婉的方式向南京送去了秋波,伸出了橄榄枝。
汪精卫的呼吁即刻得到南京方面的回应。南京方面通过以“中央某要人”名义公开发表对汉赣事变态度的方式,寻求宁汉双方进行合流的最大共识、最大公约数。
八月八日南京电,顷访某要人,询汉赣共产党内讧,中央抱何态度?答: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原冀合作到底,完成革命,不料共产党少数人唆使,倒行逆施,破坏革命工作,势难再容,乃有清党之举。现在共产党内讧,在中央视之,亦堪为痛惜之事。目前唐生智、朱培德、汪精卫等纷纷来电,声请通力讨共,最近张发奎亦有来电,表示合作。此间当根据前次徐州会议之蒋冯联衔马电,凡武汉忠实同志归来,自无不纳。中央决通电全国,宣布汪唐各电,声明讨共为政府目标,希望汪唐勿为共利用。[19]
这则电讯包含着几个关键之处:一是共产党是武汉和南京的共同敌人,宁汉双方在对待共产党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二是唐生智、朱培德、汪精卫、张发奎等纷纷主动来电联络南京方面,声请通力讨共,表示愿意合作;三是南京方面愿意根据蒋介石与冯玉祥徐州会议商定的条件,接纳武汉反共人士来归。
宁汉在南昌暴动问题处理上,不仅借此在政治上眉来眼去,而且在军事上也进行联络和达成某种谅解。南昌暴动发生的第三天(8月3日),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就致电南京方面的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请求“弟等分道追剿,切望诸兄通力合作”[20]。蔡廷锴所部原为十一军第十师,在战斗序列上受张发奎节制。蔡廷锴在江西进贤脱离叶贺后,曾发电张发奎“请示进止”,张去电令除将共产党员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外,“并着该师向进贤会合,追剿叛逆”[21]。但蔡廷锴率部没有遵照张之命令,而是开到浙江余江集合“听候总座及陈军长真如命令”。此后陈铭枢“为蔡师(蔡系陈旧部)事于昨日午后晋谒蒋总司令,请示机宜,昨晚即偕蒋师长光鼐等,乘九时半特别快车赴沪,转往浙东,与该师接洽一切,想陈氏抵浙后,该师必唯命是听也”[22]。蔡廷锴不服从武汉方面的命令,开往浙东投蒋,武汉当局竟未予谴责或采取其他惩处措施,此事意味深长,充分折射出宁汉在反共问题上的默契。8月12日,由于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逼迫,蒋介石只得辞职离宁。19日,武汉政府宣布迁往南京,宁汉合流实现。
总的看来,南昌“八一”起义之后,武汉当局采取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善后举措,基本达成既使中共南下失利又加速推进宁汉合流格局形成的结果。
——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