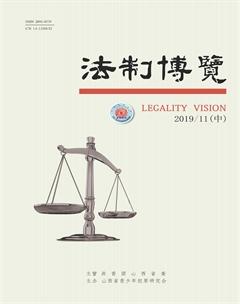我国海上保险告知义务之研究
摘 要:由于缺乏体系化机制,我国海上保险法律规则存在法律移植漏洞、逆序立法和法律更新的不足,法律对告知义务的告知事项、义务期间等内容的规定存在法律间隙。笔者通过对各种学术观点的比较、分析,结合实践提出了多种告知模式并存的新模式、多个告知时间段、明确“合理谨慎”的形式要求和“影响”程度等改革建议。
关键词:告知模式;海商法;体系化
中图分类号:D922.2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32-0057-02
作者简介:邱楠(1995-),女,汉族,江苏南通人,法律硕士,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民商法。
海上保险作为最早发展的保险交易类型,属于财产保险的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十二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所构建的海上保险告知制度存在规范裂隙,在具体案件中不能明确告知义务的主体、告知内容、告知时间等内容。所以,我国海上保险相关法律需要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海商法》和《保险法》规定的告知模式不一致,且《海商法》并未对主动告知的“重要情况”作出明确规定,仅要求被保险人在合同订立前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告知内容的范围模糊不清。对此现状,学者们的看法不一,存在争议。
二、我国告知义务法律规则现状
(一)告知模式规定不一致
根据《海商法》确立的被保险人主动告知模式,责任的主体是被保险人,告知时间为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需告知的是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在正常业务中会影响保险人的重要情况;根据《保险法》确立的投保人询问告知模式,告知义务的主体是投保人,投保人可能为被保险人,保险人询问的情况是通知的内容。
比较这两种不同的告知模式的可行性,一方面,我国《海商法》第222条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负有主动的无限告知义务,另一方面,询问告知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在立法技术上优于主动告知的立法模式,避免了不能确定的问题的出现,然而,笔者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没有从海上保险法律一体化的角度解决海上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本质存在的信息不對称问题。为了解决海上保险法律一体化的不足,人们应当将最大诚信原则纳入海上保险法律规则修改与完善的指导精神中,制定一部体系化的海上保险法律。
(二)关于告知义务期间之争议
朱作贤认为,告知义务的时间范围是从开始提出投保要求到保险合同订立前,但是李微认为,仅凭这两部法律不能全面地规定多种情况下的告知义务的具体时间。在合同复效或者合同变更导致危险增加等特殊情况下,合同订立的实质条件会发生变化,这会导致新的条件下的新的未订立的保险合同的出现,此时保险人有权作出选择,决定是否订立新的合同。所以,为了保险合同的订立,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应该负有在合同变更范围内将新产生的重要情况告知保险人,促使新的合同成立的告知义务。
关于前合同告知义务,《海商法》并没有明确这一时间范围,只规定了在“合同订立前”的告知义务,那么是否存在其他阶段的告知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案例①,我们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告知时间范围的解释是“投保时至保险合同成立前”,即在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保险要求后,就要开始履行告知义务。再比较《海商法》和《保险法》的规定②,前者规定“达成协议”后合同成立,而后者规定“同意承保”后合同成立,两者存在不一致。现实中由于当事人对“达成协议”的解释有误,产生了关于签发保单是否为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的争议。③
(三)关于“影响”程度之争议
关于对告知义务主体违反告知义务对结果的影响程度的规定,《海商法》第222和223条第2款中只规定了两个“影响”,而《保险法》第16条第5款的规定为“重要影响”,两部法律规定不一,从文义解释上,后者比前者要求的“影响”的程度更高。
对此,海商法界的三种学说:有风险增高可能性的影响、纯粹性影响和决定性影响。相比这下,决定性影响更有利于维护各方公平利益。“决定性影响”的包括范围有限,只有在告知义务主体未告知保险人对承保决定或保险费的确定有决定性影响的重要情况时,保险人才有资格解除合同,可以防止保险人凭借滥用权利解约。《保险法》第16条第2款的规定就是按照“决定性影响”之标准,但是该条第5款的“重要影响”并不明确。
三、告知义务体系化完善的建议
(一)新型告知模式
为了促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诚信对话机制,笔者认为,立法者可以在修改《海商法》的告知义务相关法律规则时以主动告知为主要告知模式,以询问告知为辅助告知模式。主动告知模式更能体现最大诚信原则,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不仅不能有主观恶意,还要主动地如实告知保险人相关的重要情况。
其次,即使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根据“合理查询”义务及时地如实告知了保险人自己应当告知的相关重要情况,还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这就需要保险人进行询问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因为要想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了解保险人的全部心理想法是不可能的。如果应用询问告知模式,能够弥补主动告知模式的不足。
(二)多个时间阶段的告知义务
《海商法》告知义务在时间上的规定应该包括订立合同前和特殊情况这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海商法》规定的“达成协议”应该解释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签发保险单并非海上保险合同成立所必备的要件。由于当事人对《海商法》第221条的“达成协议”的理解容易发生偏差,应该修改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以不达成书面协议,以避免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在字面上的局限性解释而产生的误解。在第二个阶段,在合同复效或者合同变更导致危险增加等特殊情况下,被保险人或投保人负有在合同变更范围内将新产生的重要情况告知保险人的义务。
(三)告知形式必须合理
我国《海商法》对告知义务的实质要求较为完善,但是由于我国在海上保险法领域缺乏一部体系化的法律,缺乏对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的详细规定。立法者可以通过借鉴英国,规定告知义务主体的告知形式必须清晰易懂且合理。④立法者还可以修改告知义务主体的履行义务的具体形式,例如填写书面表格、按时间顺序、重要性大小的顺序进行整理后再提交给保险人等方式,这样一方面,保险人的负担将会减轻,双方之间也能够形成良性的沟通氛围,另一方面,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能够明确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是否正确履行义务。
(四)“影响”程度之区分
在对主观状态的区分问题上,尽管我国《海商法》相比于MIA1906已经较为详细,但是和《保险法》相比,《海商法》在这一方面还不够科学还要继续完善,应该借鉴《保险法》划分为故意和重大过失,并排除保险人在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不存在故意且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的合同解除权。
在后果的严重程度区分问题上,司法解释可以进一步明确“决定性”影响之标准,并可以借鉴“保险法”第16条第2款,在《海商法》第223条新增关于被保险人违背告知义务的“影响”的影响程度的规定,或者用“决定性影响”替代该条的“影响”。
四、结语
从理论的角度,当初订立的规则现在是否能够完全正常适用,这是海商法学术界一直研讨的重要议题,当初参与制定我国海商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学者也普遍呼吁修改现行法律。当前学者研究的焦点是如何完善《海商法》的相关规定,从而明确告知义务的告知模式、告知范围、告知的时间阶段以及告知方式,明确各方的权责。
因此,立法者需要对告知义务进行适应当下海上保险业发展的、全方位的综合考量,细化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和形式要求,进一步完善告知义务法律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诚信对话机制,中国海上保险业才能更加健康有效的发展。
[ 注 释 ]
①《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11期刊登案例:江苏外企公司诉上海丰泰保险公司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
②《海商法》第221条及《保险法》第13条.
③案例:福运物流有限公司与中国人寿曲靖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案例索引:(2013)民申字第1567號.
④2015 Insurance Act第3条第3款第2项:”which makes that disclosure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be reasonably clear and accessible to a prudent insurer.”
[ 参 考 文 献 ]
[1]司玉琢.海商法.第3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98.
[2]李微.海上保险合同当事人告知与说明义务的法律问题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4.11.
[3]王海波.论中国海上保险法与一般保险法之协调[D].上海:复旦大学,2012.83.
[4]傅廷中.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再检讨[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2,1(1):36.
[5]朱作贤.对海上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误读[J].世界海运,2015,38(6):44.
[6]巴里斯·索耶,郑睿.英国保险法改革对《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影响[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4,25(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