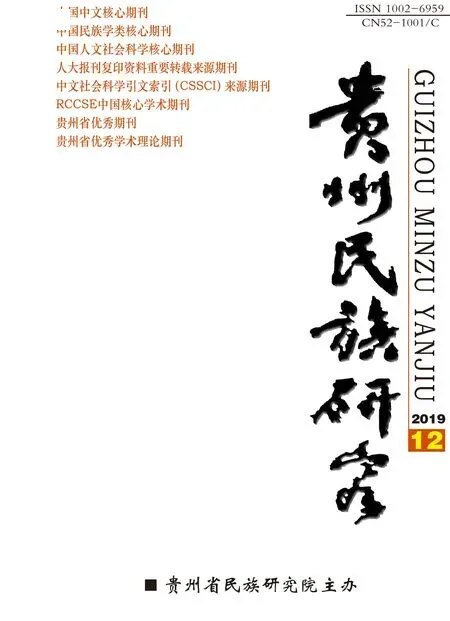对话“斯科特”:是逃避?还是规避?抑或是适应?
罗康隆 舒 瑜 麻春霞 杨庭硕
(1.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 650500;2.吉首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湖南·吉首 427000;3.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201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室与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开展为期一周的“生态文化研究工作坊”,此后又有三次吉首大学博士学术沙龙,期间除了对生态文化与田野调查进行了深度的交流,更多地涉及到了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的讨论。在讨论中认为,对“赞米亚”区域的研究,如果换一个视角,也许会有更多的思考。比如从生态民族学的视角出发,就会对该书的“逃避”做出更为符合该区域不同民族文化事实的阐释,也许这样的阐释更具有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于此,四位学者从生态民族学角度对“斯科特”的“逃避”进行了对话:是逃避还是规避生计风险?是逃避还是生态适应?现将这些对话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罗康隆(以下简称“罗”):我想谈一谈我对斯科特这本书中逃避的理解。首先,逃避这个词成为斯科特研究赞米亚地区最为关键,也是最有学术魅力的一个词语。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因此,本次的学术工作坊我们不妨就斯科特的“逃避”展开一场学术讨论。我先做一个引语,仅作为个人的一点见解来抛砖引玉,以引起大家的兴趣,聚焦于《逃避统治的艺术》著作中斯科特有关“逃避”的思考。美国学者James Scott 于2009年出版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一书,受到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得到许多年度出版大奖,予以肯定,多种语言的译本同时诞生。就中文译本而言,目前已有的译本包括大陆地区《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2016年,王晓毅译,三联书店),以及台湾地区《不受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国家主义者的历史》(2018年,李宗义译,五南出版社)两个版本。引用与围绕该书讨论的相关文章,难以枚举,已积了相关的数量。为什么在James Scott的诸多专著中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受到最多的注意,会受到中国学界如此大的重视。我想国内学术界之所以对该书的重视,或许就是该著作中“逃避”二字在吸引中国学者的眼球。因为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站在“中原”“王权”的立场上我们看到的多是“怀柔”“归化”“镇宁”“安化”“羁縻”等词汇,而极少用“逃避”一词来分析该区域众多族群的历史。
麻春霞(以下简称“麻”)其实,James Scott在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一书的见解有其贡献,但也有其限制。斯科特取得的学位是政治学博士,但是对长期在亚洲高地与岛屿进行民族志研究的James Scott而言,我认为,他的作品具有更多的“社会体制与空间的结构对比性”,而缺乏纵向的“历史事实分析性”。在结构对比的过程,由于长时段的许多差异无法被共时态的结构性吸纳入他的研究之中,因为该书中有太多例外与差异,也就无法构成一种清楚的结构,于是对该区域族群的生存样态也就无从辨识。说明白一点,就是斯科特把该区域的族群规避生计风险看成为“逃避”,甚至把适应“山地”文化策略也看做是“逃避统治”,并且还冠以“艺术”之名。请各位就这个问题谈谈你们的看法。
杨庭硕(以下简称“杨”):熟悉中国历史,特别是西南区域史的学者,很容易从斯科特的描述中找到反证与破绽。鉴于“国家”一词的不确定 性 ,James Scott 在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一书中大量地使用了另一个词汇“政体”(polity),以此与国家互用,保留了对于“国家”一词的松散理解。包括具有松散政治权力的各种形态“王国” (kingdom)都是“政体”的一部分,而非一定要是大型的帝国或是晚近的民族国家。在此前提下,熟悉中国西南历史的学者可以轻易地指出,难道高地社会与高地人就缺乏对于建立“政体”的政治热忱吗?或是事实吗?当然不是。藏族形成中央集权社会的时间可以推溯到唐代之前。唐宋时期云南有南诏与大理国的建立。如果我们把“政体”的解释再放宽一些,传统彝族社会具有高度的阶序性,贵族家支通过大量捕捉奴隶形成家族性的武力,进一步对于其他非贵族家支和其他民族的支配。彝族这种普遍可见权力的集中性与武力的可支配性,让我们很难说传统彝族社会不具有“政体”性质。除此之外,元、明以来,西南地区土司制度的建立,大量由高地社会当地土著民族“权力者”建立的土司治理体系,也无法不被视为是一种“政体”。
舒瑜(以下简称“舒”):James Scott在本书中提出的空间概念“赞米亚”,原本由荷兰学者Willem van Schendel于2002年提出,是一个包括喜马拉亚山西缘、西藏高原,中南半岛高地的跨国区域。James Scott进一步指出这个区域包括了东南亚诸国与我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四个省区。[1](P17-28)这种地理上的亲近性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然而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一书内容对于此一地区居住于两种地理区人群的政治理解,却与中国学者的认识似乎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两种人群分别是居于丘陵、山区与高原地带,即“赞米亚”地区的人群,其最重要的文化与政治特征是尚未被民族国家所完全纳入,而处于一种非国家的前国家社会条件,生产条件落后、缺乏文字、流动性大等等。另一种则是低地的国家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不断通过战争扩张国家的版图,对于境内的人群进行服劳役、征税赋的治理。对于James Scott而言,高地的非国家社会与低地的国家社会处于一种辩证关系,高地人是因为拒绝国家治理,而选择了来到高地。换言之,高地人具有与低地人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
罗:斯科特本身不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最多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学学者,他对中国历史是不懂的,但斯科特也一直在声明,他这本书《逃避统治的艺术》适合于18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区域研究。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西方是不同的,中国历史是一个文化渐染的过程,是一个在“文化中国”的历史脉络下延展的中国历史,所以中国边疆的形成是一个“文化”的过程,中国是以文化来区分历史边界,不像西方那样靠战争、殖民或者其他方式来划定国家边界。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边界会因文化的影响程度而具有变动性,所以我们的边界是不断变动的。而这些变动又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来实现的,比如边郡制度、羁縻制度、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流并治等,到今天这些制度是与我们的文化综合的进程是契合在一起的。正是因为这种历史背景,而斯科特对其知之甚少,或者说略知一二。因此他在他的这本《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只能是以他所熟知的西方历史观来看待赞米亚这个区域变化,因而在他的论述中对族群、政权强弱实力的消长、中国与东南亚、乃至南亚之间空间体系都显得十分模糊而不清晰。因此,我们在阅读他的这本著作时,需要用一个长时段的中国式的历史解读方式,才能把这些问题解读清楚。而更具有诱惑性的是,斯科特在面对这一区域漫长的历史却使用了民族学文化结构的笔法,以现今的所有民族的状况来推演到历史过程中去,导致大家在阅读时感到模糊和吃力,从公元前一下跳到18世纪,然后又到了现在。所以这个历史的维度需要自我梳理,可能才能够正确对话。
杨:斯科特的这本书,讨论的跨度太大,2000年的时间,中国都换了几十个王朝。所以读者在阅读该论著时,要知道这句话的背景是具体在哪个时代,哪个地点,需要定点定位,这样一来,所有的骗局暴露无遗。所以熟苗给娃娃祈福的挡箭碑,这种将文字神圣化的行为肯定是后期的事情。至于斯科特说部落都是模糊概念,因为他把时空错乱了,概念当然就模糊了。将文字神圣化以后,你还讲部落,部落的概念肯定不清楚,因为它已经导向了王朝,成了王朝的臣民以后,部落在哪里?当然也就不清楚了。所以,在研究大跨度历史过程的专著时,还有一本书是濮德培的《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这里的万物并作讲的就是游耕文化[2]。这本书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西方人在治学当中,因为美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而我们是几千年历史,他把几千年压缩到一百年,那么一切都是混乱,而且还将这种混乱说得津津有味,别人也都相信。但中国人可能不会相信,因为他所说的哪一句话,是哪个时代出来的内容,我们一清二楚。所以这个时间和空间的界定,或者是事物类型的界定非常重要。
罗: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段其文化取向会有差异。就以斯科特该著作所涉及到的“赞米亚”地区而言,在明代以前,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这片土地的管理,更多的是自北而南的路线。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以旱地作物作为主要文化的交往,这个交往是北方旱地文化和西南地区的山地文化的同质性是可以有交集的。但从明代以后发生了转变,该区域族群和汉族文化的交流,主要是从东到西,方向发生改变。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异质性,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越来越大?因为刚好在东南地区,所建构的中国(华夏或汉族)文化,是以水稻农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历过宋代的历史发展,水稻已经成为这个区域汉族的主业,支撑起了国家的强大与强盛。到了明代,就达到了“苏杭熟,天下足”的程度。实际上,农耕文化已经作为基础。这个时候,进入西南的文化,与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是不对接的。那么,这时,国家的同质和地方的异质化问题出现了,国家如何对地方进行管理?通过税收是最好的办法——主要征收稻谷。因为只有稻谷才能长时间地保存,但是像芋头这种山地挖出的块根类作物弄干后,要作为税赋上交,可能就有难度,至少比谷物要难得多。既然西南地区要纳入国家地区的行政管理,从明代开始,云贵也好,湖广也好,建置了国家的行省制度体系,纳入国家的真正版图。这里以前可能是边郡、羁縻、土司等形式,一旦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管理,这个时候可能产生斯科特所讨论的问题了。这些族群在国家强大的政治面前,他们是去是留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那么当时的选择是有很大空间的。要留下来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得按照汉人的方式生活,以农业或者说水稻为主。如不服从国家管理,仍然可以进行自己传统的生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是希望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中,至少可以扩大税源,获得更多的财富。正是因为有多族群不愿意改变自己传统的生计方式,国家难以获得充足的财富,于是,国家才在赞米亚地区开始建立大量的卫所、屯田等,使得中原地区的士兵和家属进入该地区。所以,后来看西南地区这些城市的兴起,包括县城,甚至包括乡镇,实际上都是在卫所、屯田的聚居点上发展起来的。
杨:对,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错乱了时间和空间范畴的界限。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长时段、整体性、系统性的范畴,而逃避或者说民族迁徙是个短暂的时间,或者说这个逃避针对的某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是某一个“点”形成的事情,而做出的一种行为。但文化是永恒的,一个族群(民族)适应了河谷平坝,对于河谷平坝该族群已经建构了非常精致的文化,你叫我逃避,逃避的结果就是饿死。同样,山地民族吃块根类作物,逃避的结果也是一样。20世纪50年代,我国土地改革时,贵阳市人民政府好心将水田分给苗族,但苗族都不要,苗族把分到的水田偷偷地卖给布依族。他把一个整体性的“面”上的立体事情,用一个简单的短暂时间过程的行动来并列,这在逻辑上以偏概全。因为逃避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线性的过程,但是理论文化建构是一个立体的过程,线性的历史事件无法替代整个文化。因为逃避以后,他要把文化“背”着走,然后到了一个不能够适应以前文化的地方,肯定无法生存,也就说,如果不能把文化带走,作为一个族群是根本逃不掉。
舒:我想用陶云逵在1936年的研究成果来做进一步的分析,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一文中明确指出:“云南土族分布的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不同的高度,居住着不同的人群。这与云南地理形态很有关系,就是说在不大的区域中,地形的高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为中国任何省所无,亦为全世界所少见。”[3](P113)陶云逵进一步发现云南气候与海拔的关系更大,西北部的江边也会很闷热,而西南部的山巅也是较凉爽的。“这种因为高度不同,而生的气候变异,以及因此而生的其他自然现象如植动物,农作方法的不能一律,是促成云南各民族的分布在垂直上有分别的原因之一。”[3](P121)在云南西南部,摆夷住在低热但肥沃的山中平地及河畔,采用“集种法”,使用水牛犁地,利用人工灌溉及筑阶形阡陌;藏缅语各族的生活样法大体相同,在凉爽但贫瘠的山头上从事“广种法”或刀耕火种,他们不会利用人工灌溉,没有阶形阡陌及犁与牛之利用。摆夷不会去争山地,他们的集种法需要平坦的地形且有川河流贯其间,在倾斜度过高的山坡则无所用其技;藏缅语族人群的广种法需要极广的区域,有森林,少莠草,山地是最合适的。他们亦不能适应低热潮湿的气候,所以摆夷与藏缅语族人群由此垂直分布而能相安无事。可见,生存方法经过长期的选择而能完全适应某种环境,要使一个人群去适应新的气候或者接受农产方法的改良,都是不易的事[3](P129)。该区域内族群的生活样法、身体对环境的适应、农产方法等,并不是被他族所迫而不得已的选择,而是一种对所处生态环境的有效适应。
罗:对,文化构建是一个主动过程,人们认识、改造、利用这个环境,然后生生世世与所处的这个环境相依为命。如果被迫逃避,放弃了一切,另搞一套。是几十代人的事情,一代人是无法完成的,不是一代人能够逃避掉的。在西方人写的著作当中,像类似的这种矛盾,有很多,不仅仅是这本书,而这些都是最明显最低劣的逻辑矛盾。但是外国人看不懂,因为他们不懂中国历史。比如藏族为了应对与利用青藏高原环境而建构起了独特的藏族文化。,与其自然生境之间呈现出多层面多形式的综合适应状况。在生境资源利用方面,藏文化以其特有的农牧相辅方式,从耕牧品种到耕牧制度,以至于技术传承相联系的一整套生产范式最大限度地利用气候多变的高山荒漠资源。从习俗方面看,为了对应严寒多变的气候,衣着制度中披着长袍,防日晒的润肤酥油,厚重多功用的毡氆,共同构成了足以抗拒恶劣气候的综合体系。饮食方式中,为克服高原气压低的环境,食物制品中采用了烘焙炊事法,肉食为保证特需维生素不至于在加工中散失,往往采用生食,乳制品的酸制法,起到一乳多用的效果,饮料中的酥油盐茶,目的在于有效地调节身体内的盐分及水分平衡,并且是调节食品营养偏向的手段之一。严寒的气候制约了人口的密集,为辅助行政力量的不足,宗教信仰在行政上产生较大的平衡作用。宗教的影响又在衣着上的噶乌得到反映。在葬习上又随各地的需要,而分别呈现了天葬、水葬、火葬、肉身塔葬等一系列复杂制度。在文学艺术上,一方面以宗教形式发展起锅庄、堆谐、璇子等舞蹈样式,另一方面这些舞蹈成为世俗集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样式中的热巴、藏戏、析谢同样为僧俗并用。藏文化的知识结构中除了各种各样教育传授上的宗教形式和依附的内容外,又明显地反映出知识积累偏向于生态认识,哲理思维偏向于对自然的综合性领悟而不重在度量的客观精确。伦理观表面上打着宗教烙印,但却一直紧扣着对现行一切适应生境现象合理性的阐释。使藏族在充分利用自然与生物资源的同时,又能精心维护所处自然生境的安全[4](P3-4)。
杨:这个说法很对,我一再强调。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非常完备和严密,生活也极度舒适,但是从汉文化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落后的,我们看到的史料是说他们落后,但他们是否真的落后,有待进一步研究分解。从我们田野调查来看,事实上是相当完备和精巧的。人类面对所处的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通过人脑的处理来输出有用信息,去应对生境的变化。人类为了其生存发展延续,文化这样一个信息系统在选择、认识、应对自然生境时,就可以建构出与自然生境相关的文化事实出来,诸如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刀耕火种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等。在这些文化事实之下还可以细分出若干的文化要素。比如狩猎文化又可以分出辨识狩猎对象、狩猎空间、狩猎时间、狩猎工具、狩猎队伍、猎物分配、猎物食用等。采集文化也是如此,可以分出采集对象、采集空间、采集时间、采集工具、采集物的使用等等。刀耕火种文化也可以细分出刀耕火种的区域、路线、时间、作物种类与匹配、作物收割、作物加工、作物食用、作物储存、种子的保存、野兽的驱赶等。游牧文化也可以细分为游牧种类与匹配、游牧线路、草原的牧草种类、森林与水源、牲畜肉制品、奶制品、皮毛制品、有害野生动物的防备与驱赶、有害天气的规避等。农耕文化可以细分出耕田的建构、作物的培育与选种、作物的栽培、中耕管理、收割与储存、加工与食用,以及与农业生产周期匹配的24节气等。比如人类之所以这样穿着服饰,是因为气候、习惯、信仰等作用于大脑,然后经过人脑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游牧民族多居于高原,气候多变化,因此多以皮毛为服饰原料;赫哲族用鱼皮做服饰原料,因为他们主要以渔业经济为主,便于取材;山地民族多以植物纤维做服饰原料,因为他们时常与这些植物打交道,对植物纤维比较熟悉,而且取材便捷。这无不体现出特定民族对所处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智慧。
舒:上山,就是逃避吗?其实,我们还要区分“山下”“上山”与“在山”的文化内涵。我认为斯科特把赞米亚地区“在山”的族群理解为是“上山”而来的族群,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我认为“山下”“上山”与“在山”都是民族文化适应其所处生态环境的结果。英国人类学家利奇20世纪40年代在上缅甸地区所观察到的崩龙人(今称为德昂族),正是在山上种植茶叶为生。典型的崩龙人是居住在东彭邦(缅甸的北部掸邦)的山地人,他们用通垭(游耕)的方式种稻,但经济上主要还是依靠种茶以从外地换取稻米和现金。崩龙人讲不同的方言,都源自通用语——崩龙语,与其他群体的语言都很不同。崩龙人虽然是山地人,但依靠长期以来确立的茶叶贸易,所达到的生活水平也与掸人相当。在利奇看来,崩龙人的生计方式更接近于克钦,而信仰和政治组织上又更接近掸人。他们是信仰佛教的山地人,这一点使得他们既不同于掸人,又不同于克钦人。利奇敏锐地注意到,处在掸人与克钦人之间的崩龙人,他们显著不同的生计方式就是种植茶叶。而之所以选择种植茶叶是因为这个地带谷物种植的收成很差,出于贸易的需要,栽培茶、罂粟、黄莲这样的经济作物成为人们的首选。崩龙人的富足正是来自茶叶贸易,并依赖茶叶贸易换取粮食。“以前东彭的崩龙人山地邦有一条法律,贸易商队除非载着米或者盐来,否则不准进入邦内买茶。”[5](P224)这一基于特定生态环境的生计选择,决定了山地的崩龙人必须得依靠谷地掸人提供的米粮为生,因此,这一生计选择其实是嵌入在区域民族关系的格局之中。缅甸境内的德昂族长期保持了种植茶叶的生计方式,时至今日,他们依然种植茶叶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但德宏州境内德昂族的生计方式却发生了变化,茶叶不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根据三台山乡出冬瓜村口述史资料,从缅甸回迁后只能居住在半山区。半山区因水田数量稀少,没有固定耕地,长期以来利用坡地择肥而开,轮荒种植,形成以旱谷生产为中心的轮作制度。旱地轮作制围绕着主要作物利用各种作物的特性进行巧妙的安排,使前后作物之间及各种作物相互之间关系协调,互相有利,以提高或恢复地力,达到多种多收、全面增产。可以认为,德昂族生计方式的变迁很大程度是适应其生态、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
罗: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湘西苗族先民们在明代以前主要是以刀耕火种兼及狩猎采集为生。明代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强化土司制度,在湘西地区推行屯田、上缴谷米等政策,这一政策也影响到苗族地区,开启了在湘西苗族地区开辟稻田的先河。在湘西地区种植水稻最关键的就是要克服自然生境中的“水温”与“日照”问题。湘西苗族主要聚居在腊尔山与吕洞山,这里山高谷深,森林茂密,是刀耕火种与狩猎采集的好地方,但不是农耕的好出处。在这里要种植水稻,要么要依山修筑层层梯田,要么在沟谷修筑水坝。这里由于森林密布,日照不充足;这里高山峡谷,水温很低,要种植水稻就必须克服这两大生态系统的缺陷。于是,湘西苗族在文化的作用下,应对如此的环境,采取了如下的措施。首先砍伐森林,使开辟的农田有充足的阳光照射,以满足水稻的光合作用。再次在农田的底部铺设林木,并在铺好的林木之上填充砂石,尽量抑制地底低温泉水渗出,以解决、缓解稻田水温过低的问题。这就是湘西苗族“铺树造田”法。以这样的方法使大片深水沼泽地改造为良田。为了实现稻田的产量稳定,与此同时还实施了复合种养、育林蓄水、施自然肥等方法,今天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为了防治野兽尤其是野猪等大型动物前来糟蹋作物,苗族居民开始从刀耕火种的半山腰地段往农田周围搬迁,形成定居在农田周围的村寨,以至于村寨聚落的公共空间,如道路、桥梁、水井、墓地等也开始被建构起来。苗族的住房也由原先易于搬迁的叉叉房演化过渡到稳固厚重的石板房、木屋房、泥木房。这一变迁见证了湘西苗族文化与自然生境的“偏离”—“回归”的耦合历程[6]。一旦这样的耦合关系确立后,苗族的自然生境也就被模塑出来了。
麻:斯科特在他的著作也谈道:“山地社会也有生产的剩余,但是他们没有用这些剩余去支持国王或和尚。由于缺少大规模、持久和吸收剩余的宗教和政治机构,所以在山地的社会学金字塔比谷地社会更扁平和地方化”[1](P10)。就是这样一个“剩余”的关键词,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社区和社会是不贫困的。他们有生产的剩余、有财富的积累。这犹如萨林斯笔下所描述的“原初丰裕的社会”的生活场景。这样的“生产的剩余”在赞米亚地区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并非都呈现出比谷地社会更扁平和地方化。
罗:这样的事例,我可以再举一个案例来证实。清代雍正年间,在开辟千里苗疆进程中,为确保军需物资从清水江进入苗疆,在接近苗疆的清水江中游的锦屏地区的茅坪、王寨、卦治三个码头开设木行,一是“抽收捐饷”,年交白银二千两,提供军饷;[7](P35P67-75)二是“例定夫役”,护送军需物资,“雍正年间,军略张(广泗)大人开辟清江(今剑河)等处,兵差过境,愈难应付,酌于木商涯(押)运之附寨,三江轮流值年,量取渔利,永资公费,沿江别寨均不准当,咨部定案,有碑存据”。所有兵差军械辎重往返概由三寨抽夫输送,夫役之重数倍于府属差役,三寨民人不堪重负,黎平府等“各宪”“给示”三寨当江取利,以之补助夫役费用。于是贵州巡抚为例定三寨夫役再次明确三寨轮流值年设行当江,木材贸易开始兴起。清朝一代,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持续稳定进行,木业兴旺不衰,中原地区“三帮”“五勷”经营木材商人,皆溯江而上至清水江流域侗族地区,每年来茅坪、王寨、卦治三江购木植者不下千人,贩运木业极盛。据光绪初年编修的《黎平府志》记载“黎郡杉木则遍及湖广及三江等省,远省来此购买……每岁可卖二三百万金。”[8](P1419-1420)由此可见,当时木材贸易的繁荣景象。由于木材贸易不仅给江淮木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给侗族苗族群众带来了极大的实惠,这刺激了该区域侗族苗族群众对山地林木开发利用的积极性,驱使清水江沿岸的侗族苗族林农对林木人工营造的萌动,人们开始了对林地的更新,开启了人工营林业的先河。侗族苗族林农历经数百年劳动经验的积累,发展出了独特的营林地方性知识体系,包括炼山整地、育苗植树、林粮间作、抚育管理、砍伐运输等知识体系。与此同时,随着人工营林业的发展,在侗族苗族文化网络中对其文化进行构造,使侗族苗族社会建构起了适应人工营林业发展需要的新型文化。国家对地方的治理依托了宗祠文化进行地方的“儒化”,使得清水江流域两岸至今祠堂林立,地方社会精英在“文字入疆”的引领下,以林地契约与地方教育的方式规制了地方社会,出现了市场关系中伦理道德、语言文字、家族社区组织、土地资源配置方式、林地保护规约、民间信仰、交往行为、服饰时尚等等,都发生了系统的全面的文化事实体系改组,实现了文化的再构造与社会转型。
舒:我以滇西南多族共生为例,来说明该区域多个族群的互动关系并非是“逃避”,而是一种生计互补,是一套规避生计风险的文化策略。首先,在民族分布方面,傣族占有了怒江、澜沧江河滩平坝,直接阻滞了周边各族进入同一自然生境的速度,增加了进入的难度,使得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取向逆平坝而行,往高山迈进。其次,在经济活动上,傣族的稻作经营,其产品盈余将流向周边各族,而缺乏的山地农畜资源又必然招来外族产品。再次,在语言使用方面,由于傣族处于交通枢纽地带,经济实力雄厚确立了其语言在滇西南族际中的介语地位,直接引起了周边各族语言的趋同性发展取向。最后,在社会组织方面,历史上傣族的土司领主制度及其行政控制能力直接作用于周边各族,当地不少民族的头人、山官都受治于傣族土司,又通过傣族土司受辖于中央,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解放前。民主改革虽然废止了土司制度,但是傣族在当地的政治中枢地位却仍然持续着。其实,傣族在多方面影响着其他民族的同时,也受到了外族的多方面作用。在产品上,傣族不断吸收景颇族提供的柴薪,布朗族的茶叶,汉族的工业品,阿昌族的铁器,苦聪人的猎物,佤族的山地粮食。政治上,傣族又得靠各族山官、头人、寨老去节制傣族与景颇、哈尼、基诺等民族的协调关系。宗教上,布朗、阿昌、德昂等民族是傣族小乘佛教的传播对象,又是傣族寺院的资助对象;德昂族、佤族的自然崇拜又渗诱进入傣族的佛经义理,成为傣族僧俗文学的宣讲描写对象。
罗:看来我们要深入讨论的话题还很多,可以拿来反驳斯科特所理解“逃避”的事例不胜枚举。在赞米亚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从本质上规约了住居在该区域的族群,其生计方式不可能划一。不同民族生计方式的多样性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又是人类活动的必然结果。生存在赞米亚地区的各个族群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凭借各民族特有的智能和智能传递建构起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以对付赞米亚区域千差万别的自然生态环境,去实现共处该区域各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文化成为人类的适应方式,文化为利用自然能量,为人类服务提供了技术、以及完成这种过程的社会和意识方法。”[9](P20)也就是说,在特定文化规约下的民族生计方式也决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无数多种。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文化的多样性,没有多样文化规约的人类多样化的生计方式,也就不会有人类的今天和人类世界的繁荣。由于任何“一种文化种系发生演变的原物质来源于周围文化的特点、那些文化自身和那些在其超有机体环境中可资利用或借鉴的因素。其演变过程便是对攫取自然资源、协调外来文化影响这些特点的适应过程。”[9](P20)如果说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的话,那么各民族文化规约下的生计方式便会随着自然生境的不同,而走上不同的道路,随着自然生境的变迁,其生计方式也将发生变化,而呈现出系统性差异。人类生计方式的系统性“差异在于整体定位的不同方向。它们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追求着不同的目的,而且,在一种社会中的目的和手段不能以另一社会的目的和手段来判断,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们是不可比的。”[10](P173)因此,各民族文化在适应不同自然生境所形成的特有生计方式,对于特定自然生境而言是极其有效的。
今天的讨论就此为止,期待以后有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