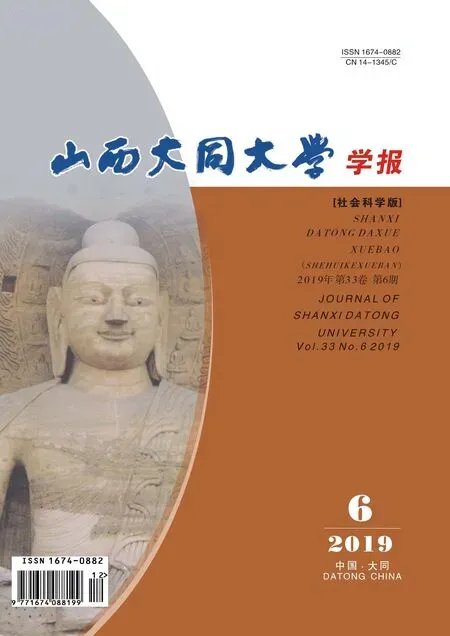城镇想象与地域传奇
——刘宁小说印象
郭剑卿,陈 曦
(1.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2.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近年来,在表现变革时期的生活和世道人心,讲述中国背景下的山西故事方面,晋军文坛出现的新元素给山西文学带来新的生长点。在从乡村文学向城市文学的历史转型中,相较于山西文学悠久的乡土经验书写历史,“城市题材创作一直是山西文学的弱项,尽管‘晋军’作家中的钟道新、蒋韵等创作了不少表现城市生活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作品,但并不占据山西文学的中心位置。直到山西的第五代作家才改变了这种状况”。[1]
一、城镇框架内的地域“传奇”
作为山西文坛第五代的新锐作家之一,刘宁的创作毫无疑问是属于城镇文学一脉。城市经验书写不但是他的长项和兴趣所在,也是他的突破口。刘宁的故事和人物基本来自“石板街”和“唐州”。我猜测,石板街取自作者故乡,一个介于雁门关和忻定盆地的小城小街,那是一处号称‘跤乡’的土地,至今保留着“挠羊赛”的彪悍风俗;唐州者,应是作者现今的寓居之处,历史上的古国北唐所在地,如今是一个省城。文学要表现今天这样一个城镇化的时代,石板街也好唐州也罢,少不了高楼大厦、购物中心、高档小区之类的“地标”建筑,以及与之匹配的成功人士,但是刘宁的主人们生活的空间聚集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修车摊、烧烤摊、小卖部、理发店、按摩店、殡仪馆,卖花鸟鱼虫的犄角旮旯,养鸽户居住的旧楼顶层;一言以蔽之,“石板街”小镇人物的前世今生,内陆省城“唐州”平民的爱恨生死,构成了刘宁笔下新的地域“传奇”。“传奇”的文学传统由来已久,古代文学史上有唐传奇、明清传奇,现代文学则有张爱玲的“传奇”。前者突出神怪侠义的神鬼怪异和社会名流的奇谈轶事;后者则铺陈现代沪港的洋场奇观。刘宁的“传奇”来自当今内陆城镇的民间,一些流传于石板街或唐州的奇闻轶事,却也隐藏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难解之谜。更重要的是,所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世道变化如何渗透普通人的生活并激起回声,正是刘宁用力感受并试图以文学方式予以显现的地方。
将近一个世纪前,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涌现之时,叶圣陶则奉献了小镇灰色人物系列。那些夹缝中生存的小人物并未远去,在刘宁的小说中依然存活着。于刘宁而言,出入石板街、唐州的平民各有自己惊心动魄的“戏剧人生”。他无心“粉饰”太平,只是忠实地写芸芸众生各种各样的“战争”,甚至是足够意外的“厮杀”。《光线笔直地照射》写王卫东从修车匠到“杀人犯”的身份转换,表面看他长期浸泡在灰色生活的灰色心境中近乎麻木,却不料被几句无忌童言激发“灵感”,顺手操起扳子一鼓作气做下两桩命案,造成麻木看客的骚动和媒体激情渲染的“轰动”,事件背后,是无人细思深因的“黑洞”,这恰是作者要凸显的“细节”。孩童母亲无端的怀疑折射出某种足以致命的“世道人心”,经由孩童模仿转述的评语道出了成人世界铁一般的歧视侮辱,王卫东的瞬间失手正是对此作出的雪耻性回应,出于本能他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超越的同时也走向毁灭。《啊,小寇》中的剃头匠小寇在“钱不行,甚也不行”的现实尴尬中,先遭遇老婆与煤老板私奔的尴尬,所幸继之收获与内蒙姑娘的新婚姻,最终品尝的却是收留前妻保留现妻的“艳福”人生,贫困与尊严、情感与道义考验着小寇一日三餐的卑微人生。《牵引大师》中半仙半侠的外乡“牵引大师”扑朔迷离的遭遇,与地头蛇的乡土黑恶纠缠一起,生死未卜,五味杂陈。
读这样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传奇者,非猎奇也。刘宁的小说属于镶嵌在城镇框架中的民间生存百态,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不甘或毁灭,苟安者的隐忍或投机,看客的麻木不仁,智识者的调侃揶揄,愚弱者的癫狂怨痴,其中的“戏剧人生”“人性迷局”,答案何在?谁来解局?
曾几何时,文学评论希望作家给出问题原因进而给笔下的人物指明出路。今天人们终于清楚,对于“非文学”的现实生活,作家所能做的也只是用文学方式呈现出来。刘宁经常会用一句话解释他的故事:“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事情,有“事”有“情”,“事”是小人物的“事”,“情”也是小人物的“情”。合人性、合人情、合道德、合尊严,在小人物的世界自成体系,于是就成了“这样”的“事情”。鹰鹰鱼鱼夫妇靠经营学校小卖部维持日子,长期受校长忠忠盘剥敢怒不敢言,欲扭转卑微低下的现状,几次三番虚张声势,终又蜷缩回壳子里,在半途而废中苟活下去。(《一个虚张声势的家伙》)作者无奈着人物的无奈,接受着他们的“虚张声势”。他用文学的方式呈现着他们非文学的生存,你会发现,刘宁是站在“这样”的“事情”和逻辑中推己及人,背后秉持的是“人物本位主义”。写《鸽子的群体性上访》,他体察养鸽人黑毛的自尊羞愧与屈辱悲凉,让叙述者“我”尊称这位有爱好、有底线、努力“活着”的落魄者为“黑毛哥”。妻离子亡的打击因白兰鸽的存在而变得可以承受,却因“大人物”杨科长居高临下的阶层鸿沟而坠入深渊。悲剧意外又必然,特殊又普遍。但这悲剧的原因却深不见底,重重压在作者和读者心上无法解释。就在这沉重时刻,作者放飞的一群白兰鸽,做了民间的一句箴言的注脚。“鸽子的群体上访”事件,让现实的沉重在文学的世界获得一种释放和救赎。文学是软弱的,也是有情有义有灵性的。这算不算是作家的传奇之笔呢?《罗汉》堪称另一篇传奇——既非写人也不写事的当代《世说新语》——一生与花鸟虫鱼打交道的鳏夫三斗,看得开生老病死,却对养育多年的罗汉和被他收留的清洁工心有戚戚,这份至情竟演绎出神话传奇般的人鱼悲情,堪称一曲绝唱:那条罗汉眷念旧主老窝,不屑新贵豪宅,从鱼缸腾飞化为巨鸟,如庄子笔下的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羽化成仙,亦真亦幻,教人目瞪口呆。罗汉无疑是主角,它的传奇幻化绝尘而去,把深藏民间的世道人心推向高处。《何马史诗》在“宏大”的命题下聚焦的依然是小人物——一个殡仪馆管理员的人生迷局。在小镇人的逻辑中,身为殡仪馆管理员的何马,想要飞越绝望的日常生活,只能靠诡异的白日梦书写自己的“史诗”;作者又一次站在人物本位上,嗅到了源于职业宿命的绝望与人性深处的沮丧。何马灰色旅程中白日梦般的“奇遇”,不啻一场毁灭性的自我突围,现实的悲催与“史诗”的巧合,构成文学对现实的反讽。我们置身的生活充满了矛盾冲突,作者既是接受现代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也是与“石板街”“唐州”有着深厚地缘关系的“地之子”,在想象小人物的传奇人生时,作者的乡土感情与现代理性形成一种叙事上的张力,造成一种内在的紧张与犀利,其硬汉风格给予读者有力的审美冲击。
二、“传奇”之外的发现
小说的类型真是千姿百态,且不说一千个作者笔下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作者笔下又何尝不是花样百出。在这一点上,刘宁的写作不拘泥于题材风格的整齐划一,他不放过任何可以挥洒才情的素材,持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和“我注六经”的方式。如果说石板街和唐州作为庸众看客固定不变的生存空间,通常象征着死水一般的“生死场”;那么偶尔脱离现实走出石板街或唐州,坐上绿皮火车踏上旅途,对邂逅的“陌生人”“异己者”冷眼旁观或热讽调侃,无疑会有新的“发现”。在我看来,《美女》《流水与岩石》《天堂一直下雨》可谓灵感袭来的“意外之笔”,它们的隐喻与写意更大于形象意义。
《天堂一直下雨》借用《圣经》的结构写一个世俗版的“圣经”故事,衍生了一系列不平行、不平衡的对照。庸常凝固的石板街和流动的小火车;石板街的庸众与读《圣经》的“异己者”陆晓玲;不彻底的“我”和义无反顾的“她”,有意造成虎头蛇尾的结局,恰与“天堂一直下雨”的反讽隐喻暗合。《美女》或可看作是两个轻型知识分子合作完成的一篇有关泛美女时代的论文。对旅途中陌生人的放肆打量,多了份轻快的调侃和速写的敏捷,让杜学书妙语连珠口吐莲花的才情得以尽情挥洒,“我们”庆幸“赶上了又一个美女时代,就像当年的唐朝那样”。你会恍然间觉得“我们”——“我”和杜学书两个乘马达木船的21世纪“文人”,或许就是唐朝那些行走文人中的一员。在高等教育几乎普及化的今天,“我们”走出高校之后,不过是回归到芸芸众生当中,除解决了温饱,也再无别的“优势”可言,唯一的优越感或许仅剩下偶尔和发小同窗卖弄一点“知识”,满足一下“此情此景的学术情结”,此所谓轻型知识分子是也。然则正是这份“闲情偶寄”,不经意间道出一些习焉不察的世相背后的沉思。头发像“蓝色妖姬”的“美女”,是这个虚浮表象时代“共名化”的符号人物、类型化的世相表征。一场旁观、一席不伦不类的名词界定和复杂暧昧的案例分析,倒把“现实”和“诗意”间的距离丈量了一番。
值得一提的还有《流水与岩石》。一个恓惶又感人的石板街故事,引出“水命”和“土命”相克相生的前世今生。青石板和灰石板铺砌的石板街,造就此地人世世代代的“土命”和“石性”:干燥坚硬铁板一块,连口音和腔调都“像黄土一样细碎,像岩石一样苍老”;“水命”造就的南方人黎克华被下放到石板街,“弥漫着不可捉摸的水汽和烟雾”,成为石板街人眼里谜一样的“异己者”。黎克华对一片溪流的发现与开垦,开始了“水命”对“土命”的攻克,也开启了流水与岩石的相融相亲。南方孤独的水分子黎克华接受了北方溪流的滋养并终老于此;石板街人干涸的土命也因拥有“水性”而变得柔软。“流水”与“岩石”之谜,这是刘宁所写的又一个“难解之谜”,彼此的抚慰救赎乃至安身立命,给予读者多层面的启发与感召。《牵引大师》中的“大师”命悬一线生死未卜,令人牵挂又爱莫能助。这种担忧,关乎大师个人也关乎这一群体这份“职业”甚至这种文化的命运,让人想起老舍的《断魂枪》《黑白李》,想起汪曾祺的高邮系列小说。另外三篇一如既往聚焦小人物却又有人性的新发现。《双枪》写傻子双胞胎大哈二哈的混沌人生,他们在弱智世界里受人歧视,冷不丁爆发的人性温暖却又高人一等,令人动容,“双枪”一“响”,其声也亮;《斌斌的后花园》和《风水》的命题不乏新意与深意。生活失意为人仗义的普通青工斌斌因狗受罚,跌入雪上加霜的处境中,后又默默借一角空地,给工区栽葱种菜养花,开辟出一片让自己走出低谷的“后花园”,这份悄没声息的自爱自助令人尊重,而一直对他默默关注偷偷帮助甚至一度被误会的工长水货同样令人感动。《风水》所展现的既是一份关怀也是一种消解。以罗圈腿为代表的底层人群所仰仗依赖的“风水宝地”,不过是背靠一间公厕存储啤酒,立足人行便道摆摊烧烤。她的生存智慧就是可以方便晚上烧烤摊的啤酒供应,她要靠这份收入养活她的宝贝儿子。年轻时唱过的歌、中年时遭过的磨难早已随风飘逝,眼下记者的曝光,拆迁的日益逼近,儿子的吸毒被抓,全部压向风烛残年的她,她却挺直僵硬的腰杆,大声说出“不怕,没啥。咱们这里风水好”。 借用鲁迅先生评价萧红的话,刘宁写“北方人民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自有力透纸背之处。
三、小说的艺术
每个作家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艺术。就叙述角度而言,刘宁小说中“我”的出镜率很高。这个“我”的定位值得一提。“我”拒绝了全知全能的高姿态和道德优越感,“我”是有局限不完美的芸芸众生之一,“我”用自己的话语方式讲述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自带原生态的生活“质感”和内在“张力”。“我”也是一位戴有“色”眼镜,感觉敏锐,有着鹰的凶猛、猎犬的迅捷、狐狸的狡猾,毫不掩饰一己私欲却又良知未泯的真人活人。“我”拥有鲜明的、识别度颇高的话语风格。
读刘宁的小说是一件令人振奋且愉悦的事。如果说人有三寸不烂之舌,刘宁的笔头也可称“三寸不烂”,叙事语言的把控拿捏,把人与事编织得风生水起,写景也常如灵光乍现精彩纷呈。刘宁用个人化的语言写石板街、唐州的鸡毛蒜皮和小人物的难解之谜,有一种陌生化的新鲜可读。他的小说擅用比喻,大多鲜活不俗,让人意外,让人莞尔,充满了奇思异智。《瑞士军刀》写一个陈年笔记本“尘土满面,像个满脸晦气的劳改犯”,翻阅其中的日记,“就像蜥蜴被斩断的尾巴重新又连接起来一样”。少年陈兵留给“我”的印象,是“一张崭新的初次发行流通的人民币”,亏他想得出来!《罗汉》写那条灵异的罗汉额头,“像颗随时会被水波挤破的水密肥桃”;鱼市的倾盆暴雨落到地上“弹起壮观的烟尘”,“像节日庆典燃放的辉煌礼花,整个花鸟鱼虫市场也像一个糖块一样,瞬间就被融化掉了。”《罗汉》像是作者专门炫技的得意之作,酣畅地秀了一把刘氏笔法:描摹有质感,写景有动感,人鱼有通感,令人叫绝。他的文字有声响,有色彩,意象密集鲜活,生怕你的神经懈怠下来,各种信手拈来令人猝不及防的比喻,接地气贴生活,逼真传神,算不算刘宁写作的“异质性”之一?至少给我形象思维上的冲击,俏皮狡黠,令人产生智力上的愉快。《一个虚张声势的家伙》类似喜剧小品。人物取名无一例外被重叠化,从校长“忠忠”、前总务主任“银银”、现总务主任“金金”、食堂出纳员“红红”到主人公小卖部店主夫妇鹰鹰和鱼鱼。汇成一群了无新意的灰色小镇的灰色人物,缩在套子里苟活下去。此外,刘宁的小说艺术还表现在命题的刻意“宏大”化与主体实际上“渺小卑微”所形成的反差,造成强烈的反讽效果。身无立足之地的“大师”,罗圈腿的“风水”,何马的“史诗”,斌斌的“后花园”,弱智的“双枪”,无不显示作者的语言调度能力和文学表现力。
如果说小说的叙事语言属于刘宁“腔”,那么石板街、唐州的城镇传奇故事的主人公们则操一口与地域相匹配的方言土语。两套语言在作者笔下转换自如各得其所:叙述者的文人话语,人物的方言土语、村言俚语。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有活力,主要是地方色彩给予人物的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晋北乡镇的方言土语、地方性的个性化语言,极富动作性丰富性。
迄今为止,刘宁的石板街系列和唐州系列已经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传奇”无疑是刘宁独特的发现,辛辣而不失温情。挖掘人性的丰富性方面也用力颇深。“三晋新锐,写新一代人物质困窘、精神流浪,写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写情欲中体现的新时代的精神躁动,多有杰作。”[2]相信刘宁会越写越好。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石板镇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