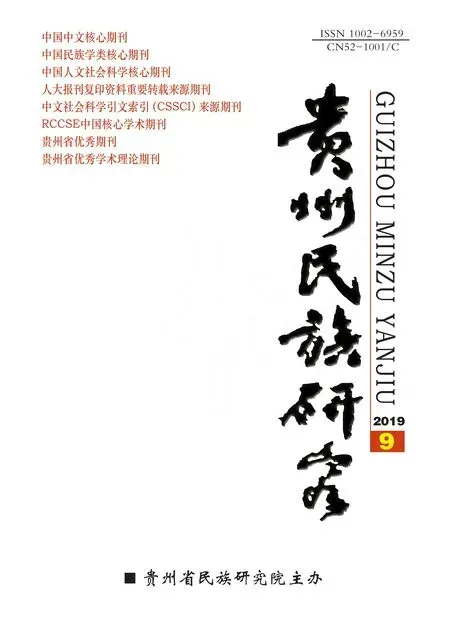贵州荔波瑶麓《同治婚规碑》再考
聂 焱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瑶麓乡(今属茂兰镇)居住着一个特殊的族群:青裤瑶。由于交通封闭,加上长期实行“闭关”的制度,这个族群与周围的水族、布依族及瑶族的其他支系很少交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自从岑家梧先生于1943年来瑶麓考察,瑶麓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特别是瑶麓的石碑制度和婚姻制度,前前后后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中有很多涉及到同治二年(1863年)竖立的《婚规碑》,并认为这块石碑具有革除了姑舅表婚,允许寡妇再嫁等婚姻改革的重大意义。本人根据石碑的内容及相关的史学资料和人类学资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同治婚规碑》的内容及学界的解释
青裤瑶主要有六个家族:覃、韦、卢、常、莫、欧,被汉人称为“苗六”“瑶六”,当地汉语方言“六”“麓”同音,所以转称为“瑶麓”。青裤瑶的通婚范围只限于这几个家族,不允许与其他族群及瑶族的其他支系通婚,使得青裤瑶从最初的外婚制转化为实际上的内婚制,对社会经济及族群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有见识的族民对婚姻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其中的一次就是发生在同治二年,即同治年婚姻改革。青裤瑶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借助汉字将相关的律法规定刻在石碑上,所有族民都必须遵守,谓之“石碑制”。目前所知的一共有5块石碑,其中一块就记载了同治婚姻改革的内容,被称为《同治婚规碑》。石碑的正面书写了永留后代四个大字,因此也被称为《永留后代碑》。
由于时间久远,《同治婚规碑》目前腐蚀严重,许多字迹都残缺不全,且模糊不清,幸而岑家梧先生早年做了记录,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同治婚规碑》所记载的规定。《同治婚规碑》的具体内容如下。
永留后代
一议……
一议讨外甥……
一议……
一议讨外甥女,男家罚牛八只,钱三十千。
一议上户财礼二十四千,中户十八千,下户十二千,众议不准多要。
一议寡妇财礼,收水牛二只,钱六百文,穷者钱三百文。
一议犯奸者,案规上户罚钱二十千,中户十八千,下户九千。
同治二年三月
根据《同治婚规碑》的内容,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黄海认为,《同治婚规碑》改革的功绩有:“永远地废除了严重摧残瑶族婚姻的姑舅表婚”,以及“允许寡妇改嫁,还妇女以自由”,并认为瑶麓人的婚姻原本没有离婚改嫁的制度,婚姻一经缔结,就必须“活在一起,死葬一洞”,而《同治婚规碑》第一次明确地宣告可以允许寡妇改嫁[1](P110-117)。覃挺生与项夔也认为《同治婚规碑》有两大重要贡献,第一是废除了青裤瑶的“九牛婚姻制度”,或者也叫“七牛婚姻制度”,也就是姑舅表婚姻制,第二是改革了“十年赔育”,也就是允许寡妇再嫁[2]。石开忠也有相同的看法,他提出,《同治婚规碑》改革的重点是废除姑舅表婚,并允许寡妇再嫁。而且,经过这次改革,还“消除了姑舅表婚的伦理及相关观念”[3]。张胜荣则认为,《同治婚规碑》改革“彻底废除了氏族社会遗留的舅权残余”,从而“避免了近亲婚配的弊端”[4]。蒙耀远也认为,这一次改革提出了根据族民的经济实力来支付婚姻财礼,同时还提出了“允许寡妇再嫁、杜绝‘犯奸’等改革事项”[5]。
虽然表述的方式不同,总的来说,许多学者都认为《同治婚规碑》展现了两项重大的改革:第一、废除了姑舅表婚。第二、允许寡妇再嫁。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观点都值得商榷,因为与许多现有的史学资料及民族学资料存在着矛盾、冲突。
二、革除“九牛婚姻制度”:从强制性姑舅表婚到选择性姑舅表婚
“九牛婚姻制度”是瑶麓人实行舅权制的典型表现。外甥女必须嫁到舅家,如果舅家没有适龄男性,外甥女也可以外嫁,但外甥女婿家必须付出昂贵的“血统养育金”。根据家庭的经济条件,最多的是支付九头牛,最低的也要支付七头牛,所以称为“九牛婚姻”,或者“七牛婚姻”。《同治婚规碑》规定,经济处于上层的上户需要给财礼二十四千,经济处于中间的中户需要给财礼十八千,经济处于底层的下户则需要给财礼十二千,而且“众议不准多要”。财礼从九牛改为最多二十四千,显然是废除了九牛婚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也废除了姑舅表婚。
瑶麓人长期实行四不通婚制:不与其他民族通婚,不与瑶族的其他支系通婚,不与同宗共祖的家庭通婚,不与姨表兄弟姐妹通婚,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1978年的下一次婚姻制度改革才被废除。[4]也就是说,瑶麓的通婚范围是氏族外婚、部落内婚。此外,瑶麓的同宗共祖并不只包括同一个祖父传下来的子孙,还包括结盟的其他氏族。比如,覃氏家族与卢氏家族因为早期结盟,即使没有血缘关系,相互也不能通婚,另一块瑶麓石碑就记载了解放前夕卢金贵与覃姓女违反同宗共祖不婚的戒律而被开除出族籍的事件。同时,瑶麓人口非常少,岑家梧于1943年的调查显示,瑶麓当时的总户数为215户,人口有813人[6](P247)。据彭兆荣等人估计,瑶人初迁到瑶麓时大约有400余户,而且那个时候是瑶麓人口最多的时候[7](P35)。在仅有几百余户的通婚圈中严格实行有选择性的内婚制,要想避免姑舅表婚非常困难。特别是其中的覃氏家族,由于人口较多,且不能与卢姓和部分欧姓通婚,剩下的常姓与莫姓户数又少(1954年时分别为3户和2户)[7](P42),绝大多数覃氏家庭只能与韦姓通婚。黄海在瑶麓的调查数据显示,覃家寨62例婚姻中,有54例就是同韦家的通婚。黄海还发现,瑶麓的青裤瑶中有不少家庭是母亲、妻子、儿媳都从同一个家族娶过来,同时又将姑姑、姐妹、女儿三代人回嫁过去,形成了“世代联姻,亲上加亲”[8](P318)。此外,通婚还要受到其他约束,比如不允许姨表通婚,经济条件差距大的家庭不会通婚[7](P185)。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避免姑舅表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瑶麓的婚姻仪式也说明姑舅表婚不仅没有被禁止,反而非常普遍。婚礼中的餐桌,要用绳子拴在屋柱上,如果是姑舅表婚,就拴3根绳子,如果不是姑舅表婚,就拴5根,但其中有一根必须由舅父来拴,展现了舅舅的权威,而舅权正好是姑舅表婚得以实行的最大力量。这种婚俗恰好说明姑舅表婚没有被《同治婚规碑》改革废除。而在女子出嫁时,父母特别叮嘱一定要生女孩,否则对不起孩子的舅舅,因为生下来的女孩要回嫁到舅舅家。因此,瑶麓实际上仍然存在姑舅表婚,所以黄海也承认,一直到解放后的1972年,三干会上通过了决议,瑶麓人才最终“革除姑舅表婚”[9](P383)。
既然姑舅表婚实际上仍然存在,为什么许多学者得出《同治婚规碑》革除了姑舅表婚的观点呢?原因估计是《同治婚规碑》有这样一个条例:“一议讨外甥女,男家罚牛八只,钱三十千”。关于这个条例,岑家梧先生认为是革除了舅甥婚。他推测,《同治婚规碑》中有如果娶外甥女,则“男家罚牛二只,钱三十千”这样的规定,估计是因为“在以前,舅甥可以结婚,久之相沿成俗”,而后来由于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交往以后,瑶麓人认为这样的习俗不好,于是就定出了这条如果娶外甥女则罚牛和钱的禁例[6](P257)。岑家梧先生的推测可以从瑶麓人的称谓得到印证。在瑶麓,称谓词汇只有12个,人与人的关系比较简单。对于男子来说,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姐妹、自己兄弟及堂兄弟的妻子、儿子的妻子以及外甥的妻子等等都统称为“娘”,对于女子来说,自己的丈夫、姐妹的丈夫、女儿的丈夫、孙女的丈夫以及姑母、姨母的丈夫等都统称为“雾”,并不做辈分的区别[1](P79-80)。从称谓来看,跨代之间的婚姻是存在过的,舅甥婚也就极有可能存在。《同治婚规碑》革除的,应该是舅甥婚而不是姑舅表婚,而许多学者误读了《同治婚规碑》的内容。当然,《同治婚规碑》对姑舅表婚也进行了改革。首先,从强制性改为选择性,过去外甥女必须嫁到舅舅家,否则就会遭到严厉的处罚,而之后只要给了财礼,女子就有机会不嫁到舅家。其次,解除姑舅表婚的代价大大下降,过去罚牛九到七头,现在则支付财礼二十四千到十二千,解除姑舅表婚后的制度设计原本是一种处罚,现在有了补偿的性质。列维斯特劳斯将通婚规则分为基本的交换和复杂的交换,基本交换是肯定性的,规定什么人必须与什么人结婚,复杂交换则是否定性的,规定什么人不能与什么人结婚[10](P119-134)。《同治婚规碑》的改革使得瑶麓的婚姻制度从基本交换转变为复杂交换,扩大了通婚范围,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婚姻改革。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打算废除姑舅表婚,只是让牢固的姑舅表婚有了松动,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废除姑舅表婚。
三、不变的寡妇内婚制:从十年赔育到吃酉
对于《同治婚规碑》,学者们的第二个观点是“允许寡妇再嫁”。这就意味着:第一,之前不允许寡妇再嫁。第二,之后寡妇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婚姻。那么,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
瑶麓流传着有一种特殊的民俗歌曲,被当地人称之为古歌,就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记录民族的历史,类似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其中,有一首古歌名叫《娘笛》,叙述的正好是同治婚姻改革的两位倡导者姚娘笛与韦银娜的故事。 《娘笛》中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姚娘笛住地相隔了二十里,来与韦银娜共同商议。说出了瑶麓人的心里话,将‘七牛’改作用银毫来抵。去掉了‘血统养育金’,‘架菊木包’也废除去”[9](P365)。
“血统养育金”是解除姑舅表婚时由外甥女婿付给舅父的补偿,也就是“九牛婚姻”或“七牛婚姻”中的九牛或七牛。从“七牛”改变为“银毫”,说明女孩子不嫁到舅舅家去的惩罚仍然存在,只是惩罚变轻了。也就是说,当时的规范仍然赞同女性嫁到舅家,不嫁过去就会受到处罚,姑舅表婚仍然是被族民们推崇、赞同的婚配模式,只是有了松动的空间,这一段歌词正好印证了上面我们对姑舅表婚所做的分析。
“架菊木包”是瑶语音译,汉语译为“十年赔育”,也有研究者称之为“哺架育”,意为“吃酒席”,是对寡妇改嫁到另一个家族的一种惩戒或补偿形式。寡妇的现任丈夫必须招待她头一个丈夫家族的全部男性成员饱食一餐,而且还规定只能吃肉、豆腐等价格比较昂贵的菜肴,不能吃蔬菜、瓜豆等族民自己种植的便宜食物。不但如此,前夫家族的男性成员还要带一个小竹篮去寡妇的现任丈夫家,这个小竹篮瑶语称为“丢”,吃完后每人装一“丢”——大约有5斤——糯米饭带回。倘若“丢”没有装满,或有人没有得到东西,次年仍然继续进行。直到前夫家族中的全部成年男性成员都能吃饱喝足并带回满“丢”的糯米饭,事情才算最终结束。由于当地土地贫瘠,加上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即使是在族民中处于经济条件上层的家庭也非常贫困,而一个家族的全部男性成员数量又比较多,有时候这个过程要持续十年才能完成,所以叫“十年赔育”,而被处罚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则往往因此陷入困顿,并一蹶不振,也就很少有族民敢违反规则去娶寡妇。这种方式也用来处罚离婚者。
除了“架菊木包”,瑶麓还有一种惩罚叫“吃酉”。和“架菊木包”一样,处罚的方式是到受罚者家中喝酒吃肉。两者的区别是,“架菊木包”吃后还要每人带回一满“丢”的糯米饭,而“吃酉”则不能带回。
“架菊木包”被废除以后,寡妇再嫁到其他家族受到的惩罚就换成了“吃酉”,覃挺生,项夔及彭兆荣等学者都提到了同治石碑后的这种改变。“(同治石碑)改革‘十年赔育’,(变为)只准吃饱,不准带‘丢’盛饭回家”[2]。“废除‘十年赔育’”,改变的内容是“准吃不准包”[7](P156)。
《娘笛》里有“‘架菊木包’废除去”的歌词,意味着在同治改革之前,寡妇改嫁到亡夫之外的家族是要受到“架菊木包”惩罚的。但是,同治改革之后,寡妇并没有获得改嫁的自由,仍然要受到“吃酉”的惩罚,只不过惩罚的严厉性有所下降。同治石碑改革“允许寡妇再嫁”的说法就不够准确,因为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寡妇都可以通过某种处罚方法来获得再嫁的机会,只是处罚的方式和严格程度发生了变化而已。
从财礼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寡妇并没有真正获得再嫁的自由。同治婚规石碑提到了两种财礼,一种是初婚,财礼的规定是上户需要给财礼二十四千,中户需要给财礼十八千,下户则需要给财礼十二千,另一种是寡妇再嫁,财礼的规定不分上户、中户和下户,统统都是要支付水牛二只,加上铜钱六百文,而特别贫穷的家庭则支付两头水牛后只需要给一半的铜钱,即铜钱三百文。初婚的财礼是货币,而寡妇再嫁的财礼是水牛加上货币。由于不清楚当时当地的物价资料,我们只能通过相邻地区的物价进行估计。根据梁凌等人的推算,与瑶麓相隔不远的四川矛头铺牛市在1810年已经出现,到了清末,上等牛价达到80到100两白银,中等牛价为60到70两白银,下等牛价也要30到50两白银[11](P54)。至于白银与铜钱在该时期的换算,刘秉璋的上疏中则有这样的描述:“同治三年为始,每银一两作钱一千六百文”[12]。即使牛价按照下等牛的最低价30两白银来计算,两头牛价值也达到了铜钱九十六千,不算寡妇财礼中的货币,其价值也远远高于经济地位较高的族民(上户)初婚需要支付的财礼二十四千,这一方面说明聘礼从九牛改为铜钱的确大大减少了年轻男子的婚姻负担,使得姑舅表婚有了松动。另一方面则说明,即便同治改革以后,寡妇再嫁的财礼还是远远高出未婚姑娘出嫁的财礼,寡妇改嫁显然没有得到社会的宽容和接受。
直到1987年下一次婚姻改革,瑶麓的寡妇再嫁仍然受到限制。其可以婚配的顺序是,亡夫亲弟、亡夫堂弟、亡夫的远房堂弟、与亡夫不同姓但同一氏族的弟弟、部落内的其他适龄男性。显然,只有嫁给部落外的其他适龄男性才肯定会受到“十年赔育”或“吃酉”的处罚,因为“十年赔育”或“吃酉”的处罚以家族为单位,不仅来吃的人是同一个家族,就连被吃的,也在家族内实行连坐制,如果受罚者的家庭无力承担,就由其家族支付[9](P187)。只要寡妇还留在亡夫的家族,就设有“十年赔育”或“吃酉”的必要性。当然,如果寡妇再嫁给了亡夫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员,但是没有按照适婚顺序再嫁,违反了规则,而新丈夫的家庭又没有贫困到“吃酉”时需要连坐同一家族内的其他家庭,“吃酉”的处罚仍然还是有的。这种案例在解放前就出现过。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推测,在同治改革前,如果寡妇遵循婚配顺序再嫁给亡夫的族人,她的现任丈夫就不会受到处罚。特别是当她再嫁给亡夫亲弟时,现任丈夫与前任丈夫在同一个家庭内部,如果有处罚就变成了自己处罚自己,处罚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寡妇是可以再嫁给亡夫的族人的。
在从亡夫亲弟到部落内其他适龄男性这个寡妇的适婚顺序中,只有当前面范围没有合适的人选,才可以在后面的范围选择。此外,选择权也不在寡妇手上,有两个案例可以说明这一情况。一例是1940年卢金贵娶寡嫂,卢金贵本来不愿意,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另一例是1944年卢双福娶寡嫂,但遭到卢氏族人反对,后来被罚“吃酉”。对于这两个结果相反的案例,彭兆荣等人的解读是,一反一正两个案例说明了续嫁夫兄弟婚这种婚配模式在当时已经处于没落期,不过还没有完全消失[7](P144)。但是,这两个所谓“一正一反”的例子都显示了寡妇亡夫的氏族在左右寡妇再婚时的强大力量。卢金贵之所以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还是接受了寡嫂,是因为寡嫂亡夫的卢氏氏族支持这桩婚姻,无论是卢金贵本人还是他的寡嫂都没有自由决定婚配的权利。卢金贵的寡嫂去世之后,卢金贵续娶覃氏女,遭到覃氏女亡夫氏族韦氏家族的强烈反对,以至于两人被开除族籍,这个事件被记载在另一块石碑上。卢双福之所以被罚,同样是由于寡嫂亡夫的卢氏氏族反对这桩婚姻。因为在卢双福之前还有其他人选,按照婚配顺序卢双福没有资格娶自己的寡嫂。寡妇并不能决定自己嫁给谁,这项权利归于亡夫的族人,特别是族人中的长辈,寡妇没有决定再嫁的自由。
可见,无论是同治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寡妇都可以按照相关顺序再嫁给亡夫家族的适龄失婚男子,如果再嫁到亡夫家族以外的其他家族,或者不按照适婚顺序改嫁,则都要受到处罚。不同的是,改革后处罚的严厉程度有了下降。此外,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寡妇再嫁都受到内婚制的约束,必须优先嫁给亡夫氏族的男子。同治婚姻改革并没有给寡妇的再嫁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四、结论与讨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同治婚规碑》展示的是一场不彻底的婚姻改革,既没有废除姑舅表婚,也没有允许寡妇自由改嫁,舅权和夫权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仍然约束着族群的婚姻自由。由于内婚制没有被打破,为1987年的再一次婚姻改革埋下了伏笔。但是,《同治婚规碑》变强制性的姑舅表婚为选择性的姑舅表婚,减弱了对寡妇再嫁的限制,不仅扩大了通婚范围,还增加了个体的自由度,是一场值得肯定的改革。
总的来说,《同治婚规碑》是从族内婚转变为族外婚的一个中间步骤,而不能被解读为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同治年婚改后,作为交换物品这一限定性角色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女性的婚姻自由,交换婚的性质没有改变。其规则是,当某个家族的一个女性甲嫁到另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必须将自己家族下一代的另一个女性,即甲所生育的女儿乙,回嫁回去作为交换。如果乙没有回嫁到舅家,就要由乙嫁进的家族给乙的舅家以经济补偿,作为“购买”乙的费用。当乙的丈夫亡故,由于亡夫的家族已经支付了“购买”乙的费用,乙必须留在亡夫的家族,按照与亡夫亲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婚配对象,如果亡夫的家族没有适龄男性而乙又不愿意守寡的,乙可以再嫁到别的家族,乙再嫁的这个家族就要支付“购买”乙的费用,作为乙亡夫的家庭上一次“购买”乙时所花费用的补偿。这个过程就是瑶麓姑舅表婚与寡妇再婚的实质,姑舅表婚与寡妇再嫁两种婚姻没有质的差异,不过是交换女性中的不同环节。在同治婚改前,“购买”女性的费用非常高昂,限制了女性通过婚姻在不同家族之间的流动,同治年婚改后,费用有所下降,女性的婚姻流动性略有上升,但“购买”的费用仍然存在,女性并不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婚姻。
1987年,瑶麓进行了再一次婚姻改革,不仅打破了结盟家族不能通婚的戒律,也废除了婚礼中新娘的夫家必须给新娘的舅家支付财礼的“母舅认亲制”。正是这次婚姻改革(而不是《同治婚规碑》改革)彻底地动摇了瑶麓社会的内婚制。1991年,瑶麓出现了第一例与外族通婚的案例,1993年,出现了第一例结盟家族之间通婚的案例[7](P167)。1987年的婚姻改革减轻了婚姻负担,进一步扩大了通婚圈,增强了个体的婚姻自由,应该值得肯定。但是,1987年的婚姻改革也产生了其他的后果。内婚制被打破后,大量的女性外嫁,却很少有外族或外地的女性嫁到瑶麓,瑶麓出现了大量的男性失婚者,性别结构严重失调。因此,瑶麓乡政府于2009年9月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于娶到外族姑娘的男性,按照时间顺序每人分别奖励3000元到1000元不等,以鼓励外地的姑娘嫁到瑶麓来,但效果很不理想[13]。1987年的婚姻改革结果说明,第一、任何制度都有两面性,因为在压迫的同时也提供了保护,九牛婚姻、十年赔育等顽固地维护内部通婚的制度并非一无是处,也有其优点和生存的根基。第二,婚姻改革涉及到许多因素,会产生多重后果,本身就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这个意义来看,具有微调性质的“不彻底”的同治年婚姻改革事实上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