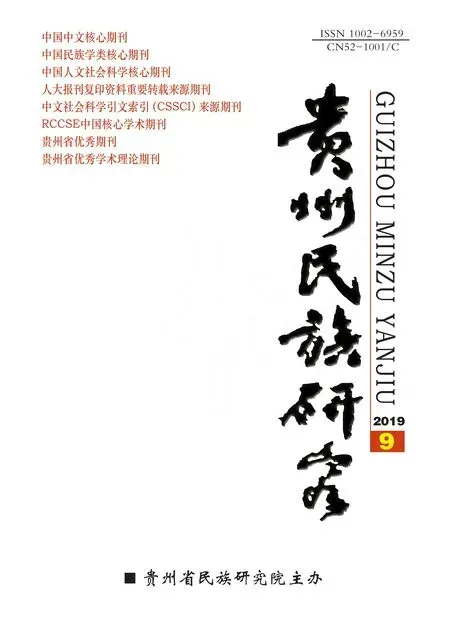贵州碑刻铭文中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文献研究
冯相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多元信仰是贵州少数民族信仰的一大特点。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内涵广泛,包括佛教、道教的佛、神信奉,历史人物崇拜,自然神、祖先、图腾、神鬼、巫术崇拜等,这些信仰习俗在碑刻、铭文文献中均有记载。研究这些文献有助于了解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类型、渊源、特点及功能,发挥其积极因素。
一、碑刻、铭文记载中的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类型
(一)对佛教神灵的信仰
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佛教的影响较为明显。东汉末期,佛教对贵州已有一定影响;唐初,佛寺在贵州已开始创建;元代,印度僧人指空在黔西北广传佛教,“苗蛮、瑶、僮、青红、花竹、打牙仡佬诸洞蛮,俱以异菜来请受戒”[1]。可见佛教在这些地区已有一定信众。明代,贵州出现了“罗汉和尚,峒苗也”[2],“苗僧,思南受水人……久之得悟,偈曰:“本是菩提种,打落有苗胎。曹溪一派水,清风引出来”[3],而据《清镇县志稿》载,清镇县城西李家寨有活佛山,相传明季有苗僧结跏洞中,至清康、嘉间,香火尤盛,远近来祷者不绝于途[4]。这说明明代贵州少数民族中不仅有佛教居士,而且还有出家为僧者。
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民间的佛教信仰,明代王守仁的《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撰于明正德三年(1508年)]中有对贵州黄平一带少数民族岁时令节到月潭寺祈求福佑的明确记载,即“兴隆之南有岩曰‘月潭’,壁立千仞,檐垂数百尺。……岩麓故有寺,附岩之戍卒官吏,与凡苗夷仡狇之种,连属而居者,岁时令节,皆于是焉厘祝。寺渐芜废,行礼无所。……乃捐资备财,新其寺于岩之右,以为厘祝之所”[5]。而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丹寨县复兴乡排莫寨跳月堂旁的“跳月堂”碑,则记载了当地苗族在行斋戒之礼时,廷请僧人、道士主持的习俗,即“斯系苗俗,荐祖超亲。廷请僧道,致斋敬神。”[6](P354)又如立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飞山庙”碑,碑文有云“窃为庙观之刹,作地方保(缺字)等自承平□以来,寺观俱无(缺字)众□居心向善,佛门修奈银钱(缺字)捐银钱兴设大小庙宇,以培地方(缺字)向善甚多,今及工完,庙廊修(缺字)守规章,视其我寨赫上成仪(缺字)”[7](P64-65),这是对当地苗族信仰佛教及建寺庙情况的记述。再如彝族宣慰使安贵荣所铸大方永兴寺铜钟[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之汉文铭文,铭文有云“贵荣叩承世禄,职守边疆,扪心有囗,报谢无由。是以夫妇谨发诚心,就于本境内之永兴寺一所,喜合资财装塑佛像,铸造钟一口于本寺,朝暮声鸣,以镇一境。尚祈保佑,俾我子孙代代绵远,宗亲目把世囗囗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今存于大方县文物管理所)而布依族聚居地罗甸县沫阳镇(布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5%)有一“金钢柱”,其上镌文有云:“十方外道尽皈依,敬教大士面然鬼王之神,南无金钢般若波罗密佛,三界大魔皆拱手,位同结善缘,民国三十七年。”撰写者对佛教的信仰可见一斑。
(二)对道教神灵的崇拜
由于地缘关系,东汉中期道教在蜀地创立时,就开始影响贵州。三国时期道教已在黔西北少数民族中传播。据刘秉仁撰于明万历年间的《武侯祠碑记》载,诸葛亮南征时,知“彝信鬼幻惑,侯故奇踪閟响以震詟之。谓所过辄有遗迹付诸山灵者,盖侯詟彝之一端也。”[8]而诸葛亮南征班师回朝时,途径毕节七星关,因见此地群峰如七星,遂祭祀之,因此,后人在此关上修有武侯祠。明代,道教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扩大。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天王庙,在方番司后,祀土神,曰天王。夷民事之甚谨。”[9]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调查贵州一些苗族地区时发现,“所访之苗族均已失去固有之宗教,而多信佛教,且多少道教化。室内皆设观音像或关帝等像。”[10]而中国当代民族学家、教育家吴泽霖也在其《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一文中指出,贵州短裙黑苗信仰的神灵有“玉皇大帝、保家菩萨、本己祖宗、阎王、士地城隍、财神、观音菩萨、岳武穆、神农、关圣帝君、树神、岩神、桥神、太阳神、月亮神、簸箕神、娘娘菩萨等”[11]。道教约在明代传入侗族地区,至清代,天柱县338寨中就有462座寺庙,而其中的金凤山有玉皇殿、观音堂、老君殿、八景宫、王母瑶池、玄女宫、南岳宫、四大天王宫、玉鼎庵等48座,其中相当一部分供奉道教神[12]。
一些碑刻记述了少数民族参与建道观及其信仰情况。譬如,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候补通判宋泽春所撰《新修丙妹城隍庙碑记》记载了重建从江县丙妹镇城隍庙及苗、汉等族人捐资情况,即“余复制剀切,晓以大义,谕令乡约等,遍告各苗、汉,大家勇跃酬金,速新此庙用。……神其有如,必当欣遭遇之隆今,而后保障一方,赫厥声,濯厥灵。凡厥苗民尊之、奉之。”[7](P17)又如立于民国四年(1915年)的黄平飞云洞“潘姓合族捐助重修飞云洞叙”碑,记述了清初黄平地区潘姓各寨苗族村民参与修建黄平飞云洞寺观及宣统年间维修寺观情况,碑文有云:“黄平城东二十余里,有洞名‘飞云’,原为潘姓施主……。每年新正,阖族齐聚吹笙。我先人恐有不测,将岩浆所滴人形以为神像而庙宇始兴,飞云洞始扬。……延至宣统二年,有住持吴理亨重为募化,吾等忆先人根基,同心合力捐资助修。”反映出飞云洞道观与苗族传统节日的密切关系。
(三)对其他民间神祇的信奉
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内涵丰富,如侗族就有自然、图腾、神鬼、祖先、萨岁崇拜等,其中仅神鬼崇拜一项就有“萨”神、火神、寨神、五圣神、五猖神、山神、地脉龙神、瘟神、郎家神等,而布依族崇拜的自然神灵多达40余种。
例如神灵崇拜。镌刻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纳雍县扯垲箐汉、彝文摩崖石(位于纳雍县左鸠戛乡坡其村扯垲箐孙家梁子东面崖上),记述了捐资修桥筑路之事,并称:“作善事者,是为了求神灵的保佑和获得长寿。为此,又在高山深谷修了一条平坦的道路,这都是积德行善之举,虔施善道就可进入福门……我俩曾向宇宙十二方的神祇许下两次愿,要作两次功德,使自己在宇宙间能顺利发展,得上天的保佑,受大地的福禄。福门者,有引渡福门,有行善福门,还有治水的果报。在阳世兴盛之时,就当为阴曹福门积善。有三个福门求富贵。福门有九十个,是由春天君来管。福门惟善者居之,善移则灾祸临。善行迎来岁神,如十六条河汇成大江;善行迎来月神,适于建桥筑路;善行迎来日神,则利于拓土开工,这是善行所报也。”[13](P157)这体现了到当地彝族群众的信仰。另外,三都水族自治县普安镇平寨村的“六姓合约”碑也有信仰“天地神灵”的内容,如其碑文称“但有六姓同老官盟誓,愿生死相顾,患难相扶,恐后人倘有疏虞之意,上有天地神灵鉴察……”[14]。
又如神鬼崇拜。在贵州布依族聚居区,如果认为是中了神鬼射的箭,就用一块木板立“挡箭碑”,上面写“挡箭碑”三个字,然后依次写“东挡明箭,南挡阴箭,西挡暗箭,北挡毒箭”等字样,最后落病者的名字[15]。再如风水术。刻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锁住斯境”碑(碑立于黎平县岩洞镇竹坪村寨脚石板桥头),其文曰:“贵境四山在远,寨脚不可无桥以锁龙脉,锁龙脉者亦斯桥。”,体现了村寨人对“风水术”的信仰。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榕江县高兴水族村寨为保护当地风水宝地龙山的龙脉不被破坏,该村寨人一致通过了各项保护措施并议定刻碑于龙山脚下,“封此龙山周围上下不准进葬,亦不许私卖与外人伤害地方,倘进葬、卖者,地方革除,送官究治”[16]。
二、碑刻、铭文反映的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根源
从诸多碑刻铭文中的记载可以发现,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根源主要有三个,即信仰需求、教化易俗和功利性因素。
(一)信仰需求
信仰是人类的一种情感需求,它的基础是对神灵的信服和崇拜。民间信仰来源于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灵魂崇拜。民间信仰是动态的,它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而在贵州少数民族中,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宗教神灵崇拜,均不同程度存在。历史上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偏僻落后,交通不畅,科技文化落后。尤其是明清时代,不仅自然灾害频发,而且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处于无望中的民众,将生存、发展的希望寄托于神灵,希冀在神灵祐助下改变生存境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本民族固有信仰中又增添了新的元素,其中尤以佛教、道教的信仰为著,这也就能更多地满足不同信仰群体的需求,扩大了民间信仰传播范围和影响。
(二)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即利用鬼神祸福之说以教化民众,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惯用的方式。基于同样目的,一些官员希望将佛教引入少数民族地区,以缓解社会矛盾。如翰林院检讨张文光所撰《贵州龙头营新建总镇府关王庙碑》[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称:“鬼国信鬼,惟神是依,而古昔威灵显赫,最著者无如汉前将军关王,则作庙以妥王神……苗纵顽冥,俗未始不严鬼神,惕王天威,尚其永销邪心,格祛逆志,与吾干羽之民相安耕凿也哉!”这便是神道设教的观点。又如陈汝忠于明万历年间所撰铜仁府《木桶观音阁记》认为:“铜素苦苗矣,苗喜劫夺、好杀戮。彼大士者,西方圣人也,恶争、禁杀,一以无诤为教,吾从而事之焉,知彼苗僚者,不闻大士之风而变于善乎?未必于岩邑无补也。”[17]这里明确指出建观音阁的目的在于传播佛教“恶争、禁杀”的义理,以教化地方民众,希望其“闻大士之风而变于善”,即是利用佛教作为教化手段,达到治理社会的政治目的。再如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安南卫守备程璧所撰《重修汉寿亭侯庙碑》,也讲了同样的道理,他认为:“安南居黔属上游,蛮烟霞翳,汉、苗杂处之区也。”而修建汉寿亭侯庙(关帝庙)“即以妥神,亦欲赖侯之忠义余风,潜移默运,俾此疆苗民革心向化,纾天子南顾之忧。则是举也,有裨于军国,有造于生民,其为地方计,岂浅鲜哉!”[18]同样,乾隆五十年(1785年)副使张扶龙所撰的《重修关帝阁碑记》记述了重建关帝庙和改名事,其文云:“楼曰‘格舞’,盖为铜苗意也。余易之而直题曰‘关帝阁’。庶令观者咸钦,过者群竦,使铜苗举首心惕也”[19]。这同样是神道设教之意。
(三)功利性因素
人们对神灵的崇拜,都有一定的目的,所期求者既有精神上的解脱,也有物质利益的期求,而通常情况下对物质的期盼会大于精神上的追求。这种信仰的功利性在贵州碑刻中亦有所见,如锦屏县偶里乡皆阳村狮子山下的“佛祖证明”碑[明崇祯七年(1634年)立],便是锦屏县偶里苗乡十二寨因赋税沉重,害怕官府层层加码而将原定租赋刊刻石壁,以企图借助佛祖证明上告苍穹、伏望天慈而立的。这一碑刻不仅反映了偶里苗乡十二寨苗族对佛教的信仰,也表露了他们希望“佛祖”佑助的迫切心理,亦隐含着对信仰佛教所抱有的功利性观念。又如立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大方县《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碑》(位于大方县黄泥塘镇大渡河桥旁),其碑文(彝文意译)云:“作祭祀,祭祖灵,多富多贵,天地母尼以来,历代相传,行善者高尚……祭天地,祭祖灵,天地保佑,神喜人悦,奉默氏为主,人们安居乐业,古今传扬……古时直嘎阿鲁有箴言:彝住中部地区,要敬奉天君地王,开创基业,有天威护佑……布摩祭祀灵验,天地间出现清平世道……”[13](P155-156)这反映出立碑者的功利性目的。
三、碑刻、铭文所体现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功能
民间信仰的特点是多神崇拜,这些神灵与民众社会生活密切关联,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一)传承文化功能
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它传承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民间信仰包含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某些知识的积累(如天文、地理、农学、医学等),因此民间信仰具有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民间信仰不仅通过固定的仪式(庙会、祠堂祭祀、家庭祭祀、节庆活动等)进行传承,还借助神话传说、民间戏曲、民间雕塑等形式宣扬,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显示了独特功能。
(二)整合文化功能
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神秘性、多样性、功利性、融合性、民俗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其思想渊源复杂,信仰对象宽泛,崇拜仪式贴近民众生活。历史上,贵州是民族交汇的大走廊和民族集结地,各族群于此冲撞、融合,各自的文化亦于此冲撞、融合,而贵州本地的少数民族则通过不断调整民间信仰的内容和方式将外来的各种文化进行吸收、整合。因此,贵州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既有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对中原文化、地方文化的吸收与融会,文化整合的功能十分明显。就文化源头而言,通常都包括儒家、佛教、道教、民间宗教、本民族文化,以及巫术、方术等内容,民间信仰在吸收这些文化元素的同时,也给这些元素以影响,形成整合和互动。
(三)慰藉心灵功能
现实生活中人们总会遇到风险、遭受挫折,尤其是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环境闭塞,交通不便,教育、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疾病、自然灾害都会给人们带来威胁,人们信奉各种神灵,祈求消灾免难、平安幸福,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例如黄平县纸房乡西堰村写字岩摩崖有“易长成人、星辰开泰、禄马挟持、清吉平安,长命富贵”等内容[7](P80),就是祈岩神保佑子女、家庭平安。又如神灵崇拜的产生,本身就是先民们创造出来的、试图借助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禳灾解厄的,它是基于对自然界的不了解或困惑。当疾病或灾荒等危机降临时,信众通过对神灵的祈祷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和谐,进而增添希望与信心。虽然,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具有迷信成分,但是,在科学尚未完全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之前,这种信仰是不会消失的,况且其中也含有对社会有利的积极因素。
(四)稳定社会功能
民间信仰具有教育和模塑作用。民间信仰的一些规约,来自世俗社会的法律、伦理规范,经过提升具有了“神圣性”,因而也就更具有规约性,成为规范信仰者行为的准则。这些规约不仅约束信众的行为,还约束其心理,效力更高于世俗法律。历史上贵州少数民族很重视“神判”,如立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锦屏县启蒙镇“因时致宜”碑就提到“爰卜良辰,齐盟帝阁。凡居款内,慎毋犯楚违规。设为拒抗不从,定要传公受罚。即我同人,务欲前呼后应,假使推辞不理,难逃神□天诛。”[6](P341)因此,由于畏惧被“神”惩罚,也就减少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五)保护环境功能
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自然崇拜,对于保护环境有积极作用。产生于“万物有灵”观念的自然崇拜在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占有较大比重。尤其是祭山、祭水、祭石、祭树,以及图腾崇拜等活动,均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由此形成了珍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观念。贵州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敬山神、树神的习俗,而三月三敬山神的风俗在少数民族中十分流行。仡佬族有俗语:“吃哪山的水,变哪山的鬼,以祭山为大。”贵州多地仡佬人聚居区至今仍存有大量的山神庙和土地庙,每到农历节气,民众都会带着各种祭品来庙里供奉祭拜,祈祷神灵保佑平平安安、五谷丰登。此外,布依、水族都兴祭河神,而仡佬、布依、侗、水、苗族等村寨一般都有一棵古树作为保寨树,每逢节日即用酒肉进行祭拜等。
四、结语
民间信仰碑刻铭文是研究民间信仰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多民族聚居的贵州,民间信仰具有与其他地区的民间信仰相同的共性,也具有自己的特性。贵州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体现了民族融合和国家认同,也对贵州的佛教、道教产生了深刻影响。贵州历代方志对这类碑刻文献均有收录,民间也有部分文献留存,对其辑录、整理并研究是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进一步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发挥民间信仰在新时代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