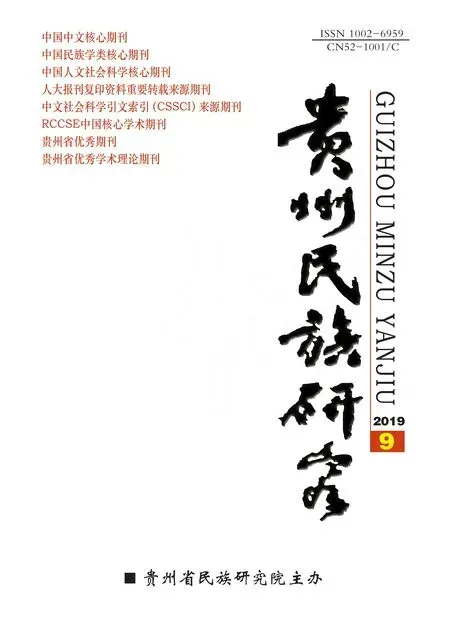地理意象的本位与出位之思
——土家族史诗《摆手歌》与《梯玛歌》研究
李志艳 陈建伟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
“任何民族都有对自身民族的起源、发生、发展过程的历史记忆,也都通过各种形式,包括文学艺术及其审美形式来表达这一文化渊源和文化传统,从而确立本民族的特质和特征,确立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性格。”许多民族通过史诗这种文学样式记录了本民族的发源、繁衍、迁徙、战争、嫁娶、丧葬和祭祀等的历史发生和演变轨迹,进而在史诗的传唱中建立起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涵,土家族的《摆手歌》与《梯玛歌》就是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摆手歌是一个大型的民间叙事诗的集合体,是土家族人民生活和艺术的结晶。”梯玛歌“担负着传承土家族文化,继承人文教化的神圣作用”,是“一部土家文化的百科全书”。土家族史诗《梯玛歌》和《摆手歌》以口头传唱的形式,糅合诗、乐、舞,叙述了土家族的历史起源、民族迁徙、农事劳作、英雄故事和婚丧嫁娶等活动,于民间祭祀时咏唱,具有重要的文学、民族学、哲学、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价值。土家族史诗《梯玛歌》和《摆手歌》中出现了大量表现土家族民族精神的地理意象,因此可以通过研究地理意象的特征洞见土家族的民族精神。
“‘地理意象’指具有显著地域特色和地理因素的外观之象进入到创作者的视野中,承载其主观情志并在代际演变过程中融合了接受者之‘意’所复合而成的文本中的‘综合体’;它作为文学文本的最小构成单元和元素,凝聚着创作者和接受者主体精神深处的地理基因与地域认知,并内化成文本中浓厚的地方情结,传递着创作者对于一个地域或超过地域的其他群体乃至全人类的精神观照。”在《摆手歌》与《梯玛歌》中,地理意象在地理客体的基础上,糅合了土家族集体对地理物象或地理事象的认知,辉映着主要居住在湖南与湖北两地的土家族人的集体无意识,在文本中可以划分为雷公、洪水、植物、动物和祭祀场所等五种地理意象。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刺激土家族人民群众思想情感的生成,在文学作品中创造地理意象,讴歌自身民族的生命意识。因此,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梯玛歌》和《摆手歌》进行地理意象方面的分析,可以烛照土家族史诗所蕴含的生命意志,可以为其他民族从史诗的地理意象窥探民族精神提供镜鉴。
一、异质同构:地理意象与人性的互文
发生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吕西安·戈德曼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首先是包含着它与整个社会大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它还与由创作它的作家的心理所构成的中间结构联系在一起。这样,只有从整体(包含文学作品在内的社会大结构、作家心理的中间结构)与部分(作为‘有意义的结构’的文学作品)的不断循环过程中,我们才能深刻地把握住文学作品。”地理意象作为“有意义的结构”的作品的一部分,是客观的地理物象或地理事象经过人的诗性体验加工而成,反映着作家心理的中间结构和社会大结构,而作家的心理结构和社会大结构与人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地理物象或地理事象而言,地理意象与人性是异质的;但就人的诗性情感而言,地理意象与人性则是同构的。在土家族史诗中,地理意象的结构和人的普遍心理属性的结构具有严格的同构关系,两者是互文的,可以联系地理意象来研究土家族人对于人性的认知结构,也可以联系人性体悟作品的地理意象,在此只从前者的角度进行探索。
雷公在史诗中作为惩恶扬善的地理意象,反映了土家族人对人性善恶并存、择善而从与抑制恶行的心理认知。娘极度渴望吃雷公肉:“我雷公的肉一口吃,我雷公的汤一口喝,死了也眼睛紧闭了”。儿子们为了实现娘亲的愿望,以糟蹋粮食的方式来引诱并抓捕惩戒他们的雷公。善良的雍尼和补所可怜雷公的悲惨境遇,给他水与火,助他逃出生天。墨贴巴意识到人性恶的无可救药,决意让雷公以洪水这一自然灾害毁灭人类。但人类中也还有善良的兄妹———雍尼与补所,他们得到了雷公所赠予的葫芦种子,在洪水到来时躲在葫芦里得以延续人类种族的生命。雷作为自然地理的一种物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土家族人将自己对于人性的理解灌注其中,并将之拟人化与神化,使之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征。雷公这一地理意象表现了土家族人对善良的憧憬,对恶意的摒弃和善良才能更好地繁衍人类的愿望。同时,雷公意象的塑造也传达了土家族崇尚自然,将惩恶扬善的行为神化,使自然与伦理合一的理念,折射出土家族认为自然与人类同构的原始观念。
洪水是危及人类生存繁衍的典型地理意象,映射了土家族对自然灾害的形象体认。史诗以湮灭一切生灵的黝黑、震颤天地的声响、极端暴虐的气候和夸张到极致的后果呈现洪水这一地理意象:“乌天黑地了,黑云铺满了,呼啦呼啦做在了,轰隆轰隆做在了,雨大来了,狂风呼呼吹来了,几夜几天落了,轰隆轰隆流来了,山坡山顶见没有,水和天一起相挨了。”洪水吞噬了作恶的人类,留存下善良的人类,具有净化人类罪恶,救赎人类的功能。洪水本身并无目的性,土家族却赋予洪水合目的性。洪水寄寓土家族人毁灭污浊的旧世界、开辟崭新的纪元的理想,呈现了土家族对人类罪恶的自我觉知和对善良唤起生机勃勃自然的企盼。
史诗里的植物意象具有孕育人类的象征意义,土家族通过描写大量的植物意象歌颂化育人类的大自然和辛勤劳作的土家族人民。春巴吞了花奇后意外受孕,花奇具有和男人精子一样的生理功能,表明了土家族认为自然之物能与人的生命相会通的集体无意识。心灵手巧的角乖痴迷织锦,把许多花都织完后,白果婆婆引导她编织白果花。为了等白果花开,角乖在树下守候了三夜,父亲在嫂子挑唆下误以为角乖去偷偷找伴,错把角乖打死,但角乖在临死前仍掐着白果花不放。白果的“白”镜照着角乖热爱织锦的纯粹与执着,表达了土家族人民对自然的亲近与对劳动的热忱。
史诗中的动物意象一面是土家族人征服自然的强力意志的生动显现,另一面又是土家族狂欢与达观的生命精神的形象化表征。“走过麂子走过的路,攀过猴子攀过的山。跨过螃蟹爬过的沟,踩过鲤鱼漂过的滩”和“爬在岩坎走,攀着葛藤行”等诗句形容土家族进行民族迁徙时的地势险要、路途艰辛。面对“身披红毛,眼若铜铃,手如尖刀,牙像锯齿,鼻孔高翘,吃人吃牛,人畜遭殃”的人畜,当人们“刀子斧头斫不进,不伤皮肉不伤毛”时,白胡子公公献计,让大家十指手套竹筒,将人熊“团团围住,对他背后猛然一叉,人熊滚下了万丈岩。”土家族人智斗人熊的史诗赞美了人类运用智慧战胜自然的困难的能动性。土家族人翻过山坳到新廊场后,以“对对白鹤飞天边”“绿竹丛中画眉叫,白岩山上猴子跳”“野鸡飞,锦鸡啼,斑鸠唱,走兽跳”等狂欢化的动物传递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透露出土家族人生命中流淌的乐天基因。
史诗中祭祀的地理意象既是土家族人民请神拜神的活动场域,又是土家族崇尚神灵的空间化象征。安正堂、腊月堂、三月堂、四都衙门、九都衙门、九月堂、十二板桥等地理意象是人与神能直接沟通的神圣场所。原始人类无法合理解释发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各种神奇现象,便将理解的愿望投注到无法实证的神灵。“他舌头没有骨头啊,哩哩啰啰把人咒骂,他膝盖没有骨头啊,东晃西撞乱闹家。你儿孙家里遭了孽,好像在悬崖上趴,高声大喊无办法。”土家族人民面对诡异的病症,无法主宰自己和周围人的命运,将治愈的希望诉诸神鬼与菩萨。请来的算命先生说“碰上了——那些大神鬼啊,那些小菩萨啊。欠了他们的纸钱,没有烧到堂;欠了他们的香烛,没有敬到家。要敬他们啊,要做一堂土菩萨。”《梯玛歌》的第一首诗就表明了土家族人祭祀的缘起——人们期盼自己与亲朋好友岁月无忧、身体康健等。人类不同的膨胀欲望对应不同的神灵,对越能实现土家族人膨胀的欲望的神灵就越虔诚。土家族人对神灵的崇拜蕴藏着他们对生命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神祇的崇拜也是一种对生活与自然的深情。
地理意象是土家族人民对主客体不加区分,将诗意的想象力付诸客观物象上,使客观事象能承载人类的情意簇,具有传达作者思想情感作用的主客体浑融为一物。经过上述分析,雷公和洪水初步朗照了土家族人民对人性善恶的认知与抉择;植物和动物则烛照了土家族人民对化育万物的大自然的赞美、对生存困境的征服欲和直面险阻的达观精神;敬拜神祇的地理意象则折射了土家族人民对生命无虞的祈望和对生命本身的呵护。综上所述,土家族史诗揄扬了土家族人民对天地神人的崇拜和对滋养人类万物的自然的无限歌颂。
二、境随事转:地理意象更迭的叙事性
叙事学家普林斯这样定义叙事:“叙事是对至少两个在时间顺序上相关的真实或虚构时间或情形的表达,这些事件或情形并不互为预设或互为暗示。”按照普林斯的定义,构成文学作品的叙事性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时间序列的标志;其二,事件的演变具有因果逻辑。史诗意在讲述历史,历史的展演具有时间性,而且在叙述过程中呈现出事件变化的逻辑性,因此,史诗具有叙事性。
在史诗这类文学体裁中,历史的演化必然伴随着地理意象的转变,而地理意象的流转呈现出空间的演变,以空间的转变展演时间的线性绵延。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地理物象或地理事象是文学创作的起点,这个起点以其空间性转变言说着历史时间的流转。《梯玛歌》开天辟地一章中,开篇“没有天,梦一般昏沉。啊尼!没有地啊,梦一般混沌。没有白天,梦一般什么也辨不明;没有夜晚啊,梦一般什么也分不清”,以地理定位的模糊描述天地晨昏为诞生前的混沌状态。绕巴涅“把树搬上肩”,“大树连蔸”;惹巴涅“把竹扛上身”,“大竹盘根”。“大树飞起做支柱,大竹飞起把天撑,大鹰展翅横起身,大猫伸脚撑得稳。”人类与动植物齐心协力开天辟地,从无法确定地理位置到天地两个地理意象的创立,史诗以地理意象所呈现空间的转移操演了人类历史时间的流逝。紧接着三个太阳的出现使万物生灵涂炭,“绕巴涅来了,一脚踢走一轮日;惹巴涅来了,手脚并用又赶走一轮”,“这才有了夜晚,这才有了白天啊,白天黑夜这才分。”天地分离后,三个太阳的炙烤无法让万物存活,两位神灵分别踢走一轮太阳才出现晨昏的区分。天地的间离使人类开始有了对地理的感知,白天与黑夜的形成使人类有了简单的时间流逝感,而人类对时间流动的感悟皆缘自于地理空间的颜色变化即白与黑。适合生物成长的地理环境得以塑造后,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才得以创立。 《开天辟地》一章以人类的法事收束全文——“太公太公啊!父公父爷啊!赶往龙洞去围魂啊。”人类的生生不息源于祖先的辛勤哺育,所以人类以祭祀活动歌咏祖辈。综观全诗,主要地理意象从“梦一般昏沉”——“天成地也成”——“白天黑夜这才分”——“龙洞”。不同的地理意象划分了天地人形成的四个阶段,亦即万物混沌——天地产生——日夜形成——人类出现、婚配、生育与祭祀。人类民族越发展,地理意象对地理标志的定位便愈加明晰,史诗以地理意象传达的地理方位感区分人类的发展阶段。地理意象是人类创世历史不同时间划分的主要标识,不同历史时间段确证自身差异性必须附着于地理意象所创造的空间上。
地理意象具有语言属性,能与人进行交流,以人化的形态参与史诗的叙事进程。土家族人民赋予地理意象神性与人性或只赋予地理意象以人性,使意象具备叙述的能力,推进历史的叙事。雷公具有神性,作为墨贴巴的手下,拥有掌控水火的能力和惩戒恶人的权利;雷公同时也具有人性,具备人的七情六欲,在被抓后,“天喊天应不哩,地喊地应不哩,雷公他各伤心在了”,“喉咙哭得痛在了,眼睛哭得肿起来。”神灵在被捕时亦抒发类似人的悲伤与无助之情,以哭泣发泄情感。为了成功出逃,雷公央求补所给他火:“事好一下做要哩,我给火一个送啰,三夜三天哩烟袋拿没有”,补所回答:“做不得,做不得,哥哥我讲着在,火有你给送不得。”紧接着,雷公像人类一样,向人类妥协让步,让补所拿尿泡过的火炭给他。同样地,他以话语乞求雍尼给他几滴水,拥有了水火的雷公恢复了神性,顺利出逃。从雷公被囚禁——雷公使计拿到水火——顺利逃脱的一系列叙事进程,都是在语言性的对话下推进的。民族史诗的创作者给予地理意象以语言属性,使意象具备人物形象的功能,令意象拟人化,为人与地理意象的贯通提供条件。雍尼追求补所却无法找到她时,询问野猫:“野猫哥哥吔,山上雍尼见见没有?水边雍尼见见没有?”野猫回答:“我各有事哩,鸡崽吃着过在,你雍尼见着没有哩。”史诗通过补所与野猫、人熊外婆、牛公、麂子大嫂、喜鹊嫂嫂、老鸦舅舅、野鸡姐姐和乌龟先生的诸如上述对话推动补所找寻雍尼的叙事过程。期间,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和水里游的都被补所咨询过,且补所的多个提问和焦急的语气说明了雍尼追逐补所的历程的艰辛,象征男性求偶过程的困难。土家族史诗没有意象与人物形象的创作自觉,对两者不加区别,所以,地理意象也拥有以与人对话来推演叙事历程的性能。
地理意象所创造的空间暗含着土家族集体认识历史的因果逻辑。在《摆手歌》中,开篇讲述土家族人于神庙备社巴和庆丰收。在欢快的节日中庆祝丰收,让土家族人萌生了追溯土家族起源的想法。首先,在天地这一地理空间说追索人类的诞生,叙述天地由混沌一体走向二分的原因,紧接着叙说人类的塑造:“竹子砍起骨头做,泥巴捏起肉做,树皮剥起皮子做,叶子摘起肝肺做。”根据人的塑形可以窥见土家族人亲近大自然、崇尚大自然的缘由;其次,以洪水重塑的两个世界叙说土家族人兄妹成婚的习俗,洪水这一地理意象将抓雷公、雷公出逃、雷公以洪水毁灭人类、兄妹逃出生天并成亲与毕兹卡、客家和苗家儿女再生等情节勾连起来;再次,土家人认为“好山好水好落脚,好山好水好生根”,因此开始了民族迁徙的史诗叙述,各种各样的地理意象的流转是土家族迁徙的证明,言说着长途迁徙的准备、坎坷艰辛的迁徙路、路途中定居的良地、在征途找寻乐土和于途中战胜野兽邪魔的历史;最后,在定居处艰苦劳动,借耕作物的意象叙说斫草、挖土、做秧田、种包谷、插秧、薅草、打谷子、种冬粮等劳作行为。综上所述,土家族以天地——洪水——迁徙——定居地这四个地理空间展开土家族形成过程的叙述,符合一个人类族群发展的因果逻辑。地理意象所呈现的空间是事件叙述得以进行的场域,同时也是后世族人把握民族演变历史的主要线索。地理意象是史诗叙事的支点,是土家族利用空间变易述说民族繁衍进程的标志物。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洞见史诗之所以具备叙事性的由来。单个地理意象是构成史诗的最小结构单元。文学所创造的空间以单个意象为基点,以意象的排列组合构建史诗的宏大地理空间。史诗以地理意象形成的序列展演空间的递变,在空间的更迭中表现叙述时间的流动。地理意象人化倾向显著,能以语言讲述事件,具备推动情节的叙事作用。地理意象耦合的空间的特征与情感表征参与建构史诗的叙事程式。地理意象所结构的叙事程式以其叙事目的与价值意义为最终旨归。史诗的叙事目的与价值意义体现为史诗讲唱者的叙事逻辑,而史诗讲唱者的叙事逻辑显现为地理意象互相耦和所表现的空间递变和所爬梳的感情脉络。综上,史诗具有叙事性,实质上是因为地理意象的变化实现了其叙事功能。地理意象创造的意境随着土家族起源和发展等重大事件的演绎而改变,这一演变是时间序列、空间流转、语言传输与逻辑操演的有机统一。
三、狂欢与静穆:地理意象蕴含的生命诗学
“当意象仅仅是传统观念中的视觉物象或直观心像时,它容易局限在事物的外部属性上;当意象只作为普遍象征符号时,它又容易流入因袭的窠臼。而把意象解放为语词,可以调动语词的原生力和组合力,创造事物看不见的联系。”土家族史诗的地理名物在民间歌手吟唱时被解放为语词,民族诗性精神决定地理意象之间的组合,而地理意象反过来也可以召唤民族的集体意识,以语词的原生力和组合力映现民族的原始生命力。从地理意象与人性的互文关系可以窥见共时层面土家族的集体品格,从地理意象的叙事功能可以洞见历时层面土家族的民族基因,从地理意象的“诗”与“史”的维度,即地理意象的本位(对人性的感性体认)和出位(叙事性)之维可以蠡测地理意象所包孕的民族精神。
“作为文学文本的最小元件,地理意象发挥以一总多的效用,勾连起的外在世界与文学主体。成为主体意志具象化呈现的载体,表现创作者和接受者对于文本之外的社会群体的关注,实现‘天——地——人’之间的三维耦合。”就土家族史诗而言,地理意象是沟通外在世界与创作主体的媒介,是破解土家族民族意识密码的钥匙,是窥探土家族“天地神人”四维和合理念的符码。从上文分析可知,史诗中的地理意象“乱花渐欲迷人眼”,揭示了土家族对人性善恶的体悟、对化育万物的大自然的歌颂和对征服自然的人类原始生命力的赞美之情。同时,史诗记录了“开天辟地、原始神话、民族起源、民族迁徙、人类繁衍、狩猎农耕、征战媾和、音乐舞蹈、文学艺术等内容”,时间范畴跨度之大,表现情感之繁复多样,故土家族“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土家族人载歌载舞,以高亢饱满的热情咏唱民族历史。在娱神悦人时,民众忘记社会身份的差别,纵情欢笑,宣泄心中的真实情感,将社会性的规约、地位与身份的长幼尊卑置之脑后,完全解放人的自然本能,于史诗表演中重建民族集体的精神世界,具有狂欢化的特征。摆手歌歌词的狂欢化特点十分明显:“大喜的日子到了唉,土家山寨好闹热,摆手歌儿唱起来,摆手舞儿跳起来,盘咚盘,哟嗬吔。”摆手歌是土家族民众在重要喜庆节日所表演的曲目,全族人民以摆手的动作将欢乐的情绪感染他人,共同营造狂欢的节日气氛。“大摆、小摆、单摆、双摆、前摆、后摆、摆成一朵花,花就艳艳地开了;摆成一条河,我就汤汤地流了;摆成一座山,山就漫漫地绿了;摆成一朵云,人就浪浪地飘了;摆成一只鸟,鸟就叽叽地飞了。”摆手的式样简易却多样,土家族人民将舞蹈与地理物象结合起来,以狂欢化的“一”消弭身份地位不等的“多”,同时也将狂欢化的生命体验延及自然万物和神祇,以人的物化表现人化归于自然的本然状态,具有包罗万象特性。在节日的狂欢中,史诗为地位崇高的神灵脱冕,为地位卑微的人类加冕,颠倒日常的权利秩序,暂时解放压迫人性的社会关系,召唤人类最本真的诗性体验,彰显生命作为一种自然本体的独特与平等。
土家族人认为自然是万物之母,是伟大、神圣而崇高的,赋予地理物象或地理事象神性,并在吟诵用于祭祀的《梯玛歌》时保持“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伯克认为“凡是能够以某种形式激发我们的痛苦和危险观念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以某种表现令人恐惧的,或者那些与恐怖的事物相关的,又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事物,都是崇高的来源;换言之,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知到的最强烈情感。”现实世界存在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超越了土家族人的认知边界,对自然的无知激发了土家族人的痛苦和危险心绪,让他们感到恐惧,从而使他们的心灵触手捕捉到敬畏的心理岩层,在请神、颂神、劝酒、托梦、告兵、拖魂、再劝酒和撤正堂等一揽子祭拜神祇的活动时保持静穆的卑微状态。“你头戴纱帽啊,身穿金银袍,神威啊神貌。奉敬的是谁啊?你,头王太公啊,奉你啊,向你禀告。”演唱者凭借世俗的金装银饰设想头王太公等诸神的形象,虔诚谦卑地向神灵禀告。土家族人为了摆脱对自然的恐惧心理,将自然神化,以供奉神灵的方式消解生命不可承受之崇高。祭祀神灵与生命自我言说的仪式施洗下,人类与自然发生冲突时的彷徨与畏惧转化为对生命的崇敬与合理解决矛盾的冲淡平和,能够消解人类与自然的隔阂,使参与祭拜的土家族人达到天地神人四维相互会通和合的静穆心境。
地理意象所烛照的土家族对人性认知的历史叙事表现了土家族生命诗学的“一体两面”。一面展现出讴歌自然包孕万物和本民族顽强生命意志的狂欢化;另一面则呈现出土家族人敬畏自然神祇的静穆。狂欢与静穆是土家族人既对立又统一的民族意识。狂欢是抵达静穆的前设准备,静穆是狂欢达到最高峰的静止状态。土家族人感应到了自然的伟大,以娱神悦人的方式将自然人化,与之平等地酣畅歌舞,塑造人类自我的尊严;也正是因为自然的伟大,以供奉敬告的方式将自然神化,对之卑微地顶礼膜拜,构筑神灵的权威。从根本上来说,地理意象是土家族天地神人四维合一理念的具体表征,具体表现为狂欢与静穆的民族诗学。
综上所述,站在地理意象的本位,可以观照土家族人的崇尚自然、择善而从、抵制恶行和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集体情意簇;跨越地理意象的本位,可以洞察土家族人对地理意象叙事功能的运用,即土家族不区分地理意象与人物形象,使得地理意象具备推动史诗叙述的作用,使土家族的世世代代都传承着本民族发源繁衍的历史记忆。在对地理意象的本位与出位的思考下,朗照了土家族狂欢与静穆的民族品格。